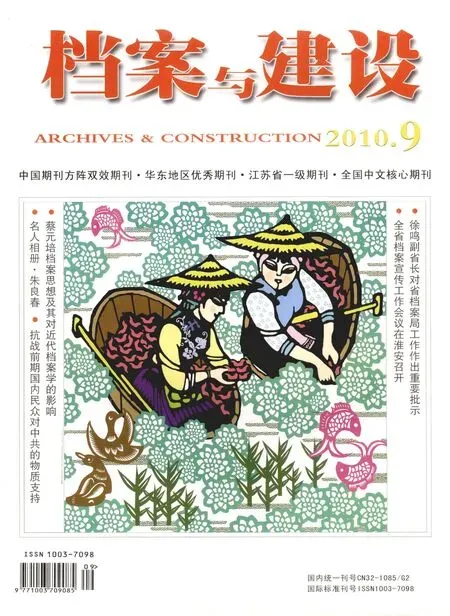想起抗美援朝岁月我就要流泪
□黄全洪口述 黄剑宝整理
“每次想起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我就要流泪。想起我那些死去的战友,活蹦鲜跳的战友啊!大家相仿的年龄,刚才还活生生地在你眼前,一忽儿就阴阳两隔,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永远地离开了祖国和亲人,永远被埋在异国他乡。想起那些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天当被、地当床,草根树皮充饥肠,饥寒交迫、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天。这些往事,我活着记在心上,死后就记在骨头上。”这是4月23日上午,我采访的志愿军老战士黄全洪老人的开场白。
老人显得很激动,面对我的照相机,嘴唇抖动得话也说不上来。他想不到60年前想忘又忘不掉的往事,今天居然有人来重新提起。他泪眼婆娑,一边擦泪,一边做着手中的活,一边说着他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
老人今年79岁,家住原峭岐镇(现徐霞客镇)新宕村(现东宏村)。1951年3月,19岁的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六十八军二0三师独立高炮营当汽车司机,专门拖运高炮和为前线输送弹药,拉伤兵、粮食等。
现在,他在峭岐集镇的老街道旁摆了一个铜匠摊子,专门为人家修配钥匙。一年365天,你几乎天天可以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电动车从乡下赶往镇上,车箱里除了有一大串一大串的各种钥匙坯子和必备工具外,还有一只旧饭盒,里面装满一盒冷饭,一只旧搪瓷杯里装着简单的下饭菜。我问:中午你吃冷饭?他说:到茶店里用开水泡一泡,端起来三下五除二地吃完。有时生意好,一天能挣20多元钱,我就改善一下,到面馆里吃碗鸡蛋面,或者回去时到菜场上买点荤菜,回家和老太婆一起享用。我说:你太节俭了。他笑笑说:已经蛮好了,想起朝鲜战场上吃过的苦,想起那些死去的战友,我太幸福了。现在政府还每月给我一千几百元的生活费,我很满足了。
我问:当年你是怎么想到去当志愿军的?他说:我出生苦,娘死得早,兄弟三人都要吃饭,1945年至1947年,我出去做长工,1947年至1951年出去学厨师,勉强维持生活。1951年3月份,国家号召抗美援朝,我想在家里也没什么大出息,不如出去闯荡一下,见见世面,再说我们靠了共产党、毛主席翻了身,应该为国家考虑考虑,于是就报了名。我问:你想到了死吗?他说:怎么会想不到?打仗总要死人的,但那时有一腔热血,何况出去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峭岐也有不少年轻人和我一起入伍的,后生家思想顾虑要少一点,能够穿上军装,戴上大红花也是很光荣的。所以,在我们路过鸭绿江前,我就将多余的东西全部扔掉了,我是准备一条命的。
我们这样交谈着,有几个配钥匙的人急等着,于是就停下来,让他干完了活再继续谈。
我入伍后,先是到青岛去集训了三个月,专门学习驾车技术。1953年6月1日,部队出发开往朝鲜,我们驾着车拉着高炮开过鸭绿江。哪知朝鲜正在发洪水,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加上美国鬼子的大炮和飞机的轰炸,公路被洪水和炸弹糟蹋得坑坑洼洼,弹坑和水潭一个连着一个,常常要下车填坑后才能开得过去。记得我们一支车队在路上艰难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目的地——泉城车站。而步兵和我们同时出发,用两只脚步行也只用了同样的时间到达。到了泉城车站一看,民房和车站早已被炸毁,我们没有地方住,天还下着大雨,怎么办?就选个有树木隐蔽的地方,每两个战士为一组,将发给每人一块的油布(约一平方米左右大小),一块将四只角用绳子吊在树上作为挡雨,地上铺上另一块油布作为床,这样背靠背躺着抢时间休息,一共住了20多天。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泉城车站和182、183、184、185 号四座大桥的安全,共有12门高射炮和4挺高射机关枪。然后就是不断地为前线输送步兵、弹药和从前线拉伤兵到后方。
时隔60年,有好多经历现在还没有忘记,我讲几件给你听听。
生死封锁线
我们运输兵虽然不在前线打仗,但也有随时牺牲的危险,因为我们整天在敌人的飞机和大炮下送弹药、拉伤兵和其它军用物资,一不小心就要被炸弹击中。有一个叫周余里的地方,是我们运输兵的必经之路,足有40公里的路程,美军在这段路上用炮弹24小时不断轰击,而且不是一个点一个点地轰,而是用排炮连起来轰击,形成了一条名符其实的生死封锁线,叫你驾着车不敢往前开。我们每次驾车到这里,都是将脑袋提在手里的,抱着如果被炮弹击中就算为国捐躯、如果逃过一劫就算命大的想法。部队领导也规定,汽车开到这里,将出发前先休息一小时,然后憋足了劲开足马力勇往直前,靠自己的驾车技术左冲右突,绕过一个又一个炮弹坑一路冲过去。我命大,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地完成运输任务。当然也亲眼目睹了不少战友惨死在敌人的炮弹之下,车毁人亡,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是美国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

皮大衣上的七个洞
有个战场叫新高山战场,那山又高又陡,从山下沿着盘山公路往山顶开,要整整一夜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为了躲开美国鬼子飞机的轰炸,使军需物资不受损失和所拉的伤员免遭再次受伤的危险,白天将每辆车用树枝做好伪装,等天一黑,我们就开足大灯,拼命往山上或山下开,争分夺秒,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有一天,天已放亮,我们将车停在一片树林子里,抓紧时间砍伐树枝将卡车伪装起来,免得被敌机发现。不料美国鬼子的飞机还是来了,当时我正肩扛着一根粗长的树枝急速行走,由于跑得快,身穿的黑色皮大衣也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只听得“哒哒哒哒”的机枪响在我的身后,我想这下完了,性命完结了。等待“嗡嗡”的敌机声远了,爬起来一看,还好,没有伤皮肉,只是皮大衣的后襟衣边上多了七个洞,美国鬼子还打得很有艺术,七个洞在一条线上,且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很相等。
汽油弹险些要我的命
美国鬼子的飞机有时真的说来就来。有一次,我们车上装着炮弹,驻扎在一个地方,只听得“嗡嗡”的飞机声由远而近,随即“哒哒哒”的机枪声一阵扫射,正好打在炮弹箱上引起了大火,顿时整车炮弹爆炸,侦察班班长吴洪才的一只手被炸掉了五个手指。随后,敌人又用汽油弹再次袭击,以致地面上所有的易燃物都烧了起来。我正好在枯草旁边,那熊熊的火势燃着了我的衣服,一刹那间,我被火势包围,心急如焚,边脱衣服边就地打滚,最后在四川战友杨国志的帮助下终于将火扑灭,但腰部和腹部已严重烧伤。后来,我的好战友杨国志驮着我跋山涉水,将我送到27军医院治疗。
死神与我擦肩而过
这是抗美援朝最后一战的事情。时间是1953年6月21日,当时我们已准备回国,集中在朝鲜新高山等待命令,突然接到20师师长杨东良的命令,重返前线,备战一个月,消灭美国王牌军老虎团。这老虎团确实了得,武器精良,作战顽强,我们志愿军以一个师对付他一个团也没有拿下,最惨时一个团只剩下6个人,实在叫人咬牙切齿。而且这老虎团的每样武器上,以至官兵的穿戴上都印有一只凶猛的老虎图案,可见其猖狂之极。
也许是老虎团的劫数已到。志愿军部队一举冲进老虎团团部,俘虏了所有的美国鬼子,将张牙舞爪的老虎团旗踩在了脚底下。记得是27日的清晨,部队命令我们去老虎团缴获所有的美国武器和装备。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汽车,我和司务长一起看中了一辆崭新的中卡,月城公社的黄建良也是运输兵,看中了一辆崭新的小吉普,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一是因为美国的王牌军终于被我们消灭,二是我开上了美国造的新卡车。
我驾着新车,司务长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和我说着话。由于山洪暴发,公路上尽是积水的泥潭,我的卡车底盘高,勉强能开过去,而黄建良的小吉普因为底盘低,排气管被水淹没,怎么也开不过去。我们正想下去推一把,不料从西海面打来了不少炮弹,那弹片像雨点一样向我们的车内削来。坐在旁边的司务长还没回过神来,一颗头颅就骨碌碌滚到我的身边,一股热血冲向车棚。我惊呆了,又一发炮弹打来,将黄建良的小吉普连车带人轰向空中。说来也怪,待黄建良从空中落到地面,眼看小吉普被炸得粉碎,而他只是眉骨上擦掉点皮,真是命大。我也命大,密集的弹片只是击中了司务长,而我却安然无恙,司务长离我不过一尺之余,死神与我擦肩而过。
我深深怀念我的战友
60年来,我深深怀念我的战友,每次想起总是夜不能寐,泪流满面。
1954年春节,我们结束了在朝鲜两年半的艰苦生活,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怀抱,先是在天津参加三个月的学习,然后回到家乡,在江阴县民政局成立的一个转业军人生产组工作。这个生产组后来先变成麻纺厂,再改为工农染织厂。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地质勘探队来江阴勘探,急需找一位会开汽车的人,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很少,经县劳动局介绍,我被借用三个月。期满后,由于我工作出色,要求带我走,得到单位同意后我就跟着勘探队到山西龙门勘探黄河大桥的桥址,后又转战到四川泸州、孟庄牛角渡等地,最后调我到武汉大桥服务区食堂专门开车。那单位大啊!每天都有上千号人吃饭,我的工作也很忙,领导也很赏识我。
待工作稳定后,我提出了将老婆调来武汉工作的要求。为让我安心工作,领导很支持,于是就回江阴将老婆的户口迁入武汉。哪知还未入迁,中央下达疏散大城市户口的文件,外来户口一律不准迁大城市。怎么办?老婆已停工在家,户口证明放在衣袋里,且由于老婆已有三个月未去上班,早已作为旷工除名处理,总不能这样夫妻俩人相隔千里过日子吧。于是我打算回江阴老家,上级领导做我工作要我留在武汉,我不愿意,同时闹情绪,领导没办法,最后同意我回江阴,但不安排我工作,作为下放处理。我想这是命,下放就下放吧,就回到了江阴城里的大毗巷,夫妻俩当起了无业游民。
日子总是要过的,没有收入怎么办?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也巧,那时大毗巷里有一个老铜匠,天天在巷子里给人家配钥匙,我反正没工作,就天天坐在他的摊头上去看他配钥匙,于是产生了学门手艺活的念头。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老铜匠心好,加上我有点无师自通,很快就学会了,并且还触类旁通地学会了其它铜匠活,如用废铜浇铸脚炉、手炉、汤婆子等。要知道,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些东西家家都用得着的。1963年,我拖儿带女回到了自己的乡下老家,农闲季节,天天挑着铜匠挑子转村头。那时,我是方圆十里有名的黄铜匠,还带过几个徒弟,日子穷穷苦苦总算过下来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政府还给我每月一千几百元的生活费。如今年纪大了,在家也闲着,就操起我的老本行。正是这老本行,帮我圆了60年的梦啊!那是2006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平常一样在摊头上帮人配钥匙,忽然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中年男子也要配钥匙,于是就坐下边聊边做,闲聊中谈到了我有位老战友也是四川人,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难忘的岁月。那男子说,我的父亲也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现在在家养老。你父亲姓什么?我父亲姓杨。叫什么?住哪里?叫杨国志,住成都。呀!真的?是真的!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一把握住男子的手说,你知道吗?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哪!当年要是没有他,我早就被美国鬼子的汽油弹烧死了,是他帮我扑灭了火,又是他驮着我到后方医院治疗。50多年来我一直想念他呀!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他的儿子啊!快,快打电话请你父亲来江苏,我们老战友叙一叙。那男子听了也很激动,随即用手机将这一千载难逢的喜讯告诉年迈的父亲。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凑巧,这位男子真是老战友杨国志的儿子,叫杨玉丁,在徐霞客镇的一家钢厂打工,星期天闲着没事,就专门跑到峭岐街上逛逛,顺便配把钥匙,没想到几句闲聊竟聊出了人世间难得一闻的一桩美事,奇哉,美哉!
黄全洪老人激动万分,远在四川成都的杨国志老人也心潮澎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50多年前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的老战友会在几千里之外巧遇自己的儿子,于是决定赴江苏一叙,随即买了火车票,千里迢迢奔江苏而来。
几天后,50多年前生生死死在一起的两位老战友终于相见,两双苍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张饱经沧桑的脸上,两双眼睛饱含热泪,千言万语涌上心头。这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啊!这是思念了半个多世纪的救命之恩的战友之情啊!在场的人们为之动容!他们聊了许多许多,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杨国志老人回到四川后,嘱咐儿子常去黄伯伯家看看,还特地从四川捎来腊肉和火腿等。不幸的是,杨国志老人在两年前因病去世,黄全洪老人听说后心痛万分!
讲到此,黄全洪老人掩面而泣。老人说,我深深地怀念亲爱的战友杨国志!还有我们的司务长!还有,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