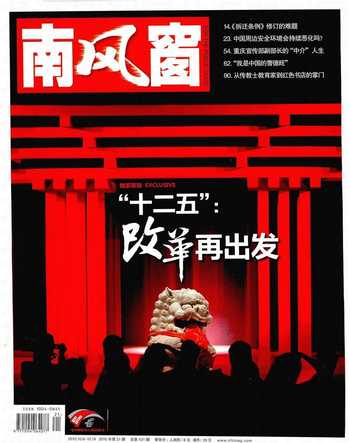发明创新出点子
南方朔
全球最早对“时髦”(Fad)现象作研究的乃是美国前代学者鲍加德斯(Emory Bogardus)。他在1915至1924年间,每年找113人问他们当年最时髦的5件事。他的10年研究,方法上并不严格,但结论却极精彩:
(一)绝大多数“时髦”事务都是朝生暮死,能撑过3年已经极稀少,那个时代只有“男子腕表”取代了“链表”而留存下来。
(二)因此,人们所谓的“新鲜事”,其实是很可疑的。它初起时很能吸引人,造成“羊群效应”,大家都一窝蜂地凑热闹,但因为新得没什么道理,于是很快就冷了下来。
鲍加德斯的早期研究,其实已碰触到了今天所谓“创新”这个问题的根本。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可分三个层次:
——最高层次乃是“发明”,无论科学、制度或商品,它能针对基本的环节加以突破,这种“发明”自然可长可久。
——到了近代,人类更加鼓励“新”和“不同”,于是“发明”的概念遂被俗化成了“创新”。“发明”里的真正原创性不见了,与别人不同的“新”开始成了主流。这也是我每当听到大家夸夸而谈“创新”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原因。
——及至到了现在,全球都把“创新”这个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创新”已成了引人注目的花车,不赶搭上就觉得有压力,这种“赶流行压力”(Bandwagon Pressure),使得搞政治做学问,或者做生意的都要“创新”,在这种时代气氛上,“创新”已被庸俗化,变成了“出点子”“搞花招”。由于这种“新”,都只是在小地方研究,因而“新”虽然多,但多数都只是“符号式的膨胀”(Symbolic inflation),来得快,去得更快,许多时髦的事,都是“短命的热狂”(short-lived enthuslasnl)!
因此,在这个大家都在说“创新”的时代,我们当然也必须“创新”。但在谈“创新”时,却不能忽略了“发明”、“创新”、“出点子”之间的分际:
“发明”乃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事业,各行各业的发明家,必须对该行业的过去现在有综观式的理解,当对过去现在有了理解,对未来才可能有愿望及想象,而愿望和想象乃是“发明”的基础与动力。这是“出点子”的人不可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贯主张、重视“发明教育”,透过研读发明家传记和发明史,让人们懂得发明的逻辑,才可能使人眼光放大放远,免得误把“出点子”当成了“发明”的理由。
至于讲“创新”,人们不能忘了前代经济思想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谈到“创造性毁灭”时所说的“创新”精神之本意,那是一种新财货、新技术、新组织、新模式的创造。他所谓的“创新”,比起“发明”毫不逊色,那是一种更整体性的“发明”,其综合效果可能更大。在我的认知里,中国近年来的整个铁路运输提速计划,就当得起成功“创新”的典范。
无论“发明”或“创新”,它都需要某种大聪明。但近年来在“创新…‘创意”之名掩护下的“出点子”,却显然与大聪明无关,它有“新”的外衣,却少了知识的含金量,因而看起来花俏,但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特别是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概念高唱入云,世界各国也投入了大量资源,看起来很热闹,各种“创意活动”也大张旗鼓地在举办,许多人并将它与“国家软实力”扯上边。但若把这本账好好算一算,它究竞积淀出什么成果却颇堪忧疑:它是否只是以“文化创意”为名,照顾了某些特殊文化人?花大钱搞很多炫酷的活动,是否只不过等于放了许多昂贵的文化炮竹?这种赶集式的“文化创意”搞多了,除了产生一堆文化创意过动儿,又与国家软实力何干?我们不能忘了,美国奈教授(loseph Nye)在谈软实力时,可是以学术力、思想力、知识力等为基础的!
美国德拉瓦大学教授乔·贝斯特(IoelBest)在谈到“创新”时,特别提起1958年的呼拉圈热,呼拉圈只流行了半年就冷了下来,全美卖出2500万个,为人口的1/7,5至11岁的小孩则人人皆有一个,呼拉圈是个“好点子”,至少那家公司赚了钱,但它有贡献吗?其实并没有。但这比起另外许多搞不出名堂的“创意”还算是好的。由此也等于提醒了我们“创新”是应该的,但在做“创新”时,還是要多一点盘算,多一点大聪明,少一点小点子。“创新”时还是要看看有多少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