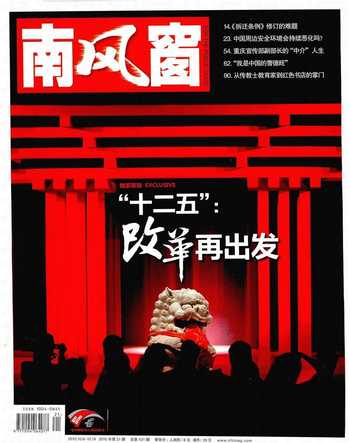《拆迁条例》修订的难题
田 磊

9月10日,因为拆迁,江西宜黄县政府将一户人家逼上了自焚之路,拆迁户钟如奎一家一死两重伤。
大约一年前,四川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北京大学5位法学教授沈岿、姜明安、王锡锌、陈端洪和钱明星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废止或修改这一条例。
随后的半年多里,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先后召开3次座谈会,讨论法律修订,并很快出台了草案。人们也都寄望法律的出台能够规制拆迁乱局,自焚式拆迁能够从公共视野中消失。
然而,当自焚的惨烈气息从公共视野中逐步散淡,法条的修订也陷入了困顿,拆迁背后的利益格局致使新法出台一再拖延。与此同时,因为拆迁酿成的自焚事件,短短半年内,至少在吉林长春、江苏东海县和江西宜黄发生了3起。
那么,法律是否还有力量保护那些无所依凭的被拆迁人?在更广袤的农村,除了法律,人们还能依靠什么来保卫自己的房屋和土地?
难以遏制的强迁
自从去年底,北大5名教授“上书”要求修订《拆迁条例》,国务院法制办启动了相关程序以来,拆迁所引发的恶性事件同比突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5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一条紧急通知,“对采取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逼迫搬迁,以及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但国务院的政令并没有完全阻止野蛮拆迁,停水停电式的野蛮拆迁还时有发生,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五四村农妇李卫在强拆队的逼迫下,点燃了浇在身上的汽油,烧成重伤,经救治后保住了生命。
一直到9月10日的江西宜黄,已经讨论了将近一年的《拆迁条例》修订仍然没有下文。沈岿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也参与了每一次的专家座谈会。9月底,在北大法学院见到他时,他说,“座谈会都开了3次了,到现在仍如泥牛入海。”沈岿说,技术层面的讨论其实已经非常充分了,各方专家基本也都能达成共识,最后只是需要一个决定而已。
但这个本不该犹疑的决定,却显得困难重重。在沈岿看来,背后的阻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地方政府附着在土地财政上的利益。沈岿说,任何法律要顺利出台并被有效执行,都要尽力清除其背后起阻碍作用的因素。
就拆迁背后的利益角逐而言,新公布的《拆迁条例》将保护的力度适当倾向于个人,这样原来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可能会不高兴,这就要求制度设计者要考虑构建一个新的利益平衡机制,适当平衡地方政府的利益。
“自焚户”与“钉子户”
由于城乡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拆迁有着并不相同的轨迹。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此类一线大城市,出现更多的是“钉子户”,北京核心城区的住户张长福守候房屋7年,致使城市道路改道;广州地铁修建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同样的情况。2007年,重庆拆迁户吴苹夫妇更是被誉为“史上最牛钉子户”。
这些拆迁与被拆迁者之间的斗争,虽然同样艰苦,但还算不上悲情,是2009年成都郊区的唐福珍,让拆迁开始与自焚相连。事实上,过去的几年里,唐福珍、陶会西,以及钟如奎一家,这些真正走上自焚之路,采取最决绝抗争手段的个体,大部分都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的拆迁问题,换句话说是农村的拆迁。
所以,有網友哀叹,在大城市,你还有可能做个“钉子户”。可是在偏远县城和农村,你可能是个“自焚户”。
在大城市的拆迁进程中,人们基于私有财产的抗争,即使没有完善的法律保护,可依凭的资源也相当多。也因此,到今天,大城市的拆迁成本事实上已经相当高昂,因拆迁而产生的城市寄生阶层也越来越被人们提及,在沈岿“上书”后收到的信中就有地方政府法制办主任质疑他们所倡导的新《拆迁条例》过多地保护个体,而忽略集体利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
虽然新的《拆迁条例》到今天还没有出台,但就其已经公布的草案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试图在经济发展和个人权益之间小心翼翼寻求平衡的法律,其进步性显而易见。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城市的拆迁终将走向阳光地带,法律和舆论赋予了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力量,个体至少能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脆弱。
但经过近30年的大拆大建,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代城市建设的雏形,伴随而来的野蛮拆迁,在这类城市也已基本接近尾声,这部法规真正的价值恐怕要等到几十年后,最近几年在大城市买房子置业的一代人,当他们的房子面临被拆迁时,才能体现出来。
不能忽略的农村
而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最野蛮的拆迁所涉及的主体,却大多与这部法规所规制的对象关系不大。因为用地性质的不同,在法律关系上,农村与城市的拆迁事实上有着极大的差别。
如果说,城市拆迁中发生的恶性事故,还可能得到关注,对于那些偏远县城和农村的野蛮拆迁,大多数情况,则关注较少。以宜黄事件为例,如果不是钟家姐妹的微博直播,很难想象这起发生在偏远县城边缘的拆迁故事,会有如此关注度。
法律是不是也把他们忘记了?沈岿说,在法学界内部,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和对国有土地的关注是同等的。“据我所知,不论是人大法工委还是国务院法制办,都已经将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问题纳入了议事日程。”沈岿说,只不过农村的问题更加复杂,现在还没有公开的立法讨论。
在沈岿看来,新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农村拆迁纠纷的解决,法律程序和技术层面都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难点是补偿的标准问题,城市的房屋因其有交易价值,套用市场价格即可,但是农村房屋,并无市场交易价值,那么,如何来确定其补偿标准,并不能简单模拟国有土地的定价流程。
事实上,即使是法学界内部,这个问题也存有争议,最典型的是“土地涨价归公论”和“土地涨价归私论”,前者认为农民对土地进入一级市场后的增值过程并没有投入,因此增值的部分应该是公共的。
在包括宜黄在内的几起恶性拆迁事件中,争议的核心无非是赔偿标准的巨大分歧。由于缺乏明晰的市场价格,农村拆迁赔偿协议的达成难度远远大于城市,也因此,那些行事粗暴的地方政府往往根本没有多少耐心去谈判,很容易就选择诉诸暴力。
沈岿说,除了补偿标准的难题之外,还有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所有权人的虚化造成集体拿到钱以后,还面临如何公平分配给个人的问题,此外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同样要充分考虑。
但这些问题显然涉及更加复杂的体制改革,远不是单靠土地征收法律能够给予规制和解决的。事实上,在政府严格掌握土地一级市场、乡村治理失范等情况下,农村的拆迁纠纷解决起来的难度要远远超过城市的拆迁,不论是政府还是法学界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
不动产之重
在去年底的那次领衔“上书”之后,半年多来,沈岿收到了各地拆迁户们寄来的500多封信,还有不断来访的。那些全,国各地的拆迁户们所诉说的各种各样的拆迁遭遇,让沈岿感到震惊。但面对来访者的求助,沈岿也时常感到无奈。在沈岿看来,对法律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真正对民众负责的政府基础上。
“对不动产的征收、补偿不足以保证其所有权人所期待的价值,他就会不遗余力,拼死抗争。”沈岿说,执政者应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民众对于不动产的捍卫对整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后,将对不动产的征收、补偿真正纳入法治化运行轨道,这绝不仅仅事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