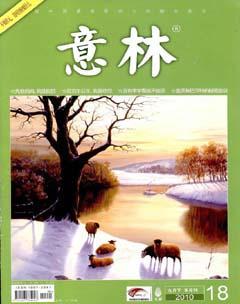《余震》的不能承受之痛
兰 溪
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女作家王小灯,曾三次自杀未遂。她长期被一种无名头痛折磨,焦虑失眠,只能靠服用助眠止痛药物维持生活。她几乎做过医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病原。
后来心理医生发现,她的“无名头痛”来自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
当年王小灯七岁,正在唐山,父亲在地震中遇难,她和弟弟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下,在只能救一个的情形下,她亲耳听到母亲说“救弟弟”,就这三个字让她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然而,她没有死,奇迹般从尸体堆中爬出来,成了孤儿。
她被一对夫妇领养。养母在她中学时去世,她又遭到养父的性侵犯。她考到离家很远的南方上大学,在大学恋爱,之后结婚,生子,移民加拿大。
但王小灯的痛并没有随着时空的迁移而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地困扰她的生活。
神经质的性格让已近中年的她家庭也出现危机,女儿离家出走,丈夫要离婚,而她数次割腕自杀。
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所依照的原著,张翎的小说《余震》的故事。
小说的结尾,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王小灯鼓起勇气回到唐山,去面对和打开这个漫长的痛苦的“心结”。
“痛”。是小说的重心,也是一种隐喻,它要说的是地震给人带来的精神的痛苦。
唐山大地震过去30多年,那些幸存者的痛苦平复了吗?这是作家的关怀。
而电影《唐山大地震》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痛”,强化了温暖的亲情。影片的主角从王小灯转到她的母亲身上,拿掉了王小灯心理治疗的内容,增加了母亲的内疚与救赎,养父的慈祥与正直等内容。
影院里能听到观众的低泣,毕竟对汶川和玉树地震带来的痛苦,还记忆犹新。依然要感谢冯小刚,选择了《余震》作为蓝本,从一个家庭的故事人手,比惯见的“党政军民团结奋战夺取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叙事腔调高明得多,也更符合艺术之道。
但用来纪念那场24万人遇难的旷世灾难,这部充满温情的电影是不是还缺了些重要的东西——痛感?
2006年,张翎在首都机场候机。在机场书店闲逛时,她发现了一本名为《唐山大地震亲历记》的书,书里是60位幸存者和历史见证者对唐山地震的回忆,书中关于劫难的记忆击中了她的心灵,而后才有了《余震》。
“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幸存的孤儿,他们在文章的结尾被简单概括为‘后来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和‘后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这样的表述。”张翎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
不知道张翎看过影片后,能不能接受她所着力书写的痛苦被置换成“温暖的亲情”,以及各种宣传口号,为观众准备的毛巾上印着“感恩,博爱,开放,超越”。
感恩谁?超越什么?人间永远需要温暖的亲情,但具体到唐山大地震这个大事件中,若没有对历史之痛、现实之痛、灵魂之痛刻骨铭心的记忆书写作为底色,所谓温情有时会失去其伟大的光辉,并削弱其本该具有的深沉的人性力量。
影片的两个片段值得关注: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毛泽东去世,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24万人罹难的无声,与一个领袖去世后的举国哀悼,通过镜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另一个镜头:一个老人站在唐山大地震纪念墙下,久久凝望着逝去的亲人的名字,说“明天再来看你们”,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包括他们的脆弱和痛苦,同样值得正视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