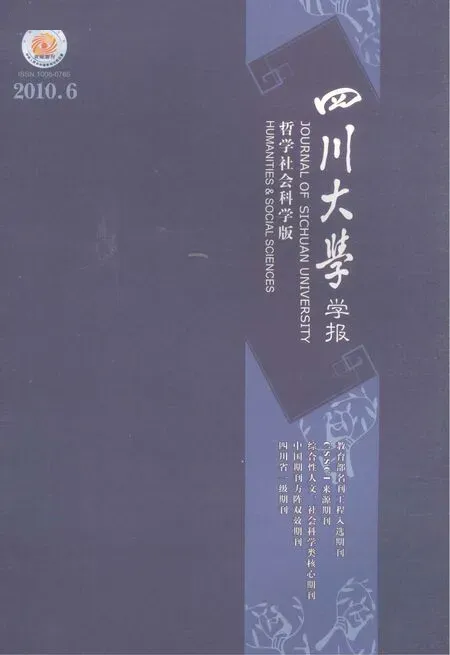全能与全善的两难——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伦理解读
张 伟,史 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柏拉图在《游叙弗伦篇》(Euthyphro)中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对虔敬之本质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虔敬是因其虔敬而为神①此处的“神”并非指基督教的“一神”(the God),而是指古希腊的“诸神”(the gods)。所爱,还是因其为神所爱而虔敬?”(Is the pious loved because it is pious,or pious because it is loved?)[1]换言之,虔敬与神的爱之间是什么关系:虔敬是由神的爱造成的,还是虔敬的内在本性引起了神自身的爱?如果虔敬是由神的爱造成的,即是说神赐予了虔敬以价值,虔敬的价值是外在于虔敬自身的,离开神虔敬便毫无伦理价值可言。如果是虔敬的内在本性引发了神的爱,则是说虔敬的内在价值值得神去爱它,其伦理价值是先于和独立于神的爱而存在的。对此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伦理解读。
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当游叙弗伦被问及“虔敬是因其虔敬而为神所爱,还是因其为神所爱而虔敬”时,他回答道:“虔敬是因其虔敬而为神所爱。”这表明,游叙弗伦认为神的爱并不是造成虔敬的原因,虔敬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是虔敬的内在本性使得神去爱它。在此,我们可以把“虔敬”一词替换为道德义务、内在价值等伦理术语。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的问题就变成了:虔敬这种道德行为是因其自身而具有道德价值,还是因为神的喜爱才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道德行为的伦理价值是它本身先天具有的,还是由外部赋予的?道德行为到底是具有天然的标准,还是其标准是神或人定的?例如,一个人做了一件正当的事情,那么,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正当的,还是说因为人们都认为这件事情是正当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正当的了?
如果再将此处的 “神”替换为其他主体,那么我们就还可以提出其他类似的问题:是因为一个行为本身是正确的,老师才加以赞赏;还是因为老师赞赏这个行为,才使其成为正确的;或者,是因为这项活动本身是错的,学校才予以禁止;还是因为学校禁止这项活动,才使其成为错的。很明显,仅凭主体的喜好判断事物的道德价值是缺乏理性根基的。如果只有当神或任何其他主体“爱”某事物或行为时,该事物或行为才成为“虔敬”的或有价值的,那就意味着该事物或行为本身是没有任何伦理价值的,其道德正当性是完全主观的、外在的,仅取决于“神”或其他主体的一时兴致。相反,如果只有当某物或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善的时候,“神”或其他主体才去爱它,这就意味着在该事物或行为中存在着“神”或其他主体之外的价值来源,其伦理价值是独立于 “神”或其他主体的 “爱”的,因此是具有内在价值的。
那么,什么是内在价值呢?“说某一类价值是‘内在的’,仅仅是说某一事物是否具有这种价值和在什么程度上具有这种价值,完全取决于事物的内在本性”[2]。就是说,内在价值是由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或者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实际上,人们通常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使用内在价值的:第一种是指某种内在的属性;第二种是指独立于评价者的评价;第三种是指其自身具有目的。因此,如果说虔敬是 “因其虔敬而为神所爱”,即是说虔敬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内在于虔敬之中的,是不依赖于神或其他主体的评价的某种属性。
当前,在科技伦理中就存在着对科学价值中立性问题的争论:如果说科学并非价值中立的,就是说科学的伦理价值依赖于科学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外部价值介入,科学的内在价值无法保证其完全的独立性。“一旦我们从科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看问题,则显然地,科学既不是伦理价值无涉的,也不是伦理价值中立的。”[3]科学是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的手段,并且,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也决不是无目标的,也不是价值无涉的。马克斯·韦伯之所以认为科学是与伦理价值无关的,是因为他将科学仅仅归结为有关事实的知识,将科学仅仅看成是客观知识的体系,而科学知识本身不能回答“应当”的问题。在韦伯看来,科学甚至不能回答“科学自身是否能够决定什么值得知道”的问题,“科学既不可以,也不能够决定它所揭示的任何事实是否值得被揭示……它既不可以,也不能够决定,什么值得知道,什么不值得知道”[4]。
在生态伦理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问题的争论。例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就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而自然所具有的这种内在价值就是人对自然负有直接义务的原因。罗尔斯顿说自己要跟几千年前的苏格拉底抗争,因为苏格拉底把人规定为“政治的动物”而忽略了大自然的意义,而实际上,森林和自然景观却能够教给我们城市哲学家所不知道的东西[5]。他认为,人对自然所负义务并不是出于人的主观原因,比如说出于仁慈(因怜悯而不虐待动物),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因崇拜自然、神秘主义),出于某种偏好 (因兴趣、爱好而为花浇水),或者像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出于邻居和公共的利益,出于自然物本身的原因,即内在价值。
二、价值的同时性问题
我们不禁会继续发问:倘若事物既具有内在价值,又具有外在价值,那么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孰先孰后呢?或者在它们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着先后关系呢?它们能否同时发生呢?
游叙弗伦在选择了“虔敬因其虔敬而为神所爱”之后,被苏格拉底绕了个大圈,最后陷入了迷惑。其实,即使游叙弗伦选择相反的答案,也会被引入迷雾之中。因为,苏格拉底是以一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这两个词的:或者是某物先变得虔敬而后神开始爱它,或者是神先爱某物而后某物才变得虔敬。但如果我们回答说“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我们先说“神爱虔敬是因为它是虔敬”,然后又说“虔敬之所以是虔敬是因为神爱它”,这样实际上是陷入了循环论证,并使虔敬与神的爱孰先孰后的问题最后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么,虔敬与神的爱能否同时发生呢?以湖水中一个盛满水的杯子为例。杯子里装满的是湖里的水,同时,湖里的水盛满了杯子,杯子里的水与湖里的水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先后之分。
再以“看”和“被看见”为例。某物被看见是因为某人看见了它。但实际上某物被某人看见和某人看见某物这两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我们通常不会说某人看见了某物是因为某物被看见了,因为这违反了我们的直觉,即看的行为导致被看见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用另一个词“可见的”代替“被看见”,那么,该陈述就变成了:“某人看见某物因为该物是可见的。”这就说得通了。
可见,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或许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神与虔敬是分离的、存在先后关系的,并且一方可脱离另一方而存在。而事实上,虔敬与爱都是神自身的属性,它们是同时发生、不可分离的。因此,如果游叙弗伦回答说“两个陈述都是正确的或都是错误的,因为虔敬和神的爱是同时发生的”,或许苏格拉底的“游戏”就会到此结束。
如果在逻辑上,虔敬和神的爱确实可以同时发生,那么在价值论领域也就意味着内在价值与外存价值也可以同时发生。我们可以再从科技伦理的视域来理解价值的同时性问题:来自科学家的外存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内在价值 (如果科学并非价值中立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时发生的。从一项科学技术被创造发明之刻起,它便具有了自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产生的同时也附带着来自科学家主体的外在价值。例如,科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伦理价值判断使原子弹或克隆人等研究继续或使研究中止,因此,在原子弹或克隆人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原子弹或克隆人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的同时,也融入了来自科学家的外在价值,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来自科学家的外在价值是同时发生、不可分离的。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内在价值是无法完全中立于来自科学家的外在价值的,科学家也不能以科学技术内在价值的中立性为由推托道义责任。
三、宗教伦理问题:“全能”与“全善”、“信仰”与“理性”
如果虔敬具有先于或独立于神的内在价值,就是说虔敬这种道德价值与神无关,然而,一个全能的神①“全能”(omnipotent)与 “万能” (almighty)之间是有区别的。通常用 “全能”来表示上帝能够做任何事情,而用“万能”来表示上帝统治万物的权力。当然,柏拉图笔下的神并不是全能的。又怎能被排斥在道德王国之外呢?神是所有道德的来源,还是独立于道德王国之外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宗教伦理问题。
一方是行爱之举的神,另一方是虔敬:神的爱是虔敬的原因,还是虔敬的本性是神爱它的原因?如果神是为某些好的原因才爱某物,那么就是某物的本性使其值得神去爱它,从而神所做的事情只是认识事物的客观价值而已。那么,神是否可以不为任何原因而随意地“爱”某物呢?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神学中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转变为一个伦理价值 (如通常所说的“善”)与一神论的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个一神论的神就是后来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为万物的全能创造者的神。
如果神是万物的绝对创造者,那么它也应该是所有价值标准的创造者。从而伦理价值 (如“善”)就是神自己自由、任意和全能意志行为的主观设定,即,是神想要的任何事物。于是,无论神想什么或做什么,仅根据定义就能判断其伦理价值是善的,而不用管它们到底是什么。然而,这却会让我们对神感到失望,并会使我们对神的全善及荣耀的赞美变得没有意义。但如果相反,神认识到什么是善的并因为它是善的才去行动,就会使伦理价值的本质独立于神的主观意志,从而神自己也必须服从于客观的伦理价值。这样才会使赞美和尊敬神的全善变得有意义。然而,这又意味着神不再是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价值标准是在神的控制范围和创造能力之外的。这正是柏拉图的思想:形式先于神的创造活动,并为神的创造活动提供标准。
可见,在神的意志万能和神的善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我们可以把这种紧张称之为“全能”与 “全善”的两难。在宗教与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近代哲学中强调神的意志万能的最好代表是斯宾诺莎,他认为神不会为了一个善的或理性的原因而行事,因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识”[6]。伊斯兰教也将神的意志万能提升到其逻辑极限:“神做他想做的事”,“信徒们难道没有认识到,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意志,他会让所有人都有罪”。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则常将神的善与理性理论化。近代哲学中强调神的善与理性的最好代表是莱布尼茨。他相信,这是“最好的可能世界”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因为仁慈与全能的上帝不会创造别的世界。由于上帝的意志是全善的,并且上帝是一切必然理由的依据,因此“他所选择的现实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7]。
同时,《游叙弗伦篇》还暗示了一种选择:或者最高的存在者是争斗的诸神,或者最高的存在者是理性。可见,不仅在神的“全能”与“全善”之间存在着紧张,而且在人的“信仰”与“理性”之间也存在着紧张。我们在开始宗教之旅时,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先得弄清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果否认理性是第一位的,那人们就只需对争斗的诸神保持信仰就足够了。但是,为什么诸神要争斗?说到底,因为他们不知道。但知识,真正的知识乃是先在的,是关于不变者、关于必然性、关于理念的知识。理性是先于关于理性的知识的,因为如果没有理性的先在性,就不可能有知识。因此,如果人们否认理性是第一位的,那么也就否认了知识的可能性。如果理性不是第一位的存在者,那么,最初的事物就不可能是能被认识的事物。它们的行为必定是盲目的,所以它们才会相互争斗。换句话说,如果最初的事物是诸神而非理性,那就是说,任何事物之所以是善和正义的是因为神爱它,而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更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这样的话,首要的活动就不是知识或理解,而是没有知识或理解的爱,即盲目的信仰。而这种“盲目的信仰”正是一神论所需要的。我们不可能以《游叙弗伦篇》为基础来判断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篇对话中单数的“神 (上帝)”从未出现。然而,《游叙弗伦篇》却似乎给出了这样一个暗示:即便是最古老的神也必须被设想为服从理性。如果价值标准服从或依赖于上帝,或由上帝所创造并可以被上帝改变,那么它就不再能够作为标准了。上帝必须被设想为服从必然性,使必然性高于他的创造。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假定上帝高于必然性,或者不受必然性的约束,那么,严格说来上帝就不能进行认识,因为认识乃是对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的认识。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帝的行动将是全然任意的。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他可以创造别的许多个神 (诸神),但是这些被创造的诸神不可能有知识,因此,它们会争斗。但是,基督教必须缓解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因为只有理性的协作,“基督之道”才能“作为普遍有效的真理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下来”[8]。
[1]麦凯南.伦理学:原理及当代论争 [M].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
[2]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96.
[3]杨耀坤.科学价值理性的诠释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74.
[4]韦伯.学术与政治 [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43.
[5]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19.
[7]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7.
[8]潘能伯格.信仰与理性[C]∥斯图沃德.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周伟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