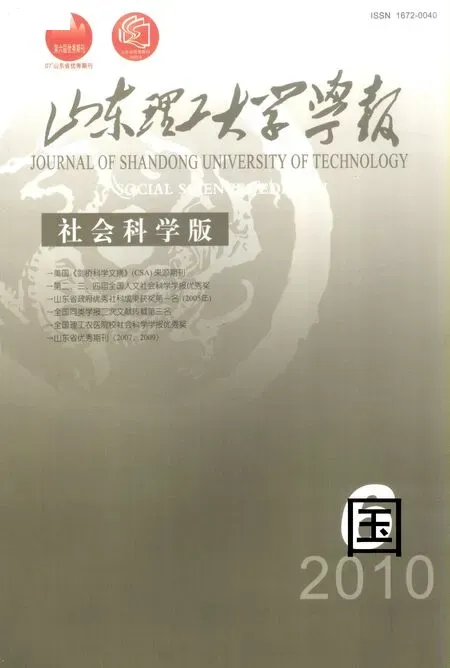论“讲真话”利器对社会的辐射与流播
祥 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随想录》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作家讲了真话,这是非常表面的。因为讲真话的意义仅仅相对于说假话而言是有价值的——其实,说假话在任何时代都无价值,不过是一个灾难岁月的可耻象征而已。真话作为构成普遍人格的条件,本身并无很高的价值。陈思和先生通读《随想录》,潜心研讨,找到了老作家巴金反复强调的“真话”内涵:这就是作家站在人民立场上,对历史现象作了认真的独立的思考,只有当这种思考的结果与人民的利益相符,作家的真话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时,他的真话才具有人民性的价值。[1]237-238巴金把“讲真话”作为一种批判与拯救社会的利器,他在《随想录》中创作了“讲真话系列”共五篇文章:《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随想录》中其他文章也有“讲真话”的种种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部长达一百五十篇之巨的《随想录》就其内容而言,真真切切都是老作家真实心路历程的写照,称得上“讲真话”的一部大书。这是给读者最初的直观感觉。巴金历尽“文革”劫难、死里逃生,作为即将告别读者的文学家,自觉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俯瞰“文革”甚至建国以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风雨征途,顶逆各种各样“极左”势力的围攻,要把心里话作为“遗嘱”写下来,让国人永远铭记这场民族大劫难,避免悲剧再次重演,道出了亿万人民心灵的呼声,从而使“讲真话”的意义从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必备的条件上升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具有人民性的价值”。
一、“讲真话”内涵丰富多彩,践行“讲真话”碍难重重
关于说真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三鹿奶粉不知坑害了全国多少小孩,给他们的家庭造成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有人对各种虚假统计数字深表痛恨,官员为了有“政绩”,用民脂民膏大作“政绩工程”,大作“表面文章”,是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教育为政者;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表现了对社会的失望。
巴金先生以赤诚的情怀,以长者对世人循循善诱的方式,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对“讲真话”的见解与心愿。
“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这样”。[2]220
巴金“讲真话”,一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而不是别人要他讲的话;二是要“讲自己相信的话”,而不是鹦鹉学舌地高喊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豪言壮语;三是要“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而不是为着哗众取宠一鸣惊人去胡说八道。巴金清楚地知道,真话不等于真理,真理并非一蹴而就、自封掌握了就算数的;只有讲真话,才能纠正谬误,最后接近或达到真理,假话则永远达不到真理,只不过是“骗人骗己”而已!1991年秋,他在致成都“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信中,回答那些对“讲真话”的攻击时说: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认为“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对一个作家来说,还必须做到“写作和生活的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这是做人的准则,也体现了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人权又何从谈起?对每个人来说,讲真话,既是个人道德上的自律,也是价值权衡的一个起码的尺度;同时,他还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的重要保证。[3]371-372
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社会要健康正常发展,“讲真话”是必备的条件。“文革”的社会就是“谎言”制造的大工厂,结果使中国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从小的方面来讲,“讲真话”也是世界芸芸众生的每一个个体安身立命之根本,试想一想,一个靠“谎言”过日子的人,人们一定会视之如瘟疫,因为骗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无论是个人发展,还是社会发展,“讲真话”都是一把锋利的器具,伴着这柄利器,会畅通无阻,我们的世界才能真正成为美好的人间。
“讲真话”的前提是真诚的态度。慈祥的母亲从小教巴金“对人要真实”,作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巴金历来再三强调:“无论对于自己和别人,我的态度永远是忠诚的。”巴金《随想录》创作,是怀着真诚的心面对读者,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奴隶”与“帮凶”的角色,让“文革”历史清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
“讲真话”这个呼喊里有明确的针对性。几十年来,说假话流行于上下左右各个阶层,形成社会风气。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了无数荒诞古怪的故事,使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带来巨大的灾难;更为可怕的是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由此出现的寡廉鲜耻的虚伪欺骗言行招摇过市,说真话、真诚待人反倒招致打击这种与现代精神文明相悖的怪现象。文艺界几十年来曾经不断地批判“写真实”这个口号,胡风、秦兆阳、邵荃麟等人为此受到打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遭到践踏。因为“五四”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体现在文艺观念上就是真、善、美,“真”是艺术美的第一要素,这本是普遍常识,但是某些人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4]335胡风等著名文艺家为了坚持自己的文学纲领,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留给后世的人们以深沉的思索。
“讲真话”,就是“把心交给读者”。晚年的巴金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20世纪20年代,巴金在追随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是被人误解,受人攻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坦然地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安那其主义。六十年以后,当人们从浩劫中熬过来,纷纷把责任推到已经被历史宣判死刑的“四人帮”身上时,巴金却敢于在报纸上公开说出:“‘四人帮’绝不只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不能把一切都推到‘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2]156应当说在当时,与一些由别人说出的真话比较起来,这是最重要又最不容易说出来的真话。这是巴金深入思考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演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法西斯专政的一个结果,这是巴金围绕反对专制主义尤其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问题展开的思考链中的一环。[5]160-161
巴金先生“讲真话”,是受鲁迅、高尔基、卢梭等历史巨人的影响的。他曾经说:“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6]335巨匠的真情构筑了“讲真话”的巨大丰碑,世人们仰望着这座丰碑,文艺作品才会散发出感人肺腑的光辉。
“讲真话”随口说出轻而易举,但真正践行起来,碍难重重,需要当事者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否则无从谈起。巴金在“文革”复出不久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着他的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那篇文章就好了。”他害怕巴金不理睬,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那是指他的《大寨行》。巴金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1964年8月巴金在大寨参观时,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每天都有几百人参观与学习。巴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可是《大寨行》却这样写道:“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那个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巴金有意留下自己这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时期“遵命文学”,旨在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自己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巴金《说真话》对过往的岁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我从未考虑到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2]129
在“极左思潮”支配下,从1957年“反右”起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在政治高压态势下,人人自危,争先恐后制造谎言,上面需要什么样的揭批材料,下面的人们无条件地“响应”,整个中国成为“谎言”横行肆虐的国度。
要写出实情,讲出真话,实非易事。因为我们的习惯总是喜欢歌功颂德,不大愿意揭露矛盾,特别是当问题牵涉到自己的时候,更是不敢坦言。所以会制造出一些历史的垃圾筒,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往里面丢,或者会制定一些历史呼号,以便把民众的义愤都附着其上,而显得自己非常干净了。但这不是历史。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确和错误也会纠结在一起。巴金的要求是:“让大家看看它的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这要求当然很高,但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写出历史的真实来。当然,能扛起讲真话的大旗就很不容易,这只要看到当时的阻力之大,就可以想见其难。但巴金还是敢于冲破阻力,尽量讲出真话的,虽然有时候欲说还休,有时不免用了曲笔。比如对于“文革”的罪恶根源问题,巴金也常常用某种符号来代替,似乎未能免俗,但细读全书,就知道他其实看得很清楚的。这在游岳王坟的文字中透出了信息。在谈到加害岳飞的责任时,他引用了岳庙古碑上所刻明人文征明所作《满江红》,并特别强调其中的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是点睛之笔。[7]巴金“讲真话”在某种场景之中,不得不使用“曲笔”,不能将批判的锋芒尽情展露,似乎给人留下一点遗憾,难以让人阅读文章有着一泄千里、酣畅淋漓的痛快之感。但是这也在反面说明巴金在《随想录》中“讲真话”的阻力是何等巨大。巴金在《再论说真话》中这样坦言。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香港《开卷》)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大寨行》),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我才知道受了骗,把谎言当成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含宽容的”。[2]134
在“歌德与缺德”、关于《假如我是真的》讨论等问题。巴金畅所欲言,坦言直言。到了后来,渐渐地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林治贤先生当然不可能感受到,但巴金先生是明显感受到的,这就是后来他不断抱怨的“冷风”,于是渐渐地,意识到一个知识分子还没有到达畅所欲言的时代。所以要强调“讲真话”,就是因为讲真话之难: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因为他真实地感受到言论的困难。陈思和先生指的其思想之远,感情之诚,都是指这种精神状态而言的。随风转向、说话如唱山歌一样好听的人,是不含有如此压力和遭遇、是不含有如此言谈困难的。而他为了把某些精神状态通过最易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只有强调“讲真话”,正如林先生所说,整个社会做不到讲真话,那么岂能有效地教育小学生呢?[8]林治贤先生撰文抨击巴金“讲真话”,讥讽它是“小学生三年级水平”。陈思和先生撰文反击,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坦荡的情怀。“冷风”、“冷雨”等都是巴金使用曲笔的写作技法,象征着“极左”势力与多种邪恶势力,正如鲁迅先生当年对黑暗世道的控诉,也使用了不少的象征性隐语。
“十九世纪全世界良知”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对当时沙俄政府横征暴敛猛烈批判,用“讲真话”的利器抨击,展露了被压迫者的心灵呼声。然而托尔斯泰成为政府和东正教会迫害的对象,多种反对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八十二岁那年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沃车站上。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代的确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他作为作家,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多种欲念作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而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巴金在《“再认识托尔斯泰”》向世人吹出了响亮号角:“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2]340-343
如果说谎是“不善”的,那么不讲真话则是一种“犯罪”,因为这触犯了公民社会的道义底线。从伦理学维度终端显现着价值论的东西。“讲真话”和“大善”意味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与世界的“大利”。就像生物伦理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伦理不是为了让人能装模作样而发明的文化装饰,而是“确保各种交易能够进行的手段”,关系到人类根本利益的兑现。[9]179这是以澄清“何以要讲真话”的逻辑困惑:讲真话关系到社会公正的落实和公民权利真正得到保障,能否让真话畅通无阻,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全与否的重要标记。[10]188因此,“讲真话”的利器早已超越它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而牵涉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大是大非的层面,突显其社会文化的深层次的根结所在,从而彰显它应有的深远意义。
二、批斗会催生谎言,封建专制为假话根源
“讲真话”践行起来,困难重重,有来自各种势力的阻挠,也有来自“讲假话”成风的社会状态所形成的无形压力。其中,政治运动、风波涌起,高压之下,闭住了“讲真话”之口。1962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本来是真实的心声,却不想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在重重围攻之下,巴金沉默了,继而跟着大众学习“讲假话”。他在《三论讲真话》一文中把这一心路历程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
“关于学习、批判会,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说不出我头几年参加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总不是表态,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过以后参加的许多大会小会中整人和被整的事就在所难免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表态,说假话。起初听别人说假话,自己还不满意,不肯发言表态。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于是叫我表态就表态。先讲空话,然后讲假话,反正大家讲一样的话,反正可以照抄报纸,照抄文件。开了几十年的会,到今天我还是害怕开会。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从来不曾对人讲过。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我只讲自己的经历,我浪费了多少有用的时间。不止我一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2]212
批斗会是整人的重要手段。批斗者往往是凭空捏造“罪行”,借群众大会打压人的声浪,会上人人要“表态”,相应“长官意志”无中生有罗列材料,这样的批斗会有谁还敢说真话呢?于是会议成为造谎的场所。原本想“讲真话”者不得不屈服专制,变为讲谎言,讲假话。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例如,196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造反派把巴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其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巴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明知是谎话,却显得装模作样,毫不红脸。这些造反派的“革命左派”靠假话起家。然而巴金并不一味谴责造反派,而是将解剖刀指向自己。他这样严厉地剖析自己带血的灵魂:
“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的‘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2]130
奴隶意识存在于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头脑中,这是“假话”、“谎言”能够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如果人人揭开“谎言”的真相,群起而攻之,即使像“文革”那样的弥天大谎都会被揭穿。
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巴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前两年巴金还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可是后来反右运动兴起,身边的朋友被打到成“右派分子”,巴金在重压之下丢盔缴械,不再以说假话为耻了。尤其是“文革”刚刚开始的八九月,巴金彷佛受了催眠术,脑子里只有一堆乱麻,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想自救,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酷刑。在无法承受煎熬的时候,巴金也有过自杀的想法:
“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来承受,自己种下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2]135-136
逼人逼到自杀的情分,这就是“假话”所导致的恶果,“假话”泯灭人性、泯灭良知,使整个社会靡烂不堪。在艰难岁月中,巴金把《神曲》带在身边。在田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但丁的诗句给了巴金以莫大的勇气。《神曲》让巴金接受了炼狱般的考验,得以重生。
“讲假话”并非五十年代以后才有的,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早就有之,而且根基深厚。巴金六七岁时在父亲广元县衙亲眼所见父亲审案:“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之下哪里会有真话?巴金把它与文革进行对比:
“我不明白造反派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体刑推广假话”。[2]220-221
提倡“讲真话”,是对民生、法制和人权的呼唤,是对专制压迫的反抗。“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古时的“大老爷”审案,动辄用刑,想靠高压逼出真话,结果得到的常常是假话;新专制主义则用高压制造和传播假话。[3]372
“讲假话”也并非巴金一人在批判,从古到今凡是正义的人士都在抨击假话。“五四”时代的李大钊就对国人唯主子是从的奴化心态,对言不由衷的社会状况进行揭批:“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迎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有迎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内心的话。甚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所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发生关系。”[11]190李大钊作为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深刻洞察到了科考场上的为主考意志是向的弊端,进而揭示中国文化有其惰性的一面:虚假性。科举考试让普天之下的知识分子应考都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都是迎合主考心理,得中高分,金榜题名,然后做忠于皇帝、忠于主子的“奴仆”。同是“五四“文化产儿的巴金传承了李大钊这种精神,在许多文章中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探讨出“假话”与“谎言”是封建专制与强权的产物。
三、辐射社会教育文学等领域,争鸣激烈、褒贬不一
“讲真话”并非过时,而是对现实具有极强的针砭色彩。巴金对社会上的“歌德派”与“见风使舵派”进行了斥责,义正词严,发人深省。他在《再论说真话》中说: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为‘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半句一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作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向哪里”。[2]134
巴金对当下社会这两类人物画了两幅画,形象地描绘这两类人物的脸面。说到底,这两类人物还是假话与谎言的传承者,背离了“讲真话”这一基本社会道义的最底线。他们站在人民的敌对立场上,为了个人利益,以假乱真,从而使社会日益陷于精神恐慌与危机之中。
“四人帮”垮台以后,巴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由“牛”重新转变为“人”。他在《三论讲真话》中大声疾呼:“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他借女作家谌容小说主人公直言,写出他自己的座右铭:要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这实际是“讲真话”在立身处世的具体体现。巴金的疾呼其实就是要求世人直面社会的正确态度,也是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这种主张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现代社会还有说假话的官员,也有写谎言的作家。故而“讲真话”利器依然可以发出它的批判现实社会锐利的锋芒。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他的侄子“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12]11如果说教育是立国之本,那么讲真话则可视为教育之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部《论语》以此开篇体现了中国先贤们对教育的重视。但离开了“真话”的传播,所谓的“学习”与“教育”便只有其名,没有其实。巴金一再强调的“讲真话”的人文意义,恰恰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语境里显得如此无意义。不能不承认,与官方组织的热闹形成强烈反差的大众心态的冷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上下默契地普遍对所谓“真话”缺乏兴趣。虽说天下父母没有谁愿意其子女成为撒谎成性的骗子,但很少有家长会鼓励他们在生活中能坚持说真话的原则。有小学生因说了真话而“得罪”同学与老师,回家被父母批评“不聪明”,这样的报道早已不是新闻;有留学生在国外上学,任课教师将作业的答案公布,让学生自己给自己评分,中国学生习惯性骗取高分,而外国学生则“愚蠢”地如实填写,这样的故事也并非传闻。这就是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诚信”缺失。这足以说明,对“讲真话”的关注必须重新提上我们的文化议程。[13]“讲真话”在教育大计方向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用。我们时下呼唤要建设“诚信社会”,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诚信”普遍缺失。
“讲真话”应当辐射到我们当今的文学家园。因为当今文坛也不令人满意,大量的文化垃圾充斥着文化市场。早在1988年巴金参加文代会,令巴金大为光火。他在11月20日《至杨苡》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开会前郭玲春两次打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两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之类?花了一百几十万,开了这样一个盛会,真是大浪费。我的确感到心痛。我不喜欢《家·春·秋》,它应当触及今天的封建主义,可是没有办到。写不下去了,祝好!”[14]11-12
“冷气”在这段文字中显然是“曲笔”,影射当时“左派”首领压制巴金“讲真话”,向文学界吹来的一股阴风暗雨。巴金笔锋犀利,直批那些擅自删除发言稿的恶劣行为为“封建主义”。巴金出离愤怒,私信写不下去而搁笔。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利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权可依,积极参加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惟一的选择。陈思和先生认为,“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的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在80年代风雨欲来的政治风波中,巴金始终没有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树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15]11《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历史的沉思与探索,用“讲真话”作为一种利器成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护身符。
《随想录》问世后,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讲真话”利器在文学百花园中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把利器的锋芒四射,照耀在文艺界和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大力辐射、广为流播。
与巴金素以姐弟相称的冰心老人在1988年10月24日《致巴金》书信中说:“你‘胆’大,可以敢说真话,精神是应有物质为基础的!”萧乾在《更重大的贡献》中这样高度评价“讲真话”:
“我认为说真话的《随想录》比《家》、《春》、《秋》的时代意义更伟大。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真话畅通,假话失灵,那就会把基础建在磐石之上。那样,国家就能强盛,社会才能真正安宁,百业才能俱兴,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不说真话,关系到民族的存亡”。[16]
《随想录》写作完成之后,巴金又用了一个八年抗战,写成了又一部“讲真话”之书《再思录》,受到友人马识途称颂。马识途在1995年6月15日给巴老书信中写到:“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5]2文如其人,《再思录》使马识途这位老作家受到强烈震撼,决心以巴金为榜样,为“讲真话”甘愿献身。由此可见,“讲真话”利器的锋芒是何其锋利、何等璀璨,折射着耀眼的人性的光辉。
汪曾祺在《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中,称巴老“始终是一个痛苦的流血的灵魂”。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不同,他对“文革”的反思,是把自己看作“债主”,自我解剖达到了近乎残酷的程度。[17]129-130谌容认为,《随想录》之所以称得起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我以为全在于作者讲的是真话。巴老把《随想录》第三集题名为《真话集》,其实,讲真话正是贯穿于五本随想录的总主题。讲真话,说起来容易,做来难,扪心自问,我们过了这么些日子,走了人生半个旅程,说了多少假话啊![18]张光年在《语重心长》中说,《随想录》的文章虽短,分量却很重。当代中外读者和后辈子孙,都可以从中得知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作家的领袖人物在十年浩劫之后的思考,它是记录一代正直文化人心灵的文献。[17]132
不仅是作家高度关注《随想录》,学者、报人、编剧等不同阶层的人们对“讲真话”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复旦大学郜元宝先生认为,《随想录》的主要内容是巴金从自己切身经验出发来反思“文革”的悲剧,他把这种反思性的写作叫做“讲真话”,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见解深刻,目光远大。这是保证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不至于苍白模糊的一个关键。巴金呼吁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更深入地探讨“文革”的成因及其对中国文化深远影响,这绝不是所谓纠缠于过去,或者老年人的思想凝滞,而是有其深远的见地。在这一点上,他不愧是五四的儿子和鲁迅传统的继承者。[6]341《中华文学选刊》总编王干认为,巴老的文学精神、艺术精神对青年人有传承性的影响,教青年人要真诚地面对现实,不要矫情,要讲真话。巴老跨越了两个世纪,巴老的文学创作和做人的精神给文学工作者,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讲真话,不虚假等等都是一些作家要汲取的。巴老的精神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巴老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编剧邹静之用一句话总括为“巴老文字不带表演”。[6]342-343
以上知名人士,或是文坛泰斗、文学巨匠,或是学术权威、传媒人物,都从“讲真话”角度再度探讨了《随想录》的各个层面的影响与意义。不难发现,“讲真话”利器一经社会磨刀石的试擦与磨切,向社会各个领域散发出绚丽奇异的光亮,这束神奇的光束,流播范围之广,辐射能量之强,可以说叹为观止,为世人注目与垂范。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论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相对而言。同样,“讲真话”备受国人颂扬的同时,它又遭受人们的反感,这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说是百分之百赞语,那才是真正的“讲假话”。有了不同的声音,才能进行“百家争鸣”,在“争鸣”中接近真相、接近真理。
深圳朱建国1989年在《明报》杂志上发文,攻击巴金为“贰臣”。香港大学生在《开卷》上展开了对《随想录》的围攻。海外某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专家,由于对中国“文革”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文学观念的不尽相同,对巴金的创作,对《随想录》很难有深刻的感觉和认识。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马悦然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有记者对他来访时说:“高行健曾对他说,中国大陆终于有一位敢说真话的作家巴金。”但是马悦然读了巴金的《随想录》后说:“根本看不出什么真话,胆子太小了,还是不敢讲真话,都八十岁了,杀掉了,就杀掉了。”[3]401优秀文艺作品的真正评审是读者,无论国内少数“左倾”势力,还是国际诺奖评审专家否定“讲真话”,否定《随想录》,也不能抹杀它存在的价值。在与反面势力较量中,正面力量将愈战愈勇,在争鸣中明辨是非,探究真相,从而在争鸣中实实在在感知“讲真话”的重要性,我们中华民族才会从“讲真话”中受益无穷。
[1]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 巴金.随想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3] 谭光国.走进巴金的世界[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
[4] 李存光.世纪良知巴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 四川作协编.论巴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6] 彭小花编.巴金的知与真[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7] 吴中杰.“讲真话”谈的历史问题[J].世界,2006,(2).
[8] 陈思和.关于“讲真话”的一封信[J].香港文学,2003,(5).
[9] [美]爱德华·威尔逊.生命的未来[M].陈家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0] 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双美丽的眼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 金净.科学制度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2] 李致.我的四爸巴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13] 徐岱.巴金的意义[M].文艺理论研究,2006,(2).
[14] 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5] 陈思和编.解读巴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16] 萧乾.更重要的贡献[N].文汇报,1994-04-01.
[17] 吴泰昌.我亲历的巴金往事[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
[18] 谌容.只因为是真话[N].文艺报,1986-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