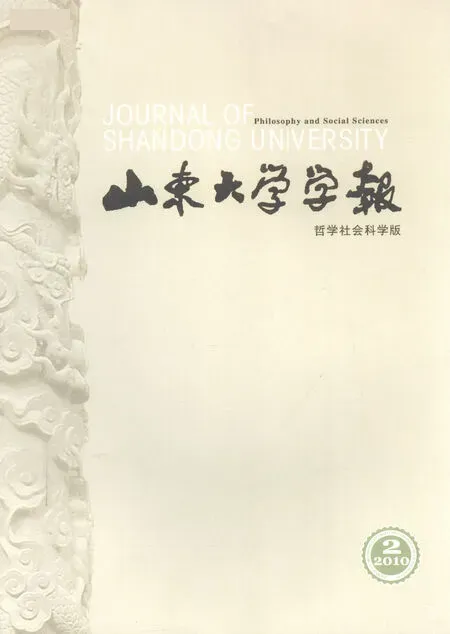以“民间说话”为词——论宋词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向
曲向红
众所周知,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借鉴诗文的写作方法与表现技巧,出现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发展趋向,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讨论与研究,但实际上学习诗文等文人文学表现手法的只是文人雅词。由于文化背景以及接受对象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差异,词坛上数量不菲的俗词多不采用文人文学的这一套手法,而是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中汲取营养,将传统文学的抒情性与说唱文学的叙事性相结合,显示出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过渡的痕迹以及雅、俗文学日渐合流的倾向,这也是导致宋代词坛雅俗对立的重要原因。
“说话”是盛行于宋代民间的一种讲唱故事以消遣娱乐的文艺形式,其远源按照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的观点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优孟、淳于髡以及汉代东方朔一类俳优侏儒说故事的伎艺。魏晋六朝的“俳优小说”和“说肥瘦”也是说话艺术的一个重要源头。其近源乃是唐代民间、宫廷以及寺院中盛行的“说话”,如郭湜《高力士外传》曾记载:“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①郭湜:《高力士外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 120页。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②元稹:《元氏长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 55-56页。说话在宫廷、文人间如此流行受欢迎,可以想见其在民间的兴盛程度。唐代寺院中“俗讲”所讲唱的变文,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也是“说话”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保障寺庙的经济来源,如元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俗讲”注中曾言:“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7850页。这说明唐代俗讲具有明显的通俗性与商业性。
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专为市民娱乐的瓦舍勾栏设立,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要求,讲唱民间故事的“说话”慢慢兴盛起来。“说话”是一种在瓦舍勾栏即时讲说、靠人际传播的文艺形式,说话人在当场要凭借其“舌辩”功夫与技巧,“使席上风生”,“教坐间星拱”,①罗烨:《新编醉翁谈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3页。因而其精彩之状是无法描述、难以重现的。宋话本是说话人讲说故事的脚本,大多简练粗糙,只是略述故事梗概以备忘,如《西山一窟鬼》话本只有短短六千来字,但一经说话人现场敷衍讲述,便“变成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因此从宋话本中其实是难以看出说话人表现伎艺的优劣的,不过管中窥豹,以之作为探究宋代说话艺术的参考还是可行的。宋代说话艺术非常兴盛,仅小说话本(话本中的一类)《醉翁谈录》里就记载了一百多个篇目,然而因为各种原因保存至今的宋代话本小说数量相对较少,根据语言风格、所引诗词,以及地名、官职称谓、典章制度等,可以考证出是宋代话本的仅仅有三十多篇,诸如《刎颈鸳鸯会》、《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西山一窟鬼》等等,散见于明人汇辑的《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小说四种》、《京本通俗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书中。虽然这些话本大多都经过后人的润色、改动,但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风貌,从中仍能感受到当时说话内容的丰富生动,感受到说话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审美领域,不愧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鲁迅选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 208-209页。,当然也能略窥在市井文化这一文化土壤上盛放的民间说话对宋词的影响。
第一,宋词尤其是俗词具有强烈的叙事性,这主要是来源于民间说话的影响。
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一文曾借鉴叙事学文本结构分析的理念和思路,详细分析了词的叙事性,从词调的点题,词题的引导叙事,词序对叙事的说明、铺垫以及正文所采取的片段、细节、跳跃、留白、诗意叙事等等,都是词叙事性的重要表现。③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2期。但如果将雅词和俗词对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雅词虽然也有叙事性,有人物语言与动作等的表现,但词人想表现的并非是故事的发展过程,其叙事往往只是抒情的依托,在景物的烘托下,情、景、事以及人物的言行举止等往往交融成一种静态性的人物画般的意境,在这意境中散发着词人的心境、情绪,并包含着潜在的叙事因素。也就是说雅词终究是要以清空的抒情笔调为主,就像张炎强调的“词要清空,不要质实”④张炎:《词源》,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页。,他所谓的清空除了指风格的空灵高旷、语言的灵动明快、审美的高远峭拔以及意境的飘逸之外,还有就是要求词人的情感表现不凝滞于事,能将事化为情感抒发的衬托,从而使作品摆脱写实、叙事的笔调,变得空透灵动,令人回味无穷。而俗词往往摒弃景物、外貌等静态性的刻画,直接通过人物的语言与动作的表现,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在事件的叙述中抒发情感,刻画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如柳永《锦堂春》:
坠髻庸梳,愁蛾懒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翦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
此词以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现了她的相思愁苦与怨恨,“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翦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将心理表现与动作描绘融为一体,剪云鬟、关香阁、“不与同欢”、“款款问伊”等行为,都是报复行动在内心的叙说,并未真正实施,但作者却善于抓住细节,加以渲染,将抒情与叙事结合,从而将心灵深处积聚的情感以行动的方式喷发出来,冲击人们的听觉与视觉,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刺激。
俗词的叙事性受同一文化场中民间说话的影响最大。最先以铺叙的手法使文人词具有了故事性的就是柳永,所谓“序事闲暇,有首有尾”⑤王灼:《碧鸡漫志》,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页。、“总以平叙见长”⑥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651页。等评价都是对其叙事性的肯定。习惯上认为柳词的铺叙手法主要是从赋体中学习的,但也有研究者另辟蹊径,指出柳词对说话艺术的学习与借鉴,如宇野直人曾指出:“作为词人的柳永,其资质中有一些‘说话者’──即与专业说话人同质的倾向,他留下的慢词中有一些令人想到讲唱文艺的内容和手法的作品,……(这些长调慢词)与诗词的传统相比更接近于〈小说〉的作风”⑦宇野直人:《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155-156页。,并进一步推断“柳永在北宋繁华街巷中,接触到了如今已经失传的‘通俗类书’,或者与之类似的、作为说话底本的 <小说 >,并且欣然领悟到了诗词与故事这两种文学形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①宇野直人:《柳永论稿:词的源流与创新》,第 130-131页。,从而将民间说话中常用的表现技巧、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手法等吸收进长调慢词的创作中来。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且不说赋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曾说过:“秦汉时代说话艺术的丰富和活跃,还派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那就是韵散结合的文体,就是赋。”②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8页。蒋先伟《论赋起源于民间说话艺术》一文也详细论证了二者的辩证关系。③蒋先伟:《论赋起源于民间说话艺术》,《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 37期。其实说话人要使自己讲述的故事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就要学习其他各种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形式技巧以及题材运用。先秦以来的史传散文,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等等,都是说话人学习的极好教材,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当然也包括在内,这样才能使故事的讲述详细尽致,扣人心弦,才能“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④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第4页。,“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罗烨《醉翁谈录》)⑤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第3页。,使听众自始至终都能被牢牢吸引,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所谓“敷演”即带铺叙演说之意。以赋为词使词篇幅增长,叙事倾向增强,而这又正好为词从民间说话吸取更多的故事性打开了缺口,使词有意无意之间在寻求故事与情节的过程中,日益向民间说话靠拢,注重通过叙述情事纠葛与过程再现情境,表现人物性格、感情以及心理等等,而这部分词就变成了与雅词风貌截然不同的俗词。如欧阳修《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表现男女私会的情景,有故事场景、人物对话以及细节描写,叙事性话语极其活跃,已成为主要表现手段,完全没有作者主观感情的渗入与抒发,如果再对这些词中的男女情事、遭遇曲折以及处境等进行想象描述以及合理扩充的话,很容易创作出一部委婉细腻的话本小说来。叙事性的渗入增加了细节的真实可感性,使词更加贴节现实生活,这是宋代以说话艺术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市民阶层的口味与文学趣味日益渗透侵入的结果。
第二,宋词尤其是俗词对故事情节的虚构性也源于民间说话的影响。
宋代以前的文学大都属于纪实的,很少是有意的虚构。抒情文学自不待言,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多不需要积极地虚构,辞赋虽然常常假设问对,虚构人物,所谓“伪立客主,假相酬答”⑥刘知几:《史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 149页。,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展开主客问答,但其虚构多重抒发牢骚之叹,凸显讽谏之意。即便是叙事文学虚构性也不强,神话的虚构并非自觉,六朝志怪也并非艺术的虚构,创作者只是在作笔记实录,如实记载逸闻奇事,干宝《搜神记》序即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⑦干宝:《搜神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559页。又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⑧干宝:《搜神记》,第 559页。注重语出有凭,事出有据,丝毫不敢凭生活经验虚构杜撰作品,其充当的仅是有闻必录、辑录故事的角色,亦即以力避失实的史家的态度来搜集奇事,以证明“神道之不诬”,并非主动虚构,其故事的奇幻色彩只是源于神灵鬼怪传说本身的虚幻性质,这与小说在萌芽阶段依附于正史之末的地位有关,小说家为使自己的奇闻轶事被人认可,不遭攻击,也乐于以之比附正史。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3页。,主动编造故事,幻设情节,在创作态度与手法上,比六朝小说增强了虚构与再创作,属自觉地进行艺术创造,但其所重仍在“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⑩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 111页。,而且其表现的故事多以文人感受与遭遇为主,并不能挥洒自如地任意运用虚构。只有到宋代民间说话等叙事文学的兴盛,才开始了真正涵义的、积极的、大规模的艺术虚构。
说话人“博览该通”,在瓦肆勾栏中凭借书本所学、师傅传授以及传闻见识、生活体验等,随意发挥想像虚构,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讲说故事。正如南宋初郑樵《通志·乐略》所言:“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357页。说话人把原本流传的民间故事、史传人物甚至当时的传闻当作素材,凭借艺术的虚构,发挥想像,穿凿附会,“肆为出入”,从而将只言片语铺叙敷衍成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千万言”,足可见其艺术功力。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言说话人“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团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①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第3页。,看来毫不夸张。此时期的小说作品开始讲究布局、结构以及情节的精心安排,不仅做到了“随意据事演说”,说话人还能根据需要驰骋想像,装扮成各种人物,虚构各色人物的言行心理,代他们抒发心声,使人物形象各肖其人,在言行举止等细节的刻画中丰满有形、栩栩如生。
从实录到虚构,是艺术演进的重要之路,俗词对故事情节的想象虚构以及全代人言的写法,就受到了注重虚构的叙事文学民间说话的影响。雅词中也有虚构的表现手法,词人常用的代言体从广义上来讲就是一种虚构,因为女性的情感、心理以及内心世界对男性而言纯粹是陌生的难以感知的世界,男性词人不以自己的口吻表情达意,而是“男子而作闺音”②田同之:《西圃词说》,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449页。,把抒情的言语尽可能放在想像中的那个女性身上,揣测其所思、所想、所感,代女子作自我表白,代其发出心声,从而使词作表现的内容、情感与唱词的歌妓的身份、心理相吻合,演唱时更易收到情辞和谐、感人至深的效果。不过雅词的虚构情节性不强,常常是点到为止,以抒情为主,而且词人的叙述视角也常发生转换,在代女性抒情之时还会渗入对自身情志遭遇的感慨,这使词在抒情品格上明显高于全代人言的词作。而俗词就不同了,俗词的作者几乎完全隐去自我,化身宾白,去虚构词中人物的言行、情感与心理,虚构情节,并展开矛盾,从而使人物因事而显,形象非常鲜明突出,当然故事性也很强。比如欧阳修《醉蓬莱》词表现男女幽会,就是以虚构的手法结撰词篇。再如赵长卿《簇水》:
长忆当初,是他见我心先有。一钩才下,便引得鱼儿开口。好是重门深院,寂寞黄昏后。厮觑著、一面儿酒。 试撋就。便把我、得人意处,闵子里、施纤手。云情雨意,似十二巫山旧。更向枕前言约,许我长相守。忺人也,犹自眉头皱。
以回忆的方式记叙当年的相知相会,虚构性也很明显。“厮觑”、“撋就”、“闵子里”等均为俗语,以“一钩才下,便引得鱼儿开口”表现男女之间的吸引、勾引,虽极俚俗,但形象生动。这些词对男女情爱故事的表现,均注重事的描绘,几乎全部都是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所做的适当的虚构,和上面所言的叙事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民间说话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使词在对事的虚构与叙述中婉转细腻、形象生动,更易为市民阶层所理解,并得到他们的喜爱。由于长期以来政教文学观的影响,词品代表的就是作者的人品,这些“不正”、“淫邪”的内容往往被看成实有其事,变成作者人品的污点被加以攻击,这都是忽略了俗词具有强烈的虚构性所致。
第三,宋词尤其是俗词的戏谑性也深受民间说话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中有说药一科,《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就曾记载当时有“说药”艺人杨郎中、徐郎中、乔七官人等,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推断说药“大概是说一些药性或医疗的故事,为自己的卖药做宣传”③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119页。。这种说药伎艺对俳谐词以及戏剧等说唱艺术中大用药名作文字游戏起到了推动作用。擅长作药名词的陈亚早年父母双亡,依舅氏为生,读书应举,其舅为医生,人称“李衙推”。陈亚工药名诗、药名词,一方面与生活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有关,另一方面大概也是以药名入诗词,为其舅作宣传促销,招徕顾客。
说诨话是宋代说话家数的一个重要类别,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曾说道:“张山人,说诨话。”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 32页。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亦列有“说诨话”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第53页。一科;《西湖老人繁盛录》“瓦肆”条记载“说诨话,蛮张四郎”⑥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 17页。;《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亦列有“说诨话:蛮张四郎”⑦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 136页。。在有一些学者如赵景深等人关于说话四家的划分中,也把说诨话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家数。说诨话的话本现今无传,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到说诨话对俗词的影响,如王灼《碧鸡漫志》曾谈到“以诙谐独步京师”的张山人对俳谐词的兴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民间说话在社会风行一时,对当时的文人词产生了强烈的渗透与影响,从而使俳谐词兴盛繁荣,出现“嫚戏污贱,古所未有”的局面。而这些俳谐词一经产生,其滑稽诙谐、幽默风趣的喜剧性效果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民间说话看好俳谐词的这份喜剧性,因而又将其吸收进话本中,作为插科打诨、调节现场气氛的重要表现手段,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曾引柳永《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词,中有“权将‘好’字停那”、“‘奸’字中间着我”等语,大玩文字游戏,还有一些话本自己创作俳谐词,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与《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篇话本小说都采用一首词《夜游宫》辅助叙述,文字几乎相同,其词曰:
四百四病人皆有(《花》作“可守”),只(《花》作“惟”)有相思难受。不疼不痛在心头(《花》作“恼人肠”),魆魆(《花》作“渐渐”)地教人瘦。 愁逢 (《花》作“怕”)花前月下,最怕 (《花》作“苦”)黄昏时候,心头一阵痒将来,一两声咳嗽(《花》作“便添得几声”)咳嗽。
以调侃滑稽的笔触,拿人相思的痛苦打趣,博人一笑,这些俳谐词基本是书会文人或者说话人自己创作的,对俳谐词一脉的保存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宋词与民间说话在同一市井文化场中各种力的作用下,并非是简单地受力,而是既影响他者,又受他者影响,二者结成的是相互影响利用、相互借鉴吸收的关系,宋词不仅学习借鉴了民间说话的各种表现技法,对民间说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宋代话本多借助宋词抒发感慨,评论故事,概括总结全篇大意,词人佚事、词作本事常被敷衍成话本等等,都是民间说话从宋词中汲取营养。
实际上,学习借鉴民间说话表现技法的词基本上都是深受抨击诟病的俗词,这些词虽然在艺术成就、思想高度等方面往往不如雅词,但也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逐步向诗文靠拢,如苏轼将士大夫的个人抱负引入词作,辛派词人将政治感受、爱国之情引入词作,使词具有了像诗文一样抒发政治抱负与遭遇的特征,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文人雅词,无疑等于以偏概全。俗词虽然与雅词一样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注重雅词与诗文关系探究,忽视了俗词与同时代俗文学的借鉴关系。事实上如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所言:“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互相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①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页。这不仅仅包括雅文学样式诗词文之间的交融互渗,俗文学样式因其开放灵活的体系更易交流互动,互相学习。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忽略词坛的半边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