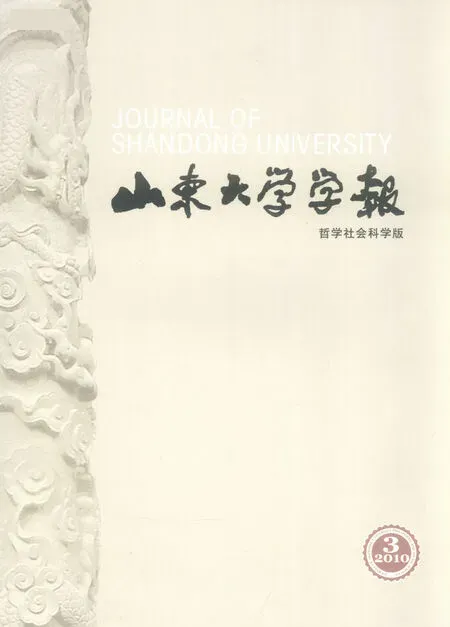公共空间视野下上海现代市民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张 娟
热拉尔·热奈特说:“叙事”最明显、最中心的含义是指“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①[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 6页。。更具体地说,所谓叙事,就是把一件或若干事情说成“如此这般”,也就是关于某一或者若干事情的一种“说法”。现代市民叙事就是围绕“现代市民”所进行的“如此这般”的“叙述”。我所谓的“现代市民”是指生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具有以人为本、物质理性、生存第一等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市民。30年代的上海,被誉为“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而经济繁荣的上海都市造就了一批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传统市民,也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等小市民的现代市民。他们与都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对都市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与都市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市民叙事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施蛰存、苏青、予且、张爱玲等作家所创作的反映现代市民生活与价值观的现代市民叙事文学。
现代市民的形成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市民叙事策略也相应受到都市生活的影响。而其最大的影响在于都市生活不再仅仅是写作的背景,而成为了小说叙事策略中的重要一环。它起到了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前进、影响叙事视角的作用。在现代市民叙事中,最常见的介入叙事策略的都市生活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公共空间,比如在穆时英、刘呐鸥等擅长描写中产阶级市民小说的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舞厅、南京路、百货公司、街道等等;二是日常生活物品,比如在张爱玲笔下经常出现的电车、镜子、电梯等;三是以电影、杂志代表的传媒空间。在 30、40年代大众文化发达的上海,大众娱乐深入人心,也深刻影响到了文学创作。本文主要探讨公共空间与 20世纪 30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施蛰存等作家为代表的现代市民叙事策略的关系。
提到公共空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哈贝马斯所讲的 public sphere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事实上,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在 3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中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它应该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生活 (public life)。研究这样一个空间,除了其本身的物质意义外,对 20世纪 30年代现代市民小说叙事策略的改变起到了何种作用,进而探究它对 20世纪 30年代现代市民深层价值秩序的影响。
一
20世纪 30年代现代市民叙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公共空间在文本中的大量出现。茅盾所讲的“百货商店的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的娱乐的消费的上海”①茅盾:《都市文学》,《申报月刊》1937年第 2卷第 5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化特征呈现出来,并在叙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不同于传统市民叙事注重情节的线形风格,也不同于 40年代现代市民叙事的日常化倾向,具有独特的叙事学意义。
首先,公共空间的使用,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的强大叙事功能。在叙事文本中,作家往往用一些标志性的现代建筑来起到这一起承转合的功用。文本中最常见的是公园、舞厅、酒吧、饭店、跑马场、街道等。
市民生活的基本场所是都市。而都市生活最大的特征就是公共空间在生活中的比重增大,人与人的关系更富于流动性和偶然性,也更有利于激发出人个性的多种潜能。早期市民小说中频频出现“法国公园”这个地方。林微音《春似的秋》、《秋似的春》连续性短篇借女主人公白露仙的信,叙述在法国公园如何拾到男主人公斯滨的手抄诗稿,引起情感波澜。从这个时候开始,市民叙事就呈现出与传统叙事不同的开放型特征,带来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后来,这个象征物逐渐被舞厅酒吧饭店所取代。刘呐鸥唯一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封面上有“scene”这个单词,从某种程度暗示了公共空间在这些小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里面的8篇小说涉及了上海生活的众多场景:舞厅、火车、电影院、街道、花店、跑马场、永安百货公司等等;穆时英的小说《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男性主人公闲逛了一个又一个都市游乐场所:回力球场、舞厅、独唱、酒吧、Beaute exotique和 CaféNapoli,最后在咖啡馆邂逅了女主人公;而叶灵凤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出入于 Feilington、国泰电影院、新亚饭店、沙利文咖啡馆和上海的外文书店。和鲁迅等五四小说家刻意用“S城”等代号标注地名,唯恐对地点的强调会干扰情节行进相反,现代市民小说家近乎炫耀地用地名作为情节转折依据,不断提示主人公行为场景的转换,以此推动故事发展,塑造人物性格。
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娱乐休闲场所,街道作为这些公共场所的连接地,也是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现代市民叙事文本中街道的出场颇为频繁,有的是无名的,更多是读者熟知和真实的,如南京路、福州路、霞飞路、静安寺大街等等,它不再像古典小说中那样,作为小说情节的发生地点和场景而依附于故事存在,而是具有了强化小说主题、塑造人物性格的叙述意义。街道在文本中取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仅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或者背景,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叙述功能。传统叙述中,行走在街道上,是为了走向某个预期地点去完成预期目标;而在现代市民小说作家笔下,走在大街上本身就是目的。主人公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地任意走在某条任意选择的街道上,等待着意外的邂逅,或者奇遇。这实质是以外界的刺激来激发主体能动性。这些文本中的街道本身是没有主动性的,但街道上任意发生的某件事情,都可能推动故事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共空间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中的作用,我任意选取穆时英的《红色的女猎神》来作一个案分析。《红色的女猎神》文中共涉及到三处公共空间:跑狗场、酒吧和宾馆。故事的开始是在跑狗场“看台沉到黑暗里边。一只电兔,悄没声地,浮在铁轨上面,撇开了四蹄,冲击了出去。平坦的跑道上泛溢着明快的,弧灯的光。”男主人公偶遇了一个身着红衣的近代型女性。这种相遇的方式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上海 30年代这个市民社会中就具有了典型性。而因为赌狗而结识,也是现代城市生活中女性走向社交舞台的结果。接着男子和她在马路上散步,到酒吧喝酒。由于这些交际场所的公共性,就造成了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每个人之间都是陌生人,任何人都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所以这种恋爱有可能导入无法预知的结果,从而更具刺激性;二是他们的感情没有任何来自社会家庭的阻碍和功利的考虑,使他们的个性追求得以最大程度张扬。所以,女子任性、野蛮、不羁、顽皮的个性在情节发展中获得最大张扬,深深打动了男子,而美丽的女子竟然是土匪首领,这个意外的结果反而激起了男子更大的热情。对天性中自我意识与冒险精神的赞美也获得了极度张扬。可见,都市空间的公共性对于主人公的个性形成、情爱选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最终推动了整个情节的发展。
其次,公共空间的出现改变了市民的生存环境,也影响了市民作家的叙事视野。在现代市民叙事中集中表现为两种叙述特征:一是跳跃性的散点扫描式,一是短视与瞬间追求。
现代都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变幻莫测的现代化街景,它给人走马灯式的跳跃性体验,同时也使现代市民小说文本呈现出散点扫描式的叙述格局,当时的市民叙事文本擅长浮光掠影的全景描写。这种写法李今和张鸿声都命名为“巡礼式”,认为就像穆时英惯常使用的用汽车浏览城市街景一样,走马观花浏览都市,以印象式的浅层体验结构全文。对比和列举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
现代市民较之乡民,生活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灯红酒绿、人潮涌动本身就代表了现代市民生存环境特征。基于这种现实情形,在写作时,现代市民作家不约而同采取了列举式的全景式扫描笔法。分析文本,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市民小说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街:晴朗的街、阴雨的街,午后闲静的街、夜晚神秘的街,喧嚣的街、寂静的街,“散发着尘埃、嘴沫、眼泪和马粪的臭味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装饰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无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道上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还是大批市民。大街上走着卖票的女尼,残日下西洋梧桐的路上,走着穿土黄色制服的外国兵,带着个半东方种的女人。(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妓女、绑匪、白俄浪人、穿燕尾服的英国绅士、带金表穿皮鞋的中西结合的商人……这些碎片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又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市民生存图景。反映在一些具体文本中,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打破了事件按时间顺序和时间之间因果律的法则,彻底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或情节线索的因素,将一些互不相干的时间和人物串在一起,跳跃性很大,就是受这种叙事视野的影响。
同时,公共空间对所有人敞开,它对市民的身份、职业、年龄、经济状况没有限制,所以,在文本中文人、乞丐和妓女经常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场景中。在穆时英《PIERROT》对街道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这一点。现代市民作家在散点扫描的同时,很自然采用了对比手法。穆时英的《街景》就对生活在外滩或街头巷尾的下流社会民众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对比式描写。这篇小说以一个老乞丐 30多年的人生故事为主线。30年前,他做着上海梦来到这个现代都市。为了赚钱,他不辞劳苦,提着篮子在大街小巷卖花生米,希望有朝一日发财了,可以接父母来上海玩。然而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上海一天一天改变了模样,马路变阔了,屋子长高了,他的头发也变白了。都市男女们在纵情声色,老乞丐却一无所有、行囊空空,梦想着回家,最后却葬身车轮之下。然而在发生悲剧的同时,这又是一条“明朗的太阳光劲头了这静寂的,秋天的街。”有着野宴的男女和温柔的修女,刚从办公处回来的打字女郎和放学回去吃点心的小学生。一切并行不悖。这种手法被穆时英频繁采用,他最著名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也是这种一个在全景描写中撷取其中几个人物作为“点”,进行对比描写。贫与富、哀与乐、暴死与逸生、地域与天堂,形成有层次有对比的全景扫描。
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身处其中的市民思维方式,城市高楼林立的空间建筑既改写了地平线也造成了视线中断。一个典型的具有意味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孤独者从阳台或窗户那里俯视街道”。这种空间透视的局限性就在于主体只存在单向视觉。这种注视城市的方式使得个体得到的城市图景是没有深度的平面景观,从而很难领悟这种景观背后的深刻含义。这也是当时的市民叙事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短视与追求瞬间快感的重要原因。
市民生活在现代都市中,最常使用的观察方式有鸟瞰、漫步与仰视。从市民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众多例子,以验证作家的视野受到城市建筑影响。他们通过高耸的建筑物获得了可以俯视都市的位置,文本中经常把拥挤在都市中的人群写成“一簇蚂蚁似的生物”;同时,他们的视线又不断受到建筑物的阻隔。“游倦了的白云两大片,流着光闪闪的汗珠,停留在对面高层建筑物造成的连山的头上。远远地眺望着这些都市的墙围,而在眼下俯瞰着一片旷大的青草原的一座高架台,这会早已被赌心热狂了的人们滚成蚁巢了。”(刘呐鸥《都市风景线》)“街旁,一片空地里,竖起了金字塔似的高木架,粗壮的木腿插在泥里,顶上装了盏弧灯,倒照下来,照到底下每一条横木板上的人。”(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则用仰视的方式描写高楼下人的渺小。不管是哪种观察方式,建筑的胁迫挤压到人的思考空间,这种都市空间带来的巨大压迫感与阻隔感使得虚无时时入侵,从而使众多文本专注于瞬间流逝的景物与情感。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跑马场的边界就是“都市的墙围”,陌生男女在拥挤的人群里相遇、散步、跳舞,看不到两人的过去,也看不到两人的未来,然后迅速分开。女子甚至宣称:“我还未曾跟一个 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快速升温又转瞬结束的爱情就如同在几分钟决定胜负的跑马比赛,快感只在于瞬间投入的高峰状态。
再次,公共空间在现代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也带来了市民叙事修辞方式的改变,城市空间自身的表意功能得到最大强调。
现代市民叙事中频繁出现公共空间,也使得公共空间逐渐成为一种表意符号,直接承担叙事功能。当代法国著名文化理论家博度(pierre Bourdieu)曾说,“社会空间”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表征”。作为小说情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城市空间本身就具有“言说”自己的意义。城市的弄堂、街衢、石库门、百货公司、舞厅等空间也从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模式,给予作品丰富的意义。陈晓兰认为“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沉缅于一种象征性地绘制上海地图的行为中”,在对公共空间强调的同时,“根据一个人的线路图和他的停靠地表现人物,某些地方总是与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些地点暗示人物的道德倾向和生活方式。而作家对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明确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正是在这种作家、人物与其所处空间的融会、交流中,作家的态度、人物的形象和上海的特性被展现出来,空间也被赋予了一种明确的政治、道德意义,因而被政治化、伦理化。”①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62页。作为一个鲜明的例证,20世纪 30年代现代市民小说往往形成模式化叙事。跑马场是用来邂逅的,这里的女子是热情开放的;大街是增进感情的,酒吧是让人意乱情迷的;旅馆是用来发泄欲望的,这个充满不稳定性的场所又是让主人公在激情之后一拍两散的。现代都市的空间功能逐渐趋向专业化,也使得不同的地点注定发生不同的情节,而出现在某一特定场所的肯定是具有某种共同个性特质的人群。曾虚白在《偶像的神秘》中用调侃语气描写了不同公共空间的表意价值与巨大功用:同样是一个女人,当她在大世界的街角傻站、转悠,便只能招来一些揩油的臭男人,一旦换了行头,住进饭店,使男人看得见却摸不着,她便能受社会之宠,转眼间身价百倍。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市民叙事文本中津津乐道于种种物质消费景观。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出现在某一场所的人群往往具有共性,消费同一种商品的人群通常也会有共同特征。对物质的描述实质上暗示了主人公的个性特征与生活状况。如叶灵凤笔下的街景“无线电播放着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消息,书店里陈列着外国书籍,橱窗里陈列着:‘堪察加的大蟹、鲑鱼,加利富尼亚的蕃茄,青豆,德国灌肠,英国火腿,青的,绿的,红的,紫的’。”(叶灵凤:《流行性感冒》)实质上传达着生活欧化的文人偏好。而穆时英的《黑牡丹》则用“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等等奢侈品来标志舞女黑牡丹的空虚物化的生活。
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市民叙事呈现出一种与传统市民叙事截然不同的空间化特征。传统市民叙事注重情节和人物塑造,以事件的因果线索来结构全文,追求完整的叙事框架;而现代市民叙事以公共空间作为结点推动事件发展,采用散点透视方法,不追求完整框架,呈现出对瞬间与片断的迷恋。这种全新的叙事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情况非常复杂,其中有西方城市文学资源的影响,也有传媒空间如电影、杂志的渗透,但有一点较少被人论述,就是公共空间的改变对市民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20世纪 30年代的现代市民叙事以一种空间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在研究城市符号系统时说:“城市是一种话语,一种真正的交际语言。”即“城市空间作为一种话语模式,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主体进行交流,并影响或造就社会主体本身的心理格式”①转引自方成、蒋道超:《德莱塞小说中的城市空间透视及其意识形态》,《名作欣赏》(学术版)2006年第 6期。。公共空间的改变是 20世纪 30年代市民语境的最大特征。随着公共空间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市民的心理格式逐渐被影响,形成注重自我、趋时求新、注重物质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市民叙事策略发生改变的深层原因。
首先,公共交往空间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私密空间,更加强调了个体独立价值,从而使得作家不再扮演启蒙者角色,而是从自我感受和个体经验角度出发反映现代市民普遍的情感和心态。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曾说:“个人的流动——交通和通讯发展,除带来各种不明显而却十分深刻的变化以外,还带来一种我称之为‘个人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得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却又使这种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大城市中人之相当大一部分,包括那些在公寓楼房里或住宅中安了家的人,都好像进入了一个大旅店,彼此相聚而不相识。这实际上就是以偶然的、临时的接触关系,代替了小型社区中较亲密的、稳定的人际关系。”②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市民叙事策略中以公共空间的移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与个性塑造,就是受这种个人体验的影响。作家不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命运审判者,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只是在城市环境的改变中随波逐流。作家也不再扮演启蒙者或者上帝的角色,而是忠实反映普通市民的情感心态。他们叙事的角度,不管是俯瞰、仰视还是浏览,都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城市生活的角度出发,忠实反映现代市民在都市生活中体验视角的转换。
其次,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带给现代市民某种“震撼”体验,同时也造就了现代市民趋时求新的价值观念。他们更善于接受和认同新兴事物,在叙事策略中也体现出对新型城市空间的敏感与把握。据此,我们可以解释何以 30年代的市民叙事如此热衷于描写现代都市生活,反映在我们看来甚至有点超前的现代市民心态。震惊体验是作家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带有审美技艺型、生命体验性的一种文学经验。30年代上海一举发展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③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2期。。对于大部分脑子里还残存着乡土中国经验的上海都市市民来说,对城市的震撼体验就是城市的空间结构给与他们的震撼。陌生的环境、明亮的霓虹、耸立的高楼、穿梭而过的车流、灯红酒绿的舞厅、喧嚣的赌场……这种空间的建筑以“语言”的形式形成了主体对于城市的基本看法,构建了主体对于城市的基本理解。“震撼体验”质疑和动摇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规则和秩序,乃至最终造成日常生活本身的断裂。这种现代意味的空间形式瓦解了传统中国人的空间感,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市民作家迅速把握到新都市脉搏、热烈都市新生活。他们迅速寻找新的文学形式来反映一个新的时代,不管是放弃线性叙述、进行空间叙事,还是散点描述、视角多变,都是他们努力适应新都市文化的改变。
再次,都市空间的不断延展与对社会文学各方面的巨大影响,使得现代市民作家快速把握到了物质对于文学的意义。这里的“物质”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现代市民叙事中的人际交往,完全不同于乡村社会那种靠血缘、邻里等传统关系,而是以流动的个人身份介入流动性的公共空间。体现出都市人的某些特质:“一是人际间接触的表面性、短暂性,局部性与匿名性;二是人物成分复杂而流动性增强,感情淡漠;三是密集的人群互不相识,作为交换媒介的金钱成为人们交往的衡量标准,更容易见出弥漫于都市社会的拜金主义。”④张鸿声:《新感觉派小说的文化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 4期。在这种情况下,“其后果之一,就是特别强调城市居民生活态度的外部的和物质方面的价值。”⑤伊思·P·瓦特著:《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钧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表现在文本中,作家也倾向于表现物质对于市民精神的影响,进而以物质性的公共空间作为叙事的某种方法与推动力。之前的文学不管是五四文学还是“左翼”写作,都是以意识形态先行的,自上而下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与中国实际社会形态的脱节。30年代现代市民作家则是在都市物质形态改变的基础上,真实反映当时上海都市现实的写作。它是自下而上的、逐步渗透的,所以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人的作品往往刊登在《良友》、《妇人画报》等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中,赢得了巨大的读者群。同时,他们在叙事策略上,也毫不掩饰城市空间、物质生活对他们思想与文字的影响,甚至以某一类物质的描述来暗示这一群体的人物个性。在林微音的《花厅夫人》中,女性的成长过程则成为一系列的城市标志性、符号性空间:“小朱古力店”、国泰电影院、福禄寿饭店、永安公司、福芝饭店、圣爱娜、沧州饭店、open air泳场、惠而康饭店,每移动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阶层,城市以它的空间诱惑促使着市民精神的形成。
三
都市是市民生活的主要环境。都市生活又具有不同层次,包括公共空间、传媒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多方面内容。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和特征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①[法]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不可小觑。市民叙事是一种反映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与思想感情的文学,和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相比,它更重物质,也更加贴近生活。是来自于市民,又以市民为读者对象的文学。从这个意义来讲,从市民生存的空间角度去分析市民叙事的特征,可以有效地揭示市民叙事的独特性,并找到这种独特性的来源。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只是其中一个途径,在都市生活与市民叙事之间,还有很大的意义空间值得开拓。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