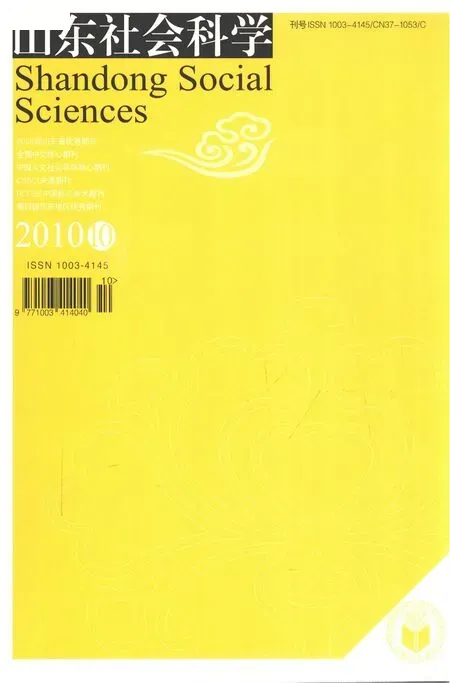新世纪和新世纪的散文精神*
刘若斌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新世纪和新世纪的散文精神*
刘若斌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对底层生存困境与命运悲剧的深沉悲悯,对个体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叩问,对历史长河中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人性深度开掘,构成了新世纪散文精神呈现出的几个新的基本走向。新世纪散文风头正劲且正在酝酿新的精神与艺术变革,我们对此有足够的乐观和期待。当然,在散文呈现出的令人目眩神摇的文体狂欢情境中,创作者还应该坚持住散文的真实品质和自由品格,应该坚持散文的理性思索和诗性追求,更应该葆有悲悯的情怀和坚守住道德的底线。
新世纪;新世纪散文精神;散文
一、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
现代散文从上世纪初诞生以来,与底层社会的血脉关联便从未被割裂过。自鲁迅以降,《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北大的“新潮社”、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萧红、左翼作家群到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他们都用手中的笔为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底层民众发出真诚的歌哭。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迫于种种压力和外在的文化环境,散文创作开始逐渐失去了真实的品格,空洞、浮夸的伪浪漫主义抒情取代了自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情感表达。为最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被艰辛和苦难长久煎熬的底层民众形象淡出了散文家的视野。即便是在文章中出现,也被斗志昂扬行走在金光大道上的“人民”所取代,真实的底层被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几位疾呼“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有良知的作家,很快便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遭到覆灭的命运。此后,散文与底层生存之间的连接纽带被硬生生切断。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文学“真实性”回归的呼唤,一些散文家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作为真实存在的底层,并尝试着将笼罩在底层生存图景之上的伪装揭开,试图在创作中还原其真实的面目。遗憾的是,直到九十年代,这种探索的力度和锐度都依然不够。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底层其实都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二十世纪的某些时段,底层生存曾经一度成为散文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盲区。有良知的作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窘于自保,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对底层的关注。但在当下中国,底层问题以其巨大、尖锐、广泛和峻急使人无法不正视其存在。这是一个民生多艰与骄奢淫逸并存的时代,一些人的歌舞升平伴随的是更多人的生计无望。通过对新世纪十年散文的阅读,我们明显感受到,众多散文作家已经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底层。欧洲人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的良心,尽管鲁迅早就断言,中国向来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新世纪许多描述底层的散文中观察到知识分子良知的觉醒,这是新世纪散文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向度。比起那些在自己的小日子里沉醉,在自己的小得失里烦恼,在自己的小悲欢里沉吟的作家,这些能够将自己的心沉入底层,将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真诚而热切地关注着底层生活的痛苦和艰辛,关注着底层的不幸人生及其人生悲剧性的作家,精神无疑是高尚和高贵的。对生活在底层的那些卑微的生命抱以深深的同情,为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和艰险心灵震颤,为他们生存的苦难而痛苦,为他们生存的权利被漠视和尊严被践踏而呼告。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言说姿态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散文中体现的已不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也不再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唤醒民众的“呐喊”,而是以深沉的关切和理解的态度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从中感受他们在沉默中深埋着的无尽的苦难,感受他们命运遭际中的悲欢离合。
李登建的《短工市》以横截面的方式选取了城市中的短工冒着酷暑等待雇主的一幕场景。这些打短工的人从事的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当雇主把他们带到场地,一见那庞然大物似的沙子车、石子车、石灰车或者煤车,他们简直就像西班牙斗牛场上瞥见舞动的红绸子的公牛……他们恼怒了,疯狂了,咬着牙在烟雾里左冲右突,摸爬滚打。他们痛痛快快地滚一身泥土,又痛痛快快地以汗洗身”,可就是这种令人心悸的繁重劳动,也会引来没有活干的同伴们的眼红和嫉妒,甚至会为了争夺这种劳动的机会付出血的代价。相较于这篇散文,朝阳的《丧乱》对底层苦难的描述则更加令人心酸甚至绝望。文章由作者祖母的去世和丧礼写起,回顾了一位在农村饱受苦难的老人无望的一生:“他们先她而去,集体腰斩了她对人生的希望,她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深渊里。无常的灾难让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不敢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受难,以自己的生命抵抗无法预知的命运,”更可怕的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中苦难在空间上铺天盖地的绵延性和在时间上永无终结的衍生性,以至于作者发出了满怀激愤和不平的控诉和指责:
农村,不但意味着物质的极端匮乏,而且意味着人生没有希望。
城市不但意味着生活得到保障,而且意味着人生的多种可能!
正因为如此,我鄙视一切把农村视作田园的人们,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给予身体的痛苦和重压。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疾,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
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当然,描述底层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不幸的人生或堆砌人生中的苦难,甚至是对苦难的展览。那样便是另一种丧失了真诚的哗众取宠。底层生活需要表现,但同样需要对人世间的芸芸众生报以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同情,需要以清明的理性和深刻的自省意识击穿生活的表象,需要以犀利而锋锐的批判意识揭示世间的不义与不公,需要以灵魂探险的勇气进入人性的深层进行探寻。这其中显现的,才是我们散文中曾经失落太久的大悲悯、大关怀和博大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
应该说,在新世纪的散文中,已经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接近或者已经显示出了这样一种精神质地。贾平凹的《我和刘高兴》记述的是一个漂泊在城市中的拾荒者。作者在亲眼见到他们贫穷匮乏的生活细节,了解到他们无处申诉的痛楚冤情之后,不由自主地做出了这样的换位思考:“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的人和他们受到的种种的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塞壬的《爱着你的苦难》更是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些人的生存之痛和氤氲在作者文字间的深沉辽远的爱与同情。散文以灵动而深情的笔触写到了自己生活在苦难中却毫无自觉意识的弟弟,可贵的是作者将这种爱与同情推向了更为高远的境界。文章中或尖锐或柔软的文字,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平等、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等难道还只是写在纸上因在书中的苍白而空洞的词汇?哪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不会被深深刺痛?哪一个有温情的人又不会因此而悄然动容唏嘘不已?
二、仰望和倾听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对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巨大冲击,物质发达与精神匮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和尖锐。人们处于一种极度浮躁和迷茫的状态之中,为生存而忙碌,为物质而奔波,为外物所奴役。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停下来想一想,在有意回避或者无暇顾及精神的问题,越来越做了物质生活的奴隶。但是,人毕竟是有灵魂的,有意回避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远离。人类生存的痛苦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富而得到解决,反而日益加剧和强烈。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的语境中,依然有人在固执地思考着追问着一些属于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问题,在真诚而严肃地关心着人类的未来和生存前景。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才更幸福?生的意义何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何在?人究竟应该往何处去?而在今天,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中同样有人在发出这样的追问。他们保持一种仰望的姿态,在追问一些终极性和永恒性的问题,将自己的生存之根深扎于大地,在以一种虔敬的态度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感受生命的荣枯轮回。而这种对生存、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灵魂栖息地的守护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主张,更是一种对物欲膨胀而精神衰退的反抗。
王开岭的《仰望:一种精神姿势》是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对人类前景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天问”。他深沉庄严地宣告,“仰望星空”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姿势,更具有美学和宗教性的意义,对人的生存意义深远:“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束信仰仪式。它教会了我迷恋和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人只有恢复到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撑,心灵才能生出竹节的高度与尊严。”可悲的是,这一切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后渐成绝响。
周国平的《走进一座圣殿》则是一位当代思想者拜谒人类先知时与其展开的智慧的碰撞与灵魂的对话。作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对话者:
那个用头脑思考的人是智者,那个用心灵思考的人是诗人,那个用行动思考的人是圣徒。倘若一个人同时用头脑、心灵、行动思考,他很可能是一位先知。
在我的心目中,圣埃克苏佩里就是这样一位先知式的作家。
在对先知精神圣殿的拜谒中,作者的思想与其产生了共鸣。沿着他的指引,作者对人的生命、对人必须面对的精神问题如“爱”与“死亡”、对生命的意义做出了严肃的思考并获得了这样的启示:“我们在大地上扎根,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牵挂、责任和爱。在平时,这一切使我们忘记死亡。在死亡来临时,对这一切的眷恋又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死亡移开,从而使我们超越死亡的恐惧。”“生命的终结诚然可哀,但最令人悲哀的是那本应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竟然也同归于尽”。这些朴素而隽永的启示录式的话语是先哲通过作者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宝藏,可以导引我们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现代社会守住圣洁的灵魂,更可以滋养我们日渐枯竭贫瘠的心田。
当一些创作者以仰望的姿态注视着永恒和终极的时候,另外一些写作者又以倾听的方式在红尘喧嚣中感受生命的轮回,追寻和思考着生命的意义。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作者以安详、宁静的语气述说着自己对生命的顿悟,同时又以决绝的勇气对当下一些时髦的写作提出警示。他在文中对罗兰·巴特提出的“写作的零度”这一概念给予了个人化的解释:“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在这样一种回归“零度”的状态中,作家才得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倾听“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对待写作的态度,更应该是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只有以这样一种朴素、仰慕、静聆甚至柔弱的态度对待写作与生命,才有可能重返生命的“零度”状态,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学者南帆的散文起落无迹,洒脱放达。在《七尺之躯的空间》中,作者以灵动不羁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另一疑难的独特领悟,那就是“七尺之躯”与其生存所需要“空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思路飞扬跳脱而又充满睿智,当然面对这种生命本源性的困境,作者也不可能给予解答,因而才会发出这样的感触:“五官四肢,七尺之躯。东奔西走也罢,梦游八极也罢,突围也罢,守住也罢,我们至今还是不明白,哪一处是我们真正落脚和藏身的空间?如同破译不了时间之谜一样,我们也无法参悟空间的奥秘,”但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已足以促使我们停下忙乱的脚步,和作者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正是因为有人在物欲横流审美理想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一些诸如“生与死”、“爱与孤独”、“幸福与痛苦”、“活着的意义”、“空间与生命”、“时间与永恒”等问题,既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着自己对生命、对永恒的领悟与追问,以诗意的方式守护着精神的高地,这才使得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获得心境的安宁与灵魂的妥贴,散文的艺术张力也从中得以充分显现。
三、拂开历史的烟尘
应该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的首开先河之作。余秋雨语言才华不凡,行文大开大合声情并茂,融怀古幽怨、现实感伤与古典雅趣于一炉,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普及功不可没。但其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则日益缺乏对人、对时代、对现实的深入体察和永恒关注,行文中日益显示出养尊处优的名流派头和令人不堪的自恋情怀。在对政治、对大众的曲意迎合中回避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意识,华丽光鲜的现代包装遮不住陈腐酸臭的现代才子气息。事实上,“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是变幻的,人性却是永恒的;历史是以往的,问题却是当下的。历史散文的素材虽然是陈旧的,但其中应该倾注着全新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视野穿透历史的烟云,透视人性、人生和精神的奥秘。好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中应该不乏天问式的情怀,不乏面对世界和当下的勇气,不乏对一己灵魂拷打的惨痛酷烈。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历史文化散文一度陷入窘境,这与一些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有关。一是作者刻意模仿一些成就突出的作家作品而又见识不够才华不及导致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大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态。文中的叙述不能开合自如地驾驭历史文化知识反而为之所累,从中难以见到创作者的主观情怀;而是缺乏坚定敏锐的现代意识观照,文中也就缺少了深沉的文化反省和灵魂的撞击,见不到对人性、人生和精神问题的独到发现与深刻体察。这样导致的问题便是:一大批为文造情、被历史文化知识喧宾夺主的作品出现,文章看似七宝楼台耀眼夺目,事实上却是拉杂成文满纸饾饤,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思考余地很小,令人读起来目不暇接却又气喘吁吁不得要领。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出自名家之手没有上述弊端,却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名士气、文人气和士大夫气,缺少文化书写、思想书写和知识分子书写的特征。这样,此类散文为人所诟病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以上问题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领域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其中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和精神,一大批有锐气、有见识、有才情的新作问世给历史文化散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对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考察,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和现代文化的吁求,对人性的深沉思考和深层发掘,对传统艺术的整理和吸收,使得这些写作者拂开了历史烟尘的遮蔽,以诗性的文字述说着在历史文化打捞和考察中的新的发现,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思想容量,产生了强烈的审美魅力。
王充闾近年来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涵、人格构成及人性奥秘的解析来探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及其精神问题,表现出对独立自由心灵世界的向往与对扼杀人性、制造奴性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如创作于2002年的《用破一生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散文作者贴着人物的精神状态行文,在历史文化语境还原中揭示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去触摸历史人物的灵魂,得出了切合实际的评断: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作者以全新的现代价值立场为思想坐标去考量历史人物,将历史人物作为活生生的文化标本与人性标本进行剖析,获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新的创造性发现。在对历史人物悲剧性的解读中,显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人性高度,同样也可以启示我们重新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林非对中外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的解读同样建立在鲜明的现代意识之上。一方面,他以文字实现着与历史上那些心志高远、灵魂洁净的志士仁人的心灵对话,向着悠远的历史敞开心扉,寻求知音。《询问司马迁》等散文作品为这些遥想中的历史先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血脉,显露出作者高绝超迈的人生志趣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则对中外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进行着深入而犀利的批判。《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中,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指向强取豪夺、为所欲为,践踏和毁灭美得专职君王,更是对我们曾经历过的那段驱遣人的灵魂、控制人的精神非正常时代的深沉反省。《在卢梭铜像前的思索》言在卢梭,指向的同样是人的精神之路问题。作者曾经被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等理念所震撼和折服,并以此点亮理想的火炬,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走过漫长的精神之路之后,却发现了卢梭精神理念的问题所在,那就是将作为国家和公民领导者的“主权者”理想化了,却忽视了人随着权力的集中相伴而生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性恶的滋生等问题。作者追问道:“难道那些领导者在掌握了庞大的权力之后,一点儿也不会滋生出霸道与贪婪的念头来?况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证措施之后,难道就不会开始走上假公济私和为所欲为的邪路?不会这样一步步地膨胀和堕落下去,成为说一不二和肆意压制别人的独裁者?”应该说,这些追问是对一些美丽却空洞的理念的深刻反思,又是能够被现实中血的教训所证实的至理名言。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优秀的写作者沿着历史回望这一向度做出个人化的思考,并努力透过历史的烟尘探索人类发展的精神之路,并发而为文,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带给我们巨大的思想启发、精神震撼和审美愉悦,这同样是新世纪散文重要的精神走向之一。
四、结语
总体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创作呈现出了新的精神气象和新的质地。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其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随着散文写作对公共视域的开放,散文创作的大众化、普泛化带来的虚假繁荣背后,是散文文体意识的淡化。散文界限的无限扩大,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对创作规律的颠覆和真正散文质地的伤害——散文中充斥的小资或伪小资情调、白领趣味、庸俗精神、市侩嘴脸,散文中显示出种种滥情、矫情、煽情、闲情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再比如散文的个性缺乏和时尚化趋势,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问题。时下林林总总的报纸副刊大都辟有散文专版,但多是一意迎合大众,而懒于思考生活叩问灵魂之作。它们往往落脚于人的欲望宣泄和精神释放,格调平庸,漠视现实,肆意张扬中产阶级趣味和享乐观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场需要的批量生产,而非真正用心灵开采生活。大量散文在现实的多样性和灵魂的复杂性面前“失语”,日渐流露出消费化、快餐化、格式化的倾向和流水线写作的特征。
尽管问题重重,经过对新世纪散文的广泛阅读和披沙拣金式的搜寻,我们依然有理由得出这样的判断:新世纪散文风头正劲且正在酝酿新的精神与艺术变革,我们对此有足够的乐观和期待。当然,在散文呈现出的令人目眩神摇的文体狂欢情境中,创作者还应该坚持住散文的真实品质和自由品格,应该坚持散文的理性思索和诗性追求,更应该葆有悲悯的情怀和坚守住道德的底线,这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艳红)
I26
A
1003—4145[2010]10—0046—05
上世纪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与发展时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蔓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叛徒,有隐士,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①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数量之大,文体品种之丰,风格之绚烂多彩,名家之多,都是异常触目的。以至于连对文学标准要求极为严苛的鲁迅也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上世纪初中国散文发展的盛况。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一晃眼间,近百年的光阴已然过去,新的世纪也已悄然走过了十年,散文是否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质地与新的精神?散文在新世纪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功利主义时代。新世纪以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经出现的问题被延续下来,甚至日渐突出和尖锐,同时,又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许多人的精神世界被物质的沙砾遮蔽,心灵被锈蚀,日益变得冷漠和麻木。一些写作者也愈发丧失了自己的真诚和心灵的自由,内心被世俗的阴霾所笼罩,处于一片精神的灰暗之中。以至于不少研究者对中国的散文产生失望情绪,有的学者甚至预测,散文踏入二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会衰退甚至会消亡。我们认为这种判断不无激愤的片面之词,因为在温暖和抚慰人心、提升和震撼人的心灵方面有其他文体所难以企及之处,有需要其生命自然就会得以延续。而且,据对最近十年散文的考察,我们欣喜地发现,散文的精神命脉并没有断绝,而是在艰难中跋涉前行,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其中孕育着新的转机和新的希望。散文的文体特质,使其在信息时代得到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和博客的流行使得散文写作的全民参与带来了现实可能,散文成为创作数量最丰、作家队伍最为庞大,同时也是最受读者关注的文体。当然,这难免会导致散文质量的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毕竟开拓了散文的题材和主题领域,丰富了其品类和艺术风格。更为可喜的是,即便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有写作者在捍卫着自己精神的高地,呵护着自己道义的洁白,寻找着灵魂的安宁,执着而倔强地用心灵的诗意光芒照亮世俗琐屑的现实生活,以各自的方式直面生命的疑难与生存的困境,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义与不公,发出尖锐的质疑和批判,做出让自己内心宁静的抉择。在各自的探求中他们是孤独的,他们并不生息相通,但在精神和灵魂的最深处他们又是同质的,可以毫无障碍地一呼百应。对底层生存困境与命运悲剧的深沉悲悯,对个体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叩问,对历史长河中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人性深度开掘,构成了新世纪散文精神呈现出的几个新的基本走向。我们这里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十年散文的整体玄览并结合具体文本的解读,来爬梳新世纪散文的精神脉络,借以勾勒我们所置身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指掌图。
2010-06-20
刘若斌(1980-),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经济学院MBA教育中心学员部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