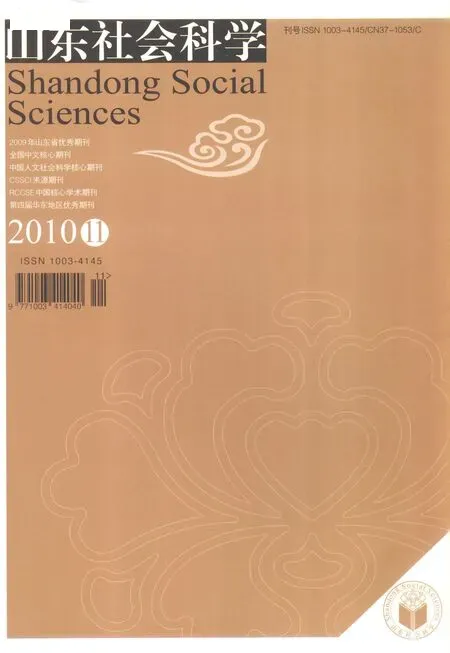《小团圆》: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
张 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小团圆》: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
张 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参差对照”是张爱玲的写作观,这种对照的写法在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中也得到圆满体现。《小团圆》的题目和内容是爱和幻灭的对照,整篇小说都是围绕九莉“万转千回”地寻求爱和一次次爱的破灭写就的。九莉对爱的渴求源于母爱的匮乏,爱的幻灭源于对母爱的幻灭。正是在疏离紧张的母女关系下,九莉才会有自我的分裂和冲突,才会对爱一边呼唤、一边绝望。《小团圆》就是一出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
母女冲突;对照;母爱;幻灭
《小团圆》的解密出版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小团圆》出版的人大多不肯放过这次可以窥探张爱玲生命密码的历史机遇。张爱玲曾说过:小说离人生的距离最近。虽然我们可从张爱玲的诸多作品中瞥见张爱玲的身影,但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一直讳莫如深,像这次如此直白地摹写和剖析实属罕见。而且《小团圆》还引发了一场考据狂潮,从文中可找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位左右的文化名人。但自传体小说又与自传不完全相同。自传据实而写,自传体小说毕竟是小说,虽以事实为蓝本,但其中的虚构、想像、删减、添加、改动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需要设计的,而不完全是作者的真实经历。所以对某些史实只能参考。我更愿意把九莉、蕊秋、邵之雍等人物看做文学形象来解读。
小说的题目是“小团圆”,象征着爱和和谐,内容则是一个接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幻灭。题目和内容互为悖反,是反讽,也是对照。在大陆版《小团圆》的封面上写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张爱玲点出了文章的题旨:这是一个热情和幻灭交织的故事。张爱玲惯用“参差对照”的写法,热情来临时有细细碎碎的怀疑和疏离;当热情幻灭时,也生出枝枝丫丫对爱的不灭渴求。《小团圆》其实是一出张爱玲小说版的“对照记”。小说描写的就是九莉对爱的渴求和爱的幻灭。九莉对爱的渴求源于母爱的匮乏,爱的幻灭源于对母爱的幻灭。正是在疏离紧张的母女关系下,九莉才会有自我的分裂和冲突,才会对爱一边呼唤、一边绝望。
一
在张爱玲作品中俯拾皆是对母爱的质疑和批判:母亲的丑恶、自私和冷漠,是施虐者或施虐的合谋者;女儿则可怜、卑微、被动,毫无抗争能力,是受害者。母女关系是一维的,单向度的。而且母女关系常常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不是主要矛盾。像《小团圆》这样完整地展示了一对母女疏离、紧张、纠结的动态过程的不多。当然《小团圆》是一个长篇,有些矛盾可以有足够的篇幅展开。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小团圆》共283页,母亲蕊秋第22页就出场了,而男主角邵之雍到142页才露面,露面后叙述者仍不时地插播一些九莉童年的故事,母女的故事,九莉与燕山的故事。而且文中最触目惊心的故事不是那段“万转千回”的爱情,而是对母爱的幻灭,母爱的轰然坍塌才是一切幻灭的根本。
在文学和艺术表现中,母爱被神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为配合母爱被神化的叙事策略,母女关系的复杂性也被遮蔽了。其实母女关系远非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单纯神圣。母女之间共生与分离、疏离与亲密、爱与恨、传承与背叛,相对于母子关系反而“更加富于戏剧性”。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不论男孩和女孩都与母亲维持着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生物学上称之为“共生”现象。“共生”是孩子成长初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它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由于母亲是女孩成长的摹本,所以女孩与母亲的共生阶段要长于男孩,所以对女孩来说,母女之间的“共生”尤为重要。然而九莉却觉得她在母亲子宫里时就“一定很窘”。也就是说九莉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与母亲就没有形成“共生”关系。母女之间那种亲密的接触和联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蕊秋出国时九莉才四岁,九莉竟然并不觉得缺少什么,毕竟母亲从未给过她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所以九莉反而把母亲的“缺席”看成了“常态”。母亲不在孩子身边,这种反常对九莉来说太“正常”了。因为从来就没有拥有,也就不存在失去。
蕊秋回国后他们开始过一种现代的生活,连九莉和九林房间的颜色都由自己选择。“九莉拣了深粉红色,隔壁书房漆海绿。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住惯了也还不时的看一眼就又狂喜起来”。①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23页,第80页,第26页,第24页。于是九莉以为现代、美丽、时尚、神秘的母亲就代表着她所向往的新世界,九莉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也让她对母亲充满着爱慕。“从前她母亲到她学校里来,她总是得意非凡”。②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23页,第80页,第26页,第24页。母亲是她的偶像,是她刻意要追求和模仿的。在九莉的回忆中只有童年的调子是轻快的,因为那时她正用全部的热情痴痴地慕恋着母亲。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着可能性。随着九莉生命画卷的一点点展开,生命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九莉对蕊秋的爱也从狂热降到冰点。
“共生”关系的缺乏使九莉和蕊秋都对对方的身体感到陌生,偶有触碰反而都有生理上的厌恶。蕊秋回国后有一次与九莉一起过马路,情理上应该母亲拉起孩子的手,但这件事对母女都是一个难题。蕊秋很犹豫,“一咬牙”方才拉起九莉的手。九莉觉得蕊秋的手“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剎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③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23页,第80页,第26页,第24页。
九莉对蕊秋浪漫的爱由于没有母女和谐共生的烛照本来就脆弱,而蕊秋对九莉的盲视和轻贱最终毁了九莉的爱。对蕊秋来说,九莉是找上门来的推不掉的累赘。蕊秋一直试图缓和九莉与父亲的关系以便把九莉送回去。所以九莉来到母亲家不得不费尽心机去争取母爱,去证明母亲在她身上的投资是值得的。当家中来客人缺椅子时,九莉积极地把小沙发椅推到客厅,精疲力尽地抬头时看到蕊秋惊异得不能相信的脸:“你这是干什么?猪!”对一个处于逆反期的敏感少女来说,她所敬仰的母亲竟然当众斥责她是“猪”,这个图景即使够不上惨烈,也足以让九莉五脏六腑起了震动。随后从小教九莉自立的母亲为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便想把16岁的她嫁掉。九莉开始尝到了母爱的苦涩,她甚至想到了跳楼。
九莉在香港大学时是经济最窘迫的学生。为了避免给母亲要钱,九莉以功课都是全优来争取奖学金。暑假时九莉没有回家的路费,宿舍不能为她一个人开着,只好腆着脸到修道院里蹭住蹭吃。当九莉意外地得到老师安竹斯私下里寄来的800元钱时,她狂喜地连银行都不舍得存。“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一路上“心旌摇摇,飘飘然飞在公共汽车前面,是车头上高插了只彩旗在半空中招展”。④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23页,第80页,第26页,第24页。但那800元钱被母亲一夜豪赌给输掉了。九莉被巨大伤痛整得“木然”无语。这幅图景与曹七巧亲手毁坏女儿的婚姻同样是触目惊心的。姜长安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九莉一回过味来,就明白“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至此,九莉对母爱完全幻灭了。她立志要把母亲花在她身上的钱还上,她和母亲的关系只剩下了一个偿还债务的程序。
地质灾害的破坏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人们的避险措施安排的不合理。在处处高楼大厦的现代社会,一旦有重大地质灾害发生时,有很少的地方可以供人们做应急避难场所,所以一旦地质灾害发生,人们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躲避,这样会使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加重。另外,山区丘陵区因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村庄要么傍山而建,房前屋后形成多级台地,滑坡、崩塌灾害极易发育;村庄要么坐落在沟口洪积扇上,长期遭受暴洪、泥石流的危害,加上农村房屋建筑防震、抗震结构措施不到位,这样更会加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
二
蕊秋和九莉母女关系没有共生和谐,只有疏离紧张。蕊秋期望看到的女儿其实只是蕊秋自我的延伸,这与九莉真实的自我南辕北辙。蕊秋希望九莉是没有好奇心、没有依赖心理,自立、优雅、美丽的淑女。九莉做不到。九莉对家族旧事、对亲戚们的风流韵事充满了好奇,而且一直苦苦寻求母爱的呵护。母爱的严重匮乏使她连对做一个童年时期妈妈家里的“小客人”都心向往之。在母亲面前她得时时留神不露出好奇、依赖的想法。她还得在母亲面前刻苦地学做淑女。这都与她的真实性情、真实自我相背离。
“比起男人对女人的压制,女人之间的自我压抑破坏性更大”。⑤南希·弗莱迪:《我母亲/我自己——女性独立与性意识》,杨宁宁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如果这种压制来自于母亲,那就是一种灾难了。九莉不愿匍匐在后母阴暗的统治下,但亲生母亲同样的凉薄直接摧毁了她的自我完整性。面对母亲的否定、审判、冷漠和厌弃,为生存和自保她不得不“克己”再“复之以礼”。九莉努力做着恭顺、懂事的淑女,尽管蕊秋并不一定满意,然而九莉的内心则翻滚着委屈、愤怒、抗争。九莉的自我是分裂的,内心是不停息地自我冲突,波澜不惊的水面与潜伏其下的波涛汹涌的暗流同时并存,参差对照。
小说中叙述者采用的是限知视角,并非全知视角。叙述者只潜入九莉的内心,揭示九莉内心的分裂和冲突下云蒸霞蔚的心理活动。对他人的行为、话语和心理则全是从九莉的角度揣测的。但是九莉并不等同于叙述者,九莉和叙述者存在着一重对照,但文中叙述的重点显然是九莉行为语言和内心世界的“双声”对照。
蕊秋第一次出现时,母女没有一句直接的对白,叙述者也没有给九莉一句话,全是九莉的心理活动。“九莉没问哪天到的。总有好两天了,问,就像是说早没通知她”。“九莉没问到哪儿去,香港当然是路过。……但是上海还没有成为孤岛之前,蕊秋已经在闹着‘困在这里一动也不能动’。九莉自己也是她泥足的原因之一,现在好容易走成了,欧战,叫她到哪里去呢”?⑥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23页,第80页,第26页,第24页。九莉表面的沉默和内心的澎湃折射出蕊秋的态度。母女异地重逢,没有寻常的亲热和嘘寒问暖。这也似乎太不寻常了。其实母女之间应有的对话都在九莉心里过了一遍。但九莉发现如果她问蕊秋只会自讨没趣、自取其辱。所以九莉的无语是蕊秋强势下的屈从,是她与蕊秋意识冲突的结果,她的沉默同样隐含着蕊秋的意识。
蕊秋暗示比比和九莉不要搞同性恋,九莉始终默然无语,但在心里却对蕊秋的言外之意极为反感。九莉站在母亲面前总像是“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⑦张爱玲:《私语》,《天地》1944年第10期。总是动辄获咎。九莉心想,其实蕊秋自己与三姑的亲密程度才可疑,九莉的舅舅就说他们是同性恋。然而让九莉愤愤不平的是蕊秋“自己的事永远是美丽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想到最坏的方面去”。①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
最初九莉从父亲家里逃到母亲家里时,还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她每次面对蕊秋的无端指责想要分辨时,蕊秋都生气地说“你反正总有个理”。②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九莉明白要想在母亲的屋檐下继续生存,就得知趣,从此不再开口了。当蕊秋想改善九莉与父亲的关系以便能把九莉送回去时,九莉真是出离愤怒,回父亲家意味着九莉所有的追求和梦想都将化为泡影。但九莉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愤怒地叫喊:“二叔怎么会伤我的心?我从来没爱过他。”③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九莉在母亲长期的漠视和打压下,已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沦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她的声音被强势的母亲的声音遮蔽了。即使在九莉心里,蕊秋的声音也像魔咒一样回荡,没有停止。
“蕊秋顿了一顿,方道:‘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我不喜欢你,’句点,”“九莉彷佛隐隐的听见说。”④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
“九莉‘嗳呀’了一声,耳朵里轰然一声巨响,魂飞魄散,知道又要听两车话:‘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还不是这样。’‘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⑤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
蕊秋还没有说话,九莉已经在心里听到了她的责难。九莉在母亲面前总是缩小又缩小,总是不着痕迹地把自己“淡出”。当九莉听说她在母亲的梦里出现时,大为恐慌,像错踏了禁区。九莉是喑哑的,是一个“板板的”“丑小鸭”或者“丑小鹭”。但她的内心却对母亲哪怕一个细微的动作或眼神都涌动着“万转千回”的揣测和回应。自恋的蕊秋只看见她想看到的九莉对自己仰视的爱,对九莉爱的渴求则习焉不察。
蕊秋一说要找个归宿,在这一刹那间九莉就看见了自己安稳悠长、“春日迟迟”的童年。即使永远做一个“小客人”,但有童年的安全感打底,她也神往。她希望母亲不要被罚作“流浪的犹太人”,有一个安稳的家,她可以有空间妥帖地安放彼此的爱。“是蕊秋最恨的倚赖性在作祟。九莉留神不露出满意的神气。平静的接受这消息,其实也不大对,彷佛不认为她是牺牲”。⑥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九莉的内心渴求和母亲的实际意愿完全是两码事。
蕊秋要离开香港了,九莉前去送行。蕊秋没有对输掉九莉的学费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对九莉的暑假做任何安排,在九莉的所有同学都回家时把九莉一人扔在修道院里。蕊秋反而对前来送行的九莉很不耐烦,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不想来送。她微笑站在阶前,等著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⑦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九莉脸在微笑,心却在滴血。她无从辩白,也无从抗拒,只等待着那种伤痛潮水一样地漫上身来。
可以这样说,九莉的所有语言和行为都是察言观色之后的语言和行为,都渗入了他人的意识。她几乎每做一件事都先揣摩蕊秋或者众人的态度,并在内心与蕊秋的意识一番交锋之后才决定。九莉心里一直充斥着不同的声音:真实九莉的委屈和愤怒、母亲的“训话”以及众人的声音,所以人前的九莉是母亲等众人意识拼接、合谋的结果,是九莉在母亲的强势压制下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自我。九莉自我的冲突、分裂和对照反映出九莉漫漫“崎岖”的成长期,“满目荒凉”。
三
《小团圆》的开头、结尾都是“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⑧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这就像一句咒语,一直在文章的上空萦绕。等什么?很显然是死亡。等待死亡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为什么把大考比作死亡?九莉明明门门功课都是优,为什么那么害怕大考?因为大考对九莉意味着不仅仅是考试,还是奖学金,还是生存和尊严。大考带给九莉的是什么?功课的优异在第一年并没有让她申请到奖学金,老师奖励给她的钱却被妈妈一夜豪赌给挥霍掉了。九莉所有优异的大考成绩记录销毁在战火中。九莉“心悸的一刹那”是“一世的功名付之流水”的幻灭。“大考”的死亡意象让九莉从根本上就否定了任何追求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小说中接下来出现的是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⑨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19页,第121页,第34页,第117页,第35页,第40页,第15页,第15页。“你”是谁?是邵之雍?是蕊秋?是他们又不尽是。纵观全文可推论出“你”原本是“爱”。从小没得到爱的抚慰的九莉生生念念的是“爱”。她祈望这种爱,她在遭遇重重幻灭时仍心存侥幸,也许爱的迟迟不来只是因为下雨才阻隔了行程。爱是生命、生机的象征。这两种生和死的意象相伴随着同时出现在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所以这两种“大考”和“下雨”所代表的等待死亡和等待爱的意象对理解本文的作用非同小可。生死意象在文中频繁出现几乎就是张爱玲参差对照的人生观的极端反映。张爱玲一生行走在常人难以企及的边缘,并彼此叛逆,相互作着反证。她的作品也充斥着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诡异精神。
如果母女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没有建立起和谐的共生关系,“我们就会用毕生的时间去寻找这种关系。不幸的是,即使我们后来找到了这种关系,我们也不会相信它”。⑩南希·弗莱迪:《我母亲/我自己——女性独立与性意识》,杨宁宁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这句话是九莉对爱的矛盾态度的哲学注脚。母爱饥渴症使九莉一生都在寻求爱的滋润;另一方面她又从根本上怀疑这种爱的存在。悠长的、乐不抵苦的人生,只是在等待死亡降临。
最初父母的离异给九莉的伤害并不深,倒是爸爸暴打、弟弟的污蔑、韩妈的冷漠让她心寒。但最后辣手摧花的却是她一直浪漫爱着的母亲。母亲的自私、滥情、冷漠、虚荣一点点浇灭了她心头“万转千回”的热情。当九莉的母亲一夜豪赌把她的奖学金全部输掉时,她知道爱已到了尽头。哪怕“万转千回”,结局总是镜中花,水中月。
当有一天蕊秋的风流和风光随着年华黯淡下去时,蕊秋终于意识到亲情比她的风流更奢侈,更昂贵。但这时母女的关系已经无法修补了。蕊秋看到女儿还钱时大哭:“虎毒不食子。”蕊秋明白还钱的潜台词就是母女关系的了结。但即使蕊秋第一次为九莉而哭,即使蕊秋使用亲情拉拢,即使强势的母亲终于示弱,这些都和九莉没有关系了。九莉已在一次次“痛苦之浴”中对母爱绝望了。九莉最终没还钱只是怕硬塞给蕊秋时碰到蕊秋的手,那“横七竖八一把细竹管子”。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母亲温暖、慈爱的手,那是一把刺伤、戳痛人的细竹管。“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从前的事凝成了化石,把她们冻结在里面。九莉可以觉得那灰白色大石头的筋脉,闻得见它粉笔灰的气息”。①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第52页,第283页。对九莉来说,那种伤害已无法修复,凝结成化石,但又新鲜得能让她嗅出伤害的气息,无法遗忘。九莉想“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胜之不武”。然而这种胜利只带给她凄凉的满足和随即而来的逃不掉的悲哀。九莉拒绝神话,根本不相信蕊秋会幡然醒悟,然而“还钱”之举也葬送了母女和解的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九莉悲哀地想:“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②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第52页,第283页。蕊秋在临终时写信来:“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③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第52页,第283页。但九莉没去。爱使她恨得那么深。她既不给蕊秋也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她对母女和解是绝望的。爱的终结是死亡的升腾。
母爱的幻灭是所有幻灭的前景。当九莉在港战中躲避炸弹时,九莉“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她“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④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第52页,第283页。她差点炸死了,她事后心悸不已,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她却无人可诉说。
所以,爱情的幻灭并非是所有幻灭中最惊心动魄的,它只是多米诺骨牌中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已,但的确是最吸引眼球的。然而即使在欢爱的高潮,九莉的心中仍然挥不去阴森森的恐惧;即使爱打上门来,她也怀疑。所以九莉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男人邵之雍和燕山都对婚后单独与她生活在一起不敢想像。除了九莉的遇人不淑外,九莉对爱的怀疑也最终使男人望而却步。即使有了自己骨肉,九莉仍然怀疑自己是否有给与爱的能力,和接纳爱的胸怀。在九莉的世界里,没有爱的传承,只有恨的传递。多年以后九莉在意外怀孕时选择堕胎,因为她从来不想要孩子,她觉得如果她有,那么小孩和她的关系一定也是疏离紧张,“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在九莉似水流年的追忆中,调子是灰暗的,是等待死亡的恐怖。可是虚空与绝望是那样的宽广深厚,没抓没挠。她又本能地恐惧了。她伸手向火,向现实生活取暖,从横绝天地的理性回落到现实。从来不想要孩子的九莉有一次梦见“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⑤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第52页,第283页。
天伦之乐,两性的欢爱,在现实当中,是那样稀薄,以至于九莉对任何爱的可能性都是幻灭的。然而荒凉、孤寂的人生又使她遏制不住对爱生生不息地追求和渴念。她的生命充满了这种生死纠缠、黑白对照。
张爱玲也是在爱的幻灭中走向隐居,在孤寂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她在生命中最后阶段写就的《对照记》中,母亲的照片占了相当的比例,字里行间也诉说出了对母亲的眷恋和赞颂,表达了她对过去和解和回归母体的愿望。《小团圆》写于张爱玲离群索居的时期,至死都在修改。张爱玲本想把它与《对照记》一起发表,但考虑到两者加在一起书太厚,书价太高而作罢。这样本来可作为互文性文本对照阅读的《小团圆》今天才面世。《小团圆》其实是一出母女冲突下的“对照记”。
(责任编辑:艳红)
I206.7
A
1003—4145[2010]11—0171—04
2010-08-20
张 梅(1971-),女,山东龙口人,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