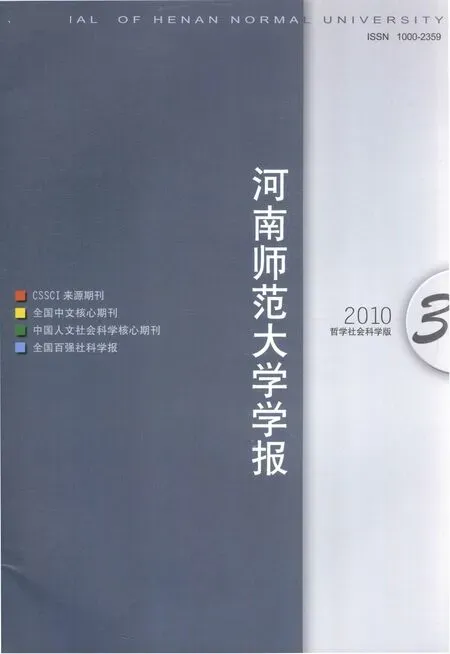女性·民族·历史救赎
——台湾1970年代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女性文学“占位”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女性·民族·历史救赎
——台湾1970年代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女性文学“占位”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乡土文学”成为台湾上世纪70年代文学场域的巨大话语,根本在于其所隐喻的意蕴已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话语形态的意义,直指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台湾社会现实关怀、中西文化对话以及被殖民历史的再审视等多重文化符码。因此,它在事实上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文化立场在内的话语总动员及其力量搏弈,并在相当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文化品格和时代精神。甚至,在随后更为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的角逐中,它以“本土”或“本土化”为表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内涵单一的话语,进而异化为一种封闭、排他和民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后话。
然而,在一个几乎集结了或隐或显的社会各个话语立场的70年代“乡土文学”场域,发韧于1950年代且已经表现出丰富的叙事实践的女性主义文学话语,却难以整合在一个线性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描述或者是“非线性”的社会文化编码之中。换言之,在一个几乎包容了各方不同话语,甚至是互为异己的文化立场的宏大话语场,女性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成为“放逐”与“被放逐”的对象。
我们注意到,关于台湾文学思潮与文学发展的论著,不论是大陆的研究,重要的如《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①参见吕正惠,赵遐秋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还是台湾地区的研究,如《台湾文学史纲》②参见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出版,春晖出版社发行,1991年版)。,以及两岸其他著述,大抵都缺乏了一种视野,一种女性文学话语“在场”的视野。一个有意味的例子:麦田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台湾小说史论》,是由台湾活跃学者邱贵芬组织,陈建忠、应凤凰、邱贵芬、张诵圣、刘亮雅等5名学者共同完成的。邱贵芬在序言中谈道,曾计划“促使一部《台湾女性小说史》问世”,“不过,《台湾女性小说史》计划不久即转化成《台湾小说史》撰述计划。……会议(应该是书稿写作讨论会议,笔者)讨论中,研究群发现要把《台湾女性小说史》独立于《台湾小说史》之外来撰述,有实际的困难,不如调整计划,放手来撰述《台湾小说史》,原先《女性小说史》的结构未纳入的‘乡土文学’断代也因此补回”[1]。这里至少透露出一些颇具玩味的信息:原先计划独立著述“台湾女性小说史”,不论困难与否,进入“乡土文学”时期,女性小说是存在“断代”状况的。那么,这是否可以用以佐证前述笔者以为的女性文学话语于乡土文学中“被缺席”的状态?推而广之,自上世纪末活跃起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批评实践都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书写想象与阐释的话语空间,但往往都对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女性书写语焉不详。也确乎有过努力于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女性文学的描述,如樊洛平教授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一书,专门辟出一编讨论“70年代:民族回归潮流中的女性观照”③参见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对乡土文学语境下具体的女性作家及其文本的讨论,这些著述固然因其“发现”而具有“补白”的意义,但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占位”说,仍不足以回答在70年代“乡土文学”这一巨大话语下女性文学的“占位”问题。而同样有意味的是,邱贵芬由原先的“台湾女性小说史”拓展为“台湾小说史”的写作,至少目的之一是希望“‘乡土文学’断代也因此补回”,但事实上最后成书的《台湾小说史论》,“女性小说”也还是被排斥在“乡土文学:‘压抑’的重返”(《台湾小说史论》第三章第四节标题,笔者)之外。
这一情形,且不管究竟是研究者的无意“发现”还是有意的“疏漏”,我们不妨从这三个方面来给予考察。
第一,女性主义与民族问题。70年代乡土文学及其论争的泛起,直接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台湾社会的现实处境。就其所隐喻的多重话语层而言,民族主义、民族文化立场无疑是其中最为突显的符号。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或者说语义混杂的概念,但它大体上意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的价值观考虑的一种思想状态或运动,还是有其获得认肯的合理性,或者因其“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定为一种包罗性和宏观的政治论述”[2]3而富有极大的社会与政治的号召力。女性主义理论千头万绪,但在根本上,作为一种话语或资源,它所要践行的就是批判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不利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性别秩序,从而建构、维护权力平等和两性和谐的社会秩序。
或许这就是问题的吊诡之处。一方面,女性主义话语的对立面直指那些本质上充满性别歧视的政治文化霸权以及那些直接表现为排斥、压制女性的男权话语;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所被赋予的“至尊”位置及其自身的包罗性,实质上使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男权话语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这也就使它在政治上获得了凌驾于包括性别在内的所有社会意识范畴之上的权力。具体到7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它以“乡土文学”为表征,牵涉到了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并最终引发了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大论战。反映在政治上,它表现为威权统治对“庶民”现实诉求的歪曲和“围剿”,指斥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学”。而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它是坚持民族文化立场、传扬现实主义时代精神与追慕西方文化、逃避社会现实两种意识状态的根本对峙,进而凝聚为民族认同、民族回归的社会主潮。由此,“民族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运作成为了政治的常态模式,而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单位或集体形式。结果,妇女问题(或者是庶民问题)若要被承认为政治问题,就必须用一种限定的民族主义方式加以表达。在这样的压制下,妇女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出路:要么被迫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脱离开来,要么寻求一种建构‘关系——综合政治’的另类方式”[2]3。从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语境下女性话语的“失语”和“缺席”情形看,其实它所能“选择”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妇女问题”实质上已完全被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收编。这恐怕就是问题的所在。而且,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符号的特别突显,因“妇女问题”的“断代”而引发质疑也就没有了理由。
不过,我们在这里“旧话重提”,既在于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性,更在于,因由认识历史的主体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主观性观之,70年代的女性话语不论是被“收编”或曰排斥,都还远不是问题的“终结”。一方面,女性主义话语经由强调男女平等、标示性别差异而指向两性和谐,这一过程则提示出,“女性主义话语”作为一个范畴,随其主体的不断丰富,是可以超逾它最初关注的独特现象,而在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获得张力的。这一点,对于思考70年代女性主义话语于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占位”富有启示。另一方面,70年代女性主义话语的“被言说”与“历史现场”的缝合有无可能。这也就给出了我们随后的考察的“命题”。
第二,女性话语“介入”乡土文学的“策略”。女性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处于不同的甚至表现为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之中,往往造成“历史”对它们共同之处的忽略,这就是它们所共同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社会实践性。回到70年代乡土文学的历史现场,如果说,“乡土叙事”构成了此间民族文化立场的实践性表现的最突显的着陆点,且人们或者耳熟能详或者能够如数家珍地对黄春明、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青矗等一些乡土作家娓娓道来,那么,这似乎能够从一个方面提示出乡土文学语境下女性话语“缺席”的例证。确实,70年代的女性创作并非完全以“乡土叙事”为其重心,其间还兼及“都市”、“流寓”等其他 “游离”于“乡土叙事”这一中心话题的写作;而不论是与同时代男性创作的活跃态势相比较,还是是与之前50年代或之后80年代女性创作的丰富呈现相比较,此间的女性创作,当真颇有些“捉襟见肘”的窘迫。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高度的社会实践性”构成女性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的共同之处这一前提,那么,70年代的女性话语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乡土文学,这倒是值得我们去考究的,它能使人们避免重蹈历史虚无的覆辙。
首先,从所谓的女性文学“谱系”上看,台湾女性文学的葳蕤气象发韧于1950年代,且它从那时候开始便从未缺席过对历史的书写,直至70年代的当下,在本土“坚守”的季季、曾心仪等一些作家与留学海外的丛甦、聂华苓等相呼应,延续着台湾女性书写的流脉;其次,从其间所关怀的视角看,50年代的“乡愁”、60年代的“反叛”、70年代的“现实书写”……恰恰共同映照出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问题”及其诉求;再次,从其处置“自我”的角度看,女性书写从“乡愁”一路走来,表现出了内涵的不断拓展和不断丰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把对70年代女性话语“介入”乡土文学的考察置放在一个“当代”而不是70年代一个“断代”的背景下来进行,并非本文的“疏忽”,从女性主义的话语本身来说,一旦割裂了历史,便有可能忽略其实践性表现的发生和发展的脉络。
女性主义由追求男女平等开始而以双性和谐为指归的整个嬗变过程,事实上已在表明,女性主义的内在构成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即,在其仍然对主流话语霸权及男性话语霸权保持警惕的同时,“妇女实际的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还有妇女根本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同盟者的身份参加由政治家发动的解放运动”[2]3。与此相对应,显然,台湾女性话语对乡土文学的“介入”,也有一个嬗变过程。或者说,从上述的简单勾勒来看,其实践性表现,也恰好印证了女性已经无法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来开展历史救赎这样一个特点与态势。
50年代的台湾困窘而凋敝,这也决定了女性写作的“闺怨”姿态,诚如琦君所言,“生活初定以后,精神上反渐感空虚无依,最好的寄托就是重温旧课,也以日记方式,试习写作,但也只供自己排遣愁怀”①。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这一看似疏离于“反共文学”主流话语的“闺怨”写作,在实质上无不是“借助”女性自我的乡愁经验,述说的是家国罹难的“社会性”集体伤痛。进入60年代,台湾已由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地区开始步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主体不论自觉与否,不论是传统女性书写,还是现代女性书写,抑或是海外留学生的女性书写,共同以其刚刚获得的性别启窦的脆弱,既要依存或质疑于既定的男权历史文化传统,又企望在现实处境、外来文化冲击与家国意识重建这一多重价值理性的逼迫中,“塑造”富含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质的女性自我,使得叙事行为本身在本质目标上更多了一层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历史“承担”。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已经不再有“闺怨”的印记,她们“以同盟者的身份参加由政治家发动的解放运动”。
同样,进入到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语境,女性话语的“介入”,既表现出与历史联结的线性过程,也有其在一个“断代”中的实践性表现形态。
第三,女性叙事与乡土文学的呼应。撕开70年代乡土文学语境下女性话语被民族主义收编的历史缝隙,来找寻女性叙事“在场”的印记,局囿于“民族”这一巨大符码或许是“艰难”的。因为对乡土文学的描述和阐析,出于定势思维,关注点一般集中在“在地”的本土写作这样的主体构成和“乡土”与“社会底层”一类的表现要素上。而70年代的女性叙事恰恰在这些层面有它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在一般论述中语焉不详的原因。其大体表现为“在地”的本土写作与海外的“无根的一代”的写作相呼应,是以作为女性自身的“女性话题”去涵化对“乡土”、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基于我们的思考,从与70年代乡土文学语境有某种意义的关联性来看,我们不妨把在其间相对活跃,且不论是“在地”还是游离在海外,不论是“乡土”还是“都市”叙事的女性作家,归笼起来,大体可以看到这些作家,如聂华苓、陈若曦、谢霜天、施淑青、曾心仪、季季、丛甦、心岱、周梅春、李昂等,以及她们所提供的文本,如《桑青与桃红》、《老人》、《梅村心曲》、《常满姨的一天》、《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苦夏》、《中国人》、《蛇是女人的恋神》、《鹿港故事》等等。国族寓言的想象、与外来文化冲突的对峙、威权现实统治的批判、对“升斗小民”的关怀……所有这些,既是70年代乡土文学指涉的问题与世相,同时也是女性所承受的来自民族历史与“国家”话语对女性的钳制和设障,它们都无不进入了此间女性叙事想象或解构的空间,它们从多元的价值向度突破了民族话语对女性叙事的界定,表现出了女性与乡土/民族的另类关系。
诚然,就70年代乡土文学的“历史现场”而言,相对于此间男性作家以乡土召唤民族认同,或是以关注乡土对底层人生抒发悲悯情怀,或是以乡土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现代病”,甚或直接以民族话语进行呼号以凸显抗争意志,女性的乡土叙事,毋宁更关切自身的性别处境和生存境地。这即是女性话语对民族/乡土介入与呼应的独特性。而且,即便是时至今日主流叙述仍然没有能够给予其应有的关注,也丝毫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体历经了一个不断拓展、不断丰富,不断反思与建构的历史;同样,与“民族”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对话与依存、反思与建构的嬗变过程。因此,它留待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的空间及其价值判断也将是不可限量的。
[1]陈建忠,等.台湾小说史论[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3-6.
[2]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