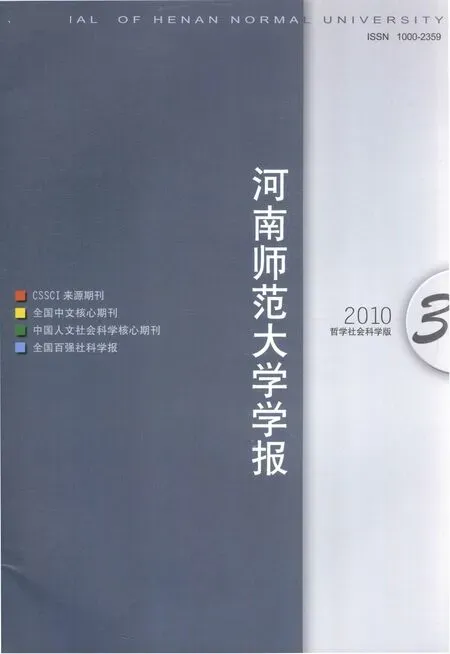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高庆国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河南郑州451191)
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高庆国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河南郑州451191)
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应界定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通信等其他法益的安全”。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对解决刑法中“公共安全”规定的不明确、学理解释的不统一,以及完善立法、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共安全;定性;定量
一、对刑法中“公共安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意义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侵害或威胁不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通信等其他法定权益的安全的行为,例如,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爆炸罪、放火罪等等。新形势下,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因为这类犯罪实际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往往连犯罪分子本人都难以预料,更难以控制,所以,这类犯罪是普通刑事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一旦实施,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而且会造成广大群众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从而防范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有关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现状不利于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重点打击。
(一)完善立法的需要:刑法中对“公共安全”的规定不明确
《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集中对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具体犯罪作了规定,共有12项条文,30种罪名,但相关法条都未对“公共安全”作出详细解释。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规定了放火、决水、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成立犯罪既遂。但对什么是“公共安全”,没有给出详细解释。《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破坏交通工具罪)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规定了破坏交通工具,“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但仍未对“公共安全”作出详细解释。
(二)完善刑法理论的需要:对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学理解释不统一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1]。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安全[2]。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3]。
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比较发现:从定性的角度而言,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把公共安全的内容限定为“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而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的内容不仅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还包括“公共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安全”。可见,第二种观点中公共安全的外延要比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大。从定量的角度而言,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把公共安全的量限定为“不特定多数”,既要不特定,又要多数,“不特定”和“多数”之间是“并且”的关系;而第三种观点都把公共安全的量限定为“不特定或多数”,即既可以不特定,又可以多数,“不特定”和“多数”之间是“或者”的关系。可见,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对公共安全量的限制要比第三种观点多。
(三)指导司法实践的需要:刑法中“公共安全”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给司法者带来的困惑
刑法中“公共安全”规定的不明确和学理解释的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侵害或威胁特定的多数人或不特定的少数人权益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困惑。例如,犯罪嫌疑人甲为报复社会,将一块砖头从天桥上砸下来,刚好砸倒行人张某,致其死亡。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侵害的是不特定的一个人的健康或生命权,因为一块砖头的杀伤力很有限,尽管犯罪嫌疑人甲将一块砖头从天桥上砸向很多行人,但不可能砸死很多人,或砸倒一片。对于这种侵害不特定的一个人的权益是否侵害或威胁到公共安全,司法者对“公共安全”理论理解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坚持“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司法者会把这种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坚持“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安全”的司法者会把这种行为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又如,犯罪嫌疑人甲将被害人张某一家四口骗至郊区一偏僻处,以爆炸的方式将四人杀害。对于这种侵害特定的多数(四个)人的权益是否侵害或威胁到公共安全,司法者对“公共安全”理论理解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坚持“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司法者会把它定性为爆炸罪,坚持“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安全”的司法者会把它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二、对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研究
概括应具有抽象性和全面性。将公共安全的内容限定为“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安全的法益。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过失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刑法规定来看,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和过失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被归类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它们侵害或威胁的不是“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而是“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的安全。基于此,我认为公共安全在定性的时候应概括为“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通信等其他法益的公共安全”。
三、对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量研究
“公共安全”的“公”是形容词,指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跟“私”相对),如公事公办,也指共同的,大家承认的,如公约。“共”指“相同,一样”,如共性;“彼此都具有、使用或承受”,如患难与共;“一起,一齐”如共鸣;“总计,合计”,如总共。“安”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全”指“使完整不缺”[4]。从字面解释看,“公共安全”应指“集体都具有、使用或承受的完整不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可见,“公共安全”具有的“国家或集体”属性,排斥私人属性,即公共安全应是公众的、多数人的安全。
在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量研究方面,目前学者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坚持“不特定多数”,第二种主张“不特定或多数”。两种观点中都提到“多数”。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语言习惯,多数的解释应该是“三人、三次、三项以上(包括本数)”。例如,2005年6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中的‘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推理得知,“少数”指一或二人、次、项。两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特定多数”既要求不特定,又要求多数,把“不特定的少数、特定的多数、特定的少数”排斥在外;而“不特定或多数”包括“不特定的多数、不特定的少数和特定的多数”,仅将“特定的少数”排除在外。
(一)特定的少数人,即特定的一或两个人
例如犯罪嫌疑人甲将被害人张某和李某骗至郊区一偏僻处,以爆炸的方式将张某和李某杀害。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侵害的是特定两个人的生命权,没有侵害或威胁到公共安全,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二)特定的多数人,即特定的三个以上的人,根据具体情况又可细分为特定的多人和特定的很多人
1.特定的多人指特定的三个、四个、五个人等,例如犯罪嫌疑人甲将被害人张某一家四口骗至郊区一偏僻处,以爆炸的方式将四人杀害,本案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较合适。
2.特定的很多人指特定的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等,例如,犯罪嫌疑人甲将被害人张某家族十四人骗至郊区一偏僻处,以爆炸的方式将十四人杀害,本案定性为爆炸罪更合适。因为它侵犯的是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或从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的角度而言,已经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
总之,特定的不是很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或其他利益安全不应视为公共安全,而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或其他利益安全应视为公共安全。特定的多人和特定的很多人的区分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结合刑法规定,又要适应司法实践,既要考虑社会观念、习惯,又要考虑刑法理论。
(三)不特定的少数人,即不特定的一或两个人
例如犯罪嫌疑人甲为报复社会,将一块砖头从天桥上砸下来,刚好砸倒行人张某,致其死亡。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侵害的是不特定的一个人的生命权,因为一块砖头的杀伤力很有限,尽管犯罪嫌疑人甲将一块砖头从天桥上砸向很多行人,但不可能砸死很多人或砸倒一片,没有侵害或威胁到公共安全,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四)不特定的多数人,即不特定的三个以上的人,根据具体情况又可细分为不特定的多人和不特定的很多人
1.不特定的多人。例如犯罪嫌疑人甲为报复社会,将一颗手雷从天桥上扔下来,手雷爆炸后,杀伤半径为两米,当场炸死八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安全,应定性为爆炸罪。
2.不特定的很多人。例如犯罪嫌疑人甲为报复社会,将一个炸药包从天桥上扔下来,炸药包爆炸后,杀伤半径为四米,当场炸死十八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安全,应定性为爆炸罪。
综上所述,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应界定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通信等其他法益的安全”。
[1]高格.刑法学教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2]赵廷光.中国刑法原理:各论分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DF61
A
1000-2359(2010)03-0075-03
中国法学会2008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中国交通犯罪立法完善研究”(D 08050)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