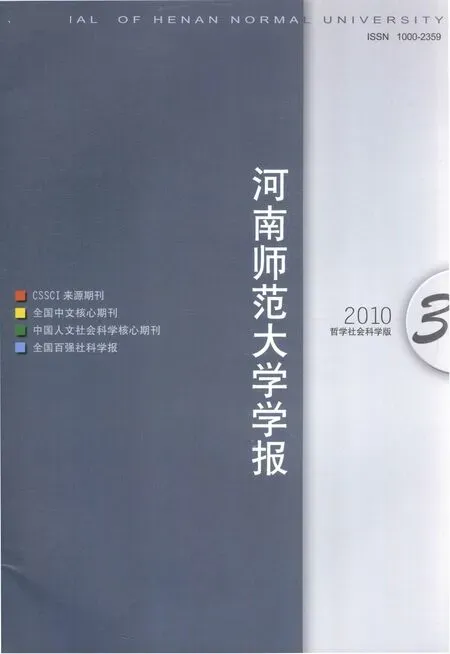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述评
吕晓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述评
吕晓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公平是社会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社会公平感是对社会公平问题进行判断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认知和情绪因素都对公平判断的形成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对公平感心理机制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之争,前者强调人类认知在公平判断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重视情绪、动机等热认知机制对公平判断的影响。在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中,内隐情绪、文化情境差异都将进入关注的视野。
公平感;心理机制;热认知
公平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年的《正义论》中指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实是思想系统的基础。”罗尔斯通过阐述“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基本理论而设计了人们相互奉献福祉、公正、和谐、稳定的理想王国[1]。社会公平也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个体的行为深刻地受到他们是否感知公平的影响,当人们感到公平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积极的亲社会行为[2]。公平的话题充满了组织管理、经济交易、法律政治、婚姻家庭等各个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引起了各学科研究者的普遍兴趣。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出发,对公平感的概念进行阐述,剖析其动因,力图为社会公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一、社会公平感的含义
公平这一概念由来已久,《管子·形势解》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颠;地公平而无私,帮大小莫不载。”意思是天地最大公无私,所以能包涵一切,容纳一切,公平是统治自然和人类的宇宙秩序。唐朝吴兢在《贞观政要·公平》中言:“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指出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在于处事要公平和正直。
西方文化中对公平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正义作为政治秩序的首要品质。正义意味着各个阶级各司其责,每个人安分守己。事实上,在西方语境中,公平(justice)和正义(fairness)通常是交换使用的,前者是指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态度或行为方式,而后者侧重社会中人或物的正当秩序[3]13。
总的说来,公平是一种正当、合理的状态,它不仅表现为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合情合理性,同时也表现为社会成员相处关系中不偏不倚的状态。然而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并且社会成员在诸多先天及后天因素上存在差异性,使得“合情合理”的状态很难达到,人们对“不偏不倚”的评价也呈现差异性。因此,所谓的社会公平,既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可以认为社会公平感就是对社会公平问题进行判断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它基于对社会公平事实“应然”与“实然”状态之间关系的看法。对不同个体(群体)而言,认知经验、价值立场、实际情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社会公平感的差异性。
社会公平的维度问题是这个领域研究的焦点。《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给出社会公平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不应受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二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种福利公平,要求赋予每个人以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较多有关公平维度的实证研究来自组织管理学领域,1965年首先由Adams提出分配公平的概念[4],1975年T hibaut和Walker提出了“程序公平”概念,认为个体在对分配程序获得控制权之后,不论结果如何也能引发公平感[5]。1986年Bies和Moag关注在程序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与公平感的关系,并提出了“互动公平”的概念[6]。事实上互动公平主要体现在人际敏感性和信息共享两方面,因此在Greenberg的研究中前者被命名为互动公平,后者被命名为信息公平[7]。现在学术界一般把社会公平分为三类:发展机遇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权利公平[3]55。
二、社会公平感的认知动力机制
有关公平感形成的心理机制,长期以来存在着理性主义(rationalist)和直觉主义(intuitionist)之争。理性主义强调主要通过认知过程判断公平,这是“冷认知(cold-cognition)”过程,对社会公平事实的判断基于谨慎地评估权衡相关信息。直觉主义者则提出在有些情境中,人们冲动的反应导致快速的公平判断。强调理性认知因素在公平判断过程中作用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经典公平理论
早在1965年,Adams提出公平理论并考察了分配公平感形成的心理过程。这个经典的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投入与获得之比来判断是否受到公平对待,人们通过社会比较获得公平感受。比如两个员工的投入是相同的,其中一个却获得了更满意的回报(高薪,晋升),那么另一个会判断自己的获得不公平。因此他人的获得(与其投入相比较)是个人形成公平感受的重要参照源[8]。
公平理论确实对公平感研究贡献颇大,但对于解释公平感形成的机理尚存不足。首先,该理论仅仅考虑人们获得的经济或物质结果对公平感的影响。其次,它较少地考虑公平感形成过程的影响,也很少涉及不公平待遇反应的决定因素。此外,该理论无力解释和不同参照源比较引发的各种行为类型。
(二)参照认知理论
Folger在1986年提出了参照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体认为有另外一种可能存在的途径可以让其获得更好的回报时,个体的不公平感便加深了。根据参照认知理论,人们通常有三种模拟认知:参照源评估,合理性评估,改进可能评估。首先,参照源是指可选择的、与当前实际不同的决策过程或情境。比如在绩效评估过程中,个体在认为存在另一种评估的方法可能比目前的这种对自己更有利时,便会产生不公平感。将参照源对照当前获得的结果,人们开始想象他们可能会获得的结果是怎样的。不管分配原则中的哪一条被破坏了,只要所发生的并不是应该发生的,就会使人们感到怨恨。其次,在比较现实过程和参照过程时,个体会考虑哪种参照过程比当前过程更公平。如果当前的程序不及参照程序,那么他对目前分配结果的公平感知就是很低的,相反,则有较高的公平感。因此,当现存程序的合理性被认为不及参照程序时,个体便产生强烈不满意感。再次,人们将目前结果视为暂时的,公平感通常受他们所期望的未来结果影响。头脑中出现对未来状态的模拟,是一种对改进可能的评估。当人们期望的前景越来越好时,不公平感程度降低。比如,如果人们相信社会变革会越来越好,那么他们对目前分配的不满意感就会降低,但如果人们没有这种评估,那么目前的不良结果会导致离职,缺勤,以及低的绩效[9]。
(三)公平启发理论
公平启发理论最早由Lind等人提出[10]。该理论认为个体通常会处于一种功能性的两难困境中。一方面,参加一个社会组织能帮助个体实现个人目标,获得安全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对组织权威的屈从会使个体面临被剥削(或丧失身份)的可能。处于两难困境中的个体因此不太能确定他们和权威之间的关系。这种不确定让个体疑惑“当权者是否能被信任”,“当权者是否将无偏地对待自己”,“当权者是否将自己看作群体中合法的一员”。Lind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功能性社会两难的决策是无所不在的,人们也无法计算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影响因素。我们即便想评估这些关系,也得不到全面精确的信息。因此,人们依赖于启发或认知捷径来引导自身行为。比如,我们对前期获得的信息给予更多权重,意味着我们也许受制于最初的公平印象,也许在无法知晓他人所得结果的信息时,会倾向于更多地依赖过程信息进行公平判断。
公平启发理论也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一项对265对主管—员工的调查发现,员工对组织整体的公平感是他们对特定事件公平感与行为反应间的中介因素,对组织整体的公平感是员工行为的一个启发物,即使在某个特定事件中体会不到公平,员工仍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11]。当用以评估公平与否的信息并不突出的时候,个体更多地转向那些显著可得因素来决定其行为方向,比如领导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可信任度)也能成为公平的替代因素,当个体感觉领导人是可信赖的时候,个体便更多地表现出积极行动[12]。公平判断的形成取决于人们易于掌握的信息,比如人际经验、正式规章或程序的特征、成员间的分配方式等都可能引发一个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的整体印象,然后个体会使用这个公平知觉来决定是否依从权威,是否接受妥协,是否信任其他成员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一旦这个公平感判断形成后,个体就会形成认知上拒绝改变的固执,后来的经验和信息将被同化到已经锚定的公平判断中,这样,信息的不全面,便可能导致误入歧途的风险。
(四)公平感发生的连续带模式
经典公平理论、参照认知理论和公平启发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公平感发生的认知心理机制,并且每个模型都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目前的很多研究尝试将三种模型进行整合,以获得更全面的公平感解释框架[13]。尽管所有的模型都认为公平需要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发生机制却不尽相同。我们如果考察包括信息过程的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相关模型,则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公平理论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境。
经典公平理论和参照认知理论提出公平感的判断取决于有意识地评估自身及参照源信息,它是一种控制过程。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认知资源时,这类决策过程是很合适的。然而,当认知资源有限时,个体常常会借助更自动的或启发式的过程进行决策。公平启发理论描绘了这一自动自发的过程。在认知资源的需要发生冲突或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个体作出公平决策的过程与公平启发理论所描绘的一致。1998年Lin d等人的研究发现,当个体与一位新上司交往或与一位不熟悉的人发生冲突时,有关公平的信息显得特别重要。研究者指出对早期相关信息的仔细留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决策形成,它就会被储存并在未来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公平感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14]。
在进行社会公平判断时存在一种连续带模式。一般而言,社会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在进行慎重决策时,人们的判断过程从一种纯理性的系统方式变化为迅速而自动的方式,也就是说从深思熟虑的思考变化为依赖即得信息作出判断。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公平感理论恰恰处在这一连续带的不同位置。
三、社会公平感的情感动力机制
社会公平感的判断是一种特殊的决策过程,公平与否是个体判断决策的结果,而决策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情绪、直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人们对事件是否公平的判断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当前事件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是先体验后判断。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人们很少计算公平,而是体验一种和公平相关的情感,并对此作出反应,有理由相信识别和明确社会公平中情感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公平判断的主观和直觉的特征。
(一)情绪即信息理论(Affect as information)
情绪即信息理论由Schwarz和Clore(1983,1988)提出,该模型假设,“人们不是基于任务特征进行判断,而代之以询问自己:‘我感觉如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将先前的情绪状态误认为自己对当前情境的反应”。AA I运用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途径,用自己的感受作为判断的标准[15]。在社会公平的判断中,情绪同样对公平推断发生作用,但作用方式取决于情境特征。
(二)模糊信息下的情绪替代
在形成公平判断的过程中,人们倾向于自己先寻求与特定情境最相关的公平信息。毫无疑问,人类对相关情境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Van等人提出的不确定管理模型(Uncertainty Management Mod-el)预言,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境中,人们尝试借助其他信息——就像启发式替代——来判断公平[16]。
在分配公平的判断中,人们往往通过社会比较,对自己与他人的投入和获得进行比较,经典公平理论假设人们是很清楚自己与他人的投入与回报状况的,事实上这很难衡量。人们会面对四种不同的分配结果:和他人一样,比他人好,比他人差,不知道他人的获得。对于前三种情况的公平判断,被试者主要依赖社会比较的信息,而在最后一种情况(不知道他人的获得)中,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者比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者判断结果更公平,也就是说在分配结果信息不明朗的情况下,被试者更多依赖自身的情绪线索来判断结果的公平性[17]。
在判断特定程序是否公平时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话语权(voice),当有机会在决策过程中表达观点的时候,人们通常体验到公平感,而在没有发言机会时就会觉得不公平。在明确的有话语或明确的无话语情境中,人们依赖程序的这一特征进行公平判断。而当人们不清楚自己会被如何对待时,即不向对象挑明是否有话语权时,人们通常借助自身情绪进行公平判断,处于积极情绪中的被试者认为程序更公平[17]。
(三)模糊信息下的他人情绪
决策情境的不确定和模糊性促进个人寻求更多信息以增加判断的确定性,DeCremer在研究中发现在模糊的决策程序中,人们会受其他人情绪的影响。在一个信息不确定的情境中,当其他人表现出生气时,被试者就更确信拒绝他发言的权威人物是不公平的。而当其他人表现为内疚时,被试者会认为领导并不是那么不公,而他们自己的消极情绪(生气)程度会低一些[18]。近年来的移情研究发现:移情被认为是在个人身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心理品质,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以及分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19]。在个人寻求判断社会公平的信息过程中,他人情绪状态成为一个推断的输入因素,从认知上将它作为判断的信息依据,而在情感体验上,个体也分享了他人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这些情绪成为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替代,从而引发公平或不公平感。
(四)社会公平感的热认知机制
情绪曾被认为是狂乱的、无法控制的力量,传统的判断与决策研究一直回避着情绪和其他主观因素对判断决策的影响。不过事过境迁,近年来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情绪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建设性作用,情绪可以发动、干涉、组织或破坏认知过程和行为,认识到对事物的评价可以发动、转移或改变情绪反应和体验[20]。公平感源于对社会事件的判断与评价,社会判断是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平判断必然深受情绪因素的影响。正如林文瑞指出的,社会判断具有感情性,判断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联想[21]。意识之外加工的环境刺激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之前注重理性因素的“冷认知”概念,目前“热认知”的研究更受关注。所谓热认知是一种积极的推理判断现象,其中个体对刺激的情绪(或动机)作用非常显著。由此可见,社会公平感的形成恰恰是理性认知和情绪、动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认为热认知机制更能全面地反映公平感形成的过程。
四、研究展望
(一)考察情境因素对热认知机制的影响
在肯定公平感的热认知机制基础上,认知因素和情绪、动机因素共同作用于公平判断的过程,那么认知因素和情绪动机因素的作用会不会因为判断情境的变化而不同呢?在Van之前的研究中,信息不确定成为一个中介调节因素,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情绪作用显著,那么动机因素是否会有类似的表现呢?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情境特征充当中介因素?张静在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观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的公正观是情境性的,情境主义的公正观是关系导向的[23]。这也使我们对关系框架是否会影响公平判断的形成机制发生浓厚兴趣。
(二)比较各类情绪的功能
在情绪与认知以及情绪与决策关系的实验研究中,通常采用D.Watson和A.Tellegen的情绪两因素模型,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维度[23],不过现实中人类情绪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未来研究将更关注细化的各类情绪在公平判断中的作用表现。
(三)揭示内隐情绪的作用
人们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近年来无意识认知(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和内隐认知(在不注意状态下发生)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关情绪是否可以是内隐的话题值得重新思考。已有一些证据支持内隐情绪的存在,Monahan、Murphy和Zajonc在研究中发现对纯粹暴露的潜意识感应效应,就是对重复出现的项目有更积极的反应。在无意识中重复接触一些中立刺激的被试者比没有重复接触的被试者声称他们的情绪状态更好[24]。紧接着的问题是内隐情绪是否有足够强度影响行为。Berridge和Winkielman通过实验发现被试者无意识接触的一些表情能引起情绪反应,这种反应改变了被试者的消费行为[25]。那么,内隐情绪在社会公平判断的过程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令人期待的。
(四)描述跨文化视角中的公平感
民族文化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对事件的判断,社会判断是具有全球化和中国化双翼的课题[26],描述跨文化视野中的社会公平判断显然是这个课题的重要内容。早期的跨文化公平研究主要讨论东西方的分配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公平感,比较丰富的实证研究聚集在组织公平领域,考察民族文化因素在组织公平感与员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过结果是复杂的[27]。有关文化因素是否影响了人们的公平感知,影响公平判断形成的心理机制,此类研究尚不多见。因而社会公平感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这个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2]Jan-Willem van Prooijen,Kees van den Bos,et al.How do people react to negative procedures?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hority’s biased attitud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2006,42(5):632-645.
[3]汪行福.社会公正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3.
[4]Deutsch,M.Equity,equality,and need: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5,31(3):137-149.
[5]Thibaut,J &Walker,L.Procedural justice:A psychological analysis.Hillsdale[M].NJ:Erlbaum.1975.
[6]Bies,R J &Moag,J F.Interactional justice: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J].Research on negotiations in organizations.1986(1):43-55.
[7]Greenberg,J.Stealing in the name of justice:Inform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moderator of theft reactions to underpayment inequity[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3,54(1):81-103.
[8]Adams,J S.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J].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3,67(10):422-436.
[9]Folger,R..Rethinking equity theory:A referent cognition model[M].Justice in social relations.New York:Plenum.1986:145-162.
[10]Lind E A,Kray L J,Thompson L.Primacy effects in justice judgments:Testing predictions from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2001,5(2):189-210.
[11]Choi,Jaepil.Event justice perceptions and employees’reactions:Perceptions of social entity justice as a moderato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8,93(3):513-528.
[12]Dan S Chiaburu,Audrey S Lim.Manager trustworthiness or interactional justice?Predicting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3(3):453-467.
[13]Russell C,Zinta S B,et al.Moral Virtues,Fairness Heuristics,Social Entities,and Other Denize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1,58(2):164-209.
[14]Lind,E A,Kray,L,Thompson,L.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justice:Fairness judgments in response to own and others’unfair treatment by authorities[J].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1998,75(1):1-22.
[15]庄锦英.情绪影响决策内隐认知机制的实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16]Kees van den Bos,E.Allan Lind,Uncertainty management by means of fairness judgment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2:34.
[17]Kees van den Bos.On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social justice:The role of affect as inform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justice judgm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3):482-498.
[18]De Cremer,D,Wubben,M J J Drs &Brebels,L.When unfair treatment leads to anger:The effects of other people’s emotions and ambiguous unfair procedures[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8,38(10):2518-2549.
[19]刘俊升,周颖.移情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概述[J].心理科学,2008,31(4):917-921.
[20]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21]林文瑞.社会判断的深层内在性[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3):60-61.
[22]张静.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9.
[23]张卫东,刁静,Constance J Schick.正、负性情绪的跨文化心理测量:PANAS维度结构检验[J].心理科学,2004,27(1):77-79.
[24]Monahan,J L Murphy,S T &Zajonc,R B.Subliminal mere exposure:Specific,general,and diffuse effects[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0(11):462-466.
[25]Piotr Winkielman&Kent C Berridge.Unconscious emotion[J].Current Direction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4,13(3):120-123.
[26]李朝旭.社会判断的内隐和外显过程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7]Tae-Yeol Kim,Kwok Leung.Forming and reacting to overall faireness: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2007(104):83-95. [责任编辑 张家鹿]
B842.2
A
1000-2359(2010)03-0027-05
吕晓俊(1973-),女,江苏苏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CSH027)
201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