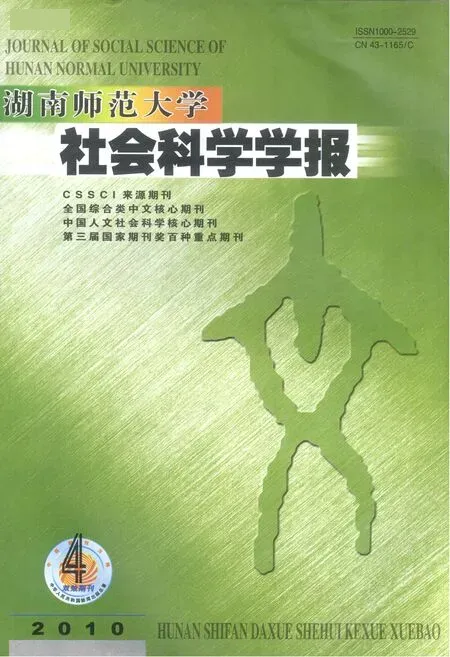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张金荣
(中南大学 政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张金荣
(中南大学 政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近代西学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备至,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期间,近代西学在中国的失落又促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播;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选择机制,被中国先进分子理解、接受、信仰和发展的,是一批中国先进分子本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念,努力向西方寻求的最佳思想武器。这其中,西学的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近代西学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但不久因中外各种原因而被迫中止。西学再次传入中国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西学东渐的主体,早期是外国传教士,之后是清政府出使各国的外交官员和随从翻译,以及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和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再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是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
自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出使西方各国的外交官员或随从翻译,以及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与国内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向国内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同时,也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如崇厚、高从望、张德彝、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王韬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期间正值巴黎革命爆发和巴黎公社建立,崇厚将他所见载入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目睹情况写成《三述奇·随使法国记》一书。稍后,王韬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此外,高从望撰写了《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了《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了《使德日记》,汪凤藻翻译了《富国策》,这些书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介绍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如把巴黎公社起义人员称为“乱民”、“叛勇”,高从望甚至直呼公社战士为“匪类”,《中国教会新报》也称之为“贼党”,但这毕竟让中国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立宪政体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遂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康有为1894年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经多次修补,后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康有为为完成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进一步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定贡献。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改良派代表,1902年起,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马克思及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直言不讳地讲:“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骤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1]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林云垓、陈炯明、李人杰、徐苏中、沈仲九等人,也更加关注社会主义。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还在马克思的名下列举了五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为恩格斯所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2]。孙中山于1905年至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样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富强。孙中山坦言:“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3](P339)
中国在海外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先后形成两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新世纪》杂志。他们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正如吴雁南等人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辛亥革命前各类报刊中,不仅介绍数量多,论述也有精到之处”[4](P405)。1911 年 7 月 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推举江亢虎为部长。中国社会党成立后,江亢虎和社会党其他骨干成员,如陈翼龙、沙淦等人有组织、有刊物地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说服中国人民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甚至大肆批评“马氏学说之弊”,但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述各群体在传播近代西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5],尽管他们的目的大相径庭,传播环境也有所差别,但是,他们使马克思主义由附带的、零星的传入,到较为广泛地介绍,至五四时期成为重要社会思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近代西学东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研究甚至推崇过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很有代表性。
李大钊于清末民国初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经主攻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和经济学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并对之深信不疑。1913年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该校政治经济科一、二年级的课程表中包括国家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英文、哲学、第二外国语、政治学史、财政学、统计学等。而且该校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这些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为李大钊日后的思想变迁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主要受到英国功利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法国学术思想涉及不多。但他对法国的柏格森哲学却予以特别的关注,并接受了他的一些哲学观点来建构其早期哲学体系。如李大钊把柏格森的“绵延”说用来作为反对封建复古论的武器;研究柏格森的“直觉”说,倡导国民个性的充分发展;阐释柏格森“变的哲学”,得出社会改造是合理的结论;剖析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宿命论。[6]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法国学术思想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对法国学术史上进步观念演进轨迹及其唯物史观形成的贡献有重要的评述。
李大钊崇尚西方的自由理论。在他看来,自由是西方文明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公民行使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李大钊不仅接受了卢梭、鲍桑魁和穆勒等人的自由理论,而且还有所发挥。他转述穆勒之语:“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不独专制政府其行此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无有是。”[7](P159)穆勒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个人的自由问题,认为个人是自由的主体,言论自由则是个人自由的首要前提,个性的发展和完善是自由的目的。李大钊认为穆勒对自由的论述是“透宗之旨”。只有遵照穆勒的自由理论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度,特别是要尊重民众的思想自由,中国才能成为立宪之国。
李大钊到日本后不久就接受了托尔斯泰的“群众之意志”的“累积”是“历史上事件之因缘”的看法,并将其同自由主义观念融会在一起,探讨了“民彝”,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民彝”政治观念。李大钊进一步把卢梭“契约论”的平等精神和穆勒的自由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民彝”为出发点和价值尺度,以代议制为形式,以自由、平等为其精神,即“民彝”与国法之间愈益疏通为目标的民主观。同时,他称赞托尔斯泰“唱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是“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7](P174)。希望人伦关系达到普遍的爱,甚至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7](P180)
李大钊对西方民主精神的接纳,既表现出引进西方文明的开放心态,又表现出很强的民族心理选择机制。这奠定了他民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世家,十七岁中了秀才。1898年,陈独秀考入杭州求是书院,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还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之前,陈独秀曾三次东渡,留学日本,广泛地接触并学习研究西方各种思想学说。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道:“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8](P174-175)对于每个国度,陈独秀首先提到的都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科学家,如法国是哲学家卢梭和科学家巴士特(今译巴斯德);德国是哲学家康德和科学家赫克尔(今译海克尔);英国是哲学家倍根(今译培根)和科学家达尔文。这足见陈独秀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广泛与深入。陈独秀的早期宪政思想,以法国的民主主义为基调,其中亦杂糅了英、美等国的自由宪政思想。陈独秀关于民主的大部分观念沿袭了卢梭的“主权在民”学说,而他以个人主义阐释的人权观念和有关法治的一些主张,实际上更多地源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
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他以《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浓墨重彩地颂扬法国文明,还选译了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和同样是法国人的Max O’Rell的《妇人观》;在《青年杂志》的第三、第四期《世界说苑》栏目中登载了李亦民编译的《法兰西人之特性》。在陈独秀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类似“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9]这样的文字。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把他认为足以代表“近代文明之特征”的三件大事——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都归功于法国。他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8](P81)在他的笔下,法国不仅对近代文明有其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就连法国人的国民性也远非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所能比拟。“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弊也失进步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弊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二者之间,为可矜式。”[8](P129)对比德、英两民族而独独推崇法国人。“从陈独秀所受法国影响的来源看,即有来自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因素;又有来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因素;他还受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10]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领导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取自近代西方,尤其受到了来自法国的重大影响。由于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迫切地要为中国的问题找到快捷的解决方法,这促使陈独秀思想上经历了急剧变化,即从一个倡导“人权”的自由主义启蒙者,一变而为高举“民主”旗帜的民主主义者,再变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毛泽东同样具有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国史地、古典文学。在对西方文化的求索中,毛泽东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他回忆说:“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斯·密勒)所著的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11](P37)毛泽东回忆中谈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书,都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课程由杨昌济采用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课本。该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阅读时写了12万字的批语,这就是《〈伦理学原理〉批注》。当时杨昌济翻译的由日本人所写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毛泽东将其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一师毕业之后的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潮。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12](P479)这三大哲学家即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英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毛泽东自觉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为他日后改造、融合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日后没有出洋,却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备至,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前提。
三、近代西学在中国的失落促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在崇尚西学,宣传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盲从,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持有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8](P80)李大钊对民国建立以后的政治局面始终是不满意的,这就促使他去探求理想的民主政治,于是,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政治设想和方案。在李大钊的构思中,最适宜之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7](P149)。尽管“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7](P158)。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2](P86)。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成份,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前途的认识,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其他论者一样,首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维护世界人道公理的战争,是反对暴力的正义、和平、公理的战争。在《威尔逊与平和》中,他说:“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7](P268)从而表达了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陈独秀曾真诚地欢呼协约国方面的胜利,他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表达了这种“公理战胜强权”的欣喜之情,并真诚地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8](P304)。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李大钊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中,有如下的论述:“方今世界各国,罔不投于战争漩涡之中,一时军事内阁之成,自为其应有之象。顾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昙华幻现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也。吾人挟此最有势力之世界潮流以临吾政府,武断政治之运命将不摧而自倒。”[7](P280)坚信“平民政治之精神”将会代替“武断政治”而成为“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这正是李大钊观察、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出发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李大钊对国际政治和民主主义运动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对俄国二月革命后形势的发展格外关注,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一系列文章,促使他后来能够在国内较早地关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认为,俄国二月革命“由内政言之,则实自由政治之曙光”[13](P1),意味着“平民政治之精神”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在此意义上,他又在《庶民的胜利》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看成是相对于“大……主义”(专制的隐语)和“资本主义”而言的“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此后,其论著中就反复出现“平民政治之精神”(平民主义)的主题,这促使他较快地接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当巴黎和会中中国主权和利益被包括法国在内的列强所出卖之时,陈独秀发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8](P397)他心目中几近完美的法国形象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写道:“法兰西国民,向来很有高远的理想,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正是一个反对。现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执政的多是社会党,很提倡缩减军备主义。而法兰西却反来附和日本、意大利,为着征兵废止、国际联盟、军备缩小等问题,和英美反对……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8](P358)其实,他在 1918 年初就已经看到:“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8](P254)此时,随着“巴黎和会”所引起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和“五四运动”的开始,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俄罗斯,投向了这一 20 世纪“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8](P381),并由此开始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不可否认,近代西学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近代西学东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近代西学的传播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这种启蒙作用不能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之后抛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认为可有可无,实际上这种启蒙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日后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解、应用的质量。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经历了器物——制度——观念由表层到深层的过程。就在高举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与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中国先进分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失望之余,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民族国家的希望,时代的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梁启超.秘密结社之机关报纸[J].新民丛报(38,39合刊),1903-10-04.
[2]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1),1903-02-04.
[3]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卷[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4]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5]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63.
[6]吴汉全.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法国学术思想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87-88.
[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
[9]陈独秀.陈独秀答一民[J].《新青年》2卷 3号,1916-11-01.
[10]韦 莹.陈独秀早期思想与法兰西文明[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94.
[11][美]埃德加·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汪 衡译)[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1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1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彭大成)
Promoting Effect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 on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ZHANG Jin-rong
(School of Polit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There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brought Marxism to China.Chinese advanced elements did in-depth research on and even highly praised modern western culture,which laid a cultural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acceptance of Marxism.However,during World War I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the loss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made the advanced elements choose Marxism.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Marxism;spread;effect
A81
A
1000-2529(2010)04-0027-04
2010-04-05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三次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比较研究”[07YBB028]
张金荣(1960-),女,河北平泉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