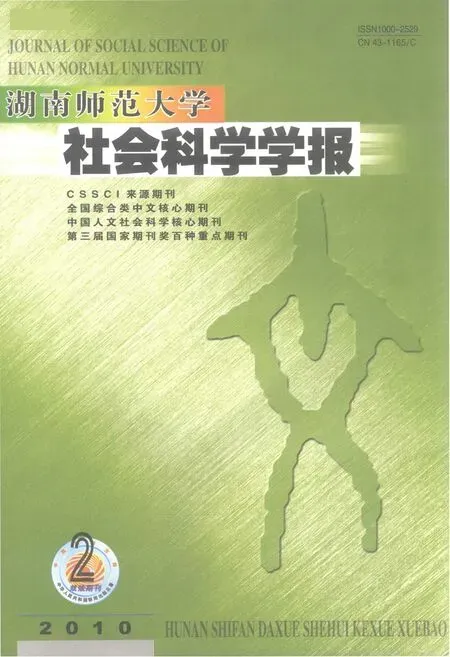宋人的词体审美观念之重新审视——美学视阈中的宋词形态研究之一
沈家庄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宋人的词体审美观念之重新审视
——美学视阈中的宋词形态研究之一
沈家庄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本色”与“骚雅”,是宋人关于词体审美的一对重要形态。北宋人讲究词的“本色”,南宋人强调词要“骚雅”。这既是时代风气使然,又是宋词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它既反映出中国文学审美内涵的丰富性和审美品味的多样性,又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流变与承传的恒定性。
宋词;审美形态;婉媚;自然;本色;骚雅
本文所论及的有关宋人对宋词审美观念的见解,其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宋人有关词体审美的论述(其中主要是宋代词话)。宋词虽号称宋代“一代之文学”,但专门论词的宋代人著作大致都集中在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所收词话12种。其中惟杨《古今词话》一种以“词话”命名,其他11种(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阳居士《复雅歌词》、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词话》、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张侃《拙轩词话》、魏庆之《魏庆之词话》、黄升《中兴词话》、周密《浩然斋词话》、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原始版本出处较复杂。如《碧鸡漫志》与《词源》相应完整且独立成篇,可以视为《词话》著作;《能改斋词话》、《苕溪渔隐词话》和《魏庆之词话》分别从《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和《诗人玉屑》的《诗馀》节出,称为“词话”也未尝不可;但《拙轩词话》辑于作者文集《拙轩集》,《中兴词话》附于《诗人玉屑》之后,《复雅歌词》与《时贤本事曲子集》乃失传久远、一鳞半爪的遗存文本,由后人从不同的著作收录——即便如此,梁启超先生仍认为《时贤本事曲子集》原本“具录原曲全文,实是最古之宋词总集……且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1](P10-11)又鉴于宋代谈词的“话”或“论”相对不多,所以本文在讨论“宋人词体审美观念”这个论题时,是将宋人笔记、文集及宋代诗话等涉及到词的论述以及少数与词话内容相近的宋人词集序跋等,纳入宋人文本遗存系统进行考察的。当然,为了论述清楚,文中亦涉及明清时期的有关词话理论。
宋人在词的审美方面提出了众多概念。最为常见的有:婉媚、婉美、婉约、软媚、妩媚、柔媚、柔婉、清婉、纤柔、纤艳、柔丽、艳丽、绚丽、侧艳、浮艳、淫艳、世俗、俚俗、自然、本色、高妙、俊逸、旷达、横放杰出、豪放、古雅峭拔、高雅、高古、骚雅、雅淡、雅正、浑厚和雅、清劲、格力、清空等。以上审美概念与司空图《诗品》中列举的二十四种诗学审美概念比较,其中“豪放”、“旷达”、“自然”、“高古”字面完全相同,“纤艳”与“艳”、“横放杰出”“浑厚和雅”与“雄浑”、“骚雅”“雅正”与“典雅”、“绚丽”与“绮丽”意思和字面都比较接近外,其他大都是宋代词话提出的新的概念。事实上,在以上众多概念中,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组:
与《二十四诗品》及前人诗论、诗话比较,第一组和第二组中所出现的新概念(如婉媚、软媚、柔媚、纤艳、柔丽、艳丽、侧艳、浮艳、俚俗、本色)要比第三组和第四组多。这就说明三、四组的审美概念基本上是承续传统诗学审美标准。而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审美概念中,有不少是代表了对当时新文体——词的新的审美认知。我们再稍作分辨,又可以发现这四组概念中每一组概念的审美内涵十分接近,几乎形成四个不同的审美形态。明代人张在做《诗馀图谱》的时候,就将宋词风格归为两大类:一曰婉约,一曰豪放。宋词的这两大风格,实际上也就标出了宋词的两大审美形态。我们说“婉约”作为一个审美形态代表第一组的诸多概念,“豪放”则代表第三组的诸多概念,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张
1.婉媚、婉美、婉约、软媚、妩媚、柔媚、柔婉、清婉、纤柔、纤艳、柔丽、艳丽、绚丽、侧艳、浮艳、淫艳
2.世俗、俚俗、自然、本色
3.高妙、俊逸、旷达、横放杰出、豪放、格力
4.高古、古雅峭拔、高雅、骚雅、雅淡、雅正、浑厚和雅、清劲、清空的“婉约”“豪放”说,风靡词坛数百年,至今虽有不少专家提出质疑,但词学界与文学史一般尚维持张氏成说。
细究起来,惟将“婉约”“豪放”作为宋词独具的两大审美形态,诚然有许多可议之处。“婉约”一词,作为语辞,较早出现在《国语》卷十九《吴语》①;刘勰《文心雕龙》所谓“经文婉约”,②首次用来评价文章形式特征;后来徐陵《玉台新咏序》则是首次用“婉约”谈及诗歌风格③。至于用来品评词风,在宋代词话中首见许《彦周诗话》:“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2](P381)许氏好以“婉约”评诗,如说“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便是一例。[2](P391)“婉约”概念与第一组诸多概念的最大不同,在一“约”字。“约”者,节省也,含蓄也,内敛也。作为诗学审美概念,就是以少胜多,隐秀含蓄。用它评温飞卿词或《花间集》中某些词作还行,评秦观已十分勉强,若评晏几道、黄庭坚、周邦彦、吴文英,特别是柳永,就大谬不然了。所以说,“婉约”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不能起到统领第一组诸多概念的作用。“婉媚”与“侧艳”倒是更能代表第一组的美学意味。至于“豪放”与第三组其他概念相比,尽管与之相近或相似的概念有一些,但却不是词体所专有的审美概念,尽管早在《二十四诗品》中,“豪放”就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诗学审美形态提出,但宋人用“豪放”来品评词人词作的却很寥寥。倒是第四组“骚雅”或“雅正”庶几能拢括宋人论宋词的多数概念。张炎《词源》特标“骚雅”作为反对“浮艳”的美学标准,沈义父《乐府指迷》推举“雅正”作为抗衡“市井语”的审美圭臬,不但代表了一种美学风潮,而且建树起了一套有影响的词学价值体系。同时,我们从二人标举的这两个审美范畴的反面可以了解到宋人心目中对词的另外两个审美概念的体认:“浮艳”与“市井语”。“浮艳”属于第一组;“市井语”即“世俗”“俚俗”,属于第二组。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组合。因为“浮艳”与“市井”在美学范畴上都属于“俗”。事实上,按照美学意义衡量,“婉媚”和“侧艳”接近于“俗”的价值标准,而“婉约”则更接近于“雅”。也就是说,若把“婉约”作为一种宋词的审美形态来认识,它是缺乏代表性的。说宋词“婉”尚可,说宋词“约”就没根蒂了,因为多数宋词铺叙直陈,抒情坦露,并不含蓄,而“媚”和“艳”却能凸现大多数宋词的美学风范。
这令人想到一个大家熟悉的宋人评价宋词的概念:本色。如果人们稍稍留意一下上文所论列的关于宋词的审美概念,会发现那多是南宋人的评价,而很少北宋人的意见。恰巧“本色”一词,作为词体的审美话语,是北宋人首先提出,并几乎成为宋词审美评价的实质性标准。以“本色”论词,首见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3](P309)历代治宋词学者一般也注意到了陈氏这段话的特殊意义,但以往的研究多着意于苏轼是否“以诗为词”及其“以诗为词”的意义,或讨论苏轼词“是本色”还是“非本色”,对于“本色”这概念的诠释也只是停留在“对词的音乐性的规定”这一简单的理解水平,而将其颇富文化内涵的文学审美特质留给元曲家去审味和研究元曲了。
“本色”与古代戏曲术语“色”不能混为一谈。《辞源》(旧本)释“色”:“教坊有部有色。部有部头,色有色头。部如‘法部’‘胡部’;色如‘杂剧色’、‘参军色’、‘舞旋色’之类。”此所谓“色”,即今天所谓“脚色”也。又释“本色”曰:“1、谓本来面目也。《后山诗话》‘韩退之以文为诗……’2、凡租税征收物品曰本色。”“本色”即“本来面目”。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谓“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其中“本色”即“最初原始颜色”,也是“本来面目”之意。《辞源》释“本色”,正是以陈师道以上这段话为例证进行说明。那么,词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呢?刘克庄认为:“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④刘克庄此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长短句”“可歌”方为本色,二是说“长短句”须由“雪儿、啭春莺”这样的女孩儿“歌”方为本色。一般人们只是注意到了刘氏第一层意思,然而那被忽略的第二层意思乃是词体的一个更重要特色。拿今天的话说,词的“本色”在于它的女性美;拿以上宋人关于词的审美概念对照,就是第一组所列举的词应具有“婉媚、婉美、软媚、妩媚、柔媚、柔婉、纤柔、纤艳、柔丽、艳丽、侧艳、浮艳”等的审美趣味。事实上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词应该具有“阴柔美”和“女性美”这个层面得到启发、并进行强调的。[4]宋人论词,都看到了词的这一本色特征。王灼谓:“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1](P79)接下来他又举具体事例证明当时词人的这种“重女音”而“尚婉媚”的特点:“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似伊模样,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沉于习俗。”[1](P79)宋代“习俗”“重女音”正可印证刘克庄的“本色”说。王炎《双溪诗馀自序》道:“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⑤同样强调宋词的本来面目在于“曲尽人情”“婉转妩媚”。即便像提倡“雅正”的沈义父也认为:“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直只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1](P281)他所谓的“闺房之意”、“ 艳语”为“词家体例”,亦是陈师道和刘克庄“本色”说的阐发。汪莘则从“喜爱”苏辛词、不喜欢艳词的立场出发,认为:“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于淫,谓不淫非词也。”[5](P270)他此处所谓的“淫”,也就是沈义父的“艳语”和“闺房之意”,提法不同,实质一样——正如鲁迅先生在分析人们读《红楼梦》的不同观感时指出的:“道学家看见淫”也。但无论如何汪氏至少也是道出了宋代“词主于淫”的事实——为宋词的“本来面目”乃“重女音”“婉媚”及“侧艳”(或“浮艳”甚或“淫艳”)从反面作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至此,陈师道和刘克庄所谓的“本色”,是指宋词“婉媚”、“侧艳”、具“女性美”等审美特征,乃宋人对于词之审美的、具代表性的一个审美形态似乎已经没有问题了。
尔后历代学者也基本上是从这个层面上来体认宋词之“本色”含义的。如明代茅说“:香弱脆溜,自是正宗。”⑥“香弱”就是典型的“女性美”特征。清代贺裳说:“词虽以险丽为工,实不及本色语之妙。如李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萧淑兰‘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恋伊’,魏夫人‘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孙光宪‘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严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楼,为怕见、分携处’,观此种句,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安排一个字,费许大气力。”[1](P716)其所列举的五句“本色语”,有三句出之女作家之手,另外两句作者虽为男性,但词句乃“香软”之属。清代彭孙说的更为明确:“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如韩魏公、寇莱公、赵忠简、非不冰心铁骨,勋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词,有‘人远波空翠’,‘柔情不断如春水’,‘梦回鸳帐馀香嫩‘等语,皆极有情致,尽态穷妍。”[1](P723)
此处所谓宋词的“审美形态”,是对诸多语义相似、相近或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之有关宋词审美观念进行“类”之综合的表述。作为宋词审美形态之一的“本色”,除综合了上文所及第一组概念涵义外,还具有第二组“俚俗”和“自然”的意蕴——及《辞源》释“本色”的第二义:“凡租税征收物品曰本色”。上缴“租税”不以货币而以“物品”,这是一种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形态。以物换物,保持了货币的天然属性。这种自然与天然,质朴而通俗,就是“本色”。宋词的可贵和可爱处,正在于它反映了人性的自然与天然。张耒为贺铸词所作序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5](P121)这是北宋人对词的本色天然之性的理解和呼唤。王灼以“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做拍,应之不差”证明词之音乐乃“自然之度数”[1](P80),也从另一侧面强调了词曲天然童真的特性。
宋代文人对“自然”“天然”的审美境界情有独钟。如王灼评晏几道:“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5](P83)苏轼评欧阳修书法云:“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⑦“有自然绝人之姿”者,便为“天下之奇迹”,东坡的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在北宋文人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东坡词的佳妙处,亦首先在于其词中表露的性情自然而然,大多“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从“自然”这个审美层面观察,东坡词也算得上有些“本色”味儿,所谓“英雄出语多本色”,殆此义也。但他却并不是一位北宋人心目中的“本色”词人,只是他公开批评“世俗”“未见好德如好色者”[6](P243),反对士大夫热衷“艳情”,加之他的词作涉及“艳情”和话语“通俗”“俚俗”者委实很少,故其弟子陈师道说他“词似诗”、“非本色”。这并非贬义,而是说出了北宋人(甚至包括苏轼本人)所公认的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北宋人认为词的“本色”,除了自然而然,出自个人独有个性而外,还需具备写“艳情”、辞意“婉媚”“艳丽”和通俗易懂的特质。如柳永,尽管人们批评他的词“卑俗”、“尘下”,但却从不否认“耆卿词多本色语”。柳耆卿词的“本色”,除了多写“艳情”,情辞“婉媚”“侧艳”和“自然”“天然”外,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俗”——这也是柳永最为士大夫所不齿的主要原因。但是,柳永词在宋代却最有市场,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⑧,与柳永词通俗易晓关系极为密切。因为这“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除了说明柳永词流传甚广外,还证明了柳词的通俗易晓,群众喜爱。自然而然地运用社会习语、俗语,便通俗易晓,便为本色。正如王骥德所云:“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⑨
历代论者都注意到了“词须自然,方为本色”的审美特质。如元代陆辅之说:“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1](P301)清代刘熙载所谓“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7](P122)亦是此意。“天籁”,即自然之声。这种自然的天声,乃经过“极炼”归于“独得”的词家“本色”,是词家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故沈祥龙云:“词以自然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诠也。”接下举宋词例句证明道:“如‘梅子黄时雨’、‘云破月来花弄影’,不外自然而已。”[1](P4054)
概览北宋人的词话、词论文献,论者常常将“本色”(或“自然”或与之接近的概念)作为宋词审美的重要评价标准,而很少用到“雅”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评价语辞。看看欧阳修对词这一新文学样式的功能体认对我们的这一认识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他在其《采桑子》组词的小序《西湖念语》中写到: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上。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⑩
我们且不详论欧氏这番话是怎样反映了北宋人向往自然和追求心性自由的文化价值取向。单就其“欢然会意”,“旁若无人”,“陈薄技”,“佐清欢”的创作态度,便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文人对于词的文学功能不同于传统诗教的新体认。这样一种任运自然、率兴畅游的情趣,正是宋人对自然本色的人性和率朴真淳生活的向往。北宋人认为“词”就应该表现此类带“童贞”意味的人生境界,而不很在意于“雅”或是“不雅”的话题。
当然,“雅”又委实是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概念。所以黄庭坚在《小山集序》中评价晏几道词为“狭邪之大雅”⑪,这近似于玩笑的评价,正可印证黄氏自己“作乐府以使酒玩世”⑪的调侃风味。因为无论从传统诗教的视阈还是从语义学的角度,“狭邪”是无论如何也“大雅”不起来的。因为“狭邪”是人性的原始状态,而“大雅”则是以“礼”修饰原始人性后,使“本色”人性受到文明教化后的一种修饰性形态。黄氏称小山词为“狭邪之大雅”可能还有一层想拔高小山词词品的意味。但是,这“狭邪”倒是真正道出了小山词的个性特征。如清人陈廷焯评晏几道词:“《诗》三百篇,大旨归于无邪。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8](P10)又说:“小山虽工词,而卒不能比肩温、韦,方驾正中者,以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也。故悦人甚易,而复古则不足。”[8](P196)所谓“复古”的“风人之旨”,即传统诗歌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雅”致和“雅”趣。陈廷焯认为小山词“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也是就小山大量艳词言情任性放肆、叙哀感伤直率而发。尽管叔原本人在小词的创作中已十分注意写男女情爱的朦胧化、抽象化,尽量避免世所非难的柳永式的“淫言渫语”。但是,由其父晏殊大量制作艳词所煽起的“缘情绮靡”之风已成为北宋前期词坛的普遍好尚,加以叔原本人性格“磊隗隽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9](P467),所以他词中的“邪”,也就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了。若用词学审美标准衡量,实在宜属“本色”的范畴,而并无“大雅”可言。所以,我们可以说,晁补之评晏殊词“风调闲雅”,大概应该是北宋人以“雅”评词的首例——事实上珠玉词的确以文词清雅而见长,这也是晏殊本人自认为与柳永虽同样填词,却与永不同科的分歧所在。但我们认为晏殊充其量是一个讲究文采的“本色派”作家。[10](P3-20)李清照历评北宋数家,虽也指责柳永“词语尘下”,但却肯定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我们知道,柳永“新声”的审美特征却正是“俗”。[11]如是可见,“词语尘下”的柳永词“大得声称于世”,证明北宋人对于词体的“本色”之审美意趣,是群体的选择。
与北宋人不同,南宋人论词却偏向于“骚雅”的审美向度。“骚雅”(或“雅正”)作为宋词的审美形态虽是由南宋末的张炎和沈义父提出,但倡导者首先是王灼。他一方面反对“艳语”提倡“庄语”,另一方面反对柳永“浅近卑俗”赞扬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其词学审美观念虽不乏有价值的创见,但趋向传统和道统,其观点与前所论的“本色”基本上是对立的。宋词的雅、郑之分,也是他首先提出:“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1](P80)于是他欲通过《离骚》以救“轻浮”“卑俗”之弊:“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1](P85)遂认为得《离骚》之旨趣的作品“最奇崛”——所有这些,透露出南宋人词贵“骚雅”的先声。
从北宋向南宋的这个宋词审美观念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关注为叶梦得《石林词》的题记探得消息,其文云:
“右丞叶公以经书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圣功为镇江掾,公为丹徒尉,得其小词为多,是时妙龄气豪,未能忘怀也。味其词,婉丽绰(按:疑脱“约”字,下同)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岂近世乐府之流哉!”[5](P131)
作为世之“宗儒”的叶梦得,作的小歌词尚且“婉丽绰(约)有温、李之风”,可见北宋词的“本色”说浸染人心之深。值得注意的是叶梦得“晚岁”的变化,所谓“简淡”“雄杰”,“不减”“东坡之妙”者,正是这一变化的实质所在。有趣的是,叶梦得值“妙龄”时生活在北宋,“晚岁”二十余年则生活于南宋。其词作之审美观念的变化,正是南北宋之交宋词审美观念转变在一个文化人创作实践中的具体反映。在词史上正式推崇“东坡之妙”,也应该是从此开的先河。尔后胡寅为向子词作序,声称:
“诗出于《离骚》《楚辞》。而骚辞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者异。名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5](P168)
胡寅在这里不仅第一次将东坡词提高到超过《花间》和柳永的崇高地位,而且第一次正式将“楚骚”与词曲相提并论。后来陆游在自己的《长短句序》中以“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为前提,指出“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并认为“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⑫亦反映出陆游本人词的审美观念逐渐变化的痕迹。而其“雅正”与“郑卫”之说,正可与其同时代的王灼的观点互相发明。
从南宋词的创作考察,这个由“本色”向“骚雅”的转变,是由姜夔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张炎在标举“骚雅”的旗帜、强调“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时,特举姜夔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23](P16)为范例进行强调。其后历代“骚雅”派治词学者就是以姜夔词为范式,进行学习和模仿。并以“骚”或“雅”为衡绳品评历代词人词作。如陈廷焯评贺铸:“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12](P15)冯熙评秦观:“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1](P3586)陈廷焯评王沂孙:“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白石词,雅矣正矣,沉郁顿挫矣,然以碧山较之,觉白石犹有未能免俗处。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8](P40-41)
当然,张氏在强调“骚雅”时,并没有忘记词家本色“婉”及“近情”:“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如陆雪溪<瑞鹤仙>……辛稼轩《祝英台近》……皆景中带情,而存(按:夏注本作“有”,此从《词话丛编》本)骚雅。”[12](P23)这也正是张炎《词源》千百年始终能成为词家正轨,其理论观点一直影响元、明、清三代的原因。
总之,“本色”与“骚雅”,是宋人关于词体审美的一对重要形态。北宋人讲究词的“本色”,南宋人强调词要“骚雅”。这既是时代风气使然,又是宋词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它既反映出中国文学审美内涵的丰富性和审美品味的多样性,又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流变与承传的恒定性。由于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多样与丰富,所以宋词才表现出如此多姿多彩、内涵富赡的审美趣味。
注 释:
① 《国语》卷十九《吴语》:“申胥谏曰:‘……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使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
② 徐 陵.玉台新咏序:“阅诗敦礼,非直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无异西施之被教。”
③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然睿旨存亡,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
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翁应星乐府序》.
⑤ 王炎.双溪诗馀[M].四印斋刻本.
⑦ 苏轼书欧阳修《试笔》后,《欧阳修全集》,1052页,北京,中国书店 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6。
⑧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48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 王骥德《曲律》。
⑩ 《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055页;标点据唐圭璋《全宋词》第一册,120-121页。
⑪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十六《小山集序》[M].四部丛刊本.
⑫ 《陆游集·渭南文集》中华书局排印本.
[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陈师道.后山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汪 莘.方壶诗余自序[M].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苏 轼.仇池笔记(卷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7]刘熙载.艺概·词曲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9]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沈家庄.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J].文学评论,1998,(4):143-152.
[12]夏承焘.词源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责任编校:谭容培)
Re-examination on the Aesthetic Ideas of Song Ci——One of the Morphological study of Song Ci from Aesthetic Perspective
SHEN Jia-zhu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Guangxi 541004,China)
“Nature”and“grace”are a pair of important aesthetic shapes of Song Ci.In Bei Song Dynasty,people paid attention to“nature”of Song Ci,and stressed“grace”of Song Ci in Nan Song Dynasty.This is the result of atmosphere at that time,and also is an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Song Ci.The two are complementary and can be replenished each other perfectly.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aesthetic taste of Chinese literature,but also reflects the constancy of rheology and heritage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Song Ci;aesthetic shape;gentle;nature;grace
I207.23
A
1000-2529(2010)02-0102-05
2009-10-28
广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临桂词派及粤西词人群体研究”(05111003)
沈家庄(1946-),男,浙江绍兴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