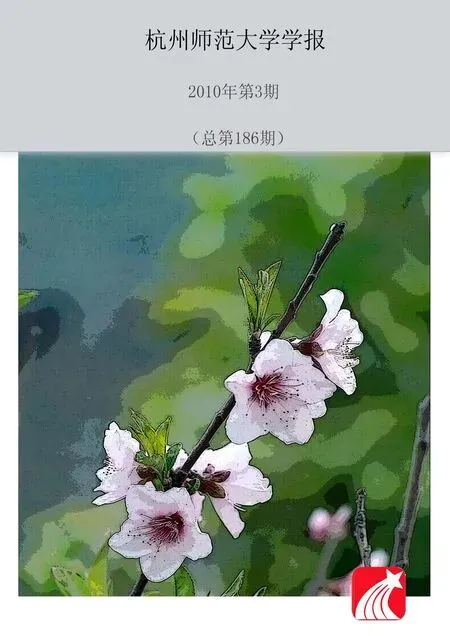重思智慧
张汝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043)
虽然philisophy在古希腊文中是“爱智慧”之义,但在西方哲学中,除了古希腊哲学家还对它有所思考外,近代西方哲学家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主要的思考对象。在哲学的诸研究领域中,有知识论,却无智慧论。知识研究蔚为大宗,智慧却少人问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开始,知识而不是智慧,才是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从柏拉图区分意见与真理开始,西方哲学的真理概念也基本是与知识有关,而不是与智慧有关,真理就是得到了证明的知识。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知识问题更是成了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在认识论哲学家看来,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研究知识的性质、结构、条件和可能,提供形式化的知识说明。而“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不仅反映了西方人对知识的理解,也反映了知识在西方思想中的霸权。
知识受到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的极端重视,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各种知识不断扩展了人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识,开阔人们的眼界和思路,成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知识由于其客观、普遍有效和可证实性,自然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
近代西方的知识概念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它的特点是追求规律性、追求确定性、追求可证实性(经验或逻辑证实)。知识是对一切对象的客观认识,具有普遍有效性。只有对事物进行高度抽象和一般化以及其他人为的技术操作得到的知识,才能符合上述要求。上述知识要求也意味着知识必须是价值无涉的,即知识就是知识,知识无禁区,它及其应用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什么后果,那不是知识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与人生有关的种种问题,也不属知识的范围。这就是知识的盲区。知识似乎无所不可知,却唯独不去思考和认识它对人们的生活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人们天真地认为,知识的后果总是正面的,却不去思考任何知识都会有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由于将知识视为绝对正面的东西,对于知识的追求几乎成了现代思想的唯一目的。其极端的结果,则是知识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莫大的危险。例如,核裂变的知识。
在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知识与信仰互相制约的时代,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去魅过程,今天已经不再有什么牵制知识的传统力量了。人们从上天入地到心理问题都要请教专家,说明知识已然成为人类生活的绝对权威,它的影响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知识在现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科学技术,更是在许多人眼里将决定人类的命运。人们越来越只知知识,不知智慧,甚至以知识来代替智慧。智慧被人遗忘,至少被最不该将它遗忘的哲学家遗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智慧从一开始就与知识不同,它固然不排除知识,但与知识有很大的不同。在日常用法中,智慧首先指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如对生死的理解、对生命目的的反思、对行为方式的斟酌、对实践事情的判断和洞察以及对价值取向的决断。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即表达了这种智慧。当然,在东方,智慧还表示对宇宙奥秘的洞察。而在今天,人类恰恰缺乏这两种意义上的智慧,结果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借用老子语,非老子原意),知识越多,智慧越少,不但生活越来越没有方向,而且使知识成了一种威胁。
一
希腊人最初把一切知、教养、能力或机智称为“智慧”,希罗多德和其他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称有“七智”,梭伦是其中最著名者,但他既非哲学家亦非科学家,而是政治家和立法者。赫拉克利特说,“热爱智慧者必须精通许多事情”(残篇35)。而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伯利克里的口告诉人们,智慧是怎样的知与能:“我们爱美却不挥霍,我们追求教育却不溺爱。”在古希腊,智慧最初是指与直接的生活实践有关的知与能,而非哲学理论。在古典时代,从事哲学的人会处于很大的压力;当时一个自由的男人值得做的事只是政治和战争,“教化”是奢侈,而不受信任的事情。传说中泰勒斯的女仆嘲笑主人仰观天文而失足落井,其实是当时希腊人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一起在嘲笑这个哲学的始祖。但是,到了毕达哥拉斯,“智慧”(sophía)就已经专指理论知识了;毕达哥拉斯将争名逐利与研究事物的本质相对立。希腊人很早就开始强调“智慧”的沉思意义了,因此“智慧”在古希腊主要指与实践的、尤其是政治活动相对立的系统的理论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对照理论生活方式来评估政治生活方式,得出一个非常“非希腊”的结论:理论给予人完全的幸福。[1](PP.40-41)
到了希腊化时代,智慧成了生活的艺术。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智慧就是摆脱恐惧和欲望,摆脱一切未经思考的错误想法,它是通向幸福的最可靠的指路人。人只有智慧、诚实、正义地生活,生活才会令人愉快。在斯多葛派那里,哲学具有实践和治疗的功能,它通过激发人自身的力量来治疗人的灵魂,使其遵守智慧的规定。人必须努力规驯他的自然冲动、目的和思想。塞涅卡和西塞罗一样,都把智慧视为对神与人的事物之知。恩皮里克强调哲学就是智慧的操练,智慧是对神与人种种德性之知。对于普罗提诺来说,智慧是只有神之理性才有的知本身,它与存在同一。奥古斯丁也认为智慧从根本上说是神才有的东西,它是从精神上把握永恒和神圣的东西。
托马斯·阿奎那区分哲学知识与神学知识,它们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哲学首先是从事物自身的原因得到它的论据,再从那里进到上帝的知识。哲学智慧即使也像神学智慧那样处理神圣的问题,但它的原因不是由于神学的条理而是由于人的理性。哲学智慧与神学智慧的区分必然导致理性的范围和科学知识的界限这些基本的问题。
近代西方智慧概念的重心转到了自我认识上,但这也起源于苏格拉底的传统。苏格拉底要人反思自己的生活,而蒙田在其随笔中引用西塞罗的话说:“愚者即使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还心犹未甘,而智者有了什么会心满意足,决不再去自寻烦恼。”以此来表明人“第一件要学的事是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他该做的事”[2](P.8)。他还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我讨厌自己不智的智者”[2](P.124),来表示智慧首先与自己的行为有关;智慧随聪明而来。
然而,笛卡尔却把智慧等同于知识,他认为哲学不仅研究在日常聪明意义上的智慧,而且追求对人能认识的事物的完全知识,通过纯粹天生的理性对真理的认识就是最高、最本真意义的智慧;最高的善和人类生活的完满就在于这种智慧。但是,人类智慧的全知预设以伦理学为前提,它是智慧的最高阶段,作为普遍智慧的第一规则而有效。斯宾诺莎同样赋予智慧以道德意义,他在《神学政治论》中把所罗门作为智者的典范,说真正有智慧的人宁静泰然地活着,不像坏人,内心没有一刻宁静。[3](P.25)人真正的幸福在于智慧和对真理的认识。
莱布尼茨把智慧定义为“一门幸福的科学”,沃尔夫以此定义为试金石来检验中国的实践哲学,他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基础与他的哲学基础完全一致。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而“中国人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理论”[4](P.85),中国人同样以最高的善为目的。在这篇演讲的注释中,沃尔夫还提到,莱布尼茨把智慧定义为精神的能力,它设定行为的最终目的和达到它的最可靠、最好的手段,安排中间目的的相互次序,以使它们共同作用达到最终目的。
康德把先验哲学的最高立场称为“智慧学”,它完全盯着主体的实践;但他意不在生活实践,而是要用智慧概念来肯定追求真正的圆满。这种追求是理性给自己的任务,使自己在理论和实践的目的中成为对象。然而,因为理论理性陷于二律背反,一个给定的有条件者的诸条件的整体只能在物自身中遇到,但物自身只能作为现象被认识,这就使得实践理性得在最高的善的名义下去寻求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那它作为我们理性行为的准则。对于康德来说,这就是智慧学,“而当智慧学又作科学时就是固然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含义上的哲学。在他们那里,哲学曾是对至善必须有以建立的那个概念即至善必须借以获得的那个行为的指示”。[5](P.148)康德坚持传统意义的哲学概念和智慧概念,理论思辨的基础就是对智慧不停的追求,一切思辨的知识无不如此。
在康德那里,智慧学对于人来说还是太高了,因为他并不掌握智慧。智慧只是在上帝那里作为一切理论和道德(实践)之知的最高原则。因此,康德根据传统,把哲学规定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成的对智慧的追求”。因为哲学仍只是人的智慧。[6](P.394)但是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者不再把智慧作为哲学的主导概念,因为像谢林与黑格尔等人都相信可以通过思辨来获得绝对的系统知识。在黑格尔看来,智慧是属于目的领域的东西,因为合目的的行为就是智慧的行为,智慧就是根据普遍有效的目的行动。智慧是上帝的力量,它表现为世界上的目的被理解为上帝的创造,它(上帝的力量)规定世界。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力量”,智慧是精神主体性的关键。内在的自我规定是由于“智慧的目的”,因为“内在只是主体本身”。[7](P.13)
叔本华不满黑格尔那里智慧的思辨化和理论化,在他看来,智慧是直觉的东西,智慧就是处世之道。真正的智慧的源泉是直观,与直观相比,抽象概念只是真正知识的单纯影子。因此,智慧并不仅仅指理论的完善,而且也指实践的完善。它作为处世之道无法学,只能练。智慧成为真正的生活洞见,智者成为善于处世者,其优点就在于完美的直观知识,因为正确的洞见与切中肯綮的判断来自人们把握直观世界的方式。[6](P.394)对于叔本华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智慧的形式,是一种让生活尽可能舒适和幸福的艺术。
然而,从尼采开始,一些哲学家在摒弃传统“爱智慧”意义上的哲学的同时,也不再将智慧作为自己思想的主题,而是将它作为负面的东西来对待(如维特根斯坦)。但也有西方哲学家不同意那种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而是主张如果因为哲学过于成为作为普遍科学的理论而将它摒弃的话,那么恰恰应该恢复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地位(如古代哲学所昭示我们的那样),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除了练习智慧外,岂有他哉?
西方哲学家对智慧的论述尽管有种种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智慧”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总体性知识,既完满的知或全知;再就是智慧总是与人类的生活实践有关,是对于实践和指导实践的智慧,因而它具有一定的伦理性,与道德有关。
二
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墨子·尚贤》:“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孟子·公孙丑下》:“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智慧”也写作“智惠”,如《荀子·正论》:“天子者……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但单独一个“智”字也有“智慧”的意思,如《国语·晋语》:“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也,使为元侯。”在古汉语中,“知”与“智”通,《释名·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西方的“智慧”概念也有“一切知识”的意思;但中国哲学中的“知”却并非对事物的纯粹认识,而是多少含有“实践”的意思在。而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根本要求,也使得其“知”的概念与西方近代的“知识”概念不可能完全契合;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西方的“智慧”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知”的概念就是“智慧”的意思;而只是说,中国哲学中“知”的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智慧”。
在日常语言中,“智慧”有“聪明”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却与聪明有别。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总是与人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带有明显的伦理(实践)相关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仁义礼智经常并称,更说明了这一点。在儒家思想中,“智”是一个基本的德目,它决不仅仅是聪明,而是相反——大智若愚,智慧主要并不表现为精明能干、善于处世或知性发达、反应敏捷。智慧不是知性理智的结晶,甚至也不是亚里士多德phronesis(实践之知)意义上的聪慧明智,而是超理性的、直观的根本性洞见,也是一种澄澈无比的精神状态。
《论语》中未出现“智慧”一词,但据杨伯峻的统计,“知”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116次,其中作“智慧”义有25次。[8](P.256)据此可以说孔子有其“智慧”概念。从《论语》一些名句中,可以大致了解“智慧”对孔子而言为何物。首先,智慧不是对事物的客观知识,而是一种澄澈无比的精神状态。知者之所以不惑,就因为他有之“智”,即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上智与下愚的区分,也不在于有无理性。理性是人天生的能力,只有强弱之别,没有有无之分。而上智与下愚之不移,说明智慧并非人皆有之的天赋能力,而是需要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精神状况和境界。
作为智慧的“知”不是知物,而是“知人”(《颜渊》)。《书》云:“知人则哲”(《皋陶谟》),“哲即智也”。[9](P.1185)“知人”不是客观地认识或了解某个人,而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智慧实际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而不仅仅是正确的认识。作为一种正确实践的能力,智慧不是按照所谓事物的规律机械或教条地行事,而是见机行事,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作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知者乐水”(《雍也》),就是因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10](P.90)清人黄式三亦云:“水缘理而行,经历险阻,必达平海而后已;知者通天下事之条理,无拘执,无阻窒,故乐水。”[11](P.15)智慧的实践特征决定了“知者动”,即有智慧者并非如许多西方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沉湎于静观冥想,而是不断地有所行动。*《尔雅·释诂》云:“动,作也。”
但这并不意味智者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相反,“知者利仁”(《里仁》),即“利于仁而不易所守”;“利”者,“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10](P.69)智慧的所有行动都出于仁而又为了仁,“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但这不是教条地盲目坚守,“利仁者非安,非勉强,谓明乎仁道而顺达之也”。[11](P.84)在孔子和后来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智(慧)总是与道德原理(仁道)联系在一起的,智是道德原理的一个主要特征和要素,它是指导道德实践的原则。但仁是智的先决条件,“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智慧的道德属性。智慧不是像理智那样的中性能力,而首先是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能力,它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无限发挥的东西,而是必须合乎、而不是违背仁道的原则。这从根本上将它与一般的聪明相区别。
在孔子那里就像在苏格拉底那里一样,智慧意味着知道和承认知识的有限性和盲目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分明说的是与“我知我之不知”一样的意思。有智慧的人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些许知识就沾沾自喜,甚至妄自尊大,而是永远会记得,在知识之上,还有它的指导者——智慧。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对智慧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在《孟子》中“智”字多次出现,但并不都是作为哲学概念。孟子也在一般的“聪明才智”意义上来用这个字,如“为是其智弗若与”(《告子上》)中的“智”字,便是如此。但孟子更多的是在“智慧”的意义上来使用“智”字。他把“智”定义为“是非之心”(《告子上》),也就是判断力。这种对“智”的理解在孔子那里就有了,只是没有明说。朱熹在诠释“择不处仁,焉得知”时,就把“知”释为“是非之本心”。*“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也。”(朱熹《四书集注》,第69页)孟子说“智”是“是非之心”,明确地把智慧作为判断力的这一维度彰显了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作为“是非之心”的“智”只是人心的善端之一,它与仁、义、礼一起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和起点。“智”在孟子这里同样有明显的道德伦理属性,它主要与生活世界的实践有关。智慧就是对如何生活和要怎样生活的洞见与判断,是对伦理秩序朗然于心,而昭告于天下:“始条理者,智之事也。”*戴震对此种意义之“智”有精当的诠释:“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第6册第151页,黄山书社,1995年)(《万章下》)伦理秩序通过智慧而得以阐明。但这并不等于说智者是如康德的主体那样的道德的立法者。相反,智者之智就在于顺天理事宜而为,不穷逞机心,“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里娄下》)。
孟子同样认为,智慧不是对事物的个别知识,而是全知,“知者无不知也”(《尽心上》)。这当然不是说智者具有一切知识,而是说智者对于所有知识有一种总体观,知道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尽心上》)即此之谓也。这当然也与智慧的判断力有关。智慧的判断力首先与是非判断有关,“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知言就体现了这种判断力。但是,在孟子那里,智慧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能力,同样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能力,“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公孙丑上》)则表明了这一点。智慧就表现在当仁不让,当为则为。是非之心只有扩而充之,转化为实践行动,才真正是智。
荀子把知分为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和役夫之知。后两种知共同的特点是言不及义,行不中矩,不讲是非,不论曲直。*“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荀况《荀子·性恶》)只有前两种知才称得上智慧,它们或“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或“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荀子·性恶》),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它们发出的言行,无不中规中矩,恰当合理。“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荀子·非十二子》)但智不仅仅是一个言而有当还是无当的问题。荀子同样将智视为判断是非之能力:“是是、非非谓之知”(《荀子·修身》),它是道德心的运用:“人主人心设焉,知其役也。”(《荀子·大略》)仁与知不能彼此取代,缺一不可:“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荀子·君道》)
在荀子那里,智慧有亚里士多德phronesis的意思:“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旤,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荀子·仲尼》)但智慧更是对一般事理的洞察:“知惠足使规物”(《荀子·君道》);“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但这不是要以其主体性来洞察事物的秘密,替天行道;而是顺天而为,“不与天争职”,“大智在所不虑”(《荀子·天论》),“不虑”的意思不是不思考,而是不把自己的主体性强加于事物。近代人以为凭仗自己的理性就可以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古代人却认为智慧正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另一方面,智慧也不是让人无所作为;而是要“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于天地之间”,是为“仁知之极也”(《荀子·君道》)。荀子一方面赋予智慧以洞明宇宙真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同样坚持它的实践特性。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强调了智慧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莫近于仁,莫急于智。”[12](P.202)智慧为人生所急需,没有智慧,人生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人的种种才能如遇“邪狂之心”的话,“适足大其非而甚其恶耳”。[12](P.202)人光有仁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是非判断的能力,也就是“智”,才能爱其当爱,“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爱也”。[12](P.202)董仲舒显然也把智慧看作是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智慧是正确行为的指导,经过智慧规划的行为,才会有好的结果。智慧不是一般的聪明才智,而是一种整体的实践能力,它融对事物吉凶利害的预见,对事情前因后果的洞察,行事得当,语言精练中的于一体:“智者见祸福远,其知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常务。如是者谓之智。”[12](P.203)可以说,智慧就是得道,得生活实践之道。
从以上对早期儒家思想家关于智慧的论述来看,智慧是实践之道,是对人对事的整体把握与判断,是实践的指导,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它不是对事物的旁观者式认识和客观知识,而是实践的决断。然而,智慧也不是一般日常意义的聪明才智,那只是一种中性理智能力;智慧总是与伦理道德相关,与仁义相关。智慧不是理论推理,而是超理性,但不排斥理性的价值直观,它一方面不离仁义;另一方面总是能就特殊事情作出适时适当的决断并付之行动。智慧的落脚点在生活世界,但其观照却在天人之际,就此而言,它与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也并不完全相似,因为它包括对天道的某种洞察。
三
中国现代哲学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巨大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人将智慧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即便是那些谈论“中国哲学的智慧”的书,也几乎完全不涉及智慧的主题。人们热衷的是知识问题,或本体论问题,而不是智慧问题。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只有冯契将智慧作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加以重新提出和讨论,他的主要著作就叫《智慧说三篇》。
冯契最初是在从金岳霖学哲学时萌发他对智慧问题的思索的。金岳霖在其《论道》一书的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大意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13](P.7)冯契对此表示疑问,在他看来,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金岳霖的做法是把认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问题。[13](P.7-8,11)从此之后,“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到底如何,便成为我一直关怀、经常思索的问题”。[13](P.9)
尽管冯契把他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部著作称为“智慧说三篇”,但真正系统论述他的智慧学说的是他求学期间发表的《智慧》*该文原发表于《哲学评论》第10卷5期(1947年),《冯契文集》第九卷,第1-68页。一文。虽然他后来对该文中“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的提法有所不满,认为“单纯从‘观’来区分认识的阶段,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13](P.10)但那部著作还是奠定了他智慧学说的基础。
冯契是在与知识相对照的语境下来定义“智慧”的,他心目中的“智慧”有中国古代“圣智”、佛家的“般若”和希腊人“爱智”之“智”的意思,它“指一种哲理,即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13](P.413)在冯契那里,智慧也根本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所谓聪明才智,而是特指哲学智慧:“认识天道和培养德性,就是哲学的智慧的目标。”[13](P.415)实际上冯契是从元学即形而上学上来理解智慧的:“智慧由元学观念组成”,它是“关于宇宙或无限的认识”。[14](P.25)这个思想他其实始终也没有改变。冯契的这个思想,虽然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有其根源,却与西方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若合符节。
但与西方哲学家的思路不同的是,冯契把元学看作是广义的认识论的一部分,他认为“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13](P.8)但是,他也承认,智慧不等于知识,因为智慧要认识的是天道,而“所谓天道,实在就是全体现实的秩序,包括无量的个体与其间所有的条理”。[14](P.29)它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因此,“无论怎样累积,无论累积得多么丰富,知识者总是得不到智慧的”。[14](P.29)只有扬弃知识,才能获得元学的智慧。
天道既然不属知识,就只能体会。“体会可说是动的智慧。动的智慧是一种非知识活动的认识,它以体验得的天道为对象,以领会得的元学观念为内容。”[14](P.31)体验与领会合在一起,是为体会。“体会以玄智为体,玄智以智慧为用。……以相对的认识能力为能,玄智无能。……以相对的认识活动为知,智慧无知。”[14](P.46)这就是说,智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不以一般的事物为认识对象。它是“无能之‘能’,渊然净,廓然虚,而全体莹彻。无知之‘知’,通天道,照万物,而不识不知”。[14](P.46)这样的智慧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包括形而上学理论,相反,只有“超越元学理论而得到智慧,遗弃形而下者而蹈乎形而上的领域”。[14](P.55)然而,超越绝不是说智慧自成一体,与知识和意见老死不相往来。冯契强调:超越不是隔绝,“智慧、知识与意见,相齐、同一与至无,虽说层次不齐、阶段不同,却并非真有楚河汉界,封锁了不相交通。扬弃本有保存的意义,上升本以下层为基石。爬梯子必须一级一级地爬,登高山必须一步一步地登。正如从意见发展出知识,从知识可引申出智慧。”[14](P.57)智慧虽然要靠体会,但却也是从意见和知识发展而来,虽然它又是意见与知识的扬弃。有“动的智慧”就有“静的智慧”,“静的智慧”是智慧的内容,又称“真谛”,“真谛是作为内容的道”。[14](P.31)但是,冯契声明:“智慧虽有动静之分,内容与对象之辨,然而本来混成,本来同一,决不能析离成数片。”[14](P.31)也就是说,智慧既是体,也是用;既是天道的发用,也是天道的表达。
晚年冯契对智慧的论述不再借用传统哲学的话语,而是使用流行的主流哲学话语,但是他关于智慧的论述与早年的论述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仍然认为智慧是对天道,即绝对和无限的认识,可是,与《智慧》中的立场不同的是,他现在把智慧视为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13](P.413)而在早期他把智慧看作是对理论的超越。同时他还强调了智慧是对德性的培养,这是《智慧》所没有涉及的问题。如果说早年冯契把智慧等同于元学的话,那么晚年冯契则把智慧等同的哲学,他说:“哲学的核心是性与天道的学说,而讲性与天道,不仅在于求真,而且要求穷通。哲学要求把握会通天人、物我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培养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哲学要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揭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哲学探索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13](P.424)而这也正是冯契笔下智慧的任务。
冯契关于智慧的晚年定论有三:(1)智慧是关于天道、人道的根本原理的认识,是关于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2)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自由表现;(3)从人性与天道通过感性活动交互作用来说,转识成智是一种理性的自觉。[13](PP.119-420)这是一个统一的认识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另一方面是德性的自证,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13](PP.45-46)
可以看出,转识成智的关键在于德性的自证。虽然冯契似乎并未将德性的自证与理性自觉相等同,但他所谓理性的自觉却离不开德性的自证。[13](P.425)没有德性的自证,光靠思辨的综合,是无法领悟到无限和绝对的,因为思辨的综合怎么说也是一种理性的推理性活动,而顿悟恰恰是不凭推理而产生的洞见。虽然冯契以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来解释理性的自觉,实际上他依靠的更多是后者,关于理论思辨如何能产生转识成智的“飞跃”他并没有给出太多的说明。
尽管如此,冯契还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智慧给予系统论述的哲学家,他将智慧等同于哲学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智慧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关于智慧的思想。他结合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阐明了智慧与知识和意见的关系,论述了获得智慧的具体过程,突出了智慧的德性特征,确立了智慧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的地位。凡此种种,都是冯契对于人类智慧思想的重要贡献。
与传统中国哲学家相比,冯契智慧学说的现代特征十分明显。传统哲学家总是由智(慧)统知(识);由智(慧)说知(识);而冯契刚好相反,他的以知(认识)说智(慧),将智慧纳入广义的认识论,显然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也由于将智慧视为统一的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传统智慧学说那种明显的实践特征在冯契的智慧学说中很难找到。智慧在他那里充其量与个人的品格或人格培养有关,但他没有论述它与人类实践的关系,更没有将它视为实践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在冯契那里,智慧纯粹是对性与天道的认识,丝毫没有亚里士多德实践之知的意思。虽然他也说“明智与智慧,也要应机接物”,[14](P.66)但那也是在知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的。由于始终强调智慧是认识,他最终还是将智慧定义为“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13](P.413)而在早期,他还认为必须超越元学理论才会有智慧。[14](P.55)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家那里,智慧当然也是一种总体性、根本性的知,但这种知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它是有智者的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和根本条件,是实践之道。它不是知识与意见的扬弃和飞跃,它与它们不存在阶段性上升的关系。它是实践的指导和准则,可以容纳知识和意见,但不是认识发展的最终结果。智慧不是性与天道的理论,而是性与天道的发用或功能。它不仅是体会,更是身体力行;不是认识,而是“行义于天地之间”;它在培养个人人格的同时,也在建立一个仁道的世界。西方哲学家的智慧学说虽然没有像儒家思想家那么突出智慧的实践性,但他们更多地将智慧理解为与人的生活实践有关,而不是与理论认识有关。智慧在中西哲学家那里强烈的实践特性,在冯契那里基本消隐了。
由于将智慧理解为知识,理解为理论,而不是实践,因此,智慧在他那里也不再是一种判断是非的力量,不再是是非之心。相反,他认为智慧应该“超越是非之域而抵于无是无非之境”,[14](P.55)因为是非还是相对,而不是作为智慧目标的绝对。因此,“遗是非则得元学的理论”[14](P.56)不但要遗是非,还要忘彼我,因为有彼我,“则是非隐然在。欲彻底地无是非,必须一并忘其彼我。忘彼忘我,则超越元学理论而得到智慧”。[14](P.55)是非之心不但不是智慧,而且还是智慧的障碍。冯契一直到晚年仍然坚持这个观点。[13](PP.429-432)智慧的目标只是要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自觉超对待的“现实之流”。虽然晚年冯契强调智慧培养德性的功能,但丝毫未及智慧的判断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他智慧学说的一个很大的缺憾。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和将智慧定位为认识,智慧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机制被完全忽视了。
冯契由于深受道家天道思想以及现代西方知识论思想的影响,认为天道或者说“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应该是无对待的,也就是与价值无涉的,因为一涉价值,就是有对待而不是无对待了。但是,对于儒家思想家来说,天道体现了天理,这种天理的秩序和法则就是原始的公道和正义,就是最根本的仁与义。人世的公道与正义,人间的仁义,则天法地而来,人间正当的秩序源自天理,即宇宙本来的秩序。秩序就意味着对待,意味着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对待,否则就无所谓秩序。因此,对于儒家来说,天道具有伦理的意味,源于天道的人道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哲学根本的实践性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就是这种天道观。以洞见天道与人道的智慧就要求能在具体生活实践中,根据所面对的特殊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正确决定。冯契由于将智慧定位为“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因而他的智慧概念始终游离在具体生活实践之上,根本不是实践的智慧,而只是理论。
因为儒家首先把智慧看作是正确实践的一个要素,智慧为实践所不可缺,是实践的当务之急,即董仲舒所谓“莫急于智”,所以他们一般都把智慧视为实践的指导,仁义的行为离开智(慧)的指点是不可能的。智慧不仅仅是对天理人道的洞见,更是能人的实践行为的指导。冯契由于将智慧定位为认识(知),就无法顾及它行(实践)的相关性。
在现代世界,知识已经成了一个带有绝对正面意义的东西,人们在推崇和追求知识的同时,却没有对现代知识形态和知识本身有足够的省视。但智慧本身要求我们对知识作出批判的反思,智慧本身就暗示了知识,尤其是现代意义的知识的盲点和不足。现代意义的知识总是局部的、专门的、条块分割的、甚至是技术性的。现代知识标榜价值无涉,只是对事物的“客观”认识,即便是人类事务,也被这种知识规范当作“物”来研究。人生活的方式、目的、态度、质量和意义,则完全被这种意义的知识排斥在外。人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活,不干知识的事!知识的增进不但没有从整体上增加人类的幸福,反而使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类生命,陷于空前的危机。
在此情况下,重新思考智慧,对人类来说就十分紧要。针对上述知识的盲点和弊端,的确有必要强调能洞见和思考性与天道的智慧,因为思考性与天道意味着我们将整个宇宙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来思考、来把握,而不是将它分为无数的“领域”和“范围”来认识。因为宇宙万事万物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物件”。相反,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和做法,都会影响人类的共同命运。性与天道这两个中国哲学的概念就表明,宇宙本身不是现代知识所理解的“自然”,而是具有原始的伦理在。理解和把握性与天道,就是理解和把握这种源始的伦理,这样才能“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于天地之间”。这种既有形而上学意味,又有实践品质的智慧观念,与西方的智慧概念也相去不远。
现代知识概念注定了只告诉我们据说是无关我们命运的某些领域或某些事物的“知识”,它的价值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真还是假。可是,人类不但要知道真还是假,还得知道对还是错、善还是恶。然而,按照韦伯的说法,知识(理性)可以告诉我们真假,但是无法告诉我们善恶对错。这是信仰的问题,而不是理性和知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善恶问题上,我们只有诉诸各人的信仰,没有别的办法。充斥当今世界的价值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已经表明现代的知识中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和危害。在理性和信仰之外,还有智慧。智慧是兼具理性与信仰的某些特征的精神能力。它是“是非之心”,但不是像康德的理性意志或基督教的上帝那样独断的道德立法者,而是性与天道的洞见者,它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能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和行动决断。
最后,智慧也必须是如冯契所言,乃一种德性的能力。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来说,是非判断往往不难得出,难的是按照正确的是非判断的结论来行动。人类的悲剧就在于明知故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正义)的,可往往在行动时却选择了错误(不正义)的行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之诚,为冯契的智慧学说一再强调,[13](PP.440-445)这的确是智慧的关键。不能付诸实施、不能见诸
行动的智慧其实还是知识,至少无法从根本上有别于知识,弥补知识之不能和不足。智慧的确不仅是处世的能力,更是自我完善(成德)的结晶。
智慧本来应该是哲学的本分,但由于近代知识中心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发展,它渐渐淡出哲学思考的视野,与此同时,哲学自身也开始走下坡路,它不仅不再是“科学的科学”,而且连自身存在的理由都成问题,不止一位哲学家宣布过“哲学终结”。不管哲学是否终结,它在今天已不复当初的生气,日益成为无聊的学院里的智力游戏,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只有恢复智慧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哲学才能恢复它的活力。这不是哲学自身的要求,而是人类对哲学的要求,人类今天面临的种种根本问题,只有靠智慧,而不是知识,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1]Cf. Herbert Schnä delbach, “ Philosophie ”, Ekkehard Martens/Herbert Schnä delbach, Philosophie: Ein Grundkurs[M].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5.
[2]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M].马振聘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3]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沃尔弗.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M]//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Cf.HistorischesWÖrterbuchderPhilosophie[M]. Bd. 12,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4.
[7]Hegel,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ReligionII[M]. Werke 17,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9]阮元.论性篇[M]//程树德.论语集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黄式三.论语后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2]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M]//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3]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M]//冯契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4]冯契.冯契文集:第9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