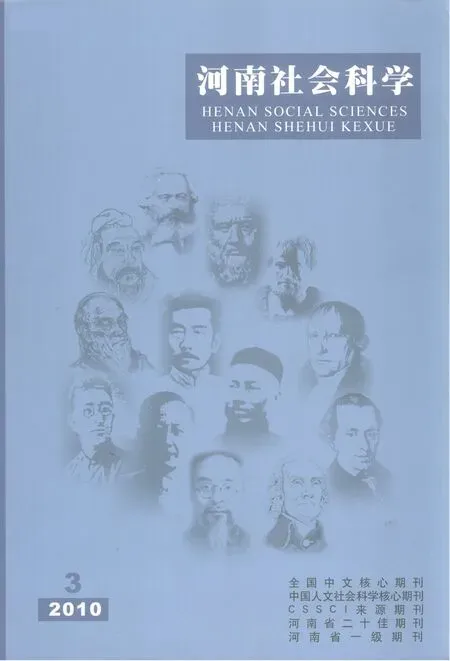思想史角度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专题研究
思想史角度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专题研究
编者按:交易费用或者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威廉姆森对其进行的理论构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向前发展。一项学科内容的构建,其方法论问题及有限性问题都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理解交易费用概念的发展过程,对于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脉络极具参考价值。本研究专题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认真审视了交易费用的方法论和有限性问题,并对威廉姆森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梳理。
交易费用经济学方法论
何一鸣1,罗必良2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一、引言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son一直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交易费用经济学——探索交易费用的产生及其行为效应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理。这一研究方向本质上涉及发展一种关于制度分析的一般性理论工具,并力图整合新制度经济学中各种各样层面上分析全部问题的统一框架。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性:重新引入和理解知识问题(Knowledge Problem)对经济行为的意义。知识问题引起交易成本,后者也因此成为制度经济分析中的中心角色。如果知识的获取、整理和传递不需要耗费任何资源的话,那么,人们在进行交易时就不需要进行激励、谈判和监督等非生产性活动,人们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也不需要向法庭求助。但在真实世界中,知识耗费(Knowledge Costs)的存在可能引发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损害效率的交易前后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交易双方通过某种形式以限制这种行为,制度就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工具。换言之,制度的存在是基于(知识)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事实。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主要探讨的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个人利益行为。
二、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的方法论原则
个人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它也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Hayek,1948)[1]。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是一种建立在该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理论科学,它通过基本的概念、定理和逻辑构建一个自治的体系以解释制度现象和事实背后的内在机理和因果规律。尤其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注重人们处于最佳状态下所能取得的成功或称为利益之物,而是在人们处于最糟糕状态下如何才能尽量减少他们做损害他人之事的机会。此外,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行为主体的资源禀赋和技能是具有差异性的,任何一个个体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理性无知”状态,因为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具有构建性的局限。即使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个人,他也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用于收集信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见,知识成本的约束是导致理性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的根本原因(Williamson,1985)[2]。这种有限理性会进一步导致契约安排的不完全性(Hart,1995)[3],从而导致“公共领域”的存在(Barzel,1989)[4]。而自利的个人又会相互争夺不完全契约的剩余索取权以攫取公共领域内的租金,导致租金耗散(Cheung,1970)[5]。因此,从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看,要判断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关键是看租金耗散的程度。换言之,如果租金耗散在边际上越少,则说明新的制度安排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如果把租金耗散视为内生性的交易费用的话,那么,这就是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小化行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效率”是一个带有个人主观判断的概念,因为它是以行为主体的终极目标为衡量标准的,当事前目标与事后结果接近或一致时,就是有效率的,反之乃低效率的。所以,“效率”和“目标”同样属于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的范畴,关键是符合谁的目标,即当行为效应实现了行为主体的个人目标时,则该行为就是符合效率原则的;相反,尽管行为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因而有利于其他行为主体,但如果它与行为发生者的个人意志不一致,那么,这种符合集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的行为对于行为主体个人而言是无效的。此时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相容,需要一套能够与技术环境相匹配的机制安排进行契约规制(Contract Governance)。
关键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之所以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之上,是因为制度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需要构建一种理论假说,并能运用可观察到的行为现象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得到可反驳的经济学含义。如果以目标函数作为解释的工具的话,可能无法得到可检验的经济学意蕴。因为我们可以把解释不了的现象转换为几个人为设计的变量放进效用函数中求最大化,这样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结论,也似乎能够解释以前还没有解释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只是主观猜想,人们难以从可观察的事实中验证该解释变量的客观存在性。因为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根据经济学家们头脑中的“玄思”任意变化,被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也无法求证是否存在,这就等于用“虚拟的工具变量”替代“主观的目标函数”。例如,有些新经济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解释国家贫富(North,1990)[6]、以文化差异解释绩效变迁(Greif,1994)[7]等。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变量无法进行实证观察,它们对绩效的影响更是难以测量,但这些经济学家却可以把它们放进理论模型的目标函数中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即在所谓的历史制度比较分析中,他们可以把非财富最大化行为放进目标函数里面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这是使用一些大家无法验证的“虚拟变量”去解释现象,这很容易使人们把解释不了的现象归结为人为臆造的概念,造成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训练和智力游戏。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意义就在于能被事实所反驳甚至推翻。科学的精神就在于研究者不断地寻找能够推翻其构建的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因此,可检验的经济解释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它是一种系统的、有组织的逻辑推导过程。作为一种纯逻辑推导,经济解释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内涵,而只是一种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但它的作用在于为经验材料的组织和理解提供文牍服务,以形成一套前后因果一致的逻辑准则。标准的逻辑准则本身可以说明某一特殊语言是否完全的和连续的,可以说明该套逻辑语言的命题是否正确,它是可验证假说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是一系列假说的综合体,从而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规律。进一步,作为一种科学的假说体系,它应该通过对想要进行分析的实际现象的解释能力来检验。但实际证据永远也不能实证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而显现该假说的合理性。按此逻辑,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制度分析中的交易费用约束条件来得到理性个人主体的行为特征,从而达到经济解释的目的。重要的是,交易费用及其转变可以测量和观察,我们可以借此解释纷繁复杂的制度现象并得到可推翻的理论假说(Refutable Hypothesis)。
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基本设定重要吗?
根据上述的方法论原则,交易费用在制度经济分析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将声明,某些力量对理解某一特定现象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力量则是不重要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重要的,交易费用又是制度分析的重要工具,因为它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交易费用假说将断言,它所解释的制度现象在实际观测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就如同在某种假设的、高度简化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一样。这一高度简化的世界只包含该假说认为是重要的那些力量——交易费用。事实上,对该类假说进行表述所借助的体系不止一种,即同一个制度现象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对解释选择的标准也不止一个,但其中一点是它能够使理论假说变得简洁、清晰和准确。而交易费用可以把所有制度问题,如产权、契约和组织统一在一个逻辑自治的理论框架内部,因此交易费用不但使理论假说变得可检验,而且可以得到简单的逻辑命题表达。在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学说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均是引起交易费用的行为因素,因此它们成为该学说的前提条件(Assumption)。我们知道,若要达到科学的目的,任何理论假说的前提假设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真实”。因为科学的目的不是复制充满五光十色的复杂事物的“真实世界”,而是从一般事物中抽象出简单的模型,使研究者能够解释它的行为和趋势以把握其中的规律性。
换言之,不管假设是否符合实际,交易费用经济理论模型的结论对现实的推测是否正确,它是否能够提供较好的经济解释。按照Williamson的阐述,交易费用学说的前提假设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前者是制度经济分析所依赖的认知假设,主要涉及主体面临特定的资源属性及构建性的知识问题。因此,在前提条件被知识问题或信息成本约束条件修正后,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知识约束对主体行为能力的限定:尽管人们为既定的目标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构造性元素,它就是“有限理性”这样一种限定,即领悟能力有限却刻意为之(Simon,1978)[8]。机会主义动机一般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和其他混淆视听的倾向。该假设首先保证行为主体以产生最高实际收入且最低成本耗费的方式行事,他们具有将资源用于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的动机。但这种事前的机会主义倾向即逆向选择和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即道德风险造成人们在与他人博弈时存在认知上的不足。
事实上,不管在什么社会结构下,人都服从理性约束,不同的是个体的理性程度存在异质性。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核,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假说或分支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不以此为前提条件来解释社会制度经济现象的理论就不属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反之,若以此为切入点来解释经济现象或某项制度安排的起源、运行或变迁,即使所解释的现象和交易及物质利益无关,它也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机会主义下的理性是交易费用经济理论的前提特征,但每个决策者面临的约束条件、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理性相同,在不同的机会主义环境下也可以有不同的理性表达和理性程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有限理性行为主体。行为主体的本质究竟是否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任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是以机会主义下的有限理性为出发点,没有例外。从这个公理性的假设出发,加上逻辑及概念的延伸,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被主体的某些行为事实所推翻。若行为事实没有推翻假说,那么,行为现象就算被假说解释了。不过,有几个方面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第一,有限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不是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看,所以所有的价值判断、交易成本衡量甚至效率等都是主观之物,这是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二,有限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的,交易费用约束条件变化了,最优选择也可能改变,但不能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选择;第三,理性的有限程度与选择者当时的认知能力和选择空间有关,认知能力一方面取决于选择者所拥有的信息,另一方面决定于他(她)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空间又受到收入、时间、制度、政策和习惯等的约束;最后,有限理性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排斥行为主体的感性成分,而理性选择更是自觉的行为。即使该前提设定不符合行为主体的所有维度,但只要由它推导出来的理论假说不与事实相违背,甚至能多次准确推测行为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暂时接受该理论。因此,对前提假设的选择标准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眼中一般是“可操作”和“可观察”的(Coase,1937)[9]。新制度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交易费用作为分析工具是因为它符合这两个标准,从而才比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更多地了解到什么是“企业的契约性质”和“经济组织的逻辑”。
四、简洁性与精确性之间权衡:交易费用范式的理论选择标准
在讨论完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体系所依赖的前提条件后,我们进一步思考其理论范式。Kuhn(1962)[10]首先把“范式”一词用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提出一套关于“范式——正规科学——危机”的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从而使“一个特定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有完全的配合”。换言之,如果交易费用经济分析拥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沿着过去的传统范式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后来,Lakatos(1970)[11]用“研究纲领”替代“范式”,认为一份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当对特定的研究纲领进行证伪时,该纲领就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科学的形而上学在硬核中隐藏起来,因此不可反驳,但可证伪的理论藏在保护带中。按此逻辑,把保护带的重新调整视为对研究纲领的修正,而对于原有研究纲领的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纲领。Eggertsson(1990)[12]进一步认为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经济分析的内核,而其保护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这样,交易费用经济学在不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核的基础上,引入了竞争、信息、契约以及产权约束从而修正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和零交易成本的保护带,而且将经济分析的研究工具运用到制度层面上,使交易费用约束条件成为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
其实,产权理论、契约理论、法律经济分析、经济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经济学、新社会经济学、新转轨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能够从某个侧面分析某种制度安排,而且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研究范式和边界,因此,我们难以判断某一理论在其中的优势与合理性。交易费用经济学只是运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和工具来分析制度经济现象而已,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对其他理论进行取舍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使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或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理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范畴,因为交易费用是该学科的一个核心。没有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就回归到新古典甚至古典理论的边界内部。我们知道,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把所有的变量都放进去就是一种纯粹的描述而非基于逻辑推导的解释了。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它不需要多么细致,如果太细致的话,那就成地球了,所以理论必然是简化的,但在简化的同时,又不能放弃理论的准确性。换言之,要简化到能够解释现象为止。所以,在确定理论中要包含哪些变量时,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比如,讨论劳动法,研究者就必须对该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条件有详细的考察(何一鸣,2008)[13]。要解释新劳动法的制度绩效,就必须把交易成本放进去,让交易成本发生变动看看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效果出来(何一鸣,2009)[14]。此外,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也是理论选择的标准,但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功能,以确保每个研究者能沿着交易费用理论框架研究下去,不至于出现学术理解上的分歧。关键是,交易费用理论得以成立的重要证据来自该理论在特殊问题上的无数次应用,以及在这些应用中,该理论的含义并没有与实际情况相抵触。例如,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既可以分析劳动合同法,也可以解释反垄断法、破产法、知识产权法等等。然而,如果要通过对这些法律的经济分析来证明该方法的正确性,那就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法律分散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而且它们主要是与特殊的具体问题相联系,而与该理论的检验并不相关,而且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典型案例。如果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或新制度经济学家持续使用并接受某一理论,而且还没有创立出一种逻辑严密、自圆其说的理论来取而代之并得到广泛的认可,那么,这就间接地证明了交易费用经济学该理论的存在价值。任何一种理论的成立都是由人们试图证明它与实际情况不一致而遭到多次失败所得以证明的。只要交易费用理论仍在继续使用,有关证据就会继续增加。但是,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它,而不能把它当做永恒的真理,当实际情况发生改变而它又无法解释时,我们就需要放弃它而另外创造一套新的理论假说出来。
由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数量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而可能的理论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存在交易费用理论与某一实际情况相一致的情况,一定还会有无数的其他理论也与这一实际情况相一致。这交易费用理论所适应的另外一种实际情况无疑可以起到剔除某些理论的作用,但它绝对不可能把这些可能的理论缩减到只是剩下它自己一种,从而独自与这一实际情况相一致。对所有这些与实际证据一致性的理论所进行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虽然对选择所采取的标准应该以简洁性和准确性为出发点,但这两个标准本身就否定了完全的、有目的的简化:交易费用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在某一既定领域内对制度现象进行解释所需要的知识就越少;它越是精确,而且进行解释时所依据的范围就越大,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具体地,当考察交易费用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具有相同可接受程度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其精确度越高,它就越值得信赖。这又意味着不能通过交易费用理论的假设来检验该理论。因为交易费用理论的假设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为了更好地应用它,就需要限定它可以应用的条件,或者限定在各种条件下该理论解释的总的误差范围。但是,这样的限定本身并不是与该理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限定本身就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它也是最有可能被修正和扩展的部分。与此同时,对应于每一特殊情况,不仅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交易费用理论,而且存在着另外一种虽不完善但更为一般化的制度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来自人们为解释前一种简单理论中存在的误差而进行的探索。在这一新理论中,人们可以对某些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的影响加以衡量,而前一种简单理论只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而存在(Friedman,1953)[15]。换言之,交易费用范式其实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和个人主义为内核,再加上交易费用的保护带,得到有限理性的假设从而推导出的一系列理论假说时。当实际发生的证据或环境发生改变而推翻了原来的假说时,不必完全放弃整套交易费用范式,我们只需要对交易费用进行加减变换就可以推导出另外一系列与现存实际一致的理论假说出来,即保持范式内核不变而仅仅修正保护带。
五、实证主义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而非纯逻辑理论推导的科学,需要进行实证检验。没有经过实证检验的理论是不能成为科学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也不例外。不过,实证的方法有很多种,它们主要分为定量和定性的经验研究。前者是通过搜集与理论假说相关的经验数据,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后者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契约案例为理论假说提供证据或通过分析某个契约安排的变换得到一些可反驳的经济学意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初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纯理论的探讨层面上,比如通过定价费用理论研究企业的性质和边界,应用制度变迁理论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以及关于产权起源的经济分析、科斯定理的外部性理论、科层规制结构的资产专用性模型等。但问题是,既然交易费用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应该具有实证主义的传统。而实证主义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一种理论,使之能对现存的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有意义的解释。
据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因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即用以分析的基础假设条件无需证明都是必须接受的。这是与自然科学完全一致的地方,至少在科学方法上是这样。交易费用经济学接受了理性的公理假设,加上理论逻辑,推导出可以被案例或数据推翻的假说,然后检验其经济学含义,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解释交易费用约束下人类最大化私利行为的方法,而自然科学解释的是物体的运行,它们只是解释的对象不同,但方法一样。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困难在于该学科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这比自然科学的难度大得多。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在人为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但对交易费用经济科学中某一特殊现象所作的解释进行检验,很少能通过经过专门设计、希望消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干扰因素的实验来进行。在一般的情况下,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检验。
此外,中国的交易费用经济科学应该更多重视产权管制放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大国中,产权管制放松实践所提供的证据是大量的,而且往往是确定性的,就像有经过设计的实验得到的证据一样,产权管制放松涉及外生交易费用或产权管制成本和内生交易费用或租金耗散代价之间的权衡。但是,产权管制放松实践所提供的案例或数据比实验所提供的证据更加难以解释。因为产权管制放松实践不仅常常是复杂的,而且总是间接的、不完全的,对这些资料的收集也常常困难重重,而且对它们的解释一般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涉及一系列的推论判断,但这些分析却很少能够真正做到把握问题的本质(何一鸣,2010)[16]。鉴于这样的困难,交易费用经济学家的检验工作很容易就退回到纯粹的规范性分析当中。尤其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学和数学有可能成为分析问题的重要工具,以便检验判断推理的正确性,发现理论的含义,确定一系列被假定为不同的理论是否不可能等价以及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差异等。但是,如果要以交易费用经济理论解释现象,而不仅仅是描述行为的结果的话,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同义反复的体系了。因为这些同义反复的体系的实用性本身最终取决于将某一实际问题划归为某类理论的可接受性。
最后,交易费用经济科学的困难与其他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一样,在于构造理论和检验理论之间的把握能力上,即人们对经验研究在理论构建中的作用往往产生误解。一方面,构造理论和检验其合理性这两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每一个部分的那些特定要素,都是由交易费用资料的收集和特定调研者的水平所决定的偶然现象。被用来检验某一交易费用假说的那些因素也可以作为用来构造理论的案例,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在构造理论和检验理论的这两个联系紧密但不相同的部分中,经验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整而详尽的交易费用资料,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而进行概括或加以解释的现实现象的代表,除了在提出新假说时具有重要作用外,还可以用来验证交易费用假说对某一制度问题的分析是否与人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当某一假说与现存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时,我们对该理论假说所作的进一步检验是要将那些事前不知道却可以从实践中观察到的新因素从中剔除出去,并对这些因素加以检验,以了解它们与经验证据背离的原因。为了使后一种检验与前一种检验密切相关,那些被剔除的因素必须与该理论想要说明的问题属于同一类型,对那些被剔除的因素所作的限定也必须足够准确,以便让研究者所作的观察能够证明这些因素是不正确的。
注:本文是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重庆)和第八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东莞)宣读论文。
[1]F.,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2]O.E.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M].New York and London:Free Press,1985.
[3]O.Hart.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4]Barzel Y.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5]Cheung S.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0,(1):49—70.
[6]D.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A.Greif.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912—950.
[8]H.,Simon.Rationality as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hough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4):1—15.
[9]R.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
(4):386—405.
[10]T.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1]I.Lakato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12]T.,Eggertsson Economic Behaviorand Institu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3]何一鸣.新劳动合同法的制度经济学思考[J].珠江经济,2008,(12):63—67.
[14]何一鸣.新《劳动法》之制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6):123—126.
[15]M.,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6]何一鸣,罗必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证据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9,(4):16—19.
F09
A
1007-905X(2010)03-0048-13
2010-03-10
1.何一鸣(1981— ),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2.罗必良(1962— ),男,湖北监利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聘教授(珠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