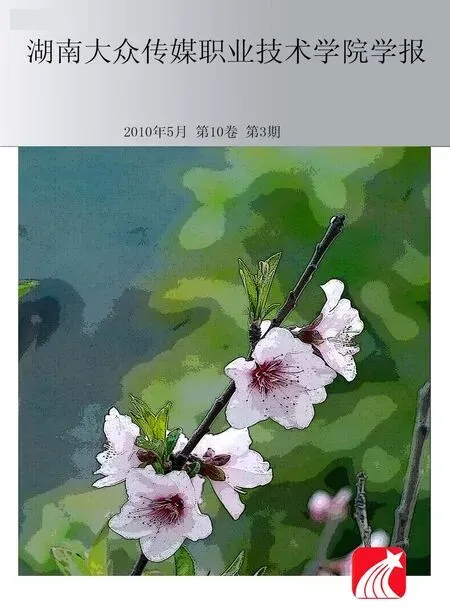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内外有别” 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李彦冰 荆学民
(1. 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2. 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与法律学院,北京 100024)
“内外有别”是我国对外宣传领域一个约定俗成的原则。历史上它曾对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工作起到过积极作用。现在,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和我国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对这一原则带来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外有别”的具体内涵、“内外有别”在现时代受到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寻求这一原则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内外有别”原则的提出与发展
“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原则究竟起源于何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源头上去寻找。
1944年9月,在延安的窑洞中,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和传播开始起步。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吴文焘、沈建图、陈庶、林迈可等人,提出了对外宣传的三个原则:“选择和编发最重要的、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消息必须绝对正确;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力求清晰易懂。”[1]79当时的对外宣传和传播只有英文,只定向针对美国的旧金山地区。这是我们所见的关于党的对外宣传和传播原则的最早论述。其中第三条“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力求清晰易懂”,其中已经蕴含了“内外有别”的含义,可以说这是“内外有别”原则的滥觞。从这一原则可以看出,“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在起源时,只是针对受众的理解程度而言的,同时带有强烈的传者本位意识。当然,我们不能站在现时代用现时代的眼光去要求前人,在斗争激烈的解放战争中,要求对外广播讲求与受众的互动是不现实的。
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人民中国》和《中国建设》等刊物,用以推进中国的对外宣传和传播事业。“从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要求这些对外的刊物各有分工,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总的方针是共同的,那就是:争取对新中国和它各项政策的理解和可能的支持。但每本刊物要针对各自的主要受众。”[2]周恩来在这里又扩充了“内外有别”的内涵,增加了“针对性”这一内容。
此后,刘少奇在1956年5月28日《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中,在谈到对外广播时讲到:“我看对外广播不请外国人恐怕办不好,以外国顾问为基础办起来,他们懂得对象的民族感情,语言也比我们好,政治上由我们主持,语言、技术等等以他们为主,这样,搞它二三年就好了。”[3]由此可以看出,在刘少奇的眼中,对外传播对象国的人民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感情,他们与我们是有差别的,由此才有必要请外国人,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比单纯讲“受众的理解程度” 更进了一步,也更为具体。
1961年7月开始,外文出版社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澄清业务思想”的学习和讨论。沈苏儒认为,这是我国对外宣传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群众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深入探讨了当时对外宣传业务中的主要问题。在这些主要问题中,第一个就是“内外有别”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讨论的结果认为:“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不同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读者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法、语言文字。”[1]81这次业务讨论涉及的“内外有别”的各个方面最广泛也最深入,以后对这一原则的论述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次讨论所确定的框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讨论基本上确立了“内外有别”的内涵。
1967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中讲到:“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4]根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周恩来还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刊物应该原则上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但在内容和风格上应该按照受众的不同而定。对这些受众应该通过实际的接触来加以了解而不是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一个刊物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向世界各地它的特定读者对象进行推广,因为我们不是在对自己而是对世界进行讲话。”[4]
综合这些论述和讨论可以看出,关于对外宣传的讨论从一开始的“照顾受众理解程度”到对刊物“针对性”的强调,再到1961年外文社涉及“读者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法、语言文字”的讨论,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对“内外有别”原则的深度开掘,这是一个从笼统到具体化的过程。
必须承认,建国后所确立的这些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也是正确的。但众所周知,上述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与日益紧张的政治形势同步的。“1957年反右斗争否定了对外广播特殊性以后,对外广播内容不考虑国外听众的多种需求,片面强调‘以我为主’,甚至把国内宣传的浮夸风作法搬到对外广播宣传中,引起外国听众的不满。”[5]这种“左”倾错误发展到“文革”阶段达到极致。把“‘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宣传目的,把对外宣传对象确定为‘马列主义左派’,任务是要通过左派‘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球’。”[6]我们国家的对外宣传与传播走上了极左的道路,把周恩来等人确定的“针对性”和“照顾受众的特殊情况”等原则弃之不顾,完全把国内宣传的一套照搬到对外传播与宣传上,致使对外传播的效果很差,这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可见一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65年的来信曾达到28万封。但是1970年下降到2万封,而且几年都在低谷中徘徊。”[7]
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内外有别”的原则被再度确立起来。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外外有别”的原则。“胡启立特别强调加强对外宣传针对性的重要性,指出目前存在的最常见的一个缺点就是把对内宣传的东西简单地照搬到国外。他说,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在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直至宗教信仰、风俗民情、语言习惯都不同。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千篇一律,不加区别,就很难做到促进相互了解。”[8]
1990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外国人和海外同胞,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都和我们有很大不同,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必须认真研究这些特点,区别对待,不能照搬国内的方式方法进行工作。”[9]
由上述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全国外宣会议所强调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没有超出“文革”前对“内外有别”内涵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改革开放后在外宣方面所坚持的原则基本上是对过去所确立的“内外有别”原则的“复归”。若要说有发展,也是“外外有别”原则的提出,即不仅认识到“内”和“外”的差别,还要认识到即使“外”与“外”之间也是有差别的。
综上所述,从建国初期探索建立“内外有别”的原则到“文革”后主动恢复这一原则,再到历年的全国对外宣传会议,“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在内涵上集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传播对象国受众的差异性。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情感、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这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接受心理状态。二是强调针对性。针对性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对传播者来说,要求进行宣传和传播活动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媒介定位进行区分;对传播对象国的受众来说,要对他们按照不同的标准(诸如地域、文化、语言、种族等)进行区分,发送信息的文本内容、目的、方法也要进行区分。将这两点衔接起来,就是周恩来所讲的“每本刊物要针对各自主要的受众”。因此归纳起来,“内外有别”就是“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通过设置职能相异的内宣与外宣机构,发送不同的信息文本,以期取得不同的传播效果。”[10]
二、新时期“内外有别”原则的困境
正如上文所述,建国初期探索建立、“文革”后重新恢复的“内外有别”原则,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初期践行这一原则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因为当时“特有且高效的政经制度将国内受众建构成为一个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既是物质生活的共同体,也是精神生活(语言文化、价值信仰和感情)的共同体——从而跟境外受众区别开来”。[10]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操作的。在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划分依据的世界中,中国与世界的相互隔绝是常态,交往则是非常态。因此,国外受众在隔绝状态下,只有通过中国的外宣机构来了解中国,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有组织的国外受众。国内外的大众传媒是有可能在这些有组织的国外受众心目中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尽管这个共同体的形象不一定稳定,也不一定积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比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更剧烈也更深刻。这对我国对外宣传带来了巨大冲击,对我国一贯坚持的“内外有别”原则也是一种挑战。具体来说,这种挑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内外有别”的原则失去了存在的内在根据。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当时特殊的物质经济条件为“内外有别”原则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诸多转变:原来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上存在主体多元化,利益也变得多元化;原来封闭的国家共同体转变为开放的、需要大多数人参与的共同体;原来领导者不知受众的知情权为何物转变为要主动地披露信息,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等。这些转变要求领导者把关注外在的地理距离转变为关注人的心灵深处的变化。对于领导者来说,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如果不关注个体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政治信息需求,仍然采用机械的“内外有别”原则来传递信息,势必事倍功半。[10]
第二,政府的宣传管理方式不仅没有适应转型社会剧烈变化的要求,甚至把“内外有别”原则作为诸多突发事件或者丑闻的挡箭牌。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计划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同构”逐渐演变为政治与经济“异构”。原有的一套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因此,整个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近年来各种突发事件的出现就是这种新秩序在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和集中体现。
作为发布信息的权威部门,面对突发事件,我国的信息宣传机构在多数情况下采用掩盖事实真相的方法来应对,在2003年“非典”之前尤其如此。2003年后,情况有所改变,将掩盖事实真相转变为有计划地披露信息,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应对是被动的,是被事件的爆发推动着的。“内外有别”的外宣原则也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中。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信息传播的管理部门应该及时公开披露信息,以满足国内外受众的知情需求,而不能再采取“捂”和“盖”的办法,甚至拿“内外有别”原则做挡箭牌。2003年“非典”初期,对外迟迟不发布消息,或者发布否认疫情发生的信息,企图掩饰事件的发生,导致疫情的大面积流行。面对强大的内外压力,非典后期才逐步转为主动披露信息。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亦是如此。纵观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在对外传播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瑕疵,而这些与对外宣传部门所坚持的已经脱离其原本内涵的“内外有别”原则有关。
第三,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在诸多方面显得不合时宜。网络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在它的推动下,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任何一国的信息传递已经不再是一国的事情,信息的全球瞬间传递已经获得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原来阻碍信息传递的距离因素已经不复存在。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距离这个曾经是共同防御能力中最可怕最难克服的东西,现在也失去了它的大多数意义。”[11]
网络社会给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带来革命性变革。在传统媒体时代,尽管有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但它们都是组织化的,在信息传播管理者的眼中,这些传播媒介是可以被宰制的,而且这些媒介从诞生之初便被纳入管理范围,经过上百年时间,已经形成行政的、法律的、政治的等一系列完善成熟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因此,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一个突发事件可以给信息管理者留下足够的信息编制和操作时间。但是,网络社会的崛起“取消了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此外,当信息以电速运动时,时尚和传闻的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世界。”[12]在此情况之下,强调对外传播的“内外有别”原则在实践上已经无法操作,尤其对于突发事件来说更是如此,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意味着它将在全球的瞬间传递。一方面,原本中国与西方的传播体制就有很大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很明显,这已经形成双方信息解读上的障碍,倘若此时坚持内外传播内容的不一致,就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我国的误解,甚至会对国家和政府形象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在信息全球传递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再去强调国外受众的差异性、传播技巧的内外不同,已经意义不大。
相比于传统媒体条件下的传播观,网络社会使“内外有别”原则产生的理论前提不复存在。“内外有别”原则的产生以传者本位的传播观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传统媒体条件下,信息传播的控制权是完全由国家的外宣部门垄断的,除书籍、报纸、广播、电视外,没有其他的大众信息传播渠道。因此,在此条件下,“内外有别”才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对于国内受众来说,对内宣传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体制化的传媒把信息传递给受众。对于国外受众来说,他们只有通过中国当时现有的传统媒体了解中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种传播渠道的垄断性和独占性使国外受众在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面前也变得组织化了。因此,采用“内外有别”方法,不会遭到国外受众的激烈抵抗,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渠道了解信息。
网络社会的崛起也导致传者本位的传播观受到挑战。在网络传播条件下,信息传播的自由性、交互性和非宰制性,使受众行为与传统媒体条件下的受众行为有着很大的区别。网络所提供的平台使得平日里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获得充分自由,因为在“使用”与“满足”的条件下,受众的“能动性是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接触’的范围之内,因而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13]当然,在网络时代,受众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被动接受地位,还成为了能动的传播者,他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这样的活动和行为体现的是人作为一个能动的实践主体所具有的独特性。
面对主动寻求信息并拥有信息发布能力和可能性的受众,而不是传统媒体条件下被动的、组织化的受众,我国的对外宣传与传播如果再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来传播信息,将受众按地区、种族、文化等进行区分,并发送不同的内容,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时的“内外有别”极有可能演变为信息的“内外不一致”。也就是说,对外传播与宣传机构按照“内外有别”原则所编制并加以传递的信息与受众主动搜寻所获得的信息是不一致的,这会进一步加剧受到自由主义新闻观熏陶和影响的西方受众对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中国信息传播机构的不信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学者张国良所言:“最好的效果来自于实事求是的传播……没有任何必要遮遮掩掩。”[14]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现实,网络社会的崛起所带来的对信息发布时效性的要求和传播观的变化,都对对外宣传和传播的“内外有别”原则发起了挑战。面对此种情况,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一原则的未来发展。
三、“内外有别”原则的出路——战略而非战术
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很多人对此抱以乐观态度,认为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取消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建立起来的。因此,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依然是我们行为做事的出发点,种族、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世界范围内也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差异在短期内无法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原则所强调的传播对象国受众的差别(包括地域、文化、语言、种族等)和针对性原则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因此,“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和传播原则依然会有用武之地,至于它以何种形态出现,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一原则所受到的诸多挑战入手来寻求对策。
笔者认为,只要在实施“内外有别”原则的时候将它当作一个对外传播的长远战略原则来实施,而非作为贯彻在每一项具体传播活动中的战术原则来实施,这一原则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第一,要正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尤其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受众的分化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关注受众的多元意识和内在的心灵变化就变得尤其重要。第二,要对“内外有别”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区分。比如对重大突发事件,就无法也不可能运用“内外有别”原则来进行信息传递;而对于介绍中国文化、民族风俗等类型的信息,“内外有别”原则依然有它的用武之地,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种族对中国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第三,信息传播的管理部门要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改变传者本位的传播观,正视网络社会崛起的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传播管理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沈苏儒.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2] 爱泼斯坦. 周恩来总理和对外书刊出版(上)[J]. 对外大传播,1998(Z1):1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72.
[4] 爱泼斯坦. 周恩来总理和对外书刊出版(下)[J]. 对外大传播,1998(3):16.
[5] 方汉奇,陈业劭.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67.
[6] 张永德. 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反思[D]. 武汉: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3:11.
[7] 谢良鸿. 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J]. 新闻战线,1999(10):27.
[8] 我国对外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N]. 人民日报,1986-12-04(3).
[9] 要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N].人民日报,1990-11-03(1).
[10] 阎立峰. 外宣“内外有别”原则:地理与心灵的辩证法[J]. 现代传播,2008(4):46.
[11]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
[12] 罗杰·菲德勒.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81-82.
[13]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5.
[14] 潘天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访全国政协委员张国良[J]. 对外传播,200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