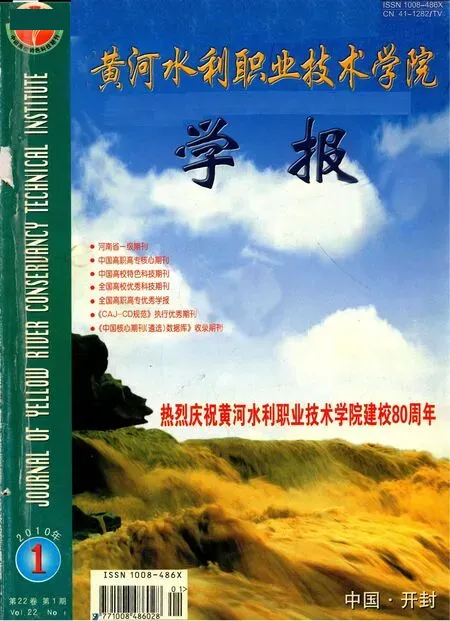鲁迅与安德列耶夫创作思想之比较
崔洁莹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0 引言
列·安德列耶夫①在本文的引文中,安德列耶夫又被译作安特来夫、安德烈夫。(1871-1919)是19、20 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坛上风格独特的一位作家,而鲁迅是第一位接触其小说的中国作家。 早在1909 年,鲁迅就翻译了安德列耶夫的《谩》、《默》等作品,并收入《域外小说集》中。虽然这本开直译先河的小册子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寥寥,但是鲁迅却没有停止对安德列耶夫的推介,他甚至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植入了安德列耶夫的影子。 20 世纪30 年代,鲁迅曾对冯雪峰谈到,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倒是安德烈夫有些影响”[1]161。 在20 世纪初的中国, 安德列耶夫能够被鲁迅注意, 有其传承了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传统的原因, 安德列耶夫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作家那里继承的,也正是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所亟待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鲁迅进一步发现了安德列耶夫异于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独特之处,并与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留着安特来夫式的阴冷”[1]161,而在鲁迅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亦分明可看出“安特来夫式”的痕迹。
1 文化转型错位下的影响
1.1 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作家
从1898 年的《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到1908年的《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安德列耶夫经历了10年的创作高峰期,俄罗斯文学也从“黄金时代”转入了“白银时代”,所以安德列耶夫可以归入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的队伍。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并不简单的是一个次于“黄金时代”的文学时期,它体现了俄罗斯复杂的文化转型时代的风貌。 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开始, 作家们逐渐意识到托尔斯泰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已无法完整地表现出他们在世纪之交的全部体验,于是象征的手法开始运用于文学创作,由此开始了整个“白银时代”对艺术的探索。 可以说,“白银时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过渡到现代主义的探索。
1.2 中国的文化转型
与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在时间上几乎同步,中国也酝酿了一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化转型,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帷幕。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作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到“五四”时期,就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热”。 1915 年《新青年》杂志创刊, 在刊物的最初几期就有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的相关作品和介绍[2]71,之后,李大钊、沈雁冰等人也向中国读者大力推介俄罗斯作家。与此同时,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安德列耶夫作品的翻译也逐渐趋向系统化[2]8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位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作家当中,除安德列耶夫之外,均为活跃在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在时间上更为接近的“白银时代”作家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响。 这一现象与当时中国新文学的总体要求是紧密联系的。
1.3 鲁迅对译介对象明确的意向性
早在1909 年的《域外小说集》中,鲁迅就对译介的对象有着明确的意向性,即作品要有助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2]68。 到了“五四”时期,处于新旧文化重要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更加期盼新社会的到来,然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国作家自然将目光投向国界之外,以“别求新声于异邦”[3]。 在吸收外国文学养分的过程中,中国作家发现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 正如王统照在《俄罗斯文学片面》中写的那样:“如德的文学,偏于严重。 法的文学,趋于活泼,意大利文学优雅。 而俄罗斯文学则幽深暗淡,描写人生的苦痛,直到了极深秘处,几乎为全世界呼出苦痛的喊声来。”[2]84这种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以及民族命运的情怀,正是“五四”时期“为人生”一派所极力倡导的。于是,最好地体现了俄罗斯文学这种传统的19 世纪文学便格外受作家们推崇。
1.4 俄中两国文化转型的同步与错位
由此可见, 在时间上大致同步的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实是错位的, 在俄罗斯作家们开始用象征表达经验的时候, 呼唤新时代的中国作家还需要首先确立“人”的价值,而这,已不再是“白银时代”作家们的主要任务。因此,在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闪耀着的多是19 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偏爱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在众多“白银时代”的作家中,安德列耶夫相对更为中国作家接受, 这是由于安氏本身就游移于流派之间。 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自命不凡自居正宗的颓废主义者那里,我是一个不屑一顾的现实主义者;而在那正统的现实主义者看来, 我是一个可疑的象征主义者。”[4]91他受高尔基的影响,在俄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也做过“海燕”式的呐喊,但他内心又被真理与自由的矛盾所折磨,无法达到内心的和谐,于是在作品中呈现出了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风貌。因此,安德列耶夫一方面以其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符合了中国新文学“改造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因其复杂的创作思想引起了鲁迅的关注, 并对后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2 “为人生”——鲁迅与安德列耶夫的主导创作意向之比较
2.1 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情怀
如前所述,俄罗斯文学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以及民族命运的情怀正好符合中国“五四”时期文学“为人生”的需求。 而作为最先接触安德列耶夫的中国作家,鲁迅之所以受到安氏影响,也有着这方面的原因。 在《<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中,鲁迅谈到安德列耶夫将“19 世纪末俄人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了作品里面[1]162。 而在处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 鲁迅也强烈地感到中国文学需要关注“人”的生活,并应学习俄罗斯文学,从“为人生”的意向出发,从“社会批判”和“民族文化心态批判”两个方面向纵深拓展[5]。 然而,在“为人生”这个大的文学主导意向之下, 鲁迅发现了安德列耶夫作品更为深刻的内涵。
2.2 悲剧心理和变革倾向
在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影响之下的安德列耶夫,从描写“小人物”的悲剧开始文学创作,但他逐渐从对人生活的观照提升到了对人生存状态的观照。作为“白银时代”的作家,安德列耶夫有着文化转型期作家极为复杂紧张的情绪,这使他尤为关注社会生活对个人心理的作用。 《红笑》描写日俄战争对人的摧残,却并没有在渲染战争场面上花费太多笔墨,而是用“红笑”这一怪诞恐怖的形象映射出战争留在人们心理上的巨大阴影。 小说用片断的方式构成,既象征了战争中人们破碎的生活,也表明描绘社会事件的完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其中的心理活动。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虽然批判了沙皇对革命者的血腥镇压,但作者在五个被绞死的革命者之外,又加入了杀人犯和江洋大盗的形象,这使得小说超越了歌颂革命者的范畴, 将人面临死亡时的心理承受作为了关注的焦点。在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是极为紧张的, 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着恐怖阴森的调子(如“红笑”的意象和《瓦西里·菲韦斯基这一辈子》中多处对夜的描写)。而在处于比“白银时代”更为彻底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鲁迅同样感受到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张心理,因为在呼唤变革的时代,改革者的第一声呐喊必然受到腐朽社会的阻碍。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就是讲述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紧张心理的故事[6]48。 作品中的狂人自始至终与环境保持着极为敌对的关系,他在周围人的目光中发现了“吃人”二字,这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礼教最为精辟的认识。 于是,与时代对立的狂人成为民族命运的预言者,但他又必将因其预言者的身份遭到迫害。 在《红笑》中,被战争摧残的两兄弟一个彻底沦为疯子,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另一个试图在疯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疯狂”作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虽没有像狂人那样象征了真理, 却从反面道出了作家的意旨。 而《瓦西里·菲韦斯基这一辈子》 中那个一生出来就是疯子的白痴则带有更多恶的意味。 他的出生仿佛就是一种凶兆,从此带给瓦西里一家无穷无尽的灾难。在这里,“疯子”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预言家,他将生活的残酷面一一揭示了出来,也给作品蒙上了阴森恐怖的色彩。 可以说,《狂人日记》这部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影响的作品, 也有着安德列耶夫阴冷的调子。
2.3 狂人形象及其历史理智
无论是《狂人日记》,还是安德列耶夫诸多描写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疯狂的作品, 都恰恰反映了对理智的呼唤。正常人变为疯子,这首先就是对社会现状的否定,对延续下来的历史理智的怀疑。安德列耶夫在谈到《红笑》的创作意图时曾说:“《红笑》应成为对理智的一个独特的赞颂——这种赞颂, 该说成是‘从相反方向’的。……理智,它不愿也不可能与战争妥协,于是就毁灭,像哨兵在岗位上一样毁灭。 这种理智,是未来的理智……”[4]98而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哥哥辩解吃人是“从来如此”,狂人随即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正是狂人对历史理智的质问,是《红笑》中的士兵用疯狂来完成的抗议。 同样,在作品《墙》中,麻风病人第一声反抗就是:“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这让人想到狂人最后那句“救救孩子”的呼唤:孩子作为未来理智的象征,是在绝境中的人最后要紧紧抓住的希望,未来的理智要战胜历史的理智。 在这个意义上,安德列耶夫与鲁迅都是进化论的信奉者。
3 阴冷的风格——鲁迅与安德列耶夫创作风格之比较
3.1 安氏的阴冷风格及其根源
鲁迅在致许钦文的信中对安德列耶夫有着较为详细的概括,他认为,安德列耶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 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1]162。 这一深刻的洞察,源自于安德列耶夫与鲁迅本人在精神内质上的相似性。
安德列耶夫一生都关注着命运对人的压制,以及人对命运的抗争, 这种抗争的悲剧性使得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形成了阴冷的风格。在《红笑》中,使主人公失去双腿的那场战役竟是同一个军的两个团在慌乱中互相打击的结果。 消息传出去后,士兵们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个荒唐的误会。 没有人愿意面对导致众多战友死伤的战役不是源于一个崇高的使命,而是出自一场荒唐的闹剧的现实。 在此,安德列耶夫无比尖锐地质疑了牺牲的意义, 然而这种质疑又透着浓烈的悲观气息:对意义的追寻扑了空,士兵们出生入死的奋战只能导致疯狂。 在鲁迅曾翻译过的小说《沉默》中,伊格纳季神父的女儿卧轨自杀,小说没有写出她自杀的原因, 却着重描写了伊格纳季神父在女儿薇拉死后的巨大沉默中悲痛恐惧的心理。伊格纳季神父想知道女儿自杀的原因,这是暗地里为女儿的死寻找意义,然而他寻找的结果却是沉默。鲁迅称这篇小说“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与神秘教派所说略同,若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而可怖亦尤甚也”[7]。 薇拉为自己选择了死寂的沉默,却给伊格纳季神父留下了“生者之默”。 这种沉默是意义的虚空,是安德列耶夫对人生的悲观。
3.2 鲁迅作品中“安特来夫式的阴冷”
同样由质疑而导致的悲观出现在小说《药》中。夏瑜为华老栓们牺牲了生命, 而流出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华老栓买去给孩子治病,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挽救华小栓的生命。最终,烈士的母亲与华小栓的母亲在拜祭的坟地相遇。 李欧梵曾分析过《药》的象征意味,夏瑜的“夏”与华家的“华”正好组合成代表中国的“华夏”,可见夏瑜与华小栓两个中国青年是一体的,他们本应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现实却是牺牲了其中一个,以徒劳地拯救另外一个[6]62。 夏瑜的鲜血无法启迪民众的智慧,也不能挽救民众的生命,烈士的牺牲变得没有意义。 在夏瑜牺牲的地方,鲁迅从围观者们伸长的脖子上发现了深深的悲哀。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到因为“须听将令”,往往在作品中用了曲笔,在夏瑜的坟头上平添一个花环,避免作品太过消极[8]。 然而当夏瑜的母亲看到花环,仍然做出了夏瑜不甘含冤而死的理解,并认为害死夏瑜的也必将遭到报应。 结尾处那只乌鸦没有显灵,最后却又自顾自地飞走了。 这一出乎意料的结局象征了人面对命运时的无能为力。前文已提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中明确指出,《药》的收束,分明留着“安特来夫式的阴冷”,表明了安德列耶夫的悲观厌世情绪对这部作品的影响。
4 结语
鲁迅对安德列耶夫曾有过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俄国作家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表现之差, 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9]安德列耶夫正是以对人的生存的关注, 将社会生活投射在人物的内心加以观照,从而达到“灵肉一致”的境地。 在这一点上,鲁迅吸收了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思想。 然而两位处在文化转型期的作家又都从来没有达到过内心的和谐,他们一生的创作思想难以用简单的流派概括。 但相同的“为人生”的创作意向、内心愤世疾俗的情绪,使得他们的作品又呈现出相似的矛盾性,构成了对当时社会以及人生失望的呐喊。
[1] 杨里昂,彭国梁.鲁迅评点外国作家[M]. 岳麓书社,2007.
[2] 陈建华. 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鲁迅. 摩罗诗力说[M] //鲁迅. 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8.
[4] 周启超.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汪介之. 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M].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39.
[6] 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M]. 尹慧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 鲁迅.《域外小说集》杂识[M] // 杨里昂,彭国梁.鲁迅评点外国作家.岳麓书社,2007:163.
[8] 鲁迅.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7.
[9] 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M] // 止庵.现代小说译丛:1 集.新星出版社,20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