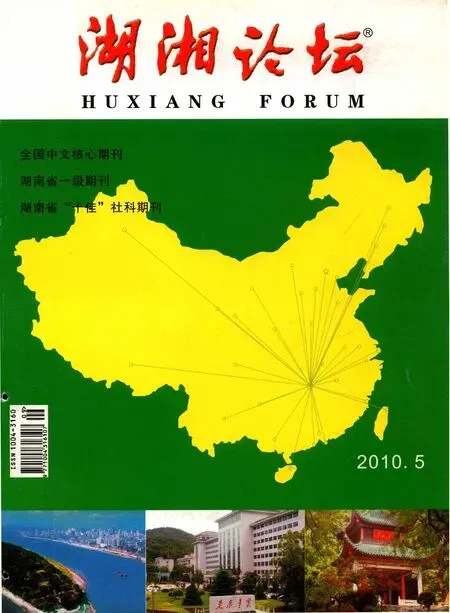论佛教对于隐逸的超越意义*
——以晚唐诗人为例
胡遂,肖圣陶
(1.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 1008 2;2.长沙市广益中学,湖南长沙4 1001 4)
论佛教对于隐逸的超越意义*
——以晚唐诗人为例
胡遂1,肖圣陶2
(1.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 1008 2;2.长沙市广益中学,湖南长沙4 1001 4)
身处晚唐时代的一部分失意文人最终选择了归隐渔樵、躬耕田园、寄情山水的道路,当了隐士或准隐士。应研究佛禅思想对诗人们具有以道统的意义来支撑其精神,并帮助他们获得身心的自由超越与心灵之止泊安定的现象。
佛教;隐逸;意义
一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引了清代著名传奇《桃花扇》中的(哀江南)(离亭宴带歇指煞)曲“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一段以后,曾经这样说:“这固然是家国大恨,也正是人生悲伤。沧海桑田,如同幻梦;朱楼玉宇,瓦砾颓场。前景何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是没有答案的渺茫,也不可能找到答案。于是最后归结于隐逸渔樵,寄托于山水花鸟。”[1]同样,身处末世的晚唐诗人们在梦醒之后,究竟往何处去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在呢?虽然颇有一些耽缅于声色犬马、风流豪华以麻醉自己心灵者,但这毕竟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做到,因为声色享受是需要财力的。而大部分贫寒出身的读书士子,连衣食都尚且难以周全,又何来金钱挥霍享受呢?因此,声色享乐对他们而言是明显不现实的,于是他们就只好走归隐渔樵躬耕,寄托于山水自然这一条路了。也许正是这一缘故,晚唐时代的隐逸诗特别多,隐士与准隐士也不少。
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有唐一代隐逸终老的诗人4 6人,而晚唐时期就有2 6人。晚唐不少著名诗人,如许浑、方干、陆龟蒙、司空图、郑谷等都是隐逸家山终老的,还有一部分人虽未隐逸山林,但其诗作同样体现了对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与羡慕。而这些隐士与准隐士们,又大多是栖心于佛禅的。也正缘于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晚唐隐逸诗时,就不能不涉及到佛禅思想与诗人及诗作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会发现在诗人们的隐逸生活中,仅有形式上的隐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具有“身隐”而非“心隐”的意义。如果不从精神上解决根本问题,即使身隐也很难隐得安稳,有时往往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烦恼又产生了。再进一步说,面对着隐逸所带来的物质生活贫乏的现实,各种各样原来始料未及的矛盾苦恼也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因此,要保证“身隐”的安稳,就必须要有“心隐”的支撑。概言之,身隐只具有隐的意义,心隐才能具有逸的意义。逸,有放逸、超逸等意义,在晚唐诗人的隐逸实践中,二者都有。一方面是放逸于统治者的管束,同时也是放逸于封建礼教、纲常伦理、教条规范等;另一方面是超逸世俗社会的眼光,超逸世俗人生的价值标准,从更高层次来看,是逸出世间,进入出世间。
二
那么,佛教对于隐逸的超越作用有哪些呢?我们认为,首先,佛门同样可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社会学家马斯洛曾经指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宿需要、尊重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就大部分不遇不达的晚唐诗人来说,在这黑暗动乱的社会,生理的需要是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攫取美食,拥有美女,更不能乘肥马衣轻裘;由于社会的动乱不已,处于“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2]的险恶环境中,安全的需要当然也得不到保证;而或屡试不第,或宦海沉浮的人生遭遇,饱经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世俗白眼,社会的尊重更不可能做到;至于通过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以垂名青史、画图凌烟的自我实现更是成了泡影。那么,身处如此困穷之境的晚唐诗人又怎样对待这五种需要呢?还有他们的高峰体验到哪里去实现呢?佛教给他们指出了现实可行的途径,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法门。在佛门里,他们一方面可以平息、平衡这种因生理需要不能实现、安全需要不能保证所带来的烦恼痛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皈依佛门、勤修佛法、积累功德使自己同样不失去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同样可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尤其是处在几乎全社会自上而下都信奉佛教的时代环境中,对于一个隐逸林泉、不慕荣利、不务竞驰、淡泊自守的读书士人来说,栖心释梵,虔诚修习,这确实是一种体现自己道德崇高、修养不凡、胸襟不俗、气质超拔于尘俗的好办法。这样不但能够抬高自己身价,而且也可以满足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佛门不但可以栖隐,而且可以“超逸”。有此自我实现的超逸,这些退居林下、不乐仕进的士子们也就完全可以平视甚至傲视红尘浊世中那些仗势弄权、洋洋得意、乘肥衣轻、颐指气使、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官场俗吏了。彼以彼的爵禄自夸,我以我的道性自高,在这些红尘俗吏们面前,不但不艳羡不羞愧,不屈辱不萎缩,相反还颇有一份耻与为伍的鄙夷与高傲。由此可见,因为有了佛教的支撑,隐逸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以内美轻外物,以道德学识来对抗势位爵禄,从而在权势财富面前保持士人的人格尊严”[3]的理论思维策略。
其次,佛门具有以道统的意义来支撑隐逸的作用。我们知道,隐与逸,虽然关系密切,但又处在不同的层面上。隐是退避,只有消极意义,而逸则是超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世俗之人,包括大部分儒者,他们基本上都是依附国家政治统治亦即政统者,当他们遭遇到挫折失败或者深感失望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离异政统的心理或者意识。这正如徐清泉先生在《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从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看,隐逸人格精神主要体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对封建政治现实始终抱有一种疏离、怀疑、厌恶、解剖、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二是总是力求与主流文化及人伦群体划清界限或保持距离;三是大多具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自由及回归心性放真的内驱力与本能冲动;四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合乎道统(而不是政统)、合乎理想的真善美“天人合一”至高境界。”[4]那么,就晚唐诗人的具体情况而言,在脱离了对于政统的依附之后,士人往何处去才能重新找到其心灵归宿与精神支柱呢?如果说这种转换还只能满足人们要求归宿的心理需要的话,那么,出于人所特有的超越心理,他们会进一步思考:是否有比政统更高的价值所在呢?进言之,政统本身又是依附于什么呢?历史表明,政统不但要依靠军事、经济的力量,而且也必须依靠思想文化的力量,很明显,虽然政权是由“马上得之”,但却未必能于“马上治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董仲舒成为万世帝王之师的意义。他以阴阳五行、奉天承运等作为支撑维持封建政统的道统,对从西汉武帝以来至后世的封建统治之巩固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缘于此,韩愈、朱熹等人,欲维护封建统治,必须先从道统上找原因、下功夫。也正缘于此,理学将封建道统直接建立在世人心中,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封建王朝政权得以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道统,乃是置于政统之上的更高层次。士人欲脱离政统进而超越政统,必须有比政统更高明者可依附,那就是道统。而儒、释、道三家的道统建构其所以不相同乃是因为它们的理论核心不同。儒家的理论核心在“仁”与“礼”,道家的理论核心在“道”与“天”,佛家的理论核心在“空”与“寂”。如果依附儒家道统的话,就始终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他人,无论你怎样独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仁”与“礼”而坚持自己的操守。道家的道统在“道”与“天”,对既派生万物又处于万物之中的“道”以及最能体现“道”的“天”亦即自然最为倾心,认为只有让自我合于“道”合于“天”,才是最高境界。佛家的道统乃是自我的内在心性,因此它最无所依待,最具自我独立性。并且,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一种相对道家而言更为出世的哲学,它既是彻底解脱的哲学,也是完全超越的哲学。它的出世正是为了超世,这在大乘佛教尤其是涅槃学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佛教对永恒的、幸福的彼岸世界,或者说是理想的、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正意味着对黑暗污浊、虚妄不实的现实的人生和世界的否定与超越。由于社会时代的种种因缘关系,晚唐诗人大部分都将精神寄托于佛门禅寺,因此也多以佛家道统作为自己的凭依,正是在道统这一意义上,佛教为晚唐诗人的退隐提供了精神超越的方便,开启了精神超越的法门。
三
众所周知,佛家的理论核心在“空”与“寂”,空、寂本不可分,但强为分之,境多用空,性多用寂。而性与境本来也是一体两面,按照大乘佛教唯识学理论即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识有境无”,也就是说,境乃是众生心识所变现,一切法也是心识所变现,依心识说故有境有法。而心识也分真心与妄心,真心为本原清净之心,是众生通过修行得以成佛的根据;妄心即是为外界客尘染污之心,正是种种染污使其产生烦恼痛苦,因此妄心乃是烦恼的渊薮,痛苦的根源。而众生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去掉妄心上的客尘染污,使其恢复本原清净之心,回归本原清净之性,如此,则真心显现,即是解脱,即进入涅槃成佛境界。禅宗六祖慧能《坛经》说:“莫起诳妄,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5]真如自性,即是般若智慧,即能观照万法,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由此可知,性有能指的意义,而境则有所指的意义。但此境亦可以说是由真如之性所生起,故此境乃是空境。概言之,空境乃由空性而来。“空”本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本性。佛教认为,从存在论上说,一切事物由于都是由一定的原因与条件构成的,因此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其实质只能是空。但众生由于妄心所蒙蔽,并不知包括自我在内的事物其本性只能是空,反而执空为有,执虚为实,遂起心动念,向外攀求,并由种种贪欲而生出种种烦恼痛苦。因此,要去掉妄心,回归真心,首先就要能了知事物皆为虚妄不实的空性。而能以智慧观照事物者,谓之空观。空观者,即能以佛教认识论证悟世间万物无不是空的存在本质,从而把握了佛教的根本真理。而此空观亦即是一种佛教修持方法,以此空观观照客观外物,心不会产生出其他不具空观的众生那样的见他人拥有珍宝财货便或生艳羡,或生嫉妒,或生掠夺之心等种种妄念,也不会见种种娇好曼妙的美色而生起贪欲邪念,因为,以空观观照之,珍宝财货也好,女色美貌也好,其实质都不过是空,是虚妄不实。故眼中虽有,但心中却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6]眼中有的乃是色,心中无的乃是空。世人因妄心故,只见其色而未见其空,故生贪欲,故生迷恋,故生出各种因攀求而产生的烦恼痛苦来。而禅人因真心故,既见其色,更见其空,故不会再执着贪求,从而也不会产生出烦恼痛苦。而修持者由于能够具备空观,体悟空性,契合空理,也就进入了生命的澄明之境——空境。空境也就是佛教得大自在、大涅槃的最高境界。达致空境,是生命的真正回归,也是精神一种质的飞跃。空境中,了见自己的本心本性与外界的山河大地、社会人群,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常不住,不一不异,无差别,无物我,甚至也无能所。内与外,表与里,都只是一片朗然澄澈。所谓“宝月当秋空,高洁无纤埃。”[7]“心灭百虑减,诗成万象回。”[8]“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沈。”[9]“山影暗随云水动,钟声潜入远烟微。”[10]“隔岸青山秋见寺,半床明月夜闻钟。”[11]等都是晚唐隐逸诗人们在得道之后对这种超越尘俗之朗然清净空境的形象展示。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思想修养、境界觉悟方面都确实超出于世俗凡尘之上。
如果说,空偏于对境的解释的话,寂则偏于对性的映证。性,作为万物皆有的自体本性,首先是指共同的法性共性而言。心性虽然是指众生心的本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法性的一种。据《涅槃经》说,释迦牟尼当日在雪山时,帝释天曾经化身为罗刹来考验他。帝释天先说了两句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释迦佛祖说,好呀,请您说完下面两句吧,我愿意终生做您的弟子。帝释天说,我现在饿得很呀,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释迦便说,请您说下去吧,我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你吃。于是帝释天就说完了下面两句,即:“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释迦听后,马上投身于地,请帝释天吃。帝释天即复为原身,双手将释迦接住。其所以释迦不惜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聆听帝释天此偈,乃是因为此偈充分体现了大乘佛学的根本要义。所谓生灭法者,就是时时处在变动不居的变化当中,即一种无常无住的状态。而寂灭则是如如不动的状态,它既无所谓生,也无所谓灭,既无所谓常,也无所谓不常,既无所谓来,也无所谓不来。所谓“八风吹不动”,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对其产生作用,都不能使其变化。只有在这种状态、这种境界下,才能得大自在、大快乐。故曰“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维摩诘经·弟子品》说:“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义。”[12]这种状态,是一种真心而非妄心的状态,它属于无为法而非有为法,是与真如佛性一体的。在许多佛教典籍中谈到人心性时,常常给出性以“性本自寂”“性本自净”“人性本寂”“人性本净”之类的界定,其实都是一回事。概言之,“本寂”是从本性不动摇角度而言,“本净”是从本性不染污角度而言。禅宗七祖神会在谈到心性时说:“我心本空寂”“本自性空寂”。[13]中唐高僧华严五祖宗密解释说:“空者,空却诸相,犹是遮遣之言;唯寂是实性,不变动义,不同空无也。”[14]由此可见,空是指远离一切事物的形相,即前文所论之空观,寂是指寂静不动的如如实性,由于它处在不为外物所动摇的状态,因此能够超越一切事物的形相区别。佛教经常认为,众生性如水,情如波,性本寂静不动,情则时时摇曳动荡不已。性与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认为已发为情,未发为性,情是人与外界接触感于事物而生起的带有冲动性的心理反应,通常指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欲又有四欲,五欲,或六欲之说,如五欲即指财、色、名、食、睡,即金钱欲、性欲、名誉欲、饮食欲和睡眠欲。由于情是是非之主,利害之根,有干扰破坏佛性的作用,因此,众生必须返回自己的内心,自寂其心,自净其性,只有实现内在超越之后,才能实现外在超越。从而不为外在苦乐所动,寂灭种种贪恋欲求,葆有清净寂灭的真如本性。
由此可见,寂者寂何物?乃是寂灭心头之欲火也。就皈依佛门的晚唐诗人来说,我性自圆满自足,灵明不昧,又何必向外在功名利禄有贪有求?我心既如如不动,平静如水,又有何辱何荣何喜何忧能扰乱我?万法皆空,五蕴非有,四大皆为虚幻,又何必为外物所牵,执着我能我所?一切人生烦恼,都是来自外在的情欲所动。因此,作为以退避隐逸为旨归的晚唐诗人而言,一旦觉悟到性本空寂,便自可“市朝束名利,林泉系清通。岂知黄尘内,迥有白云踪。”[15]放弃对种种世俗物质的追求,面对那些充满诱惑力的科举功名与仕途经济所带来的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良田万亩,广厦千间,高轩肥马,随从塞途,蛾眉细腰列屋而居,粉白黛绿争娇恃宠等世人艳羡的荣华富贵,以及因科场落第、官场落马所带来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种种嘲笑、奚落、轻慢、欺侮、讥讽、造谣、诽谤、打击、挫伤、毁损等羞辱、威逼与伤害,丝毫不为所动,始终保持自己那白云般高洁的迥然超拔之心。
李山甫的两首诗就颇可见出他隐逸生活的空寂心性,其一曰:
担锡归来竹绕溪,过津曾笑鲁儒迷。端居味道尘劳息,扣寂眠云心境齐。还似村家无宠禄,时将邻叟话幽栖。山衣毳烂唯添野,石井源清不贮泥。祖意岂从年腊得,松枝肯为雪霜低。晚天吟望秋光重,雨阵横空蔽断霓。[16]
其二曰:
石砌蛩吟响,草堂人语稀。道孤思绝唱,年长渐知非。名利终成患,烟霞亦可依。高丘松盖古,闲地药苗肥。猿鸟啼嘉景,牛羊傍晚晖。幽栖还自得,清啸坐忘机。爱彼人深处,白云相伴归。[17]
这两首诗,一首写自己的山居生活,一首写朋友的隐逸心境。前一首中,诗人说自己如同僧人那样担起锡杖,绕过竹林来到溪边定居。当他经过河津之时却不免嘲笑起儒生们的迷妄来。其实,这里的“鲁儒”,即是指诗人自己,不过这是过去的“我”,而并非今日的“我”。过去自己依止儒门,向往功业声名,其实是一种自性的迷失,是一种人生道路上的迷误。然而,“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当诗人意识到自己这种迷失之后,便抽身退出,隐栖林下,通过“端居味道”来使自己“尘劳息”,从而进入“扣寂眠云心境齐”的境界。在这里,“味道”当然是指体悟佛法佛道,而所谓“扣寂”,即有了见自己本然空寂之性的意思,扣,本有“扣求”之义,在这里是找回的意思,也就是说找回了自己本来寂然清净之心性。而一旦回归了本性,就进入了一个“眠云”的高超境界,从而下视尘凡俗世,心源与外境,一片澄澈,一片和融,了无差别。此时此刻,自己纯朴得如同从未出山的老农一样,毫无对于世俗宠辱利禄得失之计较分别的情感,而红尘中那些庸俗的事情,既然已经在心头放下了,也就不会再挂在口头。因此,经常与邻居老翁谈论的话题也多半是隐逸幽栖生活中的种种雅趣。自己的心性已经是那样的清寂自如,圆满自足,如同“石井源流”一样,再不含半点泥滓。面对着世人难以忍受的贫寒生活,自己却恬然自安,并不以为苦。由此看来,诗人通过对佛法的体悟,回归了本然清寂的心性,从而超越了世俗凡尘,超越了贪恋欲求,超越了苦乐宠辱等种种情感的缠绕,在林泉隐逸生活中进入到了一个高妙的境界。后一首诗写友人安闲意态,好象是白云的伴侣一样,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超然境界。结尾一个“归”字,如画龙点睛一般,点出李员外其所以能够具有如此高妙的修养与境界,乃是因为他回归了家园,归依了佛法,归根到底是回归到了自我心性的缘故。
与这两首诗用意相似的晚唐隐逸之作还有李洞的《题竹溪禅院》:“闲来披衲数,涨后卷经看。三境通禅寂,嚣尘染著难。”[18]薛能的《赠隐者》“门前虽有径,绝向世间行。薙草因逢药,移花便得莺。甘贫原是道,苦学不为名。莫怪苍髭晚,无机任世情。”[19]唐求的《夜上隐居寺》“寻师拟学空,空住虎溪东。千里照山月,一枝惊鹤风。年如流去水,山似转来蓬。尽日都无事,安禅石窟中。”[20]郑谷的《春阴》“推琴当酒度春阴,不解谋生只解吟。舞蝶歌莺莫相试,老郎心是老僧心。”[21]都表现了一种证悟佛教空寂之性后面对嚣尘、灾劫、贫困饥寒、富贵风流等外物都如如不动、清寂如僧的心境。正是这种心境,保证了诗人们在回避动乱现实的同时也超越了动乱现实,从而不乐仕进、不慕荣利、不惧孤危寂苦,通过隐逸的方式以安贫乐道、穷且益坚的意志在这衰乱末世中生存下去。
四
由此看来,晚唐诗人选择隐逸这种存在方式,他们最大的损失在理想的失落与幻灭,最大的收益在身心的自由与安全、安定的获得。但是,如果没有佛教,他们的心理实际上是很难以平衡的。从平定性海波涛来看,山水隐逸生活中所日日呼吸的清气,逐渐冲洗了红尘俗世中的浊气,而栖止佛门带来的超尘逸俗之清虚静默之气,更使他们含茹养习成一种恬淡平和心态,情感淡却,心境更悠然,更明净。并且,离开了世尘社会,离开了科场与官场的名利争竞,使他们更趋向于审美人生,但他们审美的视点已不在社会,而在自然,或者说在心境更为恰切。这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物象自然景观的选择,也往往是从主观意识出发的,他们的眼光,确切而言是心境,只限定在山松、溪竹、烟霞、涧石、清泉、白鹤、汀鹭、庭草、山溪、野水、荒庭、古寺、禅房、远钟之上,他们与道家不同,不求与大自然的融合,而只求泯灭情感欲念,回归本然清寂之性。因此,尽管他们也写自然山水,但其意已经并不在自然山水本身,这是他们与魏晋六朝人及宋元明清人最不相同的。魏晋六朝人隐逸山水林泉,其态度更多的是放旷,唐以后的隐逸则各有不同,晚唐人的隐逸大多是泯灭,宋人以隐逸来固穷,元人不遇就狂荡,明清则更多是追求一份自适。这与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信念都是极有关系的。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8 4. 2 5 3.
[2]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 1 9 80.7 9 50.
[3]张仲谋.兼济与独善[M].北京:东方出版社,1 9 9 8.8.
[4]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0,(4).
[5]慧能,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5 3.
[6]中国佛学院.释氏十三经[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 9 8 9.1 3.
[7][1 6][1 7]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7 3 70,7 3 6 8,7 3 6 8.
[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 1 9 80.7 3 9 1.
[9]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 1 9 80.7 4 4 3.
[10]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6 805.
[1 1]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百零五)[M].北京:中华书局, 1 9 80.8 1 1 5.
[1 2]中国佛学院.释氏十三经[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 9 8 9.1 3 6.
[1 3]石峻,楼宇烈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8 4.
[1 4]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见上海涵芬楼1 9 2 4年《续藏经》影印本第1辑第2编第1 5套第5册)[M].上海:涵芬楼书局,1 9 2 4.4 3 7.
[1 5]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7 2 9 9.
[1 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8 2 8 8.
[1 9]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6 4 7 2.
[20]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8 308.
[2 1]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 9 80.7 7 3 5.
责任编辑:黄有泰
B9
A
1004-3160(2010)05-0097-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佛教与中国文人心路历程》[批准号:04BZW034]的研究成果之一。
2010-03-02
1.胡遂,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文学;2.肖圣陶,男,湖南韶山人,长沙市广益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