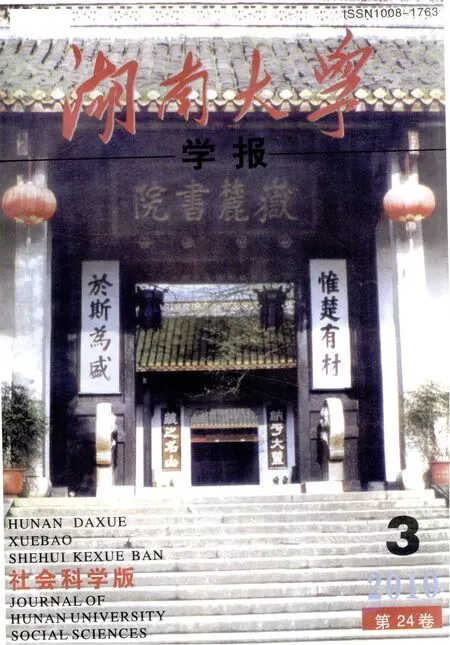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儒家圣王的比较*
朱清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9)
本体论的差异
——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儒家圣王的比较*
朱清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9)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对哲学家和哲人王的描述,而先秦儒家传统中有对圣人以及圣王的诉求。哲学家和圣人都是先知先觉者,并通过心灵及精神上的转化来觉醒他人。他们都强调道德德性,都试图用一定的秩序来规范现实的世界以实现理想政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差异体现了他们之间有着更加深刻的本体论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柏拉图的哲学家不情愿在现实中做哲人王,而儒家的圣人却以在现实中成为圣王完成自我修养的目标。
哲人王;圣王;至善;仁;本体
一 对哲人王和圣王的吁求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了哲人王的形象。在《理想国》中,作为对话的引领者的苏格拉底被追问,他所描述的那个理想城邦是否可能,是否可以实现的时候,苏格拉底一再地推迟他的答复,最后,在他的对话者的再三催促之下,才迟疑地说出他的看法,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1](《理想国》473D)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成为国家的君王,或者国家的君王学习哲学,理想的国家才能实现,国家和公民的幸福才能达到。苏格拉底之所以一再推迟答复,并不是他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而是因为他害怕人们不理解他,从而激起人们的激烈反对。这是他在对话中所遭遇到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浪头。果然,当苏格拉底说出了这个提议后,格劳孔马上就领会到了苏格拉底会因此遭到的反对的浪潮之大。他说:“我怕大人先生们将要赤膊上阵,顺手拣起一件武器向你猛攻了。”(《理想国》474A)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地反对苏格拉底,并不是因为他所说的太荒唐而不可实现,相反,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举措是对现有的城邦做出最小的改动,而使得它接近苏格拉底所描绘的理想城邦,“这个变动并非轻而易举,但却是可能实现的。”(《理想国》473C)而且,苏格拉底很肯定,“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给个人给公众幸福的。”①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页.(《理想国》473E)苏格拉底冒着被人耻笑和激烈攻击的危险,提出了哲学家和王必须相互结合,只有这样,理想的政制才能实现,国家和民众的幸福才能达到。
柏拉图的这个哲学家兼王的角色,虽然一经提出就充满争议,却被柏拉图看作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唯一途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为什么这个通常被称为哲人王的人能够给公众和国家带来幸福呢?我们可以通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洞喻”做出说明。在这个比喻中,人们日常所过的生活被指为完全虚幻不实。人们就像被捆缚住的囚犯,不能转动身子,而只能看到由洞外的火光映射到他们所面对的墙上的影子。而洞穴中的囚徒却指幻为真,他们之中最有学问的人,也不过是对这些墙上的影子出现的规律和次序有更多辨别力和记忆的人(《理想国》516D)。柏拉图所描绘的这些囚徒的可悲的生活,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些常人的心灵所处的状况。柏拉图从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那里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上,“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停的生灭变化,幻起幻灭,人们是不能够从它们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的。而我们常人的心灵却被囚禁在这些生灭变化的影像上,灵魂的眼睛完全不能够看到别处。这种悲惨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有一个囚徒被解开桎梏,可以自由的活动。他渐渐地从洞穴向上走,一直走到了洞穴的外面,看到了真实的世界,甚至最终看到了照亮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太阳。这个人饱览了真实的世界之后,就可以回到洞穴,为他人解开束缚,并带领他们也到达真实的世界。当然,这个拥有自由的灵魂的人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他能够把人们引向幸福,因为,他可以为其他人的心灵解除那牢牢捆缚心灵的枷锁,迫使他们去看真实而非幻影。而真实的世界中最崇高的,是高于存在的善自身。善(agathos)在最普泛的意义上,就是好(good)。而哲学家要认识的最终目标,就是善自身,或者说至善。他自己把握了最高的善,又将其他有能力跟随他的人引导到善的跟前,把握善自身。在国家中,哲学家能够以善自身作为模型,为国家立法,从而能够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引向善和幸福。在柏拉图这里,哲人王是实现正义和创建理想政制的必要条件。毋宁说,只要哲学家真的成了王,那么国家就可以改造为理想的模式。这样的国家是善的和正义的,也是幸福的。
在中国古代诸子那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他们都在寻求能够最好地统治国家的人——圣人或圣王。在先秦诸子中,和儒家共为显学的墨家就指出:“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②吴毓江撰《,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671页.(《墨子·贵义》)治国者只有按照三代圣王的行为模式为标准,才是正义的。又说,“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③吴毓江撰《,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330页.(《墨子·明鬼下》)庄子也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④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183页.(《庄子·人间世》)无论他们所意指的理想的圣人或圣王有什么具体的差别,相同的是,他们认为唯有圣王才能实施理想的政制。而对圣人或圣王推崇和期许最甚的,当属儒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页.(《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1页.(《孟子·滕文公下》)那么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尧舜虽然是孔子所认为的圣人,可是在孔子看来,甚至像尧舜那样的人,都不能完全达到圣的标准。子曰:“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⑦[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2页.(《论语·雍也》)《中庸》中对“天下至圣”有一个描述,说这种人知识渊博“聪明睿知”,又有雅量“宽裕温柔”,刚毅有执而又仪态端庄,其声名远播,为人敬仰如此:“足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⑧[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中庸·三十一章》)圣人是和天合德的。前面所说的那些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的圣人是圣王,而如孔子之圣则还只是圣人,圣人最终的目的是成为圣王。圣人成为圣王,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圣王的“治国平天下”不是靠武力讨伐,而是首先“修身”,才能“明明德”于天下,才能“新民”。“新民”,用孟子的话来讲,是先知先觉者来觉醒后知后觉者:“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0页.(《孟子·万章上》)那么,如何“觉”,如何“明明德”以及“新民”呢?通过宋儒朱熹的解释,这个过程变得意味深长,他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人天赋就有“明德”之天理,但是,由于人与生俱来的“气禀”或气质,天理为人欲所遮蔽。人学习的过程就是“明明德”,去除人欲之蔽,而使得天理重新彰显。圣人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了修身的目标,能够“止于至善”。同时,他又具有“新民”的使命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②圣王“治国平天下”应该也就是新天下之民,使得天下之人都能够“明明德”。而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论语·颜渊》篇所说的“天下归仁”,仁是儒家圣人追求的目标。
二 哲学家和圣人的共同之处比较
首先,通过对照就会发现,儒家的圣王和柏拉图的哲人王有一点非常接近,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自觉然后觉人的过程。自觉是他们成为圣人或哲学家的过程,而觉人是圣王和哲人王的使命。而其中的“觉”都重在心灵的或精神性的转化。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的自觉形象地体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个洞穴比喻中,从洞穴中向上攀登的过程,就是哲学家自我“灵魂转向”的过程。昏暗的洞穴好比灵魂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一种昏聩状态,它被捆缚着,说明灵魂不是自由的。现实的囚犯如果被捆缚着不能动弹,那么他会有挣脱束缚的愿望,但是灵魂虽然被捆缚着,它却不自知自己的不自由。甚至当那从外面回到洞穴的人要解放那些依然被捆缚的人的时候,他们“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一定会”杀掉他。(《理想国》517A)《理想国》中“灵魂转向”的过程,在柏拉图的另一篇对话《斐多篇》中被描绘为灵魂“练习死亡”的过程。死亡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只有在死亡之后,灵魂才能够完全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还灵魂以理性的本来面目。只有灵魂的理性部分才能是永恒的,它所认识到的井然有序的理念世界也不是生灭变化的。只有哲学家能够独立地完成灵魂转向或灵魂净化的过程,这是自觉,而后,再回到洞穴解放其他人。
在儒家的圣人那里,自觉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人之“明德”既然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就要通过修身来转化气质,去除遮蔽。在《大学》中,修身包括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首先要做的是格物致知。朱熹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③[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格物中的“物”,朱熹认为就是“事”,格物就是在事中穷尽它包含的理。事事如此,用力持久,就能“一旦豁然贯通”而体悟理之全体。达到这个全体大用之理,则意自能诚,心自会正,身自然修。修身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为新民、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圣人的目的不仅仅是做统治者,而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启蒙,使得后知后觉者从心的被物欲蒙蔽的状态转化,回归心性本体之仁善。
其次,柏拉图的哲学家和儒家的圣人都具有完美的德性,他们是完善的德性的楷模,而且,他们所追求的知识也和道德德性有密切的关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伦理德性的描述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柏拉图推出理想国的前因就是要寻求正义这种德性。在一个人身上,正义微茫难求,而在一个国家中,正义则容易发现得多。所以柏拉图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也是一个正义的城邦,从中探寻正义的起源。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城邦中,各个人做自己适合的事情,统治者进行统治,辅助者辅助统治者统治,而农工商阶层也各尽其职分,这样,社会的各个阶层就有了自己各自的美德,统治者具有智慧的美德,辅助者是勇敢的,农工商阶层的欲望受到节制,整个国家协调一致,这样国家就是正义的。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正义的国家中,才有善和幸福可言。而对于一个人而言,灵魂的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相应于国家的三个阶级,也各自具有自己的德性,每个部分各司其职,那么灵魂就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它们协调一致,整个灵魂就是正义的。作为个人,哲学家的灵魂最不会被下劣的欲望所蒙蔽,他们的理性能力最为强大,所以,哲学家是最正义的,是道德上的典范。因此,哲学家是最善的,也是最幸福的。同时,整个国家的善和幸福也有赖于作为王的哲学家。在城邦中,哲人王是国家的统治者,在“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①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9页.(《理想国》540A)。哲学家所追求的知识,正义自身,乃至善自身,都具有在道德上最高的意义。在儒家传统中的圣人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也非常突出。孔子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政治和伦理体系。那么如何达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论语·颜渊》)而礼则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中。在孔子所描画的社会中,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智慧一样,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职分的。但这种职分和柏拉图所说的职分有所不同,柏拉图是说人的天性就规定了他适合做什么工作,而不同的工作决定了他在国家中所处的阶层,各个阶层有自己专门的主德。而孔子的职分则是一个人在家庭以及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柏拉图的理想国主的每个公民只有一个职分,而在孔子的伦理关系体系中,显然每个人担负着多种伦理职分,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最好地实现了这个位置应有的德性,那么这个人就具有了相应的德性。而圣人能够在人伦关系的各个角度恰如其分地“止于至善”,具有全德。孟子提出人天性中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端倪,而朱熹进一步将这四主德归为仁,“盖仁也者,无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恻隐之体也,而贯四端。故仁之为义,偏言之,则曰爱之理,……专言之,则曰心之德……其实爱之理,所以为心之德,是以圣门之学,必以求仁为要,而语其所以行之者,则必以孝悌为先,论其所以贼之者,则必以巧言令色为甚。”③[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圣人作为“人伦之至”,最深刻地体悟了仁之德性,并实现了仁德。
再次,柏拉图的哲学家所汲汲以求的至善和儒家的圣人所体悟的仁,就其在现实中实现而言,都是具有一种秩序性的。哲学家要实现的目标是理想国,类似地,圣人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外王”,或说“平天下”。在他们所规划的理想政制中,对秩序的强调有着突出的地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辅助者和农工商阶层,他们之间各司其职,而不能互相僭越,尤其是下层的不能干预上层阶级的事情。柏拉图用一个“高贵的谎言”(《理想国》414D)说明了这点。这个“高贵的谎言”的基础在于,柏拉图相信,每个人就本性而言只适合干一件事情(《理想国》370B)。如果说一个木匠和一个鞋匠互换工作尚不会引起巨大的困扰,而一个第三阶层的人居然干预第一和第二阶层的事情,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甚至灭亡。在古希腊,秩序是善,而无序(apeiron)是混乱和恶。所以,至善在城邦中的实现一定是表现为秩序。儒家传统对秩序也非常重视。周天子有天下,天子分封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家、国、天下是逐级放大的家庭伦理结构,也是严格的政治运作结构。父子关系是君臣关系的原型。只要把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推广到国和天下中,则整个国家秩序井然。所以孟子说,“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1页.(《孟子·离娄上》)平天下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只要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就能达到。进一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9页.(《孟子·梁惠王上》)家庭伦理关系扩展为政治秩序,孟子名之为“推恩”,他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推恩自然不是墨子的兼爱,兼爱是“爱无差等”,而孟子的推恩是有差等的爱。易言之,这种爱遵循严格的次序。圣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是众人的典范,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类比于规矩,符合规矩的方圆是最理想的方和圆,而圣人就像规矩一样是人伦法则的标准。
三 终极目标的差异
从某些方面来看,柏拉图的哲学家和儒家的圣人,哲人王和圣王有诸多相似之处。哲学家和圣人都是在现实世界把握了最高知识并具有最高的修养的人,他们都以在现实中实现至善或仁从而建立理想的政制为己任。哲学家和圣人都注重用严格的秩序来规范世界,他们也都强调道德伦理在理想世界中的价值,他们自身也是道德的楷模。而他们都同样在现实世界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以按照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来改造世界,哲学家成为哲人王或圣人成为圣王,都是遥遥不可期的事情,是只在理想中才会出现的情况。虽然有这些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辨查,就会发现哲学家和儒家的圣人其实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差异体现在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以及终极关怀上本质的不同,而相应地,他们达致这个终极目标的修养过程也显示出深刻的区别。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划分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可见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有生灭变化的世界;另一个是可知世界,就是理念(相,eidos)的世界,理念是永恒的,对它们我们才能有真实的知识。这个可见的世界没有真实的存在,对它我们也不能产生知识,而只有意见。但我们的灵魂通常都紧紧吸附在可见世界上。为什么要使得我们的灵魂转向可知世界呢?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我们不是可以获得许多吗?身体的舒适和享乐,良好的声誉以及别人的尊崇,金钱和其他外在的好处。但是在柏拉图看来,这一切都没有切中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就像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说,“最优秀的人啊,你们是雅典城邦的公民,这是最伟大的城邦,以其智慧和能力而闻名于世,你们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因为你们只关心获得财富、声望和荣耀,而从不关心也不思考智慧、真理和灵魂的完善?”①翻译据Plato,Plato: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trans.By Harold North Flow l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Heinemann,1946-76.p.109.(《申辩》29D)由于我们有肉体和欲望,而欲望往往做了灵魂的主人,人就成了物欲的奴隶,丧失了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真实的存在的能力。在柏拉图看来,只有永恒的东西才具有真实的存在,可见世界不是永恒的,只有可知世界的理念(相)才具有永恒的存在。所以,灵魂要经过训练从这个充斥着各种欲望的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在那里,灵魂才能永恒,才能有真实的存在。可知世界中的理念又有自己的本源。在“日喻”中,柏拉图指出“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7页.(《理想国》508E)在可知世界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如果说其他的理念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善的理念是超越于存在的,“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理想国》509B)。在柏拉图这里,善的理念,或说至善是一种最高的本体,是一切真实的存在的来源。
如果说把握理念是把握到了世界万有的本体的话,那么把握到至善就是把握到了本体的本源。可见,在柏拉图那里,至善虽然是正义、勇敢等德性的最终本源,但是,至善自身不能仅仅划归为伦理道德范畴。因为正义、勇敢、虔敬等德性的本体是正义的理念,勇敢的理念,虔敬的理念。这些理念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其道德上的纯粹,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真实的存在,所以它们是知识的恒常的对象。而对可见世界中的可以生灭变化的东西,人们对它们没有知识,只有意见。不但正义等伦理德性范畴有理念,而且数学对象、科学的对象也有理念,甚至人造的物品,床、桌子也有理念。所以,哲学家要把握的最终目标是关于本体或本原的。他要探求的是世界的最终本原,真实的存在,以及真正的知识的来源。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述说中得到印证,当人们闻名而至来听柏拉图讲“善”的时候,“这是大多数听过柏拉图论至善讲演的人所有的经验。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将得到一种属人的、公认的善,诸如财富、健康、强壮,总的来说,某种惊人的幸福。”③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苗力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485页.但是柏拉图的讲演令大家失望,他说善是一。在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中,一是事物最终的本源。由一产生出理念和科学和数学等的对象,可见世界的事物又通过模仿或者分有理念而存有。比如,正义的行为模仿了正义的理念而被称为正义的,而正义的理念的存在又来自至善。
我们再来看一看儒家传统中,圣人所把握的最高目标:仁。《论语·子罕》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利、命、仁都是孔子尽力回避去讲的,但是回避的原因不同,如朱熹所注“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页.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仁所包含的义理极其深远,对修身成圣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谈到它非常慎重。虽然说“罕言”,在《论语》中也出现了109次,远较其他概念出现的频率要高。基于仁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孔子的学说不是别的,正是“仁学”。那么什么是仁?孔子只是说,“刚、毅、木、讷近仁。”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页.(《论语·子路》),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页.(《论语·颜渊》)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恻隐为四端之首。朱熹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更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⑦[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13页.(《朱子语类·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进一步提出,“是以圣门之学,必以求仁为要。”①[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由此看来,首先,仁是首要的德性,位于其他德性之首;同时,它又是总揽所有德性的“全德”,其他德性可以归于仁,是仁的不同表现。仁还具有本体论的含义,朱熹称之为“天理”:“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③[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朱子语类·理气·太极天地》)这个“理”是世间万物存在的原因,尤其是伦理德性的本体,这个作为本体的“理”表现在道德秩序上,就是礼,而表现在其他事物上,就是万物表现出来的规则和秩序。但是,我们看到,世间万物表现出来的秩序是以伦理道德的秩序为原型的,所以,万物的秩序都体现了仁这种最高的道德德性。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仁说》)世间万有的生成乃出于仁。所以,学者格物致知,从中体会的就是仁这个本源,“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80页.(《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仁说》)
我们看到,柏拉图的至善和儒家传统的仁都具有一种存在论上的本源的意义。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们使得事物获得它们的存在和存在的秩序。但是,这两种本源并非在同样的意义上被强调。柏拉图的至善所强调的是事物的存在和它们在被认识的意义上的真,而仁所强调的是道德意义上的终极价值。这一点从柏拉图的哲学家和儒家圣人的培养途径上可以获得明确显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整套的培养哲学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循序渐进的,准备性的科目包括算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谐音学等,其目的是使得灵魂脱离开可见世界,而保持在可知世界。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柏拉图所谓的促使“灵魂转向”的功夫。在灵魂仅仅保持在可知世界中而不再为可见世界中的事物所混淆的时候,再继之以辩证法的练习,灵魂仅仅跟理念(相)打交道,从一个理念到达另一个理念,最终到达那最初的理念——善自身。在这整个的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灵魂都在努力摆脱这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世界,它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和与之相应的真实的知识存在于另外的一个世界。这另外的世界虽然不能用眼睛看到,不能用身体触觉到,却比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更加真实。比如说,任何可以看到的三角形都是可以朽坏的,而三角形自身却永远不会朽坏。另外世界的真实性就像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二直角一样,它是存在的,对它能够有真实的不变的知识。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至善所注重的是作为存在的来源和知识的真实,由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流变不定的,不具有真实的存在,也不能对之有任何可靠的知识,所以柏拉图在这个世界之外寻求存在和知识的来源。至善之所以为至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存在的来源,也是真正的知识的来源。它的价值意义上的好,是跟随本体而来的。所以,在柏拉图的“线喻”中,真实的程度越高,就距离善越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正义的事物也有其不正义的方面,而正义的理念是纯粹的正义,当然它也更善。柏拉图要求哲学家以最高的理念——善为模型来为国家制度法律,使得国家尽可能地像它的原型,是善的,真实的和最接近不朽的。
儒家传统中修身以至止于至善,为学者修己治人乃至成贤成圣,其学习过程,以朱熹所提进程为例,“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目的是使人建立起良好的道德习惯,无违于孝、悌、忠、信。而后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小学”阶段,后者是“大学”阶段。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区别,朱熹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⑥[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25页.(《朱子语类·学一·小学》)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是同样的“事”,只是前者是无知而事,后者是知道事的理而事之。因此,格物致知等一系列圣门之教,其目的不但是认识仁,而且在实际行为中事仁。仅仅是从理论上认识仁字是不够的,朱熹指出“大抵向来之说,皆是苦心极力要识‘仁’字,故其说愈巧,而气象愈薄。近日究观圣门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实践,直内胜私,使轻浮刻薄、贵我贱物之态潜消于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便是仁处。其用功著力,随人浅深各有次第。要之,须是力行久熟,实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盖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12-1913页.(《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七)他让人去知,并且通过实践所知之道,“力行久熟”,才能“实到此地”体悟仁,恢复本心的全体大用。这里面有个“变化气质而入于道”的过程。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07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七)贤圣之人是变化了气质的人,他们不但认识了仁,而且最能够践履仁。认识仁固然是在先的,而践履仁也同样重要,“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八)知是不能够离开行的,认知仁必须在践履仁中才能得到完满实现。所以,在儒家的传统中,从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离开这个现实世界的另外的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善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仁、天理的体现。在体认仁的过程中,也从来不会有超越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企图,人只要“收其放心”,克制人欲,保持“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就能体悟仁。
柏拉图的哲学家和儒家的圣人在学习过程中,虽然有一些共同之处,如,他们都相信灵魂或者心中先天具有知识或者天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灵魂的转向或者变化气质,使得灵魂离开一种被欲望熏染或遮蔽的状态,而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达到最高的目标,善或者仁。他们都认为,到达至善和仁,需要一个跳跃。在柏拉图那里,至善和理念(相)界之间有鲜明的界限,后者属于存在,而至善是超出存在的,不能用存在来描述它。朱熹描述仁也说通过“一旦豁然贯通”体悟,所以也具有一种超越性。达到仁和至善如果说是一个上升过程的话,那么回到现实生活,就是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它们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种区别在他们成为哲学家或者贤圣之人后的选择上,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人们都希望这些体悟仁或者至善的人能够再回转到现实世界,“治国、平天下”。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引导人们达到真理,获得幸福。不过,就这些悟道的人而言,在儒家传统中,是积极的寻求入世,他们的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外王是内圣的最终理想和认知过程的完成。明明德之后就是新民,修身成功之后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成为圣王是他们的最终旨归。而柏拉图的哲学家是“不情愿”地回到城邦为王的。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回到城邦。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非城邦的培育而成为哲学家的人,完全可以拒绝回到城邦。而且他们也很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在哲学研究中认识到善,他们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幸福。从洞穴比喻来说,上升的过程的终点是达到善,下降的过程是回到城邦,治理城邦。上升的过程是纯粹的灵魂活动,返回城邦并按照善的理念制定法律,才是实践。灵魂在认识到善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最高的幸福了,返回城邦反而勉强,是“不情愿的”,是次一等的幸福。在柏拉图的这个寻求善的过程中,灵魂纯粹的思辨活动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排斥任何同这个可见的世界有关的事物干扰灵魂。只有在灵魂看到了至善之后,才能回到这个可见的世界。因为这时候灵魂能够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能够通过指出可见世界的虚幻解放出洞穴中其他的人,使得他们也能够发生灵魂的转向。但引领他人走出洞穴不是哲学家的应有之义。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差异,究其根源,在于本体范畴上的不同。在朱熹看来,仁是心之全德,“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理是不离开气存在的,所以也不离开世间万有来达到理。而柏拉图的相恰恰是同可见世界“分离”的存在,灵魂通过净化或者转向而达到那个永恒存在和真实的世界。另外,儒家的仁之概念和柏拉图的至善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前者是人伦物理在同样的秩序中,浑然天人合一,身心、人我无有滞碍统一于善的恢弘气象,后者则强调人的心灵能够超越这个世界,达到超凡脱俗的永恒幸福。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A Comparison between Plato’s Philosopher King and the Confucian Saint King of Pre-Qin Dynasty
ZHU Qing-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In Plato’s Republic there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philosopher King, while in the Pre-Qin Confucian tradition there is a call for saint and saint kings.Philosophers and the saints are all people of foresight and forethought,w ho awake the others by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l or spirit.Both of them insist on moral virtues and both try to adjust the actual world with some rul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deal regime.But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aim presents the deeper ont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It is this difference that led to the result that Plato’s philosophers are unwillingly to become a king in the actual world,while the Confucian saint will reach the final end of the self-education when he becomes a saint king in the actual world.
philosopher king;saint king;the good itself;humaneness;substance
B502.232,B222
A
1008—1763(2010)03—0011—07
2009-04-14
朱清华(1972—),女,山东阳信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