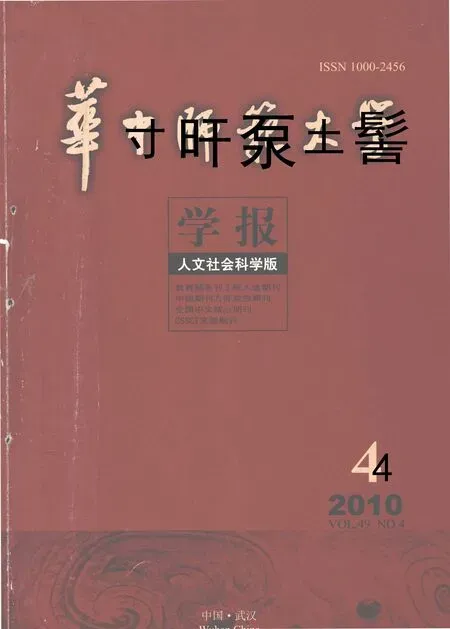论群体性事件中的传媒竞合
秦志希 芦何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传媒竞合
秦志希 芦何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国内传媒近年来围绕群体性事件报道,呈现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党报(台)与市场化媒体、本地媒体与异地媒体复杂多样的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传媒的技术偏向特别是体制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媒介间的竞合。群体性事件报道中不同媒体竞争合作过程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媒介偏向的融合与平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都已经不太可能使媒体保持“集体沉默”或被某一家媒体有意识的叙述,媒介的竞合取消了单一媒介的话语霸权,满足了公众对群体性事件“整体”真实的诉求。群体性事件中的多元媒体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反映新闻事实,同时还积极地建构事实,利用特定视野下所形成的报道框架影响和左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群体性事件对媒介具有依赖性,媒介合力影响着事件的发展方向。如何保障不同媒体的媒介偏向朝着积极的方向自由的展现,为理性沟通的实现提供合理的媒体环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传媒;传媒竞合;媒介偏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而且群体性事件还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由1万起增至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至307万。而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则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①。特别是最近的两年,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和影响范围较广的群体性事件,如“石首事件”、“瓮安事件”、“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吉林通钢暴力事件”、“杭州市飙车案”等②。群体性事件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传媒密集和持续的报道。而且围绕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不同传媒之间形成了多种形态的竞争与合作。
一
纵观近些年的群体性事件报道,不同的传媒竞合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态。
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合
围绕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合基本上呈现出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新媒体主导型。当今越来越多的民众以网络为平台,借助网络论坛、网络聊天、博客、维客、电子邮件、网络新闻组或手机短信等,通过发布或评论相关信息,引发、参与或推动群体事件。新媒体凭借技术上的传播优势使传统媒体面临巨大挑战。
新媒体之所以成为主导,往往是因为传统媒体的报道缺位或报道失当。“西藏3·14事件”当天传统媒体的刻意失语以及“厦门PX事件”前期本地媒体的集体沉默,直接导致短暂的报道真空,而新媒体则不失时机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在“厦门PX事件”的前期,当地市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QQ群等,以“散步”为由,动员当地百万市民抵制PX项目,虽然其后厦门当地的传统媒体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缓和民众情绪,陆续发表了《谣言不可信》、《相信政府,相信群众》、《道听途说写新闻的危害》、《尊重科学,尊重民意》等文章,致力于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主张,强调PX项目的科学性,但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在“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中,黑龙江电视台明知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是经过删节的仍然继续引用、对外传播,这种传播行为的失当,削弱了其后续报道的话语力量,从而使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迟滞也是常有之事。“林嘉祥猥亵幼女事件”和“周久耕事件”都是在网络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甚至开始爆发的时候,传统媒体才开始介入的。此时舆论的走向往往被新媒体所掌控,传统媒体只能被动跟随。在“华南虎事件”中,虽然是传统媒体首先报道了“发现‘华南虎’”这一新闻,但在这之后的8天里并没有继续跟进这条新闻,确证这条新闻的可靠性,而网络媒体则对这一新闻事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并主导了舆论方向:最早对华南虎照片真假的技术鉴定源自“摄影无忌”论坛的讨论,继而网友发起“人肉搜索”找到了虎照片中的原型——年画,直接导致了事件的真相大白。在这过程中,传统媒体只是紧随网络的舆论动向,追踪并验证网络最新消息。而新媒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互动式传播使受众得以直接而深入地参与到新闻事件中,从而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第二种是传统媒体主导型。围绕群体性事件,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的话语权竞争中,其话语优势有时也很明显,但前提条件是政府采取信息公开的措施。在一般情况下,之所以新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大多因为政府新闻信息的控制较为严格,致使传统媒体出现了缺位。而此时一旦网络媒体上出现某些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文字记录、具有冲击力的图片抑或身临其境式的视频,就会马上引起轰动效应,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但是,如果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采取信息公开的措施,信源的开放会使网络媒体的消息不太可能再出现“信息爆炸”的效果,网络媒体也被还原为大众了解变动中的群体性事件所使用的多种媒介渠道中的一种。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政府采取了信息公开透明的政策。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主动邀请电视、广播等媒体,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并表示:“主城区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随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每天都将事件进展情况和政府处置措施及效果,通过电视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除了及时向传统媒介发布相关信息,政府还积极利用网络传达事件处理意见并寻求各方建议。3天后重庆电视台还现场直播了政府与罢运代表的座谈。与此同时,重庆广电集团还派出8组记者分别到加气站、车站、码头等人流集中的场所进行采访,了解基层群众对事件的态度,采访人群涉及普通市民、专家学者、出租车从业人员、教师、机关干部等。传统媒体专业化的传播优势、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高质量使网络无用武之地,网络媒体也就成为了传统媒体的“附庸”。
第三种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替主导型。在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实际上是交替掌握主导权的。
“西藏3·14事件”的报道可分为“网络媒体主导”和“传统媒体主导”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传统媒体失语的同时,网络媒体通过驳斥部分西方媒体张冠李戴地错误使用图片、分析其文字新闻背后的倾向性、展示各地对西方媒体抗议活动的视频等方式获取了此阶段的舆论主导权。在第二阶段的报道中,政府开始采取信息公开的措施,主动组织了大量境外媒体赴藏进行采访报道,同时对网络媒体采用合作、引导和收编的策略。传统媒体除了努力建构自己的新闻话语之外,还大量报道和转载了网络上流行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言论。这样的做法正好迎合了网民在本次事件中迫切想要发出自己声音的要求,因此,一般网民对于传统媒体采取了友好合作的态度。在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网民开始与传统媒体所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统一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之下。传统媒体同网络媒体的新闻互动成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此后,网络媒体由于逐渐陷入民族主义情绪的藩篱中,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情绪滋生了极端行为:有网友将法国领事馆的留言地址爆出,用法文、英文写出“科西嘉独立”“科西嘉万岁”等语言,并且号召网民们将此类邮件散发出去。另外一个帖子则是号召支持科西嘉独立的网友签名。至此,网络媒体开始退出话语主导权的地位。在“3·14”事件后期,传统媒体以“理性爱国”主导着社会舆论。
2.党报(电台、电视台)与市场化媒体的竞合
在群体性事件中,“为了有效地进行群众动员,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把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③,从而将尽可能多的人与这次事件联系起来。群体性事件的积极分子如“厦门PX”事件中的反PX项目者将“散步”行动同全体厦门市民的生存环境等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引发了“百万厦门市民同发一条抵制‘PX项目’短信”事件。而“家乐福事件”中的集会组织者则利用“爱国主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群体性事件的积极分子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他们的理念和观点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大众传媒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渠道之一。在大众传媒对其进行报道的时候,由于报道视角的差异,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对于事件的言说会呈现出不同的框架,表现出一种或竞争或合作的关系。
2005年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表态,引起了多个国家的指责,当年日本希望进入联合国安理会,马上招致了多国反对。在对待日本“入常”的态度上,我国政府与民众保持了高度一致。当有记者采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的反日签名活动时,刘建超回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站在政府角度的党报还是以平民角度进行报道的市场化媒体,在“涉日游行”事件前期呈现出一种合作的关系。对于民众自发的“反日签名集会”,党报与市场化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正面报道,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些报道促进了“反日签名集会”活动在国内的扩散,除早先的重庆和广州外,北京、深圳、沈阳、成都、长沙、上海等多个城市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日签名集会活动。
“反日签名集会”由个别城市蔓延到全国众多城市,而且“签名”开始转变为“游行”,有的城市还发生了暴力的打砸行为,开始危及到正常的社会秩序。此时,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两者都注重维护国家利益,但党报从政府角度出发进行新闻话语的建构,在表达理解民众爱国热情的同时,又力求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报道中大力凸显“理性”、“维护大局”、“化愤怒为行动”、“相信党和政府”等关键词。《人民日报》就此策划了“如何表达爱国情绪”的专题,在专题中各界专家学者、普通群众、学生青年纷纷发表意见,强调爱国更要守法和理性爱国的重要性。市场化报纸则偏重大众情绪的释放,以南京《现代快报》为例,一方面针对“涉日游行”事件倡导理性爱国,另一方面,在那段时间内,报道日本的社会新闻时不仅内容局限于阴暗面,而且标题中频频出现的“老赖”、“猥亵”等负面词语也明确传达出对日本的“厌恶”情绪,如《日本议员街头猥亵女性》、《法官出击堵住洋老赖》、《日本:兄弟俩掐死家人》等等,字里行间暗涌着一股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
3.本地传媒与异地传媒的竞合
在群体性事件中,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使本地传媒不能自作主张发布相关信息。异地传媒在报道群体性事件中不会受这种制约。因此,群体性事件中的“异地监督”有时使得本地媒体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本地传媒与异地传媒之间往往竞争胜过合作。
在“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中,黑龙江电视台在10月14日的报道首先使用的是经过当地警察剪辑的视频资料,并在报道中直接援引警方对此事件的看法,多次出现“咱们民警”、“看!他打我们的人!”、“对方”等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词句,强调“民警面对多次挑衅不得不进行还击”,而对肇事警察酒后驾车、受害者停止暴力之后仍被肇事警察围殴致死的细节进行了模糊处理。在该台的报道中,受害者家属的言论明显少于警方,电视台似在扮演“官方代言人”的角色。
这种有倾向性的话语受到了来自异地媒介以及网络的质疑,全国性媒介和异地媒介开始介入此事: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播出新闻观察员白岩松解析哈尔滨“林松岭事件”的节目;香港凤凰台《文涛拍案》播出“林松岭事件”;《南方都市报》发表《夜幕下的哈尔滨,网民呐喊后的彷徨》;《南方周末》发表《暴力、谎言和录像带》……与本地媒介作为“警方代言人”不同,异地媒介充当了受害者的“传声筒”,受害者家属的言论得到充分的尊重,被遮蔽的事实得以还原。受害者家人对当地媒介和警察的质疑实际上也代表了广大公众和异地媒介对真相的追问,死者的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什么左一巴掌又一巴掌都是我儿子打人,他们打我儿子的那段为什么不播?”在这种舆论压力下, 10月18日警方第二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出面澄清了死者身份,并变相承认视频内容有所隐瞒。黑龙江电视台“新闻夜航”编导也最终承认,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的12日,他们受邀前往铁路公安局,在那里拍下了那段‘不完整版’录像带。⑤次日死者家属看到了全部视频并告知外地媒体。此时警方加快了查办力度,迅速公开了当事双方的个人身份资料、对案情进行相对完整的通报。至此,公众开始理性的回归,逐渐停止在网上的谩骂,等待判案的最终结果。在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媒介的话语呈现不仅面临来自当地官方压力,还要承载异地媒介、全国性媒介、甚至新媒介的质疑,因此更需要秉承按新闻规律办事、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二
群体性事件报道中不同媒体竞争合作过程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媒介偏向的融合与平衡。
媒介偏向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核心的理论命题之一,“媒介环境学假设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⑥,并进一步指出:“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bias)。”⑦
在群体性事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合中,不同技术偏向因素发挥着作用,导致了相应的内容偏向。网络媒体的技术偏向表现为无技术中心导致的内容“偏向”。网络具有交互性和网状传播的特点,消解了技术中心,由于没有技术中心导致的媒体内容的控制中心,因此网络媒体无法形成内容上的一致性偏向。在这种情况下,无需经过特定程序和规范的过滤,理论上各种信息都可以“原生态地”存在于网络中。网络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可以说是“散点透视”,不同的报道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去报道和言说事实,这有可能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群体性事件,使事件真相不易被单一媒介的刻意报道所遮蔽。但另一方面,把关人的缺失造成了网络信息的发布、传播的不规范,在良莠不齐的信息源中,人们根据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信息和评论,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会裹挟着真实信息迅速地传播开去,影响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判断及其舆论发展方向。“中国最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多与网络不规则的信息及谣言的流传有关”⑧。在“家乐福”事件、“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杭州市飙车案”中,网络上盛传的家乐福为“藏独”提供了资金支持、哈尔滨被打大学生是高干子弟、杭州飙车案肇事者找人顶罪等事后都被证明为虚假信息,而网络媒介的网状传播特点有可能加速以讹传讹。
与网络恰好相反,传统媒体具有技术中心偏向:信息经由统一的管道向外传输,传统媒体的信息源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其立场、倾向可能各不相同,但统一流经的管道便于信息的过滤、处理。技术中心为把关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于是导致其内容偏向的统一。并且,“每一件(媒介)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⑨传统媒体基于技术中心发布信息,通常代表了媒介及其背后组织的意见、立场和价值取向,于是,信息经过了大量的过滤、选择,在特定的目标下进行有意向性的传播。
传统媒体和网络由于技术偏向的不同,导致其传播优势和劣势各异,这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媒体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展开博弈提供了前提条件。在“3·14事件”的前期,传统媒体的技术中心使其轻松做到了整体的沉默失语,大众转而寻求网络等其他新媒体以了解事件的真相;而其后网络媒体无技术中心的控制造成“众声喧哗”,各种小道消息、谣言伴随其中,亦会阻碍大众对群体性事件真实面目的了解。一旦政府采取信息公开的措施,传统媒体依靠其技术中心就会褪去网络媒体上的谣言和非理性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就可能占据报道主导权。
另外,仅就传统媒体而言,围绕群体性事件报道,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往往也与媒介特有的技术偏向有关。电视的技术偏向是靠图像吸引受众,在“西藏3·14事件”的电视报道中,来自当地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犯罪分子“打砸抢烧”的镜头不断被各级电视台重复播出,藏独分子“违法”、“血腥”、“野蛮”的信息都已蕴含于直观的电视画面中,这种图像给予感官的巨大冲击力使得电视媒体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报纸的偏向技术使得语言的力度和重要性被强化,而语言是思想的基础,报纸强调了思考的重要性。在报道群体性事件时,报纸的魅力在于给予新闻事件深刻的意义解读,并在这种思想讯息传递过程中把握报道的主导权。在“家乐福事件”、“西藏3·14事件”的后期,报纸媒介就是以准确的新闻报道和权威评论为基础,通过在新闻报道当中大量的使用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访谈,在对事件的深度剖析中,报纸最后同其他传统媒介一起主导着社会舆论。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不仅有媒介技术产生的媒介偏向,还存在着一种由非技术性的、体制性的因素所导致的传播偏向,可称之为体制偏向。“传媒体制,是规范新闻实践的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使之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这个体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和再生,并且通过新闻实践,表现贯穿其中成为其基础的统治意识形态。”⑩在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各种权力及利益往往交织于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围绕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媒介体制化偏向远远比技术偏向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任何传播技术是由特定的传者来运用的,而传者会受到社会中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媒介体制决定了媒介的传播技术如何运用以及运用到何种程度,并对技术偏向产生规制性的作用。
党报主要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看待群体性事件,关注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对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报道视角。如在“西藏3·14事件”、“家乐福事件”、“涉日游行事件”等影响甚广的大型群体性事件中,党报更加注重将社会舆论统一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下,避免舆论的失控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市场化媒体则不直接受政治体制的制约,在最一般的情况下,更多的由市场因素形成偏向,主要根据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状态来形成其对群体性事件报道的视角,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吸引受众从而扩展自身的市场。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部分市场化媒体会出于吸引眼球的考虑进行操作,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则往往从受众的利益出发,站在受众的立场上进行新闻话语的建构,力图赢得受众的信任。虽然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围绕群体性事件报道并不形成对立,但两者报道的视角、侧重点由体制因素造成了迥异的报道风貌。
由于不受本地媒体管理体制的制约,异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报道相较本地媒体而言显得更为全面、客观。在“哈尔滨事件”中,黑龙江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明显的差别就是典型一例。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都普遍存在:“躲猫猫事件”中当地媒体对当事人死于“躲猫猫”的游戏并不质疑;“华南虎事件”中当地媒体成为“挺虎派”的舆论阵地,代表了陕西林业厅的声音;“厦门PX”事件中的当地报纸亦与当地政府的步调保持高度一致。但是,当地政府“依赖统制主义的命令方式管治社会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异地媒体的报道为受众理解事件提供了多元视角,因而地方媒体有倾向性的报道对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不仅效果有限,有时还会产生反向作用。
在群体性事件这种存在多种利益诉求和复杂博弈的新闻事件中,不同媒介往往依据自己的偏向或竞争或合作,或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从而使群体性事件的言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都已经不太可能使媒体包括新媒体保持“集体沉默”或被某一家媒体有意识的叙述,媒介的竞合取消了单一媒介的话语霸权,满足了公众对群体性事件“整体”真实的诉求。
三
群体性事件中的多元媒介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反映新闻事实,同时还积极地建构事实,媒介和技术“影响我们所处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因此,媒介在报道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当中,并非是单纯的反应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不同的言说乃至定义,正如吉特林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的光环将社会事件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媒介根据各自的传播偏向,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展现从而定义群体性事件:“华南虎事件”初期中对虎照的真假判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给予了截然不同的定性;在“涉日游行事件”和“家乐福事件”中,党报的报道将事件定义为“暴力的、非理性的爱国行为”,为此后“理性爱国”的官方话语框架建构提供了合法性,市场化媒体在认同民众爱国行为的同时通过相关报道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释放;“哈尔滨事件”中,黑龙江本地媒体与全国性媒体由于不同的体制偏向影响,就事件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各执一词。这些对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定义和言说呈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上,又反过来影响着大众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和态度,他们对事件或支持、或反对、抑或中立、从众,形成了相应的舆论,从而使大众也参与到事件当中,进而影响事件的走向。从建构论的角度看,媒介并不一定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根据各自的偏向建构现实,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使他们自以为媒介所呈现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于是媒介就有可能成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
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不得不考虑媒介在事件中的作用、在事件的传播中如何吸引大众媒介的注意、选择使用哪种媒介来进行传播会使舆论环境对自身更加有利等问题。这种情况使得“社会运动对大众媒介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于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媒介“绑架”了群体性事件,媒介不仅报道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利用特定视野下所形成的报道框架影响和左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湖北邓玉娇案”从可能被判故意杀人罪发展到最后免于刑事处罚,当事人还获得了社会大众和网友的法律和经济援助;“杭州市飙车案”不光使肇事者被绳之以法,甚至差点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重罚;“厦门PX事件”使该项目被暂停,最后迁址漳州,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因为媒体的介入而改变了事件原来的性质判定。
虽然媒介可以定义群体性事件,但是这种定义有可能会被其他媒介的偏向力量所解构,在“杭州市飙车案”中当地官方对肇事车辆车速为70码的定性被网络的恶搞(“欺实马”)和异地媒体的质疑所解构,最终促使新闻报道回归事实本身。可以发现,媒介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在多种媒介的合力中产生的。
在群体性事件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时候,“它在将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理性沟通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契机”。而这种理性沟通就存在于媒介合力当中,沟通的结果会左右运动的发展方向。并且,借助英尼斯关于媒介偏向平衡的洞见:“不止一种媒介的倾向在文明中得到反映;一种媒介的分散化偏向被另一种媒介的集中化偏向所抵消”,会促进“大型政治结构”走向“繁荣昌盛”。因此,当我们处在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社会发展阶段时,如何保障不同媒体的媒介偏向朝着积极的方向自由的展现和博弈,为理性沟通的实现提供合理的多元媒体环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赵鹏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
②本文所指的群体性事件是:由特定事因所引起的集群性的抗争行为。这种“集群性的抗争”既指现实社会中如围堵、示威、静坐、游行、骚乱等行为,也指网络虚拟社区的群聚抗争。因此群体性事件又可分为现实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在有些情况下,这两种群体性事件会交织发生,互为因果。
③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④新华网:我外交部发言人就“六方会谈”答记者问.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4/content_ 2739294.htm.
⑤刘丁:《哈尔滨警察打死学生案:暴力、谎言和录像带》,《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http://www.infzm. com/content/19224.
⑧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⑨Postman,Neil.Technolog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Technology.NewYork,NY:Vintage Books. 1992.12.
⑩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梅莉
2010-03-10
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社科研究项目(GD0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