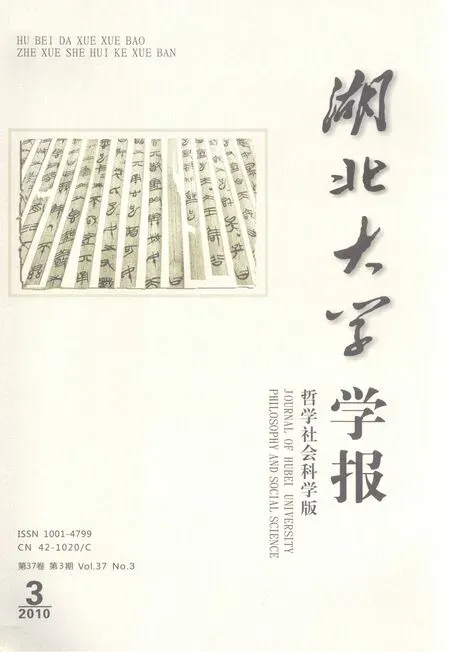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黄晓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隐喻·换喻·提喻
——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黄晓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情爱叙事;身体修辞;隐喻;换喻;提喻
身体是人类情爱生活的基点,这不仅因为身体自身的欲望是情爱发生的原初动力,而且因为身体之间的交往是情爱发展与转变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周围的身体以及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总是社会化的具体的东西”[1]236,情爱中的身体同样打着历史与文化的烙印。这种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身体,在情爱叙事中必然得到体现。作为情爱叙事中一个重要的符码,身体具有丰富的文化与审美内涵:一方面,情爱叙事中描述的身体,总是打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叙述者对于情爱生活中的身体的描述,总是出于一定的叙述目的,采用了一定的修辞手法。由叙述者对情爱叙事中的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不仅可以看出不同时期身体所折射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可以看出不同叙述者对身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产生了不同的话语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因此情爱叙事也依附于政治话语,成为一种公共话语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叙述者试图引导受述者从政治视角对身体进行审视,由此产生“身体—政治”的隐喻修辞,身体被公共化与政治化。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启蒙主义的再兴,叙述者对人性解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情爱叙事因此进入日常话语模式,身体与个性化主体建构密切相关,甚至互为因果,这种叙事以叙述者对身体的正视为基点,并建构“身体—主体”的换喻修辞。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进入“后全权消费主义”[2]时期,消费主义盛行,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身体的隐秘性也就成为挑逗并满足人们的窥视欲、进而产生巨大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砝码,私人话语模式成为风行一时的叙述模式,在这种叙述模式中,身体——首先是性——的私密性,被特别标示出来,以激发并满足受述者对身体的窥视欲,由此形成“身体—性”的提喻模式。
一、身体的隐喻与政治意味的凸显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治主导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情爱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使属于个体的情爱生活,必须接受政治的审视,被纳入公共话语空间进行叙述。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必须用受述者的审视眼光来看待身体,这种眼光使得身体的私密性被极大地弱化,而公共空间中身体的政治隐喻意味则被凸显出来。
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爱情选择与政治选择同步展开。当她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时候,她被余永泽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所吸引。一旦她开始追求进步,她马上觉得这位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人,“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3]76,而卢嘉川“那高高的挺秀身材,那聪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和那和善的端正的面孔”[3]102,马上抓住了她的注意力。这种身体的吸引与排斥,正是理念的吸引与排斥的暗示与隐喻。正是这种身体—理念的双重吸引,使得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产生了朦胧的爱情。但这种爱情在林道静未曾彻底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之前,不可能被卢嘉川更不可能被组织接受。因此,只有在林道静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之后,她才可能收到卢嘉川牺牲时写下的迟到的“情书”。
林道静不仅因为身体的政治属性而产生爱情,而且因为身体的政治属性而接受爱情。尽管江华并不是“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但“她不再犹豫”,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3]559。由于私密性的爱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公共化的信仰取代,因此,私密性的情爱身体同样可以被理念化的同志身体替代。她由对江华/党的感恩而献身:“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3]585当同居后的江华因为很少陪林道静表示内疚时,她甚至批评江华的“小资”意识:“难道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不是共同的吗?”[3]585在这里,江华成为党的一种隐喻,爱情也就成为爱党的隐喻,爱情的“献身”成为为党献身的隐喻。
杨沫以爱情与“献身”来喻示对党的忠诚与奉献,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则更直接地以爱情与身体作为引导恋人爱社的砝码。互助组组长(后来的合作社社长)刘雨生,因为忙于公事,误了家里,使得他的妻子张桂贞执意要同他离婚。遭到丈夫遗弃的盛佳秀试图把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她首先利用刘雨生劝她入社的机会,加强了与刘雨生的联系;后来则默默地为刘雨生做家务,以博取他的好感;最后,为了支持刘雨生的工作,将大肥猪借给社里改善社员生活。在这种“无私”的行为背后,是刘雨生对于自己身体的“交换价值”的充分利用。在借猪时,盛佳秀并不愿意,于是刘雨生语含威胁:“猪不过是猪,无论如何没有人要紧。”[4]225因为“她负过伤的心,再也经不起任何波折”[4]226,使得她“为了爱情,只得松了口”[4]227。
周立波的这种叙述明显含有不少“落后”因素:这不仅表现在盛佳秀因为爱人而爱社,而不是像林道静那样因为爱党而爱人,因此其情感中保留着更多的私密意味,“我只晓得你”[5]309,因信任刘雨生而信任合作社,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改造过来;而且表现在刘雨生“迁就”了社员们的身体之欲,在他们羡慕单干户的腊肉的时候,试图满足他们的肉食欲望,为此去向盛佳秀借猪。而在柳青的《创业史》中,身体之欲让位于创业之欲,爱社、爱劳动成为梁生宝进行爱情选择的标准。小说开头就谈到了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爱情纠葛。然而,梁生宝与徐改霞之间第一次牵手,就已经暗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距离:“有一天黑夜,从乡政府散了会回家,汤河涨水拆了板桥,人们不得不蹚水过河。水嘴孙志明去搀改霞,她婉言拒绝了,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从那回以后,改霞那只手给他留下的柔软的感觉,永远保持在他的记忆里头,造成他内心很久的苦恼。”[6]101而在与刘淑良第一次见面时,梁生宝就因为手而对刘淑良产生认同感:“生宝再看她托在木炕沿上的两手和踏在地上的两脚,的确比一般只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要大。生宝看见她那手指比较粗壮,心里就明白这是田地里劳动锻炼的结果。”[7]198这种对劳动的肯定,使得梁生宝“望着大方而正经的刘淑良的背影,觉得她真个美。连手和脚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高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着哩。生宝从来没有在他所熟悉的改霞身上,发现这种内外非常调和的美。”[7]308刘淑良的大手正体现出她对劳动的热爱,因此表现出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而徐改霞的柔软的手虽然有着外在美,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内在的对劳动的拒绝,因此也就是不统一的。正是梁生宝与刘淑良两人共同的对土地、对劳动以及对合作社的共同的爱,使他们迅速感觉亲近起来。
同样是握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中苏冠兰与丁洁琼之间的握手,穿越的不是思想与性情的差异,而是悠远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这部在文革后期被广泛传抄的“地下文学”作品,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文革前的身体修辞方式,只是在具体的隐喻意义上实现了由爱党、爱社到爱国的置换。1928年夏天,年方十八的恋人苏冠兰与丁洁琼在南京告别时第一次握手。然而,由于历史与命运的捉弄,他们之间的第二次握手则是发生在三十一年后。其时苏冠兰已经与叶玉菡成家生子,而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丁洁琼却是孤身一人从美国辗转归来。在苏冠兰、叶玉菡与丁洁琼的三角关系中,无疑有着人性与党性的某种对立。苏冠兰与丁洁琼真心相爱,却因为父亲专制不能得偿所愿;而苏冠兰与叶玉菡虽然是由于家庭包办订的婚约,但最终成婚却是因为双方共同的政治立场。在苏冠兰与丁洁琼的爱情悲剧中,起作用的不仅有“旧时代投下的阴影”[8]295,而且有鲁宁等代表党的意志的游说的作用,使得苏冠兰最终“让爱情服从政治,把个人问题归入革命事业的总渠道”[8]304。这种爱情与婚姻的背离,正是苏冠兰内心痛苦之源。这种精神分裂的痛苦,本来是对身体的政治隐喻的一种质疑,但作者最后却在国家的层面,实现了这种精神分裂的治疗与痊愈。对于只身赴美的丁洁琼而言,爱人与爱国已经成为一种同位结构,她的家被布置成兰草的世界,因为兰草不仅喻示着苏冠兰,而且喻示着“祖国——还有与我的祖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最美好的一切”[8]196。后来,当个人情感成为一种不可挽回的残缺时,正是在爱国这一旗帜下,苏冠兰、叶玉菡与丁洁琼化解了私人感情方面的恩怨,尽释前嫌。当丁洁琼将两颗寓示世界一流科学家荣誉的钻戒——苏冠兰送给她的“彗星”以及美国科学家奥姆霍斯送给她的“阿波罗”——奉献给周恩来时,她完成了自己的归国认同仪式。这两枚钻戒的交出,不仅意味着她将作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荣誉奉献给祖国,同样意味着她将自己的私人感情也奉献给祖国。身—心—物三位一体,意味着作为私人情感的爱情与作为公共情感的爱国之情,实现了最终的置换。
二、身体的换喻与个性化主体的建构
对身体的极端公共化与政治化,也必然消解情爱叙事存在的空间,因为情爱中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总是非公共化、非政治化的。在文革单维的政治叙事中,情爱被排除出叙事的视野。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个性解放思潮与启蒙主义的再度兴起,情爱叙事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与政治化叙事中关注公共空间中的身体的不同,新时期情爱叙事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身体。它摆脱了政治话语的单维性,转而正视身体的日常情态,由此揭示身体与个性化主体建构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
张贤亮的《绿化树》一开始就写出了身体状态与生命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它以饥饿的章永璘开始,而身体的虚弱带来了精神的疲塌。“身体虚弱的折磨,在于你完全能意识、能感觉到虚弱的每一个非常细微的象征”,最终使人万念俱灰。而这种“已经失去主观能动性的,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的万念俱灰才是最彻底的。这种万念俱灰不是外界影响和刺激的结果,是肉体质量的一种精神表现”[9]404。章永璘的这种身体的孱弱唤醒了马缨花母性的同情,由此对他特别关照,最终使他在身体上强壮到与海喜喜势均力敌。身体的强壮使他在精神上获得自信,由此获得马缨花的爱情:“对她来说,仅仅是个‘念书人’,仅仅会说几个故事,至多只能引起她的怜悯和同情;那还必须能劳动,会劳动,并且能以暴抗暴,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才能赢得她的爱情。”[9]476强壮的身体成为获得爱情的基础与前提。有些悖论的是,马缨花为了维护章永璘的身体而拒绝了他的身体:“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9]482这种对身体的拒绝使章永璘找到了“超越自我”的方向与动力。但在他获得精神超越之后,他却试图否定从前的生理性的“我”,试图否定马缨花。因为马缨花正是运用身体的暧昧性获取改善章永璘身体状态的食物。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复杂性与暧昧性。
张贤亮揭示了身体与灵魂之间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式提升,但这种提升不仅存在着传统的单向性,女性依旧充当男性提升的工具甚至牺牲;而且存在着传统的等级性,灵魂与身体之间存在着高下之分,由此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莫言则试图解构这种单向性与等级性。在《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暧昧的爱情故事正是以身体的相互吸引与相互激发为基点。正是“我奶奶”对于“我爷爷”强壮的身体的信任以及暧昧的暗示,激发了“我爷爷”的勇气与正义感,并由此一步步走上成为“余大司令”的道路。它先是激发“我爷爷”反抗劫匪,然后是半路拦住回门的“我奶奶”进行野合,再次则是谋杀患麻风病的酒庄老板,再后则是为“我奶奶”单挑土匪花脖子,最后,还是在“我奶奶”的激将下,拉起抗日队伍。情欲在这里成为一种引导人物跳出日常生活成规束缚的强大力量,使他成为他自身。对于“我奶奶”而言,“我爷爷”也并不只是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男人,他同样是激发与引导她成为她自己的一种动力与支持。遇匪时临危不乱,暗送秋波,只是揭示了她反抗礼教的潜质,随后高粱地野合,也不过是一种半被动的身体狂欢。但当单家父子被杀,她成为一家之主之后,她就必须自己去开创自己的道路。“我爷爷”的潜在支持与熏陶,“锻炼出她临危虽惧,但终能咬牙挺住的英雄性格”[10]85,使得她有勇气反抗传统伦理,开创自己的现世规范:“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10]70由此,叙述者将这位女性刻画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10]12。
莫言的《红高粱》在身体交往中,描绘了英雄的成长,而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则在身体交往中,寻找艺术的超越。《情爱画廊》无疑是一曲性、爱、美的赞歌,一曲身体与艺术的合奏。在小说中,由(身体)美生爱,由爱生性,由性生(人体艺术)美,形成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螺旋上升结构。由于失去人体模特而落寞失意的画家周由到苏州采风,遇到身体极美的秦水虹,由此引发他的狂热的爱。在他一连串以画为书的情书的轰炸下,秦水虹终于被他的艺术精神打动,离开自己的家庭。他们在此后狂热的性中,感受到了身体的激情与解放,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湎于二人世界,而是借用性的解放力量与激情幻想,实现艺术上的更大提升。而这种艺术创造反过来也巩固了他们爱的土壤。正如周由所言,“水虹你真的以为我们之间仅仅是爱么?没有我们俩对艺术的共同创造,那爱能有土壤么?对我来说,它们像空气和水,缺一不可”[11]219。身体不仅是爱的对象,更是艺术的对象,他们以身体为基点实现了性—爱—美的统一。秦水虹的身体引发了周由的性欲,但他们之间的性不仅是生理的,也是精神的,“爆炸般的性快感”不仅为秦水虹不断炸出了新的“幻想空间”,“她清楚地知道,她和他能够得到这种极度的欢乐,完全得益于他们彼此的幻想”[11]79,而且也不断地炸出周由的艺术灵感,为他打开艺术想象的大门,性快感由此通向“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11]318。而秦水虹的身体之美,不仅是周由的创作对象,同时也是一种对他的激情进行疏导的力量。为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秦水虹所言,她“也许是他的心理砝码和限压阀,而他,则是她精心培育的一棵大芒果,也是她描摹不倦的漂亮的男模特……”[11]317~318美与爱创造同时净化并引导激情,使其升华。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实现了艺术的创造,同时完成了人格的创造。
三、身体的提喻与性(别)意识的张扬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后全权消费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界的政治激情与启蒙激情都开始消退,文学陷入了商业与消费的漩涡。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身体以及关于身体的书写,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具有私密性的性,一方面因为其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获得了叙事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因为性能够激发并满足读者一定程度的窥视欲望而被商人关注。在这种双重激发下,本来属于私人空间的性在情爱叙事中被凸显并放大,性成为身体的主要机能,是性别构建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存在方式。这种以私人生活空间中的情爱为主题的叙事,创建了“身体—性”的提喻修辞模式。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讲述了一个女人漫长的成长史,情爱生活似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小部分却正是林多米所以成为她后来的样子的重要原因。她与其他男性的身体交往,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靠的是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1]235,她被强奸的那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12]165。在那次性经历过程中,她收获的不是快感,而是伤害感,她因男性对她的性侵犯而感觉到自己只是作为性对象的命运。而后来与N的性经历,同样没有给她任何身体快感,更没有给她任何主体意识。虽然林多米“希望他要我”,但这种性爱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在他心目中还有地位。“其实我跟他做爱从未达到过高潮,从未有过快感,有时甚至还会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但我想他是男的,男的是一定要要的,我应该做出贡献。”[12]220正是在这种感受的指引下,她明白,她对N的感受不过是一种自恋与自怜,因此,在离开N之后,她几乎马上就忘了他。在男性那里丧失了获得快感的可能性之后,她只能走向她自身。最后,林多米选择拒绝男人,以自慰来完成自己的女性角色的构建。
同样成为一个自恋者的倪拗拗,却与林多米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叙述者声称在“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13]154,并由此试图构建一种超越性别的角色,“我”的自慰也便成为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书写:
当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怡人……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我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
接着,那手如同一列火车,鸣笛声以及呼啸的震荡声渐渐来临,它沿着某种既定的轨道,向着芳草荫荫的那个“站台”缓缓驶来。当它行驶到叶片下覆盖的深渊边缘时,尹楠忽然挺立在那里,他充满着探索精神,准确而深入地刺进我的呼吸中……[13]239
在这里,自慰在时间上被分解成前后节,在空间上被分解为上下身。前一节与上半身被分配给女性对象禾,而后一节与下半身则被分配给男性对象尹楠。这种分配无疑有着丰富的文化意味。上半身属于审美体验,下半身则属于欲望达成,同性之爱与异性之性在倪拗拗的想象中实现“完美结合”,而超越性别的女性也由此生成。
陈染将审美与欲望分别分配给不同的性别角色,让女性在自慰中完成想象的自我构建;而卫慧则将这两种角色都赋予了男人。《上海宝贝》中的“我”一直试图在没有性功能的天天与像一匹种马的马克之间保持平衡。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潜在对应着爱与性、灵与肉之间的对立。然而,在“我”强烈的身体欲望的指引下,我一次次背叛了无性之爱,并最终导致了天天的死亡,而强烈的性则越来越多地占据“我”的心灵空间。“我”“终于明白自己陷入了这个原本只是sex partner(性伴侣)的德国男人的爱欲陷阱,他从我的子宫穿透到了我的脆弱的心脏,占据了我双眼背后的迷情。女性主义论调历来不能破解这种性的催眠术,我从自己身上找到了这个身为女人的破绽”[14]238。女性成为自身性欲的俘虏。然而,这种战胜了无性之爱的性狂欢,终究也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马克的最终离去,无声地宣示了性不能改变什么的命运。
尽管卫慧张扬了性的巨大能量,但《上海宝贝》的潜层却是暗示女性在性与爱方面的双重失败。葛红兵的《沙床》则从男性的视角,以身体的最终毁灭探讨性爱观念与身体现实的各种可能。作为一部教授级的小说,葛红兵在文本中穿插了众多对身体的严肃思考,但故事的主体还是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情爱。在小说中,性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最初,“我”的性爱充当了拯救裴紫的角色;在最后,“我”的性爱则是张晓闽的成年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性关系的设置,无疑有着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子,尤其是小说结尾的裴紫殉情自杀,更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幻觉。然而,葛红兵较深刻的地方,不在于这种性别关系的构建,而在于对性本身的质疑。他笔下的性,具有明显的悖论色彩。一方面,性爱具有生与死的双重意味:在诸葛与裴紫最初的性爱中,性完成了裴紫生命意义的承续;而在诸葛与张晓闽的性中,性则促进了诸葛对死亡的理解,“每一次抽出都是一次死亡,每一次进入都是一次复活,那荒芜的更加荒芜了,寒冷的更加寒冷了,在残冬和初春的料峭里,张晓闽,我的妹妹,带着我,找到我的生和死,看到我的阴阳两界”[15]218;另一方面,性快感存在无目的与合目的的悖论:作为“不仅是我们的工具,还是我们的目的”[15]51的身体以及其快感,并不需要外在目的作为它的价值支撑,而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却必须注意公义,而“快感是不公义的最重要的内容,不公义的快感是短暂的,而快感的不公义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却是永久的”[15]185。生与死、无目的与合目的的双重悖论,使《沙床》成为一个关于性爱与伦理之间的永恒悖论的寓言。“我”由于上了社会伦理的当,以至于“我比他们更痛恨我的身体,我再也看不到我身体深处涌动着的激情的美了,我比他们还短视,我无耻(比他们更甚)地背叛、抛弃我的身体,以及它内里伟大的欲望和激情——那是造物主赐给我的礼物”[15]121,这种拒绝与背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身体对人的背叛,使得“我”“再也不会有这种欲望和激情”[15]122。尽管小说中似乎出现了对现实伦理的挑战,出现“我”与多个女性的性爱,但“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被动地位以及“我”最后的死亡,似乎暗示了性在解放与消亡之间的终极困境。
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书写,从不同向度揭示了身体的多重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情爱生活必然贯穿公共话语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等多个空间,身体也必然展现为公共身体、日常身体与私密身体等多重身份,在不同空间中,身体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时代对于情爱与身体的规训,自然会在该时期的情爱叙事中得到反映。在“全权主义”[2]时期,情爱生活并不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公共事务,情爱叙事因此不得不采用一种公共话语模式,身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外在隐喻意义被极力凸显。尽管在某些作品中,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情爱生活也曾昙花一现,但矛盾的最终解决,无疑宣示了政治的无所不能,以及公共空间对日常空间的全面统摄。至于私人空间中的私密身体,在这种公共话语空间中,自然更为不合时宜。在“启蒙主义”[16]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再度兴起,作为展现主体建构的一种重要维度的情爱生活被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与多重内涵被深入挖掘。在这种日常话语模式中,一方面身体的正常欲望得到了正视以及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身体同样被嵌入在“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理性、启蒙与民族振兴的规约之下”[16],身体的解放与规训的双重意味被同时放置于主体建构的神话之下。而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尽管似是而非),“后全权消费主义”的兴起,身体以及关于身体的话语都成为重要的消费符号,私人空间中的私密身体成为激发与满足人们窥视欲的重要对象,私人话语也就成为商业运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在这种私人话语模式中,虽然很多作家试图通过身体穿透人类某些阴暗的潜意识,但无一例外地选择性作为这种穿透深层心理的通道。这种对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推进了对身体的认识,但由此而来的对身体的公共性与日常性的忽视,却同样是一种对身体认识的偏颇。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现代情爱叙事将对身体的理解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作为具体的作品,却存在着各种问题。在身体修辞方面同样如此。“修辞只有在不被看成是修辞时才能发挥其效力”[17]25。而要达到这一看似“无目的”的合目的,就应该兼顾辞与物、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言辞要尽可能地接近事物的真相(虽然真相也是一种建构),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站在受述者的立场进行叙述,由此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受述者对修辞目的的戒备心理。正是在这一层面,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模式展现出其自身的含混性与局限性。身体的隐喻修辞曾经对世人的身体意识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由于其只看到公共空间中身体的外在展现的重要性,忽视身体的内在需要,割裂了身体自身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时过境迁,受人诟病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身体的换喻修辞正是意识到身体的完整统一对于主体建构的重要性,叙述者一方面摈弃隐喻修辞中的片面与偏执,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隐喻修辞的宏大叙事策略,同时开创提喻修辞的某些细微叙事技巧,多向度多层面地揭示了身体与主体建构的重要关系,从而引导受述者对身体进行正视,并由此反思身体与主体建构的内在联系。虽然在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一词已经备受质疑,但这一修辞模式正折射出“启蒙主义”时期的主体建构激情。而随后的商业大潮对身体的窥视欲的激发,使得身体的私密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关注不仅有人们对私密身体进行深入理解的激情,更有欲望的激发与放纵。当这种私密身体成为公共空间的言说对象时,不仅可能出现话语的错位,而且可能出现伦理的错位。将身体狭义化为性,无疑是对身体真相的一种遮蔽,而其对受述者窥视欲的迎合,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一种商业操作,也是一种心理操作。木子美《遗情书》的一纸风行,以及随后的销声匿迹,似乎暗示了身体修辞的某种命运。
[1]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朱国华,陶东风.关于身体—文化—权力的通信[J].中文自学指导,2006,(6).
[3]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
[4]周立波.山乡巨变: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周立波.山乡巨变: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柳青.创业史:第一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
[7]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下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8]张扬.第二次握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9]张贤亮.张贤亮自选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10]莫言.莫言文集:卷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11]张抗抗.情爱画廊[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
[12]林白.一个人的战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13]陈染.私人生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14]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15]葛红兵.沙床[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16]陶东风,罗靖.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J].文艺研究,2005,(10).
[17]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书店,2004.
I206.7
A
1001-4799(2010)03-0041-06
2009-12-28
黄晓华(1973-),男,湖南隆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叙事理论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