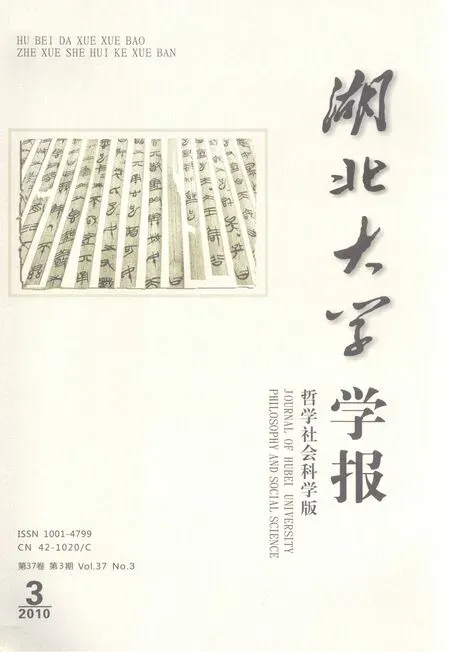论李白诗歌的节奏
孟修祥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43000)
论李白诗歌的节奏
孟修祥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43000)
李白诗歌善于把有序与无序的、简明与复沓的、舒缓与“迅快”的等各种节奏,营造成独特的语言秩序,如视角的快速转换、意象的偶然并置、杂言的句式变换等等,使我们领略到诗歌语言之节奏的无穷魅力。形成这种魅力的主要审美依据,首先是诗人内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与诗的节奏旋律的和谐统一;其次是李白诗歌的节奏源于其“天机俊发”的思维方式;其三,李白精于音乐舞蹈,有利于他对诗歌节奏的把握;其四,李白强悍的主体意识、旺盛的生命力与独特的浪漫气质,使他自然地与盛唐时代的艺术精神相沟通,使其诗具有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音调。
节奏;意象;句式;吟咏
探寻李白诗歌内在的审美机制,必须解答节拍与速度——节奏在李白诗中的表现特点。事实上,前人论及李白诗歌时就已经使用了“节奏”这一概念(如《唐宋诗醇》评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时即用到)。而更多情况下,诗论家们并没有使用“节奏”这一概念,且只是在评说“节奏”在李白诗中的表现特点,还不能真正揭示节奏之于李白诗歌的特殊作用。当代学者论及李白诗歌之节奏者甚多,却总是概而言之,多雷同之语。事实上,节奏之于李白诗歌的重要作用并不下于音乐,李白诗歌的语言善于把有序与无序、简明与复沓、舒缓与“迅快”等各种节奏,营造成独特的语言秩序,使我们领略到诗歌语言之节奏的无穷魅力,而解读这种语言节奏的魅力正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一、李白诗歌意象转换的节奏
语音有规律地运动,就能形成节奏感,这种运动规律被诗家称为“节奏律”。诗歌可以节奏的形式将诗中的各种意象编织成独特的旋律,造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感觉,从意境美的角度看,诗的基本形式就是意象的流转,在意象的流转中可以表现为节奏的变化。范德机《诗评》评李白“《远别离》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义反复曲折,行乎其间,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所谓最具有“楚人风”,乃指《远别离》有屈赋《哀郢》之意,由此,可推断此诗大约写于诗人离别京城之际,因目睹了朝政的昏暗而充满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之祸患的担忧,故借慨叹历史故实,发现实隐忧之叹,而诗中却来了一段“或云尧幽囚,舜野死”的野史穿插,打破了正史所记载的正统看法,在第三人称化的叙述中,又突然出现“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不照余之忠诚”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了意象层次的“断”与“乱”的跌宕感。在意象编织成的独特旋律中显现出“一唱三叹”的艺术节奏形式。
诗歌意象的流转可以显现出一种跳跃的特性,如《行路难》其三,全诗共十六句,写到了许由、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张翰八个历史人物,而这八个历史人物分别属于五个时代:唐尧、春秋、战国、秦、西晋。八个历史人物流转往复,反复申说功成身退之理,不仅不觉得有任何沉滞之感,反而感受到诗人李白有一股情感的激流从内心倾泻而出,势不可挡。这种按照自己的情感逻辑将古代事典、人物加以错置、对接的方式,在《行路难》其二、《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作中均有相同的表现。物理时空的无序化是按诗人情感逻辑来作有序处理的,在李白的主观时空中,可以任意驰骋于今古,从而造成一种特殊的节奏感。
诗歌语言作为一种非逻辑化语言,它使人们可以在非逻辑化的时空中自由驰骋其想象,以舒展其丰富而深邃的内心世界。李白对自由充满极其强烈的渴望,内心又极为灵动自由,因而他的诗歌最喜欢也最善于在历史与神话、虚幻与现实之间随意转换和跳跃,由意象的流转而形成一种超常的节奏,以致于使人以常规思维方式难于解读,甚至怀疑其为伪作。如《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朱谏《李诗辨疑》卷上评曰:“此诗文不接续,意无照应,故为豪放,而无次序,似白而实非也。故疑而阙之,不敢强为之说。”《江上吟》为李白酒醉之后所作,而这正是最宜于李白表达内心情感的时候,故而在诗的前面说自己携妓载酒,泛舟江上之乐,抒豪宕不羁之情。后面借对屈原的推崇,以道功名富贵的价值之虚妄。其实,诗人的情感意绪十分清楚,毫无顾忌地抒写自我的内心感受,否定神仙丹液的虚无,真诚地推崇屈原精神,都意在否定世俗的功名富贵。这种意象层次随着情感激荡而跳跃的现象,显然突出了诗歌意象之间的节奏感,即如杨载《诗法家教》所评:李白歌行“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以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
李白诗歌将意象的跳跃,做到了随心所欲,出神入化。正如李白自己所言:“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游泰山六首》之三)《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种对宇宙无限、人生之短促的巨大感慨在极富跳跃性的时空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中的想象,实现了具有神奇速度的飞翔。而绝句《早发白帝城》中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使一叶轻舟以神奇的速度极其轻快地完成了千里之旅。这些诗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现实时空加以变形、夸张,完成极大的空间转移。有时在他的无意识之中,流露出特别能体现时空转换之突兀感的词语,如《古风》其十一“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登峨眉山》“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独不见》“春蕙忽秋草,莎鸡鸣曲池”、《山人劝酒》“蝴蝶忽然满芳草”等等,这里的“忽”、“忽然”,就是最能体现李白对时间飘忽、迅疾之感的无意识流露。李白直接以他的灵心慧眼来看待空间万象,而这正是中国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1]94~95。宗白华先生的审美理论可以启迪我们对李白诗歌节奏感的审美认识。
黄庭坚说:“太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2]如何“争衡”?胡震亨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古题本辞本义妙用夺换而出”[3]334。其实,胡震亨只说对了一部分,李白不仅仅是在“辞”与“义”上“夺换而出”,而且完全按照自我的情感节奏与心理节奏来选择诗歌的节奏。他往往在情感激荡、神思飞扬之时,创造出一些具有意境美、情感美、语言节奏美的精彩之作,读之耐人寻味。
二、李白诗歌句式变化的节奏
李白由于其豪宕不拘的个性,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反律化倾向,因此,他的律体诗很少。句式参差不齐、篇幅可长可短的乐府歌行和古体形式最为李白所喜好。胡应麟《诗薮》说:“歌行无常矱,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艺苑卮言》卷四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俊逸高唱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概而论之,李白诗属“歌缘情”,杜甫诗属“诗言志”,“志”最不同于“情”之处,在于它作为一种意向性的心理活动,特别关联政教人伦,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李白诗成就最高者皆为杂言体的诗歌,而杂言体中又以乐府旧题为多,他的集子中有四卷全是乐府诗,在初盛唐诗坛上,李白创作乐府的数量最多。初盛唐所作汉魏六朝古题乐府计400首左右,李白之作122首,占百分之三十。还有不少歌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实际也深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沾溉。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九云:“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又卷三十二云:“(李白乐府)从古题本辞本义妙用夺换而出,离合变化,显有源流。”又在《李诗通·江夏行》篇下注云:“凡太白乐府,皆非泛然独造。必参观本曲之词与所借用之词始知其源流之自,点化夺换之妙。”李白乐府诗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受到了原题、原辞的制约,那么,它的“拟古之妙”、“离合变化之妙”、“点化夺换之妙”又从何处产生?除了翻出新意,在情景、氛围、音律、节奏方面进行了新的构思,尤其是节奏的把握,根据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做到了更符合诗歌艺术的审美规律。我们不妨以《将进酒》为例,郭茂倩《乐府诗集》载其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辩加哉,诗审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阴气,诗悉索。使禹良工观者苦。”全诗以三字句为主,显得非常板滞而缺少变化。我们再看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开篇就以三言领起,接下来就是七言,而七言又以四、三言的节奏形式与前面的三言构成呼应,气势磅礴,雄浑豪宕。加上“黄河”意象的非比寻常,人生之感慨无比悲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全是七言的句式,放浪形骸,率性而为,同时也道出了人生苦短、纵情欢乐而不失对前途的自信。所以严羽《沧浪诗话》说:“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诗的最后劝朋友喝酒,取醉高歌一段,又杂用三、五、七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冲口而出,如同口语,其节奏是乐府旧题无可比拟的。
李白诗歌内部蕴涵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他一方面要与传统的诗歌抗衡,另一方面确实要体现出内在的情感意绪。因此,在形式上,诗歌内部的跳跃诸如视角的快速转换、意象的偶然并置、杂言的句式变换等等,也都是由想象力来自然操控的。在句式有变换中即使纯用七言时,也多用流水对,自然、流畅,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所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认为:“太白七言绝多一气贯成者,最得歌行之体。”有时一句之中将字词有规律地重复,形成有强烈节奏感的句式,如《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风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杨义在评此诗时说:“写杜鹃的叫声时以数目字‘一’、‘三’各作三度重复,在强烈的节拍感中使鸟声与心声相应,一咏三叹,把思乡之情写得回肠荡气。可见重复字在强化诗歌节奏感的同时,呼应着心理情绪的节奏感,往往成了诗学与心理学相沟通的语言形式。”[4]412
李白的创作精神中有着一种求新的特质,他经常将乐府古题拿来加以改造,把原有的句式加以改造调配,以适应他情感表达的需要。把简短朴拙的乐府诗在句式上变得参差不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变化,而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李白的代表作如《蜀道难》、《远别离》、《行路难》、《将进酒》、《战城难》、《天马歌》等最为突显之处,就是句式变化参差错杂、长短随意,而情感抒发则酣畅淋漓,无不称意。如《蜀道难》的开首几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短短几句,句式从三言、四言变为九言,又变为五言,复变为七言,随着句式的迅疾变换,一种劈空而来的情感高潮便形成了,使作者的情思在瞬间之内就倾泻而出,读者的心灵也在瞬间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李白诗歌快速的句式转换所产生的节奏感。
这些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艺术形式的选择,在李白则是一种审美倾向的必然选择。《公无渡河》本为相和歌瑟调曲,又名《箜篌引》。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为《箜篌引》焉。”[5]而这一诗题到了李白手中则变为杂言,并且篇幅得到很大的扩充:“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将句式调整后,其节奏变得哽咽难语,正与《乐府诗集》中的《公无渡河》的主题相吻合。
句式的长短参差确使诗歌富有弹性节奏,但不仅限于此,正反虚实的内在组合,甚至包括一些带假设性或转折性的连词的运用,也可以形成诗情的波折与跌宕。如《寄崔侍御》:“独怜一雁飞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这“独怜……却羡……”的句式,以一种自然的节奏表达出了情感的波折。再如《清平调》其二云:“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以正起、反承,转以借问,合以叹息,“妙在善于转折,以情调状语转,以借问状气转,以情感动词转,转折形式多样而不落痕迹,如行云流水的语言背后蕴含着委婉曲折的弹性”[4]423。
李白诗歌句式所构成的节奏,总是放在诗歌的整体中而起作用的,它与意象转换、情景互生、气势转折与声情相称,构成一个和谐的艺术系统,从而能充分显现出李白的艺术个性。
三、李白诗歌吟咏的节奏
语言和任何声音一样有四大要素:音质、音强、音长、音高。在音乐里,音长和音强是节奏的两大要素:等长的拍子轻重间出构成音乐节奏;音乐的节奏律是轻重律。音高与节奏无关,声音的升降起伏形成音乐的旋律。诗歌吟咏不同于音乐,但在吟咏之时却具有音乐的旋律感与节奏感,它是伴随着声音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而构成吟咏的节奏与旋律。任半塘先生在其《唐声诗》上编云:“歌辞有调之始,实缘声乐,不兴歌唱;不缘文辞,以兴吟讽。自‘哑诗’、‘哑词’、‘哑曲辞’者普遍适应人事后,对吟讽之赏既较便于歌唱,亦较多于歌唱……但唱之与吟,一粗一精,一正一变,终不可混。”[6]108以《行路难》为例,虽然采用清唱的方式,但它的声调接近于吟诵。“《行路难》是按‘一人多角’、‘口语叙事’的方式表演的”,“《行路难》不仅证明了这种说唱艺术在魏晋南北朝的存在,而且具体反映了它的基本形态。鲍照辞18首主题不一,说明一支完整的说唱歌调,需要经过乐工拼合,杂集多种曲调,鲍照辞多含闺怨题材,说明这种说唱主要由女子表演。鲍照辞用‘君不见’等第二人称称谓语起句,自称‘歌路难’,并称所用的是‘抵节’而歌‘行路吟’的演唱方式,这就说明:它采用清唱方式,只作简单的击节伴奏;它的声调接近于吟诵,具有细腻缓长的风格”[7]。李白笔下的《行路难》并不旨在“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行路难三首》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变化,已不适宜于从容涵泳,而比较宜于李白《玉壶吟》“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所说的“高咏”:“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起首两句,情绪不温不火,接着便立刻跌入抑郁的、茫然的情绪低谷当中。欲渡黄河,欲登太行,却处处受阻。接下来的两句,情绪又突兀振起,想象自己潇洒地垂钓于碧溪,乘舟梦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重复的感叹和茫然的追问中,一种难以抑制的愁闷又浮上心头。按照常规思维,下一句会沿着这股愁绪延续下去,但李白却在诗的结尾,在涌起又抑下又涌起的愁绪后面,唱出了这首诗情调最昂扬的一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情绪变化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悲喜无端,迅疾快捷。郭沫若说:“诗自己的节奏可以说是情调,外形的韵语可以说是声调。具有声调的不必一定是诗,没有情调的便决不是诗。”[8]253诗人的意识永远处于流动状态,其流动有快有慢,有连贯有跳跃。流淌在文本中的诗人意识的运动速度,是诗歌速度的根本所在。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不同的诗歌必须要用不同的节奏来吟诵。如《唐宋诗醇》评李白《夜坐吟》云:“空谷幽泉,琴声断续,恩怨尔汝,呢呢如闻,景细情真。”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李白《上留田行》云:“末一段促节繁音,如闻乐章之乱。”音乐是讲究节奏旋律的艺术,诗歌的吟咏亦如此。《怀麓堂诗话》云:“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音节者,则不足以为乐。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易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这一方面说明李白诗本身所具有的音乐美;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代诗论家特别强调“往复讽咏”则能体味诗歌内在的情感流程所体现出的节奏美。
吟咏诗歌,也有一个体调问题。体调和语调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基本是一致的。实际上,体调本身就包含着语调的色彩。李白诗中的许多作品如《子夜四时歌》、《长相思》、《山鹧鸪词》、《采莲曲》、《乌夜啼》、《摩多楼子》、《清平调》等诸如此类之名在《教坊记》中就已有了“曲调”的规定,当然,李白对已有“曲调”并非一概遵守,殷璠《河岳英灵集》说:“至于《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那么,《蜀道难》究竟属何种体调呢?在《乐府诗集》中它属“相和歌辞”,所谓“相和”,《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萧涤非先生解释说:“相和歌本汉乐府之精英,而汉人不自知爱惜,四品不收,自沈约录入《宋书·乐志》,始大显于世,吴氏因首列之(笔者按,指唐人吴竞之《乐府古题要解》),则知唐人之于乐府,已知趋重于文学价值方面也。”[9]11也就是说,在汉代,“相和歌”是有音乐伴奏的古歌,但在唐代,其曲调已失,惟有作为歌辞之文学价值存在。但是,读李白的《蜀道难》,其音乐的旋律、节奏仍然十分明显。从句式上看,整首诗以七字句为主,而其中有短到三字句,长到十一字句的穿插,构成了一种起伏跌宕的节奏。尤其是诗中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给人以一唱三叹之感。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蜀道难》:“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乎指顾。”李白以内在的情感节奏统一外在的句式和声韵情调,将二者和谐统一,结构和功能互为因果。也就是说,如《蜀道难》之类的作品,首先就有了体调,但这种体调并非一成不变,到李白笔下则产生了跳跃闪跌、大气磅礴、纵横捭阖之妙,这就是李白《蜀道难》的体调。
李白诗歌既有“俊快”、“爽疾”等节奏较快的诗,也有“从容不迫”、“纡徐”、“容与”等节奏较慢的诗。喜欢诗歌的人都有其独立的阅读经验积累,但是,读李白的诗歌,可以使我们的阅读习惯被突破,从中获得一种情感宣泄的快慰。中国古代文论讲求一张一弛、奇正互参的辩证法则,一般来说,快的节奏令人兴奋或紧张,慢的节奏给人安详、从容的感觉。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看与节奏相配合的其他要素。“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耳——感官体验,心——情感体验;通过这两个步骤后,达到全身心的感应,这暗合了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耳目的感官体验,进入涵泳——释放的“心意”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气”的审美体验,即由“应目”到“会心”到“畅神”(宗炳),由“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到“悦志悦神”。“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起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10]。李白诗歌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形象美,通过吟咏,我们可以对诗中特定的情景物象、表情神态和诗情画意产生具象化的联想和想象。李白诗有的洪亮欢快,如音乐的C大调,使人激昂奋发;有的舒缓沉郁,如音乐中的小调,使人易发忧怨情思。而这种吟咏效果在于诗歌的节奏首先是音组和停顿的有规律的安排,是事物的节奏和人的生理节奏——呼吸的调节及运动感觉的反映,是个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
四、形成李白诗歌之节奏魅力的审美依据
以上三个方面只是就李白诗歌之节奏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言,而形成李白诗歌节奏的主要审美依据则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内在的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与诗的节奏旋律的和谐统一。李白有时情感如天马行空,一旦触发,就奔腾四逸,不可阻遏,猝然之间便趋于巅峰状态,发之于诗歌,便产生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和惊风疾雨般的速度。莫名其妙地狂舞高歌,莫名其妙地潸然泪下,人的爱恨深到一定程度,便成为无端无序的表现。《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句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诗人处在自我内心极度烦闷,情感处于极度冲动之时,于是,造成这首诗极快的节奏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诗的开头如高空坠石,劈空而来诉说自己的烦闷,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情绪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接着,诗笔一转,写到眼前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接下来,又从眼前之景跳入对古代才士的向往,写得俊逸不凡。再接下来,表达追求理想之冲动,情绪又振起一层,但突然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无法排遣的烦忧、愤懑构成诗人心头的巨大压力。“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消解现实的苦恼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啸傲江湖,巨大的精神压力又顿然释放。情绪大起大落,倏忽变化,内在节奏迅疾跳荡。想象大胆飞跃,好像有些不可捉摸,这正是作者当时情绪冲动,内心苦闷无法排遣的表现。有时则舒缓有致、平静旷达。如《日出人行》则体现诗人对生命哲理的感悟,言日月之运行,万物之生息,皆为自然元气,非人力所能改变,而李白的态度是:“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特别旷达,特别富有理性、富有气度的心绪,故其节奏舒缓有致。所以,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把李白诗歌对其节奏旋律按生命情感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舒卷自如,归之为诗人的天才性固然不错,但探寻其审美依据,就在于内在的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与诗的节奏旋律的和谐统一。
其次,李白诗歌的节奏源于其“天机俊发”的思维方式。《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云:“……(白)虽长不过七尺,而心雄万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机俊发,则笑谈满席,风云动天。”这是一种敏妙通灵的思维艺术特点,它需要饱满的情绪,酣畅自足的创作状态。李白往往在酒酣耳热之际,乘兴而起,发想无端,转折无痕,正如陆机《文赋》所谓:“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徵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李白《江上吟》所谓“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是也。酒之所以与其结下不解之缘,也是由于“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11]。这种思维艺术特点必须有一个前提:诗人唯有摆脱世俗羁绊,具有倾心于审美愉悦的率真的艺术人格。多样化的情感被不断刺激产生,目的不是为了情感的蓄积,相反,情感的蓄积还会破坏情感的审美化,因为单单是情感的蓄积无法形成审美的快感。审美快感的形成在于情感的刺激产生之后的大量宣泄,心智处于亢奋的状态,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我们读李白的诗歌感到有一种外向的张力,杜甫《春日忆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高棅《唐诗品汇》曰:“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质而言之,这种“飘然思不群”的“率然而成者”,很大程度上乃由语言的特殊节奏构成,艺术化的节奏感为情感的宣泄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古人早就有云:“太白《蜀道难》、《远别离》、《天姥吟》、《尧祠歌》等,无首无尾,变幻错综,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学之立见颠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为何“学之立见颠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把握住他特有的语言节奏,就像音乐中的作曲家,贝多芬是不可学的。《诗源辩体》云:“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极才人之致……此皆变化不测而入于神者也。”
其三,李白精于音乐与舞蹈,而在节奏上,诗与音乐、舞蹈是相通的。李白能歌善舞,写下了很多描写吟咏音乐与舞蹈的作品,如《白纻词》、《秋登巴陵望洞庭》、《听蜀僧濬弹琴》、《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拟古》其二、《春日行》、《凤笙篇》等等就是描写吟咏音乐之作,还有《南陵别儿童入京》之“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月下独酌》其一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东山吟》之“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泥冠”等等,都说明李白对音乐舞蹈的造诣颇深。本来诗、乐、舞在原始时代是一致的,《毛诗序》即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精于音乐舞蹈,都对他于诗歌的节奏把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其四,李白强悍的主体意识、旺盛的生命力与独特的浪漫气质,使他自然地与盛唐时代的艺术精神相沟通,只要我们看看张旭的狂草、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吴道子一日之内所画的千里嘉陵江山水,其风格都是迅疾跳荡、痛快淋漓的,那么,对李白诗歌激情式的、快速度的节奏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李泽厚所言:“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音调……”[12]167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5]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任半塘.唐声诗: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王小盾.《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6).
[8]张澄寰.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9]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刘熙载.艺概 诗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I206.2
A
1001-4799(2010)03-0023-06
2009-03-10
孟修祥(1956-),男,湖北天门人,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楚文化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