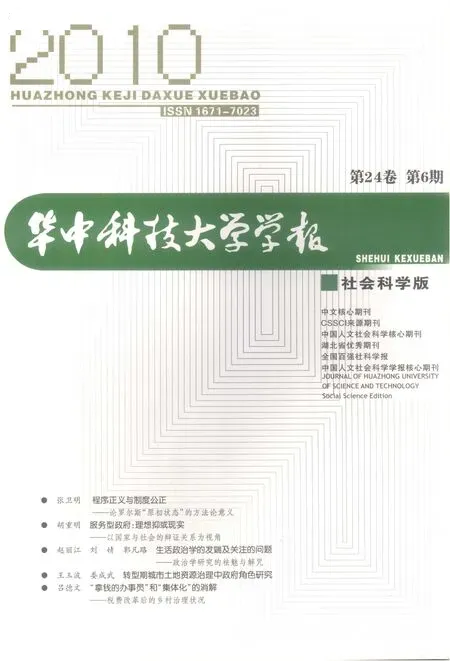主体性“向死而生”?——对《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前提的质疑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主体性“向死而生”?
——对《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前提的质疑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段德智教授这部洋洋五六十万言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是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死亡哲学》之后就开始构想的哲学,这一哲学一方面要超越他自身的《死亡哲学》,另一方面又要向现代西方主流哲学家关于“主体之死”的思想发难,要能真的实现这双重“超越”,世界哲学必定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些评审专家说“这是一项十分优秀的学术成果”确实是它当之无愧的,杨祖陶先生关于该书“是一部极富特色和创见的、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的学术评价并且因此而真实地分享到了他在该书“序”中的那些“涌上心头 ”的“欣喜之情 ”[1]“序”,5,6。在此不作赘述 ,只想从其“真理”的长长缝隙中挤出几点“意见”来,向段教授讨教,以进一步明确重构“主体生存论”所要面临的一些前提性的可能条件。
一、“主体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
主体性哲学确实是西方近代 (现代早期和中期)哲学的标志,在上世纪 80年代成为我国学界的主流话语。我们之所以至今还念念不忘“主体性”,原因就在于我们实际上不曾成为过“主体”,尽管我们一直想成为“主体”。这恐怕就是段老师在书的开头就说的人的“未完成性”的意思[1]“前言”,1。而当我们正在为之努力试图建立主体性哲学时,西方哲学界的主流却是大反主体性,并鉴于拉康、福柯、德利达和利奥塔等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独特魅力,“主体的死亡”就紧随着尼采所宣称的“上帝已死”、海德格尔所致力的“克服形而上学”之后而成为一种占主导的哲学意识。但这些反主体性的哲学竞相宣布近代以来西方哲人所孜孜以求的“主体之死”、“人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他们推行另一种“主体性”哲学的“理论策略”或“话语的狡计”[1]45-53,还是他们的确感受到了某种全然不同于主体哲学的生存经验,因而无法再以主体哲学的范式理解和处理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呢?
如果我们粗线条地回眸一下西方哲学之发展的话,可以同意一个不很准确、但也能基本成立的说法:西方哲学的主线是由对“死亡”的惊异激发出来的。这一起点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虽然被希腊民主制度处死,但如果他不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哲学家的话[2]16,他是可以逃走而免于一死的。但他接受判决,从容赴死,开始其灵魂的“第二次航行”,这确实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学生柏拉图。正是这种震撼和惊异,促使柏拉图成了一个哲学家,以至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学习哲学说成就是学习死亡,是临死的实践。
正是在苏格拉底“临死的实践”中,柏拉图清楚地看到,城邦多数人的“意见”与少数哲人的“真理”处在尖锐的对立中,而当“意见”获得由多数决定的法律的合法性时,自认为追求“真理”的哲人的自由主体,便总是处在死亡的边缘。这种生死存亡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冲突。一个是哲学家的自由个体,一个是民主的“意见”主体 (多数)。为了避免“意见”主体压倒和处死追求“真理”的主体,柏拉图设想了以哲人为国王或王国必须学习哲学的“理想国”。为了让这个“哲学王”超越单因“害怕”或单因循传统而行色法鲁斯 (Cephalus)式的缺乏思考的“正义”,柏拉图设想哲学王不仅有高于和统摄“意见”的“真知”,而且有关于善和爱的知识这种真正的“美德”。①关于好的城邦与哲学家统治的关系,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的论证。可见,这种集真、善、美的知识(德性)于一身的哲学王,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 (包括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体性的原型。
这种主体性的原型同时就是“主体之死”的墓穴,因为能够成为这一主体的,只能是三一体的“上帝”[3]172,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开始的对教会专制的批判,从对教会人员的不相信,导致了对超验的神性信仰的动摇;当人们不再相信有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上帝存在时,随着上帝之死出现的,必然就是主体之死了。而且,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知识的普及和政治、宗教宽容度的增加,“意见”又开始在人文科学、公共领域占据了上风,“真理”仅被限定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想在“总体性”上支配一切的“主体”几乎在其尚未诞生时起就注定了“死亡”的命运。
但实际上,上帝之死和主体之死的意义是不同的。意识到“上帝已死”时,人是带着兴奋、狂喜、甚至疯狂的,“他”非常得意地宣布上帝是被人杀死的,以此来显示人的至高无上的力量。这种无所不能的力量,带给人的是一种当家作主、什么都能做的解放感,从而为进一步强化人的“主体性”扫清了障碍。人自以为只要人成为主体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上帝之死的过程在近代哲学中演变为主体性哲学兴起的过程。随着反教会神学兴起的启蒙哲学,无一不是在鼓吹发展人的主体性。这种哲学的一个共同的基调是相信科学,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规律,然后对应于自然规律建立人的社会历史规律,这样人由认识的主体,变成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从服从自然律统治的因果世界,提升为由自由律主宰的自由世界。这样人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人在知、情、意诸方面都能自我做主,摆脱各种依附,成为独立、自由的无上人格。在这种主体性哲学中,应该说,一般地尚未意识到上帝之死,因为几乎所有的启蒙哲学家,在遇到主体性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时,几乎都像莱布尼茨那样,就搬出“上帝”来解围,因为“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至善的,没有牠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说有牠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与上帝概念相矛盾了。但实际上,上帝在被启蒙哲学家们工具化地作为一个单纯“概念”来使用时,牠就已经死了,因为牠不再有其活生生的作为启示的力量,不再是爱与善的源泉。所以,上帝之死在启蒙的主体性哲学中,没有引起任何惊讶,因为这种哲学相信人的理性可以取代上帝的智慧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而遇到实在解决不了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可借助于上帝的僵死概念来搪塞,只要不自相矛盾就行。因此,只有当人类理性的力量真正遭遇到实在的生存危机,只有到作为主体的人真正感受到他的无能为力时,“上帝死了还有人在”,而且人还可为所欲为的这种主体性解放的梦想,才能真正破灭。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在时间意义上,上帝之死发生在主体之死之前,但从逻辑意义上,只有真正发现了主体已死,上帝之死的意义才能得到自觉。因此,上帝之死和主体之死,具有同构性和同时性。它所表达的,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理事实”,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事实”,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经验事实。这种经验是“基于个体面对社会、政治和历史莫名的和无法控制的过程而无可奈何的经验”[4]255,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必须联系现代经验来观察[主体之死 ]这一现象:在法国,重新表述的激进的主体质疑,是作为表达个人面对无法控制和经常隐匿的变化过程无能为力的经验之中介而出现的”[4]230,这才是主体之死的真正含义。
二、“主体已死”,“生”如何可能?
毫无疑问,这种经验反映并塑造了二战之后欧洲青年一代的生活和意识,因此,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不仅在法国激进思想家中,而且也在包括德国和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当然,我们不会否认,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主体死了,还会有种种主体哲学之变相继续被构造出来。但是,问题在于,主体哲学的内在困境是否得到了意识,被重新构造的主体之变相能否真正地“生成”起来?这不是简单地提出一种新的主体性去弥补原有主体性之不足的问题,而是能否真正化解现代人的“无可奈何”的经验之问题。
首先真正意识到现代人“无可奈何”之经验,意识到传统哲学精心构筑起来的貌似强大的“主体”只不过是虚假的幻相,已经陷入“偶像的黄昏”并真正开启了后现代反主体性哲学之先河的,确实是尼采。当我们重新面对他以及各种以他为依据的反主体性哲学而想让“主体”“起死回生”时,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更强大的力量,让人类历史上一再肆虐的非理性力量“俯首称臣”,甘认理性为主体?特别是在当今,非理性力量越来越借助于高科技、民族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宗教性而显示时。以个人而言,我们如何能在这个肉身全面造反的时代,以金钱和权力衡量成功的时代,用什么更高尚的托词来鞭打和管束身体的内在欲望,而不跟随尼采及其追随者一起为身体中潜藏的巨大爆发力、感性力、意志力和野性平反,特别是,当物质生产已经异化为政治的最高目标,欲望成为拉动经济的动力,而消费成为提升“民生”经济和国民幸福的手段时,我们还能在铺天盖地的以身体、性和利益为诱饵的媒体(从前和现在还在说是“党的喉舌”)面前说有约束它们的“理性主体”存在吗?尼采的“存在即生成”不正是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理性主体”的消亡和物质、肉身、欲望“主体”的兴盛吗?
其次,主体“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必须正视 20世纪人文学术的语言经验。比分析哲学更早,在欧洲大陆也是由语文学家尼采把语言的不可控制的神秘多样性揭示出来了[5]398。传统哲学不太重视语言问题,简单地把语言看作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只要你有意识,有感觉,有想法,你都能把它们如你所愿地表达出来,语言完全是人可以掌控的东西,世界的光明与黑暗,清明与污浊,全由语言“再现”出来。但尼采发现,拉丁语单词 bonus(善),既可以解释为挑拨离间、制造纷争的“武夫”,也可表达“神圣种族”之人,“圣人”之意,而拉丁语的 malus(坏),即可表示平庸的人,也可表示深肤色、尤其是黑头发的人[6]第5节①(德)尼采:《道德的谱系》,第一章,“善与恶”,“好与坏”,第五节。,问题不在于好坏善恶本身是什么,而在于是谁在说话,谁有权力或势力掌控语言。如果你是希腊贵族,你尽可以说自己是“真诚的人”,而如果你是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强奸者,却又无力复仇,那就会说,“让我们不同于恶人,让我们成为善人!善人就是不施暴强奸的人,不伤害他人的人”[6]第13节。福柯正是从尼采这里看到了话语与权力、势力的关系,而海德格尔更是看到了语言在“表达”、“显现”的同时具有的“遮蔽”、“掩盖”的本性。这一切都使得现代人越来越感受到语言不可操控的力量,乃至于伽达默尔说出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我们被语言所说”这样深刻的话来。在这样的语言经验中,传统的那种自信操控了语言的“主体”确实“死了”,而且至今尚未看出有“复生”的可能。如果是在“一言堂”的体制中,那么人不得不处在一种“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虚假生活中,如果是在言论完全自由的民主体制中,当权者和民众同样都处在谁也无法控制别人的话语、甚至自己话语的语言黑幕中。作为传统政治领域之核心的“行动”和“言说”,如今在“公”与“私”两个领域内都失去了“主体”资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人的境况 ”[7]第2章。
第三,主体再次“生成”必须能够避免既不“绝对化”也不“均值化”的主体哲学之泥潭。主体之死不是死在强调人的生活要有主体性,要能独立自主,而是死在主体自身权力的无限扩大化,扩大到主体不仅为“自然立法”,为社会历史立法,而且把主体的理性作为法和道德的基础和源泉这种“绝对化”的做法上,人这样一个具有明显“时间性”限度的存在者,永远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将有限的存在者的主体性绝对化,就像将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力绝对化一样,都是属于不切实际的梦幻,倒不一定就像福柯说的那样,属于启蒙运动的“欺诈”。如果有“欺诈”的话,那也是在异化的政治权力领域,而不在启蒙学术领域,在学术领域,可能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自欺”。就像“我思”必然伴随着“无思”一样。对主体、理性之绝对化的批判实际上在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就一直反反复复地进行着,康德、黑格尔都曾致力于防止“绝对化”的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在海德格尔所极力维护的Dasein(人的实存)的有限性上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学者 David Kolb所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热情拥抱和倡导的“有限性,是一种同现代性的关键前提相对抗的有限性”[8]132。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对抗现代主体的绝对化。这是在重新思考重建主体哲学时必须考虑到的,不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绝对化的后果,而是为什么主体哲学尽管极力避免但避免不了绝对化的后果。
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对现代性具备高度警戒的哲学家那里,与主体绝对化相对的,就是主体的“均值化”。这种“均值化”是在与传统强调“同一性”相反的强调“差异性”的哲学中所出现的,但比同一性哲学中的“均值化”更让人无奈。因为传统的同一性哲学是从人之为人的“理念”,从先验“我思”这样的逻辑主体来构思人的主体性,尽管活生生的现实的从事劳动、思维和实践的“个人”被概念化 (等于“均值化”)了,但人的那种朝气、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理想始终存在着,他希望在人成为主体的过程中,能积极影响和推动社会历史文化朝着更好的(被认为是理性化)方向改善,如果说没有现代启蒙的哲学精神和理想,我们今天的生活离中世纪就非常接近。而后现代哲学尽管非常强调“差异性”,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不被任何东西同化的绝对权力,但是,这样的“差异性”个体,却一个个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把握和影响的能力,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在孤独、焦虑、厌世而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中,被“平均化”为海德格尔所言的那种“常人”,这种人“沉沦于”“闲言 ”、“好奇 ”和“两可 ”之中,既失去了古典Logos(作为“理性”)的那种“聚集”的力量,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也失去了 Logos(区别于“神话”—Mythos—的人的“言语”)的那种“思想”和“实践”的力量 (因为“真理”不存在了,“善”也不再向在古人那里那样是本身“可实践的”),有的只是这些“常人”的“意见”。可想而知,在这些“常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所谓“主体间性”,在失去了真理追求的“话语”之间寻求“意见共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就真无从知晓了。
在主体之死之后任何试图重建主体性的努力,都不得不正视主体或者被绝对化或者被均值化的双重陷阱,在无法跳出这双重陷阱之前,重建主体的基地或者尚不存在,或者还未夯实。
三、主体生存论不可重蹈“主体之死”的逻辑
主体性哲学是在近代“主 -客体 -关系”模式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黑格尔所揭示的“主奴关系”在现代意识中的显现。“主体”和“主人”一样,是我们意识当中意图独立、自由且只为自身存在而不为他物存在的那种“意识”;而“客体”作为“主体”的对象化存在,是主体试图“把握”、“掌控”、“改造”和“利用”的东西,是“依附于 ”主体、因而相当于被主体“奴役”的对象,即“奴隶”。当然黑格尔辩证眼光的独特和深刻,就在于他发现,主奴关系不单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中的两个方面,就是说,意识事实上作为对某物的意识,必然在自身中既包含主体也包含客体,因而它必然既是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也是依赖和被动的,在作为“主人”和“主体”的同时也必然是客体和“奴隶”。不仅如此,主奴关系的辩证法还揭示了,他们只有在一种相互承认的关系上,才能构成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但是,这种相互承认的辩证法的吊诡性在于,奴隶在“承认”“主人”之为他的“主人”时,必须“取消”(aufheben)他自己的独立存在或独立性,而这正是“主人”对他所要作的事;“主人”要完成自己之为“主人”的自我意识,即获得奴隶的承认,也不能否定而只能“承认”奴隶的独立存在,因为没有了“奴隶”他成不了“主人”,因此,他同样要取消自己的独立存在,依赖于奴隶的存在及其对他的“承认”。所以,黑格尔说:“正当主人完成其为主人的地方,对于他反而发生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所不应有之事。他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反而是一个非独立的意识。”[9]129
黑格尔之所以不看好主体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一直猛烈批判他的时代形形色色的“主体性”(主观性),原因就在于主体哲学的这种“相互承认”总是处在一种自否定的逻辑中,要真正取得“主体”地位,必须通过否定乃至统治对方的“斗争”,而通过“斗争”取得的“主体”要能实现“统治”地位,却还是需要对立的对方的“承认”,因为强行实施“统治”的“主体”不会是真正的“主体”。所以,基于“相互承认”的主体关系,一定是在“主人 -奴隶”(主体 -客体)的斗争关系上存在,在这种关系中,只会有一个“主体”(主人),而不会有现代变种的“双主体”或都是“主体”的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tity)问题,所以,“主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不属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只可能有一个主人,而不是一个主人的团体”[2]35。
这一结论对于后现代处境下的西方哲学依然重建另一种主体哲学的尝试,简直是灾难性的,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实际上宣告了在追求无统治关系的自由民主社会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不可能性。要使主体哲学成为可能,就必须完全摆脱“主奴关系”的自否定逻辑,如果依然在这种自否定关系中,那么就必须承认我们对那些不恰当理解的主体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它的外部事件,而是内含于它的逻辑进程之中的。在此意义上,尼采宣布的上帝之死,如果仅仅是以一个“超人”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或理性哲学的“主体”的话,那么,它至多是在完成主体哲学的“死亡”,而不是另一种主体哲学的“生成”。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罗森 (S.Rosen)教授才说,尼采的价值重估“完全不是激进地重新塑造独特的个人,……而是重新挪用古希腊人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的贵族精神”[10]4-5。
而对于那些有意识地激烈解构和摧毁传统哲学之逻辑,拒绝被现代性话语所同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福柯所进行的“主体释义”,是否能够被纳入到“主体生成论”的体系中来,像段老师所说的那样,“进而表明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推陈出新”[1]47,笔者对此是深表怀疑的。虽然福柯对“畸形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精神病人”这些“不正常的人”的谱系学分析,也是旨在建构某种意义上的“道德主体”,但是,对于他而言,“存在于人的力量并不必然成为人—形式的组合,…人在过去也不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未来也将不会一直存在”[11]133,所以,他所建构的“主体行走的是一条受屈从的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其自我被强取豪夺了”[12]30。这样的“主体”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归结到段老师的“主体生成论”中去。
最后笔者要申明的是,上述质疑并没有任何否认(也不可能否认)段德智老师《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的巨大成就的意思,这种质疑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我们依赖哲学所要实现的境界应该是,让我们以跳出者的身份,以间离的眼光来审视我们深陷其中的世界,以便向人们昭示它的那些真实的裂缝和断痕,它的本来模样就如在救世主的眼里那样贫苦和畸形。”[12]283
[1]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2](加)莎蒂·亚 ·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年版。
[3]普洛克罗:《柏拉图的神学》,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德国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5](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6](德)尼采:《道德的谱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美)大卫·库尔泊:《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9](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 )》,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10](美)斯坦利·罗森:《启蒙的面具——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11](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12]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