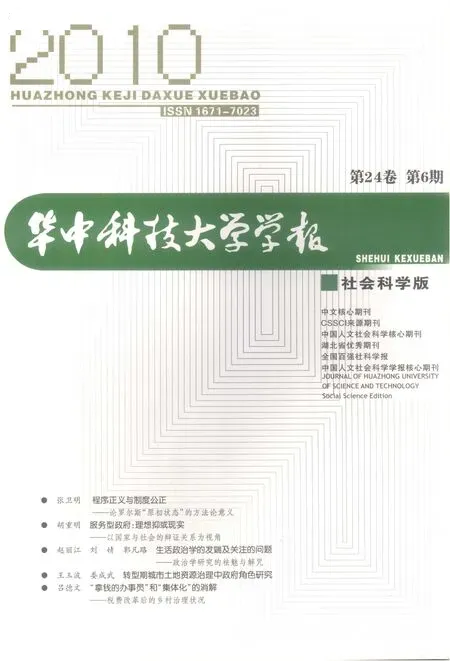依利加雷对列维那斯他者伦理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方亚中,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湖北武汉 430023;
张亚楠,武汉体育学院外语系,湖北武汉 430079
依利加雷对列维那斯他者伦理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方亚中,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湖北武汉 430023;
张亚楠,武汉体育学院外语系,湖北武汉 430079
列维那斯有关女性的论述包含激进的思想,这些论述对女性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列维那斯不是一贯的激进,而是由早期的激进转向后期的保守,最终将女性以及性爱从他的伦理学中排除,只保留了母性和性爱的有效性。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列维那斯的他者不是彻底的他者。针对列维那斯的他者伦理学,依利加雷提出了女性主义批判。
依利加雷;列维那斯;他者伦理学;女性主义批判
一
西方本体论传统追求的是“总体性”和“同一性”,这就导致了对“他者”的忽略和遗忘,使“他者”在西方哲学上中迟迟不得露面。列维那斯致力于“他者”的研究,试图用“他异性”打破“同一性”,从而摆脱“总体性”的主宰。他所论述的“他者”是“绝对的他者”,其绝对性体现在“他者”不可化简、不可还原、与我不同、具有独立的地位、不被“同一”整合。
列维那斯的“他者之脸”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学思想。“他者之脸”有三层含义:第一,杀戮是我之自由,反杀戮是他人之“脸”;第二,在他人之“脸”跟前,代表暴力的杀戮总是失败;第三,当我对他人由“杀戮”变成“欢迎”时,我就扭转了我的存在本性而进入伦理性。
列维那斯的“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脸,而是一种显现他者的隐喻方式。当“我”观察这张“脸”时,我看到上面写着“你不可杀人”的字样,这是“他”对“我”的命令,也是“他”对“我”的要求。对此,“我”必须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也是一种责任。在他人的“脸”中,“我”发现自己有暴力倾向,也感觉到“他”对暴力倾向的抵制,并意识到我的出路在于放弃暴力,欢迎他人。于是,与他者面对面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无限的维度,既使他者摆脱了整体性的束缚,走向无限,也把我带到外在性的无限中。
不可否认,列维那斯的他者伦理学包含激进的思想,最突出的在于它的主体建构方式不是属于认识论,而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从而避免陷入“我思”的窠臼。根据认识论的建构方式,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意识建立起自己的唯一性,不是别人给“我”一个唯一性,不是别人说“我”是唯一的,“我”自认为是唯一的。在列维那斯看来,以伦理学方式建构起来的主体性比以认识论方式建构起来的占有性的主体性更为原初,更为本真。虽然“我”对他人一无所知,因为他者是超越于“我”的,他者是另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主体,具有“他性”,这是“我”所陌生的、无法思议的领域,但是,“我”被要求去为他人负责,为他人的成功、错误、过失承担责任。从表面上看,“我”被他者“俘虏”了,成了他者的“人质”,“我”失去了独立的主体性,但实际上这一说法是在曲折地肯定“我”的独特的主体性。这是从责任的角度来解说主体性。为他负责的观念已经预先假设了“我”是一个可以担负责任也有能力负责的主体。这样一种担负责任的能力及其主体性在负责任的过程中真正被确立起来。当“我”在为他者负责的时候,“我”的主体性意识才被唤起,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人。因此,主体性与责任性是一致的。“我”的伦理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为他人担负责任[1]。
列维那斯的他者伦理学引起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关注,这一是因为差异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二是因为这一伦理学直接涉及性差异问题。总的来说,列维那斯的他者伦理学包含对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借鉴价值的激进思想。在 1947年的《存在与存在者》(Existence and Existents)中,列维那斯提出这样的概念:“最突出的他者是女性”[2]85;在同一年的《时间与他者》(Time and the Other)中,他补充说,他性或相异性是女人真正的“本质”[3]85。但是这种关于女性他者或女性他性的激进观点只出现在早期的作品中。在 1961年的《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中,女性受爱者被描述成是“不负责任、不说真话的动物”,是“回到婴儿阶段、没有责任心”的存在者,她“卖弄风情”,“有点傻乎乎的”,已经“放弃了做人的身份”[4]258。在 1974年的《异乎在或超乎质》(Otherwise ThanBeing orBeyond Essence)中 ,女性他者已化简为母亲的作用。整个来看,列维那斯在对女性态度上由激进到保守,对性爱和女性他者的兴趣由强烈到微弱,并越来越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最终将女性以及性爱从他的伦理学中排除,只保留了母性和性爱的有效性(指生育孩子)[5]。因此,列维那斯也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
二
依利加雷有两篇文章是直接针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的,一篇是《爱抚的丰饶:列维那斯 <整体与无限 >第四部分‘性爱现象学’的一种阅读》(“The Fecundity of the Caress:A Reading of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 section I V,B,‘The Phenomenology of Eros’”)[6]185-217,另一篇是《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提出的问题:论爱的神性 》(“Questions to Emmanual Levinas:On the Divinity of Love”)[7]178-189。在前一篇中,通过阅读列维那斯关于性爱的论述,依利加雷发现,在列维那斯的性爱关系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施爱者和受爱者的关系,也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如果列维那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性爱,这种肯定是很不彻底的,因为女人被肯定的就是她的母性,感官享受被肯定的就是它的有效性 (指生育孩子)。结果,男人进入伦理世界,实现与上帝的认同;女人没有主体性地位,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用依利加雷的话说,“他,施爱者,被送回到超越的境界;她,受爱者,陷入深渊。”[6]188她反对列维那斯把女人与世俗化、未成年和动物性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比喻把女人从由男人实现的伦理和宗教超越中排除。如果说列维那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的他性,这个他者充其量也只是性爱上的他者,而不是男人伦理上的他者。依利加雷的后一篇文章以问题的形式继续对列维那斯的批判,其中性差异以外是否有他性和他者是谁的问题是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依利加雷在文章中指出“列维那斯对快乐所作的描述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把男人表现为惟一的主体,行使他对女人的欲望,女人除了引诱男人外,被剥夺了主体性。”[7]185下面一段揭示了列维那斯对性爱姿态的描述并不符合伦理学的准则:
虽然他乐于爱抚,他放弃了女性他者,让她沉沦,尤其是沉入准动物性的黑暗中,以便回到男人在其自身之中的世界担负他的责任。对他来说,女人不代表以其人的自由和人的身份受到尊敬的他者。女性他者处于没有自己具体面孔的状态。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从根本上算不上伦理学。超越形而上学之脸恰恰意味着使女人具有她的面孔,甚至帮助她发现它、保持它。列维那斯几乎没有揭示由本体—神学造成的毁容。他的爱抚现象学仍然牵连在其中[5]183-184。
《爱抚的丰饶》是《性差异伦理学》的压轴篇,按照蒂娜·钱特 (Tina Chanter)的理解,依利加雷选择阅读列维那斯作为一本论述性差异伦理学著作的最后一篇,并对列维那斯的阅读又集中在《整体与无限》中谈论性爱的、篇幅相对小的那一部分,“这些事实决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说明依利加雷的整部著作都深受列维那斯伦理学概念的影响”。钱特认为,这篇论文“可能将性爱主题作为它的出发点,而且它还指出了列维那斯整个作品的一种阅读”。钱特还指出,在整篇论文中,依利加雷借用了迪俄提玛 (Diotima)①古代女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导师,曾向苏格拉底讲授“爱的哲学”。关于爱的阐述,后者“将性爱看成是自我和他者的某种程度上的再生”[8]214。其实,在文章的开始,尤其是在第五段,我们就能找到迪俄提玛的影子。依利加雷说,在性爱关系中,“生活总是面向发生之事,面向与尚为找到位置之物短暂的接触,面向谁也不能控制的未来的眷顾”;她所说的未来是“一种不是由向死亡超越而是由召唤自我和他者的诞生来衡量的未来,为此,每个人安排和重新安排环境、身体和摇篮,而不对一间房子、一个屋子、一种身份的任何一面进行封锁”[6]186。
在本篇中,作者首先引出“在原初时触摸这一单纯或本真的的意义”,它“浸没在情致或感觉之中”,包括“惊讶、好奇和有时面对周围事物的恐怖”;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尚不存在”[6]185。接着作者把性爱描述为“先于任何如此这般定义或设计”,也就是说,性爱先于语言,“在口腔阶段出现之前,触摸就已经存在”[6]187。所以说,性爱中的感官快乐是没有主体认识的感官快乐;如果有主体出现,这个主体意味着“能够看,会衰老,因与永恒开始的那种热情和纯真脱离联系而死去”[6]185。作者所说的性爱“总是处在开始阶段”[6]185,没有结束之时。所谓“总是处在开始阶段”,就是说性爱总是在实现一次“诞生”,这次诞生“总是被延长”,也“永远不会出现”[6]186,“从来没出现过”,“仍然在将来”[6]187。
依利加雷把主体和固定性、唯我论、占有联系在一起,认为“感官快乐可以重写和颠覆世界这一概念,它可以回到主体和客体的消失,回到借以定义他者的一切修辞手段的消除”[6]185,性爱的作用就是达到“与作为他者的他者一起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种天真无知”[6]185-86的境界,实现“所有官能不可化简为任何必须的损耗或完结的强烈愿望”,品尝到“他者具有一种吸引力但永远不会让人满足的那种难以描述的味道”[6]186。性爱的姿态总是而且依旧是先于婚礼,同时也在婚礼之中,有结合,但没有完结,在坚持他者的轮廓时变得完善。这就是依利加雷所说的“表示爱意的触摸”[6]186。她这样描述道:
在主体的任何定位之前和之后,这种触摸以肉体的形式将两人捆在一起又解开,这肉体依旧是也永远是不让占有沾边的。[这种触摸]将一个和另一个严严实实地用外衣裹起来,这外衣不是要再现、证明裸露身体的反常性,也不是要以裸露身体的反常性取乐,而是要总是第一次地凝视和装饰它,使它具有非定式的、未完成的肉体。将它盖着,又将覆盖物掀开,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像含情脉脉的受精动作,寻求和肯定他性,同时也保护他性[6]186。
突出触摸的意象,目的是为了说明爱的丰饶或爱抚的新生。性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新生命的诞生,这是性爱神秘性的一个方面;同时,性爱相互使对方变得丰饶,使肉体获得了再生,这是性爱神秘性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性爱的行为促成了儿子的诞生,在依利加雷看来,“这个儿子解不了最不可化简的他性之谜”[6]189,因为“在任何生育之前,恋人彼此将生命给予对方”[6]190。列维那斯把感官享受预先安排在它生产孩子这一作用范围以内,依利加雷把性爱的意义确立为超越了单纯的身体的某种东西,是除了导致母性以外的别的东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维那斯伦理学思想的影响,依利加雷在这一点上绝不与他苟同,并对他的性爱观念提出严厉的批判和指责。依利加雷说:
在儿子出现之前,受爱者的行为告诉了他、也使他看到了丰饶的秘密。再看一看他所爱过的女人,施爱者可能心里在思考丰饶的成果。如果受爱的女人——和施爱的女人——的纵情意味着一种天真浪漫的信任,一种动物的繁茂性,那么,如此的纵情照见了这一温情姿态的美学和伦理学,让那些从容地重新打开眼睛的人能够看到[6]190。
列维那斯把生育作为感官享受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感官享受只能在结婚的床上与生育孩子的意图联系起来才被拯救。但是,当性爱结束时,这种享受的行为和性爱的意图还能够统一起来吗?对此,依利加雷说,“受爱的女人被降为一种不是内在性的内在性,因为它是深不可测的、动物的、幼稚的、婚礼前的,而只让施爱者独自呼唤上帝……他忘记了在此时此地做爱的丰饶性,这是给具有性差异的诞生和再生的每个施爱者的礼物。”[6]202
由此看来,在性爱中,男人和女人的作用已作了规定。男人处于施爱者的地位,是作用于受爱者的主体;女人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候着接受男人。儿子的诞生对施爱者和受爱者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对施爱者来说,儿子的诞生意味着实现超越,而不是完成回归。对受爱者来说,儿子的诞生意味着完成回归,而不是实现超越。受爱的女人,通过性爱、母性和生育,使儿子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女人只起工具的作用,男人是真正的获利者。男人由性爱走向伦理,女人被剥夺了主体性,不能进入伦理世界,与神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依利加雷说,“受爱的女人的引诱在父子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她仅仅是他自己的一个方面,通过她,男性施爱者超越爱和快乐,走向伦理。”[6]203
三
在《给伊曼纽尔·列维那斯的问题》中,依利加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性差异之外有他性吗?”紧跟在这一问题之后,依利加雷指出,“按照列维那斯对女性特征的描述,女性与他自己没有什么不同”[7]178,这意味着他性在性差异之外,或者说,性差异没有放在他性的考虑之中。接着,依利加雷揭露了列维那斯的性爱观与父权制同出一辙。在父权制中,男人追求和向往的是光明,女人代表的是阴暗面,是底片。女性不是根据自身的情况,而是从男人的角度,通过一种纯粹性爱的策略被了解,这种策略由男性快乐规定,即使男人认识不到他自己的性爱意图和姿态与伦理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尤其是男神对神权的垄断。女性的性征在这样的文化中被置于阴暗之处,不能通过神性再现出来。对列维那斯来说,女性仅仅代表刺激欲望、重新点燃欲望之物。爱抚并没有触及他者,不是在它最富有生机的方面,即触摸上,接近他者,而是把他者身体的那一至关重要的方面化简为对他自己未来的详述。因此爱抚可能等同于哲学暂存性隐藏的意图。但是在这一性爱的“游戏”中,女性他者仅有的作用就是满足哲学家的饥饿,沿着未来的方向给他快乐的意图性提供营养,这种未来没有“未来事件”,也就是说,没有一天是为了在爱的体现中与他者相遇而命名的。这种对爱抚的描述说明,男性怎样利用女性。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男性主体的暂存性在快乐的意图上利用了女性维持生计。在将他者的肉体转化成他自己的暂存性的过程中,男性主体丢掉作为他者的女性是显然的。更通俗地说,男人将女人作为食物吃下,吸收营养,然后再把女人作为废料排除。
与父权制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神论。在父权制中,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他将上帝视为自己理想的化身,按照理想化的标准建构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它排除女人、压制性差异。传统上关于上帝的叙述抹去了性差异,使女性处于没有身份、没有话语权的境地。总之,不管是父权制还是一神论,性差异都不在考虑之中。因此,没有性差异的他者不可能是真正的他者,而只能是同一性中的他者。鉴于一神论给女性造成巨大的危害,依利加雷特别强调女性神学的建构。与《爱抚的丰饶》相比,《给伊曼纽尔·列维那斯的问题》更突出了女性神学的重要性,这一点从文章的副标题“论爱的神性”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创造女性神学,建构女性谱系,这是依利加雷从事的伟大事业,也是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对列维那斯的阅读使她更清楚地看到女神和女性谱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依利加雷反问道:在父权制谱系结构中,爱的结构具有什么样的生存可能性呢?没有精神和自然之间、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没有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没有这一谱系的神性在文化上的认可,女人怎么还能是属于父亲上帝血统的男人的爱人?难道后者不需要一位母亲上帝?她认为,在一个谱系中,爱只能走向绝望。所以依利加雷说,“两个谱系必须在两个性别的每一个中被神化:母亲和父亲,女人和男人,以使女性和男性恋人互爱。”[7]186
列维那斯将男人视为“施爱者”,将女人视为“受爱者”。为了表明女人也是恋爱中的主体,而不是可化简的欲望客体,依利加雷使用了“女性施爱者”(woman lover)这一术语。男人和女人作为主体互爱,体现在相互性中,而不仅仅是在男人爱女人那种及物方式中,即男人是主语,女人是宾语,男人完成爱的行为,女人是被动者。根据传统的引诱和堕落的模式,女人的快乐被夺走,被转移到男人的快乐中。在依利加雷看来,“如果有一种堕落,它位于对女性的化简中,即把女性化简为被动、过去时、男人快乐的对象,在于将女性与受爱者等同起来。”[7]185
在列维那斯那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爱关系不符合伦理关系,因为性爱包括向自我的回归。总之,列维那斯最终没能将女性视为不可化简为我自己的他者,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他对快乐的交流一无所知”[7]180,另一个是“列维那斯用儿子代替女性”[7]181。
列维那斯对快乐的一无所知表现在“他体会不到在我身上和与他或她一起之时立刻变成狂喜的那种他者的超越”,列维那斯的爱是“我向的、利己的、孤独的”,“与他者总是保持距离”,而两性的性爱应该是“两个恋人共享倾泻的激情,跨过皮肤的界限,进入身体的黏膜之处,离开将我的孤独封闭起来的圈圈,相遇在公共的空间”[7]180。依利加雷描述的这个公共空间是“一个流体的区域”,在这里,两个人变得不可区分,“最重要的是,加入到另一种能量中,既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另一个人的,而是由于不可化简的性差异共同产生的能量”;在外部的区域是无法实现这种结合的,它“缺少黏性、轮廓清晰”[7]180。依利加雷的性爱包括三项:你、我和我们的杰作;这三者存在的前提是“每一个都不能化简为其他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的杰作不一定是孩子,而是指“狂喜”,它“先于任何孩子”[7]180。依利加雷怀疑列维那斯是否意识到在生育任何儿子之前的这一快乐的创造,她把这种快乐描述为“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超越于也内在于一个和另一个,并产生第三者作为我们之间的调解者,由于第三者,我们回到我们自身,这时,我们已与我们的过去不同”[7]180-81。
谈到第二个原因,依利加雷认为孩子属于另一时间,孩子应该为他自己而不是为生育他的人而存在。当父亲得到一个儿子时,他有可能从儿子身上找到资源,于是,儿子就成了父亲将存在赋予他自己的地方,他根据由儿子构成的这种与自身的相同与不同向自身回归。在依利加雷看来,这一姿态不能实现与他者的关系,因为它没有根据她的实际认可女性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它没有把孩子留给他自己的一代[7]181。
依利加雷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者是谁?”尽管列维那斯说到“他者”、“对他者的尊重”、“他者之脸”等,但是,在依利加雷看来,如果性差异的他者没有被认可或不知道,任何对他者的定义就有可能意味着一种伪装或引诱,或者是消灭他者的一种效果[7]182。依利加雷指出,列维那斯没有看到父权制的所在地已经夺取了女性谱系的地盘,已经掩盖了母女关系。如果女人的类属从历史和谱系中被铲除,他者的任何不可化简的差异性就不再存在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伦理学变得与一种形式主义或一种无秩序的漂泊不可区分。依利加雷还指出: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有用并值得尊重,但是这种伦理学不再认识自己的毛病。对这样的伦理学而言,惟一的毛病就是它显露出来的毛病。它围绕自身自转,不能认识它隐藏的毛病;那毛病是看不见的,在两口子和家庭中,那是伦理学得以表达的社会宗教组织的核心部分,在那里,那毛病也是没有被认识的……更确切地说,这一毛病至少有两种解读:一是与我性别的未实现相适应,即我没有成为我理想的类属;一是根据他者理想的类属定义。这两个毛病不是一样的。多少世纪以来,一个被另一个残酷地掩盖,这就将社会永久地放在伦理上犯错的位置,一个常常以宗教为后盾的位置[7]182。
依利加雷发现,列维那斯运用若干词语但并没有总是给这些词语定义或重新定义,“他者”就是这些词语中的一个,结果,他的作品呈现不同的色调,有阐释学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7]183。这意味着列维那斯的话语有两个层面:对肉体关系、女性的他性、肉体的不可见性的现象学处理方法,尤其是通过爱抚实现的处理方法,通常属于描述的方法,表明我们不再处在形而上学秩序中;坚持他者总是位于父亲的王国,父亲与儿子、父亲与上帝的关系组成的王国,这样的坚持属于形而上学传统。所以列维那斯爱抚的现象学退却到由男性主体的哲学构造标出的边界范围内,它既不通向他者、上帝,也不通向新的精神或理性层面,它浸泡在作为它再现之条件的女性他者的动物性、反常性、幼稚性中[7]183。值得称道的是,列维那斯在通向他者的征程上,克服了重重障碍,与父权制的距离越来越远;可惜的是,在性爱的问题上,他转而依赖父权制作为后盾,用依利加雷的话说,“列维那斯与通向另一性、通向他者、通向他者的神秘性之路如此遥远,抑或如此靠近,到后来,正是在性爱之处他更加依赖于父权制这个靠山。”[7]183
四
在以上谈论的两篇文章中,依利加雷以性差异伦理学作为根本,既承认两个性别的存在,也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性,这是传统的伦理学理论无法做到的。传统的伦理学不涉及性别和性属问题,性差异不在考虑之列。用性差异伦理学去理解和检验列维那斯的形而上的伦理学,后者就不符合伦理学的标准了。将爱和性爱关系从伦理关系中抽掉,女人变成了服务于施爱者实现超越的工具;将母性和生育作为感官享的目的,女人被抛回到深渊,与伦理世界无缘。总之,女人被限制在性爱的关系中,这个具有性差异的存在者,这个在性爱中的另一个“施爱者”,这个在生育中的母亲角色是男人性爱的他者,不是伦理上的他者,因此,列维那斯的他者是不彻底的他者。
从另一方面看,依利加雷对列维那斯的批判并不排除后者对伦理学所作的贡献,对待列维那斯,依利加雷既不一味地排斥,也不一味地接受;她批判的是列维那斯在伦理关系的叙述中女人的从属性,利用的是他关于他者性的激进见解,包括质疑自我优越于他者,将他者的根本他性置于分析的中心。列维那斯伦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伦理学先于本体论,也就是说,与他者的关系先于主体对它的主体性的理解;先确立主体性,然后建立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在列维那斯的伦理学中,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关系,我对他者负有无限的责任;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在他者面对面地向我发出的挑战中,我变成了主体,那个我第一次变成了一个主体的我。钱特把依利加雷与列维那斯的关系描述为:对我们来说,列维那斯重新思考他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依利加雷重新思考性差异问题提供的模式;如果列维那斯的哲学计划可以描述为试图摆脱主宰西方哲学面貌的同一性霸权,那么依利加雷根据这一激进的列维那斯式的背离巴门尼德着手思考性差异[8]208。
列维那斯对他性的解释虽然激进,但不是没有问题。钱特认为,要正确理解列维那斯对他性的解释,我们需要理解他回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的冲动,在这里,女性脱离了本体论的画面;只有理解了这一意义,我们才能合理地询问列维那斯的思考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又在什么意义上,这些思考阻止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可能性[9]10。钱特是要我们从列维那斯利用和超越海德格尔中把握他的思想,理解他的思想对女性主义借鉴价值和具有的危害性。依利加雷正是在理解了列维那斯伦理学的可取之处和危害之处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伦理学,这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出列维那斯伦理学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将她自己的性差异伦理学与神学联系起来。
依利加雷的批判表明,列维那斯对伦理上超越的描述是通过将女性限制在欲望的动物性实现的。超越者是男人,对他者负责针对的也是男人。女人被归入到欲望的肉体体现,与享乐同类,与伦理学不同类。因此,在性爱这一“暧昧”的结合上,男女由于不同类被划清界限。将女性等同于性爱,这意味着女性的欲望不是升华,而是压抑;女性不能获得充分的主体性地位,或者说女人的主体性受到限制。通过性爱,男性的欲望成功地超越了身体,超越了动物性,超越了需要和满足的有限模式。总之,列维那斯的伦理学抬高了男人,贬低了女人。
关于神学,这是依利加雷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题,《给伊曼纽尔·列维那斯的问题》一文的副标题便是“论爱的神性”。虽然列维那斯的伦理学形成于对宗教神学的反思,并且这一点使依利加雷从中受益,但是在性爱的丰饶性上,两人具有不同的看法。在列维那斯那里,性爱的丰饶体现在儿子的诞生。在依利加雷看来,性爱在任何生殖之前是丰饶的,儿子不能解释最不可化简的他性之谜。如果列维那斯看到了两个恋人不仅仅是生育孩子,还有两个恋人自身在性爱中的再生,他这种丰饶性以外的再生也是不符合伦理的,在依利加雷看来,列维那斯的施爱者限制了他的受爱者的活动,否定了差异性,加强了同一性,用她的话说,施爱者“吩咐她凝固成使她与自身分离的形状,剥夺她温情流动的柔软性……吞并他者……[他 ]使他者的活动瘫痪”[6]194-95。列维那斯的施爱者在怀孕的节奏中仅仅看到了孩子的潜力,但他忽视了受爱者本人身上的差异性。依利加雷转向创造神话的意象证明自己的论点:
当施爱者将她归入婴儿、动物或母亲时,这一神秘性的一个方面,即与宇宙的关系,没有被阐明……耕作自己已经围圈起来的花园,这是地主干的活儿,他不考虑使丰饶成为可能的自然界,不考虑上帝对这一体现其化身的宇宙的关注,不考虑它的诱惑物的和谐性[6]195。
这段文字表明,列维那斯的施爱者对待女人就像地主对待土地一样,他只考虑把自己的领地围圈起来,让自己的土地丰饶,不考虑使土地丰饶的条件。上帝创造了万物,宇宙的万物具有神性,而列维那斯的“地主”割断了土地与自然、与宇宙、与上帝的关系。就受爱者来说,她停留在“丰饶性”上,就像土地一样。男人通过使土地丰饶实现自我的超越,进入宗教和伦理,女人为男人的超越提供了条件,而女人自身不具备超越的条件,她与宗教没有联系,与神没有联系,只能回到从前,回到“丰饶性”。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两个恋人之间再生,女人最终还是不能通过性爱走向伦理。
综上所述,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列维那斯的他者伦理学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危害之处。可取之处表现在试图摆脱整体性束缚,坚持伦理学先于本体论,将主体性与责任性统一起来,将他性作为分析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女性差异性。危害之处表现在将性爱关系从伦理学中排除,使伦理学失去了家庭生活这一核心内容,也使女人停留在做母亲的角色上,并成为男人利用的工具,不能进入伦理世界,不能进入宗教世界。在批判和利用的基础上,依利加雷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性差异理论学。
[1]孙向晨:《莱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及其对本体论的批判》,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5期。
[2]Levinas,Emmanuel.Existence and Existents.Trans.Alphonso Lingis.The Hague:MartinusNijhoff,1978.
[3]Levinas,Emmanuel.Tim e and the O ther.Trans.Richard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7.
[4]Levinas,Emmanuel.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Trans.Alphonso Lingis.The Hague:MartinusNijhoff,1979.
[5]Tina Chanter,Fem 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 anuelLevinas,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6]Irigaray,Luce.An Ethics of Sexual D ifference.Trans.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Gill.Ithaca: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3.
[7]Whitford,Margaret.The Irigaray Reader.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1.
[8]Chanter,Tina.thics of Eros:Irigaray’s Re-W riting of the Philosophers.New York:Routledge,1995.
[9]Chanter,Tina(ed.).Fem 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nuel Levinas.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28-52.
Irigaray′s Fem in ist Criticism of Levinas′s Ethics of O ther
FANG Ya-zhong1, ZHANG Ya-nan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an430023,China;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W uhan Sports University,W uhan430079,China)
Radical ideas are contained in Levinas′s discussion on women,which is of some merit to feminist theories.However,Levinas is not constantly radical.His early radicalis m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his later conservatism.As a result,women and Eros are excluded from his ethics,and onlymotherhood and efficacy of Eros are retained.From the angle of feminis m,Levinas′sOther is not a complete Other.Irigaray directed her feminist criticis m againstLevinas′s ethics ofOther.
Irigaray;levinas;ethics of other;feminist criticis m
方亚中 (1961-),男,湖北大冶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张亚楠 (1960-),女,湖北武汉人,武汉体育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009y083)
2010-04-18
B82-052
A
1671-7023(2010)06-0015-07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