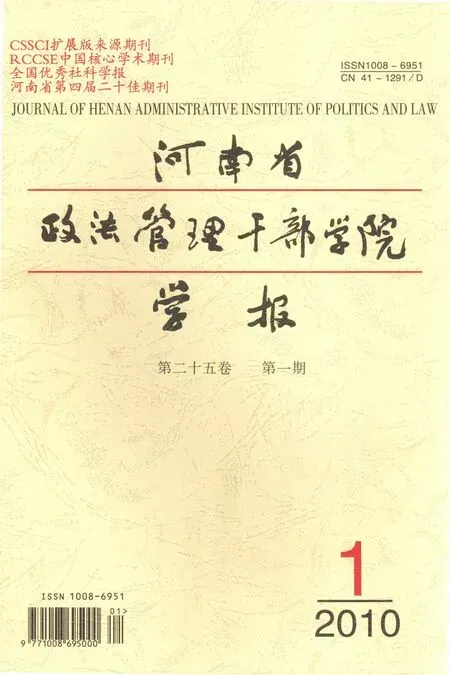论“客观处罚条件”的若干问题
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违法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的类型,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意味着该行为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必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不存在行为虽符合犯罪构成但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情形,换言之,在我国的犯罪构成当中,没有德日刑法学中所谓“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余地。但是,近年,有些学者提出,我国刑法的规定当中,尽管没有客观处罚条件概念的存在余地,但类似于“客观处罚条件”的内容却是存在的,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都属于此,并受德日刑法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论的启发,将这些内容定义为“超过的客观要素”或者“犯罪的附加要件”,认为它们虽是犯罪构成的内容,但和作为该罪的主观要件的故意、过失无关①张明楷:“‘超过的客观要素’概念之提倡”,载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页以下。另外,提倡类似见解的论文还有,刘士心:“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刍议”,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1期;陆诗忠:“刍议‘客观处罚条件’之借鉴”,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5期;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可是,在日本,近年,对传统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进行批判,主张将其还原为违法要素,同样受责任原则的支配,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的见解日渐有力[2];同时,在我国刑法当中,所谓“超过的客观要素”或者“犯罪的附加要件”在具体犯罪构成当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是否独立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范围之外的客观要素?其和我国刑法所坚持的责任原则该如何统一协调?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当中,没有“超过的客观要素”存在的空间,也没有必要提倡这种概念。以下,结合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刑法规定,对上述观点进行简要说明。
一、“客观处罚条件论”
和德日等国不同,在我国,成立刑法当中所规定的犯罪,多数情况下,仅仅有违反行为还不够,该行为还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即便在一些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犯罪当中,就实际的应用而言,司法机关在是否成立犯罪的认定上,也往往有一定结果的要求。如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伪造货币的”,成立伪造货币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金。仅从法条规定来看,成立本罪,似乎只要具有伪造货币的行为就够了,没有其他要求。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并非如此。成立本罪,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必须在 2000元以上不满 3万元或者币量在 200张 (枚)以上不足3000张(枚),否则就不能成立本罪①参见 2000年 9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换言之,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成立犯罪,行为通常必须已经造成一定的实际损害结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点,和刑法当中仅仅将实施一定行为作为犯罪成立要件(过失犯除外)的日本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于刑法明文规定行为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等场合才能成立犯罪,因此,这种“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在具体犯罪构成当中,属于何种要件,处于什么地位,难免有争议。有学者将其作为客观处罚条件对待,如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类的要件是客观处罚条件,在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犯罪,但是,不应受到刑罚处罚[3]。另有学者尽管没有使用“客观处罚条件”一语,但也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类的要件是独立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和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而仅仅是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并依据这种观点创设了自己的犯罪论体系②陈兴良:《陈兴良刑法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6页、第 97页。按照陈教授的理解,犯罪成立要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罪体(主体、行为等),罪责(故意、过失等)和罪量(数额、情节),即将罪量作为独立于成立犯罪的行为、主体和故意、过失之外的要件。。这两种观点,尽管在用语上略有差别,但在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都是独立于犯罪成立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不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范围之内的一点上,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可以看做为同一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其不仅违反了我国有关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有误导司法实践之虞。
首先,上述观点错误地理解了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将犯罪结果和客观处罚条件混为了一谈。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是指和犯罪成立无关,仅仅与行为人是否受罚有关的客观事实。一般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还原为犯罪成立条件,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政策性事由,换言之,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是和是否成立犯罪无关,只是和是否对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有关的事实[4]。这种客观事实,显然和盗窃罪中必须造成“数额较大”的财物被盗等不可同日而语。在我国,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犯罪只能是严重危害社会,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其中,“严重危害社会”的法律表现,就是侵犯了“数额较大”的财产、“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行为人仅只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但是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后果的话,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按照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可见,引起或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结果,是判断行为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的前提,是具体犯罪的成立条件。既然如此,就决不能说“数额较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和犯罪成立无关的客观处罚条件。
3.5.2 局部麻药和放射线的应用 口腔治疗采用的麻醉一般都是局部麻醉,使用的麻药是利多卡因或阿替卡因,且用量较小,不会导致胎儿畸形,孕妇可以放心使用。研究表明,电离辐射剂量<5 mrad时不会对胎儿造成危害。拍摄一张普通牙片的辐射剂量仅为0.1 mrad,所以为了协助诊断,必要时孕妇佩戴颈围和铅放射服可以拍摄牙片。
其次,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当中,不可能有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或者与其类似的因素存在的空间。我国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唯一标准,行为人的行为只要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就毫无例外地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不可能出现行为符合某具体犯罪构成之后,还要考虑该行为是不是符合其他条件,然后再决定是否对其刑罚处罚的情形。因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程度的侵害行为和应当作为犯罪加以严厉谴责的主观责任的统一,是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统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意味着该行为无论是在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上,都达到了成立该种犯罪所必要的、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不可能出现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了犯罪构成但在处罚上还要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形[5],这是从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有关犯罪概念的规定当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上述两种观点恰恰在此有问题。其认为在犯罪构成之外,还存在决定行为是不是要受到刑罚处罚的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将成立犯罪和是否要受到刑罚处罚割裂开来,无视犯罪就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的基本定义,直接违反了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有关犯罪概念的规定。
再次,按照这种观点,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来。如在行为人盗窃了一个价值 300元钱的财物的场合,按照上述观点,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成立盗窃罪或者已经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只是因为所盗窃财物的价值太小,数量不够①按照 1998年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 500元至 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所以才不予以处罚。这种结论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有关盗窃罪的规定。
二、“超过的客观要素论”
有学者认为,尽管我国刑法当中,不存在德日刑法当中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空间,但是,类似于德日刑法中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所说的事实还是存在的。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所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②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作为成立要件之一的“造成严重后果”,就是如此。因为,“本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虽然是构成要件,但不需要行为人对严重后果具有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造成严重后果’便成为超出故意内容的客观要素,属于‘超过的客观要素’”③张明楷:“‘超过的客观要素’概念之提倡”,载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页。。这个观点,从与德日刑法理论中所存在的“超过的主观要素”相对应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与客观处罚条件类似的“超过的客观要素”的存在。即“超过的主观要素”概念表明,有些主观要素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同理,有些客观要件也不可能存在与之相应的主观内容,这便是作者所提倡的“超过的客观要素”④张明楷:“‘超过的客观要素’概念之提倡”,载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页。。这个观点,跳出了德日刑法学当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议的、为了说明客观处罚条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就先说明其不是故意、过失的认识对象,但在说明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又主张其受作为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制约的循环论证的窠臼,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当中的“造成严重后果”果真就是所谓不在行为人认识范围之内的“超过的客观要素”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是指“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和盗窃罪中行为人的盗窃行为直接引起了他人占有的财物被盗、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的行为直接引起了他人的生命被剥夺的情况不同,在丢失枪支不报罪中,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严重后果”,不是由丢失枪支的行为人本人所引起的,而是指其他犯罪分子利用该丢失的枪支所造成的[6],这种结果能否看做为行为人本人的不报告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成为问题。在国外,之所以将“就任公务员”看做为事前受贿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将“确定宣告破产”看做为欺诈破产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就是因为“就任公务员”是受贿行为人以外的、具有任命权的第三人的行为结果,而“确定宣告破产”也是欺诈破产行为人以外的法院的行为结果。这种将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实施的行为事实作为决定行为人是不是构成犯罪的情形,对于行为人而言,当然是其难以预料的,所以,应当放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外。这也是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的最主要理由[7]。
但本文认为,这种由第三人所引起的结果,是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因素,属于该罪的构成要件结果,应当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范围之内。理由如下:
一方面,由行为人之外的第三人所引起的结果,在表明不报告行为具有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一点上,和行为人本人引起危害结果的场合一样,二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二者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在以发生犯罪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当中,行为的因果发展趋势由于和行为对象相遇而引起了法益侵害,而在以客观处罚条件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当中,同样的行为因果发展趋势由于和“客观处罚条件”相遇,而使得先前已经存在某种危险增大到了可罚的程度[8]。如在故意杀人罪当中,由于子弹射中被害人、夺走其生命而使该行为的危险达到最高程度而成为现实即既遂,同理,在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由于丢失枪支不报者之外的其他人“造成严重后果”,使得先前的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行为当中所潜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转化为了现实的可罚的危险。
另一方面,并不是只有和行为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要素才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影响。如刑法第三百四十条所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行为人只有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场合,才能成立犯罪。这里,“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尽管是决定行为是不是具有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要素,但其和捕捞行为之间,显然不具有因果关系。可见,那种认为只有和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才是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见解,是不妥当的。
既然“造成严重后果”在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构成要件当中如此重要,那么,从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立场来看,其当然应当在行为人的认识或者说预见的范围之内。因为,行为人只有在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有认识和预见时,才能明白自己的性质,从而打消其实施该行为的念头。行为人若只是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认识,而对于该行为所可能具有的后果没有认识,那么,就是属于行为人不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情形,不符合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因此,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故意的角度来看,也必须说,“造成危害后果”,是成立故意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相反地,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当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之类的要件作为“超过的客观要素”,将其放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之外的做法,也违反了近代刑法所主张的责任原则。责任原则的基本意思是:行为人只对在行为时所认识到或者所能够认识到的外部事实承担责任。如行为人在对远处的物体开枪时,如果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也不可能意识到对象是“人”的时候,即便客观上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但也不得以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及第十六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也坚持了这一点。即成立犯罪,行为人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具有认识或者预见,或者具有认识或者预见的可能性,否则,即便造成了客观侵害结果,但也不能成立犯罪。就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所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而言,“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是成立该罪所必不可少的结果,属于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既然如此,怎么能将其排除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外呢[9]?
对于上述观点,最近有学者撰文主张,责任原则并非没有任何例外的教条。客观处罚条件是基于刑法以外的目的设定即控制风险的公共政策需要而设置的犯罪成立条件,是责任主义原则的例外,提倡合目的、有节制地对刑事责任原则创设诸如客观处罚条件等必要的例外[10]。但是,在我看来,该文存在两方面的严重缺陷:一是该文对于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存在误解。其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都作为“客观处罚条件”,这显然没有超出我国传统观念将“犯罪结果”和“客观处罚条件”混为一谈的窠臼;另一方面,对责任原则的例外存在误解。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主观责任原则,尽管说在关注社会防卫、强调刑罚的一般效果的英美等国,具有刑法客观化优先、责任原则弱化的迹象,但是,这种理解可能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即便在英美的学者也认为,“事实上,说犯罪这种法律上所禁止的行为,是以无过错责任的基础来加以禁止的,除非被告人提出证据,清楚地证明没有过错”,“任何刑事责任情形都不可能完全不需要犯罪意图”[11]。承认作为责任原则的例外的客观原则或者说严格责任,长期来看,不仅难以实现其追求一般预防的初衷,反而有弱化一般预防效果以及特别预防效果的趋势。因为,客观责任和严格责任是对没有主观责任的人进行处罚,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感,结果让一般人丧失守法意识,而且就受到处罚的行为人而言,由于其运气不好而受罚,刑罚对其难说具有感召力,因此,也难以奢求刑法对其具有防止再犯的特殊预防效果[12]。这样说来,扩大责任原则例外的应用范围,并不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提倡超过的客观要素的学者并不完全否认“造成严重后果”之类的要素和故意、过失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只是主张二者之间只要像结果加重犯的场合一样,行为人对于结果具有认识可能性即过失就可以了[13]。但是,这种看法自我矛盾。因为,行为人既然格外强调上述要素是不在行为人认识范围之内的“超过的客观要素”,何来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发生该结果的可能性的认识呢?而且,和结果加重犯不同,在所谓“超过的客观要素”成为问题的犯罪类型当中,基本危害行为 (如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行为)本身并不是犯罪(单纯的丢失枪支不报行为是违反《枪支管理法》的一般违法行为),不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程度的可罚性,这就意味着行为人仅对基本行为有认识而对所发生的后果没有认识的场合,还不足以唤起其违反刑法规范的意识,不符合成立该罪所要求的主观要件;而在结果加重犯如故意伤害 (致死)罪的场合,基本行为即故意伤害行为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人只要对该行为具有认识,就可以说其具有刑事违法性的意识,符合成立犯罪所需要的主观要件。因此,比照结果加重犯,认为在将类似于客观处罚条件要素的犯罪类型当中,行为人不要求对该要素具有认识,只要具有认识可能性的观点在说理上也具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我国,提倡“超过的客观要素”的学者认为,承认超过的客观要素,能够解决部分犯罪中不能区分此罪与彼罪,也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的问题。如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行为人都是出于故意实施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并且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但法定刑较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认为本罪由故意构成,即对引起甲类传染病的传播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那么,就不能对本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合适区分,也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14]。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也值得商榷。在坚持将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等客观因素作为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础的客观主义刑法观的时候,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刑是否相适应,首先是根据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这些外在因素来考虑,而不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考虑,否则,就会落入心情刑法的陷阱。从行为的客观特征来看,“拒绝供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的行为并不能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之间画等号;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其危害性,就马上达到了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程度。因为,从行为分类上讲,“不消毒处理”或者“拒绝供应”都是拒不履行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而与此接近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实行行为通常则是作为,二者之间具有行为结构上的差异,不能同等看待。换言之,尽管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但仍不能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主要是因为这两种犯罪在实行行为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实际上,在行为人明知自己违反《传染病防止法》规定的不作为行为极有可能“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而故意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情节严重,足以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实行行为同等看待的时候,也完全可以看做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通常以作为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①参见 2003年 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从理论上讲,某种犯罪在主观上,到底是要求故意还是过失,其判断标准并不在于行为人是不是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这种意志要素,而是取决于行为人对行为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否具有认识和预见。尽管在故意的本质上,国外学说中有多种理解,但是,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行为人只要对行为和结果有能唤起其违法性程度的认识和预见,而没有打消实施行为的念头,就足以表明行为具有故意[15]。我国刑法第十四条有关犯罪故意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观念。将“放任”犯罪结果发生这种淡化行为人追求或者希望发生某种结果色彩的形式也作为故意的意志要素,就是其体现。因此,在我国刑法对于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到底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判断,主要还是看行为人对于可能发生的结果有没有预见。有预见而不制止的场合,就是故意;能够预见也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场合,就是过失;在没有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场合,当然也谈不上制止了,也就无所谓过失。行为人对于可能发生的结果有没有预见,主要是看法条对于行为人违反规范态度的描述以及对其违反规范态度的评价(主要标志是法定刑的轻重高低)。如就丢失枪支不报罪而言,法条对于行为人违反规范态度的描述是,在行为人明知枪支是一种危险物品,失控的话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况下,仍然“不及时报告”,这显然是行为人明知故犯、故意而为的态度,因此,属于故意犯罪形态。
至于说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法定刑很轻,这主要是因为丢失枪支不报罪,客观上就是一个不及时报告的行为,其和自己用枪杀人的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难以对其进行很严厉的谴责。虽然在本罪当中,也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但该种后果并不是不报告者本人所引起的,而是由其之外的其他人所引起的;同时,不报告也并不必然引起“造成严重后果”。有时候,行为人即便报告了,但也仍然难以找到该枪支。当然,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枪支被某犯罪分子偷走之后将要用于杀人,却仍然不及时报告,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的场合,就恐怕不是一个丢失枪支不报罪所能评价得了的。
三、结论
在德日刑法学当中,传统观点所主张的、独立于犯罪概念之外但对犯罪处罚具有重要影响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正在消失,日渐被看做存在于犯罪概念当中,说明行为的违法性的要素之一;同时,传统观念上所称的其不受责任原则制约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主张就所谓属于客观处罚条件的事实而言,行为人必须对其要有认识、预见,至少必须具有认识、预见的可能[16]。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当中,根本就没有属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超过的客观要素”的存在余地;从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超过的客观要素”,作为和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具有某种关系的结果,是表明该行为达到了应受处罚程度的具体体现,作为说明该行为达到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程度社会危害性的标志,应当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而不可能超出其外。
相反地,如果说该因素存在于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外,是独立的超过的客观要素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理论上的混乱。
首先,可能会混淆犯罪故意和一般违法故意之间的区别。众所周知,刑法上的犯罪故意和一般违法行为的违法故意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场合,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犯罪结果,即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后者的场合,则不要求行为人的认识要达到这种程度。说“客观处罚条件”或者说是“超过的客观要素”不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就意味着在以上述因素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类型当中,行为人只要对一般违法行为有认识,即便没有认识到该行为可能导致值得刑罚处罚的结果,也能说行为人具有故意,这实际上是承认“只要具有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程度的认识,就是具有犯罪故意”的观点,取消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其次,会导致追究偶然责任。所谓偶然责任,实际上是结果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要求行为人对与行为有关的结果具有预见,只要客观上发生了危害结果,行为人就要受到处罚。客观处罚条件或者说是超过的客观要素尽管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决定行为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可罚性,但是,由于不要求其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因此,即便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但只要不幸引起了该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如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在丢失枪支之后,不及时报告,如果该枪支被他人利用,造成人员死伤等结果的话,就构成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所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但是,如果该枪支没有被人利用,或者尽管被利用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话,就不构成犯罪。换言之,本罪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在于行为人本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而在于其运气。这实际上是对刑法所主张的主观责任原则的公然破坏。
再次,会破坏构成要件规制故意的机能。近代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因此,成立犯罪,行为人原则上必须具有故意,即行为人具有故意是成立犯罪的前提。但是,由于故意的内容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和实现的意思,因此,在结局上,决定成立故意所必要的事实范围的还是构成要件。换言之,构成要件具有规制故意内容的机能。但是,将作为犯罪成立要件重要组成部分的客观处罚条件的内容,排除在故意的认识范围之外,显然是对构成要件规制故意内容机能的破坏,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将一些包含有以故意违反法规为实行行为的犯罪认定为故意犯罪①如交通肇事罪就是如此。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为人只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能构成。这里,如果不考虑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后果是不是具有认识的话,完全可以根据行为人故意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认定其为故意犯罪。。
笔者认为,在将“造成严重后果”之类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时候,这种要件必须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按照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这种认识不要求一定是确定的认识,也可以是一种可能性的认识即认识到可能发生该种结果 (相反地,主张“客观的超过要素”论的学者认为,对类似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要素只要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可以了,即对该要素可以没有认识),因此,在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确实没有认识 (预见)的时候,不构成犯罪。当然,如何判断行为人是不是具有该种认识,则需要具体分析。就丢失枪支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而言,通常来说,行为人对所可能发生的后果是有预见的。因为,这里的行为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这些人对于枪支的性能、使用规则、管理规则等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对于在丢失枪支之后不报告,可能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应当说是有充分认识的。但在行为人提出反证,令人信服地说明,其对不报告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确实没有认识 (预见)的时候,便不得不说,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本罪。同样,就玩忽职守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犯罪而言,也必须如此考虑。这种考虑,和将上述要件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或者“超过的客观要素”的观点,在最终结论上,可能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思考方法更加合乎刑法规定,更加合乎责任原则,因此,更加合理妥当。
[1][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67;[日 ]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39;[日]大谷实.刑法总论 (新版第二版)[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1、458.
[2][日]松原芳博.犯罪概念与可罚性——客观处罚条件和一身的排除处罚事由 [M].成文堂. 1996.28.
[3]高铭暄,王作富.我国新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593.
[4][12][日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 [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4,158.
[5][6]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66,377.
[7][8][日 ]曾根威彦.处罚条件[A].[日 ]阿部纯二,等.刑法基本讲座第 2卷构成要件论[C].法学书院,1994.320,320.
[9]黎宏.刑法总则问题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0页以下.
[10]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J].清华法学,2009,(2):39页以下.
[11][美]道格拉斯 .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214、217.
[13][14]张明楷.“超过的客观要素”概念之提倡[A].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5,72.
[15][日 ]大谷实.刑法总论 (新版第 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6.
[16][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 (第 4版)[M].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98;[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 2版)[M].有斐阁,200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