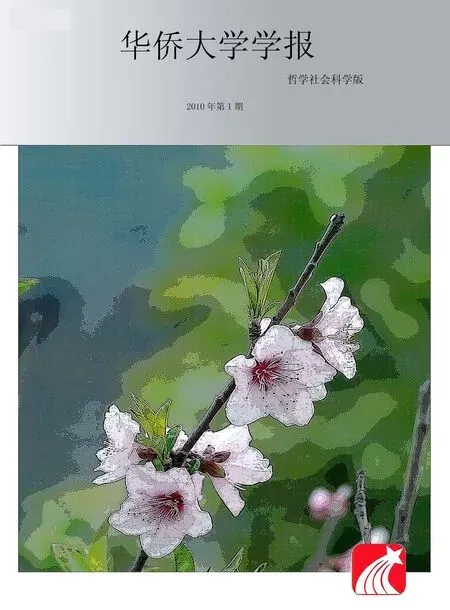艺术家的自我造就
——再读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
○万迪梅 张 燕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特有的女性敏感与直觉、高雅的审美情趣、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使她在众多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独树一帜。《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1927)是她创作旺盛时期的成熟之作。该小说是国内伍尔夫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通过检索中国期刊论文数据库(CNKI),总共找到119篇该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截止2009年9月)。就伍尔夫的单部作品研究的论文数量而言,《到灯塔去》名列首位。论文成果可谓丰富多彩:有的论者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注]申富英. 评《到灯塔去》中人物的精神奋斗历程[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 (4): 66-71; 容新芳,张士民. 人与物的相映与生辉——论《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与灯塔的象征意义[J]. 外语教学, 2004, (6): 89-92; 赖 辉. 论《到灯塔去》中的父亲意象[J]. 中国文学研究, 2006, (1): 100-102.有的论者分析小说的意识流手法;[注]李 森. 评弗·伍尔夫《到灯塔去》的意识流技巧[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 (1): 62-68; 赵秀凤. 意识的隐喻表征和合成——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认知文体学分析[J]. 外国语文, 2009, (2): 11-17.有的论者探讨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注]束永珍. 区别与整合: 《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 (1): 61-66; 万迪梅. 《到灯塔去》隐喻的女性主义解读[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87-90; 王 文, 郭 娜. 理性与情感相融合的女性表达——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J]. 国外文学,2005, (2): 101-104; 王 苹. 《到灯塔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1): 69-74.有的论者探讨小说的时间艺术;[注]秦 红. 永恒的瞬间——《到灯塔去》中的顿悟与叙事时间[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2): 37-40; 王丽丽. 时间的追问:重读《到灯塔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4): 63-67; 卢 婧. 伍尔夫《到灯塔去》的时间艺术[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3): 98-102, 120.而有的论者则对小说中的绘画因素情有独钟。[注]冯 伟. 生命中的那个美丽瞬间——试析弗·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绘画元素[J]. 国外文学, 2004, (1): 90-94; 宋 涛,朱 洁. 感觉与印象里的真实世界——析《到灯塔去》[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76-81; 张中载. 小说的空间美——“看”《到灯塔去》[J]. 外国文学, 2007, (4): 115-118.本文对拉姆齐夫人操持的晚宴以及莉丽为拉姆齐夫人画像这两大场境的象征意韵作一探讨,认为,通过成功塑造拉姆齐夫人和莉丽这两位艺术家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完成了自己艺术家身份的造就。
《到灯塔去》全书分为“窗”、“时光流逝”、和“灯塔”三部分。小说第一部分第十六、十七、十八章长达四十页的篇幅均围绕着拉姆齐夫人操持的晚宴。这场晚宴由拉姆齐一家十口与五位客人参加。拉姆齐夫人渴望通过精心准备的晚宴,体现她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房子里的天使”的成功和自豪,也希望借助精美的晚餐使在座的人们打破冷冰冰的自我,彼此敞开心扉,消除过往的隔阂与敌意,找回失落的友善与和谐。小说第一部第十七章有这么两段关于晚宴的描写:
现在八支蜡烛放到了餐桌上,起初烛光弯曲摇曳了一下,后来就放射出挺直明亮的光辉,照亮了整个餐桌和桌子中央一盘浅黄淡紫的水果。……这样突然地映照在烛光之中,那只果盘似乎有着巨大的体积和浓度,就象是一个世界……她很高兴地(因为它使大家在顷刻之间有了共同的感受)发现,奥古斯都的目光也在玩味那盘水果,他的目光深深地侵入那只果盘,在那儿打开一蓬花球,在这儿撷取一束花穗,玩味领略一番后,又返回他的眼窝。那就是他瞧东西的方法,和她的方式大不相同。但是,共同注视一个物体,使他们感到团结一致。
现在,所有的蜡烛都点燃起来,餐桌两边的脸庞显得距离更近了,组成了围绕着餐桌的一个集体,而刚才在暮色之中,却不曾有过这种感觉。[1]101
从以上节选段可以看出,拉姆齐夫人苦心孤诣地营造餐桌上的气氛。柔和的烛光至少在视觉上使原先心有芥蒂的人们沉浸在一片祥和、融洽的气氛之中。而对于一盘装点精美的水果的凝视和遐想暂时地化解了奥古斯都对拉姆齐夫人的敌视。此前我们在书中看到奥古斯都“不喜欢她,他相信拉姆齐的事业都毁在了与她的婚姻上”。[1]43烛光和水果拼盘是晚宴这一象征中的“分支象征”(subsidiary symbols),是晚宴这一拉姆齐夫人在生活中创造的大艺术品中的两件小艺术品。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与生活中的艺术家拉姆齐夫人共同象征着温暖、同情和美,使屋中每个人的冷漠和敌意涣然冰释,使大家分享着团结一致的喜悦之情,使屋内的一切变得井然有序。可以说,拉姆齐夫人就是一位善于把充满分歧和混乱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和谐融洽的生活艺术家。
在拉姆齐家做客的女画家莉丽执着地追寻生活与艺术的真谛。她一直想把拉姆齐母子坐在窗边讲故事的情景搬上画布,却无法透过外表把握住真实的拉姆齐夫人,觉得“要从四面八方来观察那个女人,五十双眼睛还不够”。[1]210在小说第一部,莉丽无奈地放弃了这幅画。小说第二部“时光流逝”被伍尔夫以诗化的象征性手法描述为漫漫长夜,把充满战争浩劫和生死变故的十年时光压缩在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中,用带方括号的几句话简单交代了拉姆齐夫人和两个孩子的死。在小说第三部“灯塔”中,战后余生的拉姆齐家其他成员和莉丽等宾客故地重游,返回了小岛上的度假屋。拉姆齐先生和两个孩子完成十年前未成的灯塔之行,追思已故的拉姆齐夫人;莉丽则重拾荒废十年的旧画,希望通过对拉姆齐夫人的回忆完成画作。她知道艺术的任务在于“表达某种意义”,要“通过象征呈现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怎样“把画幅右边的一片和左边的一片融接起来”,[1]56达到画面的和谐却一直是她长期无法逾越的障碍:谢天谢地,她重新拿起画笔想道,那个空间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它瞪着眼睛瞅她。整幅画面的平衡就取决于这枚砝码。这画的外表,应该美丽而光彩,轻盈而纤细;然而在这外表之下,该是用钢筋钳合起来的扎实结构。[1]182在一片迷茫之中,莉丽高声呼喊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她失声喊道,感到某种恐惧又回来了——不断欲求,却一无所得。拉姆齐夫人——那个身影是她完美品德的一部分——就坐在椅子里,轻巧地来回抽动着她手里的钢针,编织着那双红棕色的绒线袜子,并且把她的阴影投射到台阶上。她就坐在那儿。[1]214莉丽在回忆里发生了幻觉。此前她试图在追忆中靠近拉姆齐夫人,却没有控制住她的对象,而是被死亡所造成的分离折磨着。此刻拉姆齐夫人的幽灵回来了,并认可了莉丽的艺术意念。当莉丽顿悟而画出最后一笔的时候,台阶是空荡荡的,幽灵已离开,但莉丽已经捕捉到了她: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好像在一刹那间她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她在画布的中央添上了一笔。画好啦,大功告成啦。是的,她极度疲劳地放下手中的画笔想道:我终于画出了在我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1]221小说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暗示着:虽然这幅画作为一个物品会保存下来,但艺术家战胜自我、获得顿悟的一刻却一去不复返了。这恰恰与拉姆齐夫人在晚宴结束时意识到她的创造“已经成为过去”不谋而合。
让我们再一次审视拉姆齐夫人和莉丽。她们都是艺术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创造在混乱与矛盾之中建立起和谐、建立起秩序。虽然她们创造的形式有所不同,却殊途同归。她们都知道自己的创造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抗争。查尔斯·塔斯莱嘲笑莉丽,老是说“女人可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1]51在小说第一部里,拉姆齐夫人运用自己的善良、智慧与同情心在晚宴上获得了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瞬间。而她意识到在这创造中是没有男人的位置的,“她又一次感觉到(仅仅作为一种事实而毫无恶意),男人们缺乏能力、需要帮助”。[1]87查尔斯·塔斯莱为虚荣心所扰,“他的一切都有那种枯燥、刻板的味儿,一点也不讨人喜欢”;[1]89威廉·班克斯是乏味的,宁愿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拉姆齐先生“正在撇着嘴巴、蹙额皱眉、红着脸儿发火。……只是为了那可怜的老头儿奥古斯都先生要添盘汤——如此而已”;[1]99保罗·雷莱刚刚说服敏泰答应自己的求婚,却轻率地迟到了很久。在座男人们的自怜自艾也罢,妄自奠大也罢,他们的虚荣、贪婪、权力欲等等都威胁着这场晚宴。但是拉姆齐夫人战胜了他们,她的努力在祖传美食“都勃牛肉”上桌的一刹那获得极大的成功。牛肉的美味征服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对食物最为挑剔的威廉·班克斯和之前对她有很大成见的奥古斯都。美味作为一种纽带使大家拥有同样的感觉,将人们的心灵沟通了起来:“现在,这喜悦的气氛就象烟雾一般逗留在这儿,象一股袅袅上升的水流,把他们安全地凝聚在一起。……她觉得它带有永恒的意味;……她想,那种永恒持久的东西,就是由这种宁静的瞬间构成的。”[1]109-110是的,拉姆齐夫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的如此美好的瞬间会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犹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不会被岁月磨蚀掉它的光彩。正如莉丽在画布上画下完美的最后一笔时,虽然十年前的日子连同拉姆齐夫人都永远地离去了,但是逝去的岁月、故去的人都以艺术的形式得以永存。
拉姆齐夫人与莉丽都在不停地追问着关于自我本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也是艺术家探讨并关注的问题。拉姆齐夫人在晚宴开始时自问:“但我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莉丽在第三部“灯塔”的开头就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她有一种欲望要跟卡迈克尔先生“谈谈生和死;谈谈拉姆齐夫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随着岁月的流逝免不了会向你逼近过来的问题。那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伟大启示,从来没有出现。也许这伟大的启示永远也不会到来。作为它的替代品,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奇迹和光辉,就象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了一根火柴,使你对于人生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1]171-172这也许就是伍尔夫欲与读者分享的人生真谛:爱可以战胜死亡,人类的奋斗可以战胜流逝的岁月。它使我们想起伍尔夫在日记里对《到灯塔去》主题作出的描述:“关于我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2]76伍尔夫借助莉丽之口回答了拉姆齐夫人和莉丽提出的疑问:“在一片混乱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形态;这永恒的岁月流逝被铸成了固定的东西。你、我、她都随岁月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什么也不会留存;但是文字和绘画却不是如此,它们可以永存。”[1]191这样,莉丽在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之中,通过艺术领悟力而升华至高远宏大的境界,达成对生命的一种普遍化观照。通过已故的拉姆齐夫人在生者记忆中依然生存,生命的意义得以显现。此外,那长长的、恒定的灯塔之光是拉姆齐夫人的光芒,象征着她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带给人们心灵的安定祥和。灯塔闪烁的光又象莉丽手中跳动的画笔。她们都是艺术家,夫人的社交艺术和莉丽的绘画艺术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秩序,从而探索人生的意义,发掘深藏于表象下的内在真实。小说以莉丽在画布上投下长长的一笔、完成给自己深爱的拉姆齐夫人的画像收笔,意味深长。随着莉丽完成这完美的最后一笔,伍尔夫也成就了传世的艺术品《到灯塔去》。
伍尔夫在192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透露了她写作《到灯塔去》的直接动因:“这部作品不会太长,将把父亲的性格全写进去,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维斯岛,还有童年,……”[2]76伍尔夫也曾说过:“没有任何传记家能够猜测到1926年晚夏有关我生命的这一重要事实。”[3]81《到灯塔去》正是于1926年9月完成第一稿的,她认为这部书的写作对自己的心灵产生了净化和升华的作用。在相似于圣·艾维斯岛的赫布里兹岛的背景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她的家庭为原型绘制了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图景,占据画幅中心的则是以她父母为原型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知识贵族的人物形象。通过对父母记忆的清理,她还对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并通过莉丽这个人物表达了新一代人的观点和理念。以莉丽完成她的画来结束全书,说明了这一人物的重要地位,她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新一代人,以新的眼光对父母辈进行评判,同时通过对父母辈的超越体悟着人生,建构着自己的生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莉丽就是伍尔夫本人的化身,是伍尔夫作为艺术家的自我画像,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4]232-233
《到灯塔去》里包含着大量艺术创造的体悟和感受。莉丽在小说第一部里无法完成拉姆齐夫人的画像。作为艺术家,她直到经历了十年沧桑、以下一代的视角再次审视已故的拉姆齐夫人时,才能够把握她的对象,将她对故人的记忆转化为艺术。莉丽曾为拉姆齐夫人的魅力所倾倒,她一直无法停止对后者的爱和思念。然而多年后当具有自我独立精神与成熟思想力量的莉丽重新审视拉姆齐夫人时,发现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家庭天使型”的女性规范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她想,拉姆齐夫人已经隐没、消失了。现在我们可以超越她的愿望,把她那种带有局限性的老式观念加以改进。她已经退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1]185-186莉丽拒绝了婚姻,拒绝了拉姆齐夫人善意地强加于女性的那个“有关婚姻的普遍法则”。伍尔夫借她表达了后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观念,也体现了伍尔夫艺术家自我的成长和逐渐成熟。小说结尾实际上是描写了一个艺术家的成熟,一个女人从往昔中获得了解放。莉丽没有屈从于先辈的画像,而是展现了现代人对绘画艺术的新阐释。艺术家以一种有控制、有选择的方式运用了往昔而获得解放。[5]282伍尔夫也承认:“我把那个世界[斯蒂芬家庭的世界]包含进了由我自己的气质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之中。”[3]84她毫不留情地抛掉父母身上那些陈旧的、不健康的习性,通过莉丽在记忆中筛选他们的性格特征,找出那些能完善她的艺术的成分,从而将新学会的现代艺术策略同她父母遗传的古老禀赋结合起来,在传统和个人才华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5]279
在母亲去世后的许多年头里,母亲的灵魂始终缠绕着伍尔夫。“我能够听到她的声音,看见她,想象着当我进行日常事务时她会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她这样回忆道。[3]80当这部小说完成后,她就不再看见母亲朱莉亚·斯蒂芬,也不再听到她的声音了。伍尔夫完成《到灯塔去》的草稿时是44岁,恰好是小说中莉丽的年纪。她写作《到灯塔去》就好比莉丽画成那幅画,她使生命永存,完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正如莉丽依据对拉姆齐夫人的回忆作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父母逝世多年后通过对他们的怀念和追忆,带着新一代人的视野超越了他们,支配了父母的遗传禀赋,排除了他们的不良影响,从而将自己造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到灯塔去[M]. 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 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Diary[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1.
[3]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M]. The Hogarth Press, 1985.
[4] 伍厚恺.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 [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M]. 伍厚恺,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