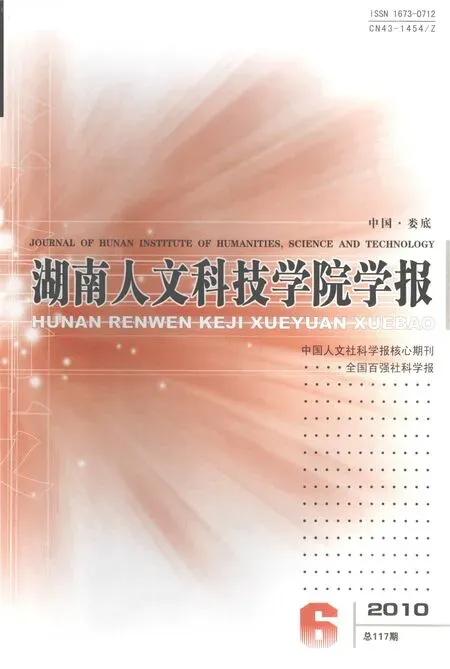身体的回归
——对王安忆、铁凝、刘恒1980年代创作的解读
胡 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 娄底,417001)
身体的回归
——对王安忆、铁凝、刘恒1980年代创作的解读
胡 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 娄底,417001)
新时期以来,身体在文学中获得了全面表现。在文学自身发展需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和消费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下,1980年代,以王安忆、铁凝、刘恒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将文学关注的目光投向身体的自然欲求,接受并肯定这种基于本能的天然权力。在他们的努力下,身体得以回归文学。
身体;回归;欲望;本能
文学作为关注人类存在的审美方式,与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奠基于个体身体的在世体验,并由这种身体体验调动起不曾经历过的境况,召唤出未曾谋面的他者的身体体验,从而以一己之身穿越充满迷雾的生存隧道,探究永恒的自我之谜。然而,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重视理性、蔑视身体的意识形态的操纵,身体始终未能积极贴切地溶入文学创作中。新时期以来,身体从重重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的幕后走到前台,成为进入文学创作视野中一个重要视点,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 理论与现实催生的写作
首先,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建国后的文学负荷着政治、革命、人民等宏大话语的沉重包袱,因其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注,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使它的总体艺术成就偏低。一部文学史几乎沦为一部政治斗争史、概念图解史,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只是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附庸而存在。政治对文学的钳制恰是以对身体的极端压抑为前提的,我们很少能在作品中看到关于人物情感、欲望、本能等与身体相关的描写。政治以对个体身体的绝对否定来消解它自身蕴藏的巨大能量,使它服从于自己“革命”和控制的目的。新时期文学要召回自己强劲的生命力,只有回归人自身,回归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生命载体的身体。这样,它才能从那些排斥个体自由的意识形态、道德、国家、伦理、政治运动等宏达话语中返回自身。梅洛·庞蒂曾指出:“身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唤起向我们呈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1]。有压抑必有反抗,并且越是禁锢和封闭,便越需要得到表现,因此,新时期伊始,身体便盛重登场,喻示着文学回归自身的要求。
其次,新时期以来,西方身体性理论的大规模引进与传播,对当代文学身体写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实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身心二分法的肇始。人类相应的文明史、伦理史几乎是不断遗忘甚至蔑视身体的历史。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身体性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共同关注的对象。身心两分法的既定设想受到了质疑和批判,身体获得了全新的诠释与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包括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现象学,坚决反对灵肉分离,认为身体决非仅是一种物质客体,而总是作为一种意识体现,是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存在。“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2]。理论与创作从来都是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身体性理论的引入,深化了作家对人的理解,拓宽了他们的创作领域,从而使身体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呈现。
再者,消费文化的强大刺激和影响,也是促使身体在文学中频频亮相的重要因素。新时期以来,以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生气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正在中国悄然兴起。生活的各方面相继受到市场的影响,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隐退。正如汪民安在《身体转向》中所指出的,“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3]。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类信仰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日渐衰落,旧有的社会群体逐渐瓦解,个体无法再在群体中找到依靠和支持。“我消费故我在”几乎成为今天的大众自我确认、自我认同的核心意识。然而,消费在使个体摆脱了外在权威而获得自主和独立感的同时,又使他们失去了安全和归属感。在这样的生存困惑中,人们只能将求助的目光转向对自身内在要求的确认,只能相信自我身体的感觉和判断,以此为基础重新寻找自我价值、主体性及生存意义,并由此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二 返乡途中的身体
早在20世纪初,周氏兄弟就呼唤过“人的文学”,在周作人同名论文中,他强调人乃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4],旨在强调人的灵肉二重性。他尤其强调人的动物性,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该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同时期许多作家一样,他希望藉此引起人们对人类身体性存在的注意。重视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是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建国后,这一优良传统却不断被忽略、扭曲甚至抛弃。文革时期对人的钳制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严重地偏离了五四时期开创的人的文学之路。在这种政治先行的文学环境中,作家们往往只取人的社会性、观念性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而将人的自然性、非观念性内容作为文学的盲点,将人架空为缺乏本能、缺乏血肉的本质人。新时期伊始,文学借助人道主义话语,试图摆脱极左思潮与政治权力的控制,获取独立品格。强调身体的存在,成为文学摧毁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武器。返乡途中的身体遭遇1980年代思潮迭起的小说创作潮流,便迅速融入各种流派中,悄然寻找自己的位置。混迹于纷至沓来的思潮流派中,被压抑已久的身体在众多作家不断突破自我的努力下逐渐从被遮掩的历史中浮现出来。作家们的努力为身体赢得了在文学中的合法地位,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力。本文选取王安忆、铁凝、刘恒三位作家的创作简要谈谈1980年代作家对返乡途中身体的关注。
(一)王安忆:欲望的诗意凝眸
在1980年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这个现实主义再度高扬的时代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仍然是个书写“共同梦”的时代。秉着对个体生命的体察入微和深切同情,王安忆是新时期较早释放两性间的“性”,将生命欲望推向前台的作家之一。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的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性史上无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我们主要分析她的《小城之恋》。
《小城之恋》选择背景的是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王安忆却摆脱了伤痕文学倾诉痛苦、抚摩伤痕的旧窠臼,而将目光投射到个体的身体性存在。《小城之恋》中,他和她是一个小剧团中不引人注意的演员,是大时代里两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没有太多的知识,对于时代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只是循着本能散漫地生活。急剧变化、自导自演的时代也无暇关注这两个小人物,他们自在地活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他们自小一起练功,彼此熟悉。他帮她开胯,她帮他将绷直的腿朝头顶上推。青春期生理的骚动使他渐渐无法忍受两人身体的亲密接触:“这要求(指帮她开胯)便更加折磨了。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起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再克制不了内心的骚乱了。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制,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5]165。而她也渐渐感受到了与他的身体接触是“一种压迫的快感”[5]181。他们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却无可救药地渴望身体的纠缠、搏斗。同是剧团小演员的身份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彼此的身体,他们终于实现了肉体的结合。一方面,他们沉浸于肉体融合的欢愉中:“经过激动的抚摸与摩擦的身体,是那么幸福的疲乏,骄傲的懒惰着。那爱抚好像是从毛孔里渗透了,注进了血液,血是那样欢畅地高歌着在血管里流淌。幸福得几乎要叹息,真恨不能将这幸福告诉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来嫉妒他们”[5]185。另一方面,当时封闭紧张的社会现实完全避开人的生理需求,他们无法正常地从社会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只是模糊地感到这是罪恶。他们为这充满欲望的身体而痛苦万分,“不争气的是她的身体。她的身体背离了她的灵魂,如痴如狂地渴望着与他的身体接触,摩擦。即使是虐待至死,也在所不惜”[5]224,他更是如此。他们就在这样的欢愉与痛苦中挣扎度日。直到她不慎怀孕,在母性的召唤下,才得以摆脱这纠缠良久的罪恶与绝望。《小城之恋》中的她和他,不过是女人和男人的集约符号,他们演绎的也不过是最自然的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即使处在文革这样扼杀人欲的时期,这种男女间最自然的关系依然释放着璀璨的生命活力。王安忆以极其细腻的笔调记录了两个略为懵懂的年轻人在社会环境的压迫和扼制下,在莫名的时代氛围的挤压和浸淫中,面对身体欲望时的冲动、欢愉、无助、挣扎的种种微妙幽深、刻骨铭心的感受感觉。作者用艺术的形式还原人类最自然的本质,揭开了长久的文明伪饰,将洋溢着生命气息的自然本真呈现于人们面前。
(二)铁凝:卡吉娅和阿蕾特的选择困惑
与王安忆一样,铁凝也以她独特的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巧妙地从时代的网罗中逃逸出来。她摈弃了从认识论角度对人性世界进行政治、社会、道德的评判,直接进入人的本体论范畴,通过对人的生命状态、身体体验及灵肉思考的客观描述,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人们生存的原初模样和生命本态。与王安忆“三恋”同期发表的《麦秸垛》(1986)、《棉花垛》(1989)及《玫瑰门》(1988)是铁凝1980年代基于身体而创作的重要作品。在《麦秸垛》里,铁凝设置了一个类似卡吉娅和阿蕾特选择的故事。
卡吉娅和阿蕾特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神话中,赫拉克勒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卡吉娅和阿蕾特两位女性,她们都许诺要给他带来幸福。不同的是,卡吉娅以其丰盈而柔软的身体许诺将提供感官的适意、满足和享受。而阿蕾特则以她的质朴和娴静期许了辛劳、沉重但却美好的幸福。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以道德戒律的形式告诫人们,“应该和阿蕾特在一起”(苏格拉底语)。尤其在中国的伦理中,卡吉娅这类人物更是千夫所指、万人所骂的对象,处于被绝对否定的位置。在启蒙后的现代气候中,铁凝编织了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相似的故事:知青陆野明正面临着卡吉娅和阿蕾特的选择。传统伦理意识的积淀使他理性地认可作风正派,品行端正,言行举止符合道德要求和社会规范,代表圣洁精神的杨青,但他的本能、身体需求却让他无法拒绝泼辣奔放,以身相许的沈小凤。“陆野明暗自诅咒沈小凤这个魔鬼,却又明白只有她才能缩短他和那诱惑的距离。怀了莫可名状的希望,他愈加强烈地企盼超越那距离,到那边去体验一切”[6]。他终于无可挽回地和沈小凤倒在麦秸垛中。尽管杨青最终得到了陆野明,得到的却是一个精神上趋于阳痿的男人,与“卡吉娅”狂欢的自责和服罪使他丧失了男人的伟力。隔着身体的距离,欲望冷却的陆野明与杨青处于冷漠中。刘小枫曾这样分析道:“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服从灵魂的法则”[7]。铁凝于此暗示:卡吉娅所代表的感官适意、满足和享受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一味地用文明理性加以压制并不能造就健全的人格。享乐生存原则的正当性正是基于身体的自然感觉,就个体的身体感觉而言,身体的享乐本身只是属己的自由,无所谓罪恶美德。同时,陆野明的选择也标示着阿蕾特对卡吉娅的绝对统治时期已开始瓦解。充满本能欢娱的卡吉娅不再处在被永远放逐的路上,她开始踏上返回自己的合法位置的途中。
(三)刘恒:自然本能的冷酷审视
相对于女作家们对身体欲望洋溢着欢快而诗意的描叙,而在同样对身体欲望富于探索精神的男作家刘恒发表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本中,身体却成为异己的无奈存在,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伏羲伏羲》(1986)和《狗日的粮食》(1988)的出现开始确立刘恒在当代文坛的位置。在这两部作品中,人物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刘恒痴迷于给人物设置生存困境,将身体的生命本能和承载生命本能的日常生活推向永恒的无法和解之矛盾境遇。
《狗日的粮食》讲述的是一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有关粮食的故事。洪水峪的农民杨天宽用200斤谷子买回了媳妇曹杏花。长了一个硕大瘿袋的媳妇因为“丑狠了”[8],以致人们觉得她不配拥有这样美丽的名字,而干脆以瘿袋代其名。但是,对天宽来说,“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得地里也做得,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8]321。在匮乏的限制中,满足便已足够。在冷酷的生存透视下,刘恒冷静而坦率地认可了人们基本的身体本能需求。与之相伴随,更为严峻的则是身体维持自身生存的对“食”的需求。作为类的存在,瘿袋集中了众生相中一般状态最强的生存本能欲望:为了粮食,她刁蛮泼辣,不顾脸面,毫无羞耻,无所谓尊严美丑。她可以顺手牵羊,可以明目张胆地将邻居及他人之物据为己有,总之无所不用极,地里长什么,她就往家拿什么,似乎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这样一个挣粮好手却恰恰死于粮食,因意外丢失了粮本而自杀身亡。动机与结果的严重背离凸现了身体的欠然,即个体欲望。刘恒曾指出,人的悲哀就在于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欲求的生命个体。身体是无法回避的物质性存在,保全自身是它最基本、无条件服从的欲求。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中,对身体的接受意味着将身体等同于粮食:一方面必须疯狂地觅食以满足身体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因此而严重地异化了人的生命。对于瘿袋而言,粮食严重损害了身体的伦理和尊严,使她的生命被迫退守到生物性本能,物化了她本应得到丰富发展的生命,最后无情地夺去了她业已严重蜕化的生命。
《伏羲伏羲》记叙的是一个飞蛾扑火式的乱伦故事。与传统写法相异的是,作者没有抱着一种谴责态度来叙事,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和悲壮肯定了侄子与婶婶的偷情。年轻的菊豆作为生育工具被堪作父亲的杨金山买回,不知自己已丧失生育能力的杨金山却迁怒于菊豆肚子不争气,从而百般虐待她。正是在这种非人的状态下,不堪蹂躏的菊豆在与杨金山年轻的侄子杨天青的共同劳动中,迸发出爱情的绚丽火花。与天青的融合,菊豆摆脱了作为生育机器的屈辱与被动,真正享受到了鱼水之乐,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快乐。同时,他们又陷入了身体正当欲求与传统人伦矛盾纠结的深渊中。自然欲求遇到禁忌的压迫,合情合理的身体冲动,被无边无际的罪恶感覆盖。儿子天白的不理解,他人异样的眼光使他们一辈子只能在黑暗中寻找快乐,背负着沉沉的罪恶感走完惨烈而沉重的一生。爱的结果不是幸福,而是罪恶感的升腾。杨天青最终以自杀的方式彻底中断身体这架永不停歇的欲望机器,寻求人生的彻底解放,而菊豆在漫长的生命余年孤独地回味着曾经的欢乐和痛苦。
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身体的基本生理需求无法满足时,附加于身体的一切社会规范、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等便纷纷滑落,本能开始自我救赎,尽管是以黑暗为帷幕。身体在这种境遇中“洗尽铅华”,显现出它纯粹的本来面目。刘恒正是通过匮乏的生存困境的设置,揭示了这样一个生活道理:人后天被赋予的社会伦理和时代规范,包括对伟大与尊严的认同都不能忽视身体的生物性本能,人类的自我超越永远受制于身体的本能需求。
在文学自身发展需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和消费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下,1980年代,以王安忆、铁凝、刘恒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将文学关注的目光投向身体的自然欲求,接受并肯定这种基于本能的天然权力。在他们的努力下,身体得以回归文学。通过身体写作,新时期作家重新诠释了对社会、文化及个体的思考,同时作家们也借助身体自身的欲望、个体性、感性、真实性等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和张扬。以“性体验日记”而出名的木子美等人的出现,预示着身体写作在反抗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欲望、性、情绪、快感享受充斥于世纪末的创作。身体解放逐渐接替了思想解放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似乎身体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带来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欲望写作及作为观赏交换的女性写作,身体在消费文化的泥潭中,再次成为异己的他者。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里,我们既要警惕不要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沉沦于肉体的狂欢,也不能蔑视身体的肉身性,浮于灵魂的虚无,而是应该在文学的场地里将二者自然地衔接、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鲜活、真实、深邃和强健的文学肌体。
[1]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65.
[2]南帆.身体的叙事[J].天涯,2000(6).
[3]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M]//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出版社.2003:20 -21.
[4]周作人.人的文学[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集.赵家壁.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4.
[5]王安忆.荒山之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6]铁凝.麦秸垛[M].青草垛:铁凝文集1.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6-37.
[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83.
[8]刘恒.狗日的粮食[M]//刘恒作品精选.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320 -321.
(责任编校:文君)
Returning of the Body——Explanation on 1980s’Creation of Wang Anyi,Tie Ning and Liu Heng
HU Yan
(Chinese Department,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417001,China)
Since new period,the body has embodied completely in literature.In 1980s’,under the stimulation and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such as the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and consumption culture,with the need to develop literature itself,some writers ,represented by Wang Anyi,Tie Ning and Liu Heng,began to cast their eyes on the body’s natural desire,accepted and confirmed this instinctive right.With their endeavors,the body was back into literature.
body;returning;desire;instinct
I206.5
A
1673-0712(2010)06-0049-04
2010-10-26.
胡艳(1980—— ),女,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