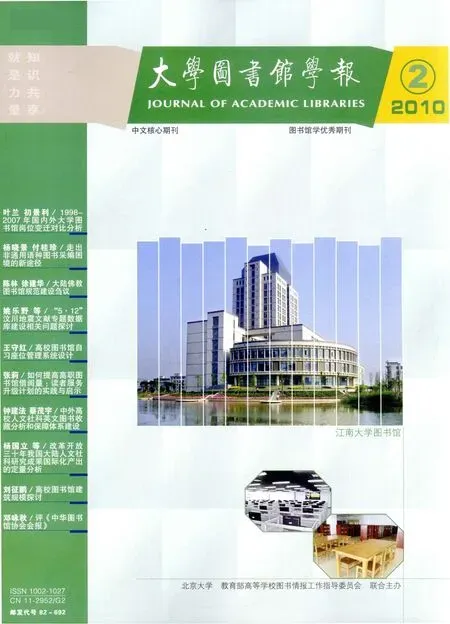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邓咏秋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①《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发行时间长(1925-1948),卷期多(共发行21卷102期),目前海内外大图书馆也很少能有完整无缺的收藏。2009年6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该刊全部按原样影印出版,精装为5大册,另附一册新编的索引(赵俊玲等编,单独列为一册,即第6册),本文的写作要感谢这部索引的指引和帮助。(以下简称《会报》)与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分不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25年4月25日成立于上海,并于6月2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在抗战前,总办事处一直设在北京。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传达消息的刊物,《会报》于当年6月30日在北京创刊发行。该刊为双月刊,于1948年5月出版第 21卷第 3、4合期后停刊。从1925年至 1948年,仅有一年停刊(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共发行了21卷 102期(第2期和第3期合并刊行,只算作一期)。
《会报》与《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并称为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另两种刊物的价值,相对比较忽视《会报》的价值。但笔者认为,《会报》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地位独特,不可替代。本文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会报》的价值。
1 有助于增强图书馆界的凝聚力,促进事业发展
从学术高度来说,《会报》不及《图书馆学季刊》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但是在揭示全国图书馆界的状况、增强本行业的凝聚力方面,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历史不长。要想取得较快的发展,并且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和重视,光靠一个馆或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图书馆界和教育界的一些人士认识到群策群力的必要性,同时受到美国图书馆界友人的推动,于是组织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个全国性组织,以便在图书馆界内部加强合作与交流,对外以图书馆界集体形象去争取本行业的权益。《会报》全面报道、广泛刊载全国各地图书馆界的各种信息,实际上办成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总通讯社。“本报为本会传达消息之刊物,极愿以此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讯机关。凡图书馆或各地图书馆协会之任何消息,皆愿代为露布”[1]。《会报》设有“图书馆界”栏目,报道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各种消息,如与图书馆有关的法令颁布、某某图书馆工作近况、某图书馆最近获得一批特色馆藏、图书馆学暑期学校招生、图书馆界的新发明、湖北黄安七里坪设农民图书馆、香港轮渡上设图书室等,都有介绍。《会报》对与图书馆有关的各种信息皆尽量刊载。通过这个独特的平台,图书馆界人士的行业认同感和自信心得到了强化。
在促进事业发展方面,《会报》曾发表《图书馆学书目举要(初学书目)》、《图书馆学中西书目举要》等,这些对于促进图书馆员继续学习是很有用的。还刊载过《图书馆员的生活》(金敏甫)、《图书馆员立身准则》(于震寰译)、《图书馆员应有之真精神》(喻友信)、《办民众图书馆者该怎样鼓励人民乐于来馆阅览?》(朱金青)、《办理农村图书馆应注意的几点》(杨海樵)、《创设和办理图书馆应注意之点》(方金镛)、《弹性组织之县市图书馆》、《对于图书馆建筑应注意之数点》等,这些文章涉及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或者饱含专业热情和创意,或者介绍成功经验,对图书馆界很有指导意义,有助于促进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
2 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行业领导作用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一个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民间团体,它不具有政府组织的强制性权力。作为行业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要想发挥引领全国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作用,必须通过开展多方面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服务,以获得行业内的认可和尊重。比如,协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个人会员和机构会员上缴的会费,关于这些会费的使用情况,《会报》上有详细的记载。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可以让会员了解协会的财务情况,并加以监督,使大家信任协会。另外,协会的各种活动、周年总结等,都在《会报》上有详细刊载,中华图书馆协会还开展过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如调查全国图书馆等,这些也反映在《会报》上。可以说,因为有了《会报》,就有了集中宣传中华图书馆协会所做工作的阵地,协会的领导能力和凝聚力得到了增强。
协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外争取本行业的权益。据《会报》所载,中华图书馆协会曾致电当局,反对印刷品邮资加价;向立法院力争,强调图书馆这种社会教育机关的重要性,要求私立图书馆及民教馆之奖励或补助应列入宪法;还曾力争平津书籍免税等。通过《会报》的出版,协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得以传播到全国图书馆界,使他们面对政府和其他行业时,不再只是孤独的一个馆,而是有一个全国性行业协会代表他们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样一来,也让图书馆界更加信服协会的领导。
3 推动学科建设,提高图书馆学在学科之林的地位
《会报》与《图书馆学季刊》都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办的刊物,但它们在刊载内容上有区别。《图书馆学季刊》主要刊载图书馆学专业的长篇论文。而《会报》上很少刊登长篇学术论文,它虽设有“论著”栏目,但主要刊登的是对图书馆实践工作有指导性的文章,或某图书馆的概况。可是,我们仍然强调《会报》具有推动学科建设的贡献,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会报》虽不直接刊载长篇学术论文,但它经常通过小消息和“新书介绍”栏目,简要而广泛地报道图书馆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如图书馆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创新与发明,常在《会报》上有介绍。(二)中华图书馆协会下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经常在《会报》上介绍,这对于推动本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的。(三)《会报》重视刊登对图书馆实践工作有指导性的文章,还经常发表有关文献学研究、索引编制的成果,如《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袁同礼)、《山西藏书考》、《册府元龟索引》(吕绍虞、于震寰编)、《川大旧藏书版修印纪》(孙心磐)、《东北事件之言论索引》(钱存训)、《进行中之各种索引》等。这表明,当时的图书馆界一方面继承传统目录学的思路,在文献整理方面继续努力;另一方面则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注重编制索引、提高检索效率的思路,在参考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实事。通过报道这些研究成果,《会报》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专业研究氛围,有助于鼓励图书馆界开展类似工作,从而推动学科建设,并提高图书馆学在学科之林的地位。
4 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图书馆史资料
《会报》是民国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一种,跨越24年(1925—1948),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图书馆史料。在内容上,《会报》很重视报道图书馆界的动态,广泛刊载国内外图书馆界的消息、协会的各种活动、会员消息、新书介绍等,这些资料本身研究性不强,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宝贵的基本资料,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开展很多研究。
《会报》不仅报道大图书馆的动态,也相当重视对小图书馆,如县图书馆、乡村图书馆和特色图书馆的报道。现在我们研究图书馆史,诸如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大馆的资料并不难找(因为大馆常编有馆刊、本馆概况等文献),但是如果想从全局和宏观上把握当时图书馆界的情况,如全国到底有多少图书馆,各图书馆的经费和读者情况,全国图书馆教育开展情况,抗战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等等,我们就必须求助于《会报》。《会报》对当时各图书馆的经费、章程、藏书、读者人数等都有相当的报道。这些调查数据对于我们研究图书馆史是很珍贵的。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条件艰难、很多期刊停刊的情况下,《会报》编辑部仍辗转昆明、成都、重庆三地,坚持出版,报道全国图书馆界消息,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相当可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离开《会报》,就写不了抗战时期的图书馆史。
而且,并不是每个行业都如此幸运。比如在研究出版史时,由于当时出版业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行业组织和这样一份内容丰富的“会报”,因此我们很难获得当时全国出版社的各种宏观数据,因此在研究民国出版史时,现有的研究不得不过分集中于商务印书馆等少数大出版社。
5 会员交流的平台
《会报》有一个重要的栏目是“会员消息”,主要报道协会个人会员的消息,如工作变动、地址变更、新著出版、婚丧嫁娶等。被报道的会员达600多人,有些比较活跃的会员多次被报道。从当时来说,《会报》起到了会员之间互相联络的作用。从对后世的作用来说,这些会员消息也是我们研究当时图书馆学人生平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此,我想到,当前图书馆界也有不少新闻消息(或称“八卦”),但往往分散在小范围,处于一种无序流传的状态。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界已经很重视这些业内同人的新闻消息,通过《会报》来网聚行业内的新闻,加以系统的整理和刊布,这种做法或许也能给我们今天的工作带来一些启示。图书馆界是否仍然需要类似的平台,来集中发布一些本行业的娱乐和非娱乐新闻?我想,类似的行业平台,对于聚集行业人气、提高行业归属感和从业快乐感,会有一定帮助。
6 有助于国际交流,相互了解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代表中国图书馆界,派员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年会,与国外图书馆协会平等往来,在促进交流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这些在《会报》上都有体现。《会报》为中国图书馆界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使他们能从全世界范围汲取养分,从国外同行那里取其所长,从而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如国际图书馆大会代表沈祖荣撰写的《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2],使许多无缘出国参会的国内同行能够分享他的所见所得。又如,中华图书馆协会推举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为名誉会员。1925年 9月,74岁的杜威致信给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登了这封信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稿[3]。在信中,杜威回忆了自己于49年前创立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情形。他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会员仅30人,经费全无,杜威服务其中,不仅没有报酬,而且经常要自己负担费用。而49年后,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员将近一万,并且通过其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还获得了包括卡内基在内的基金会的资助。杜威以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打气,鼓励中国同行克服草创时期的困难,以图将来协会和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可以说,类似的国际交流,对于鼓舞中国同行的信心是很有益的。《会报》还积极报道国外优秀的图书馆界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如《日本图书馆学杂志目录》、《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约》(美国图书馆协会职业道德规约委员会拟订)、《关于索引的方法》(黎劭西译)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图书馆和文化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会报》来看,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展了一些工作,如致函各国图书馆协会并争取到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活动促进了当时国际图书馆界的互相了解。
简要地说,《会报》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它在当时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是它对后世的意义和价值。就当时来说,《会报》的出版,给全国图书馆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增强了行业的凝聚力,对于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有促进作用。从后世来说,《会报》留给我们一笔丰厚的历史数据,不仅对于研究图书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专门研究图书馆史,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丰富的数据中找到学术研究的兴奋点,获得事业发展的灵感。
1 本报启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3):2
2 沈祖荣.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5(3):3-29
3 杜威博士来函(致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函,中英文).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3):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