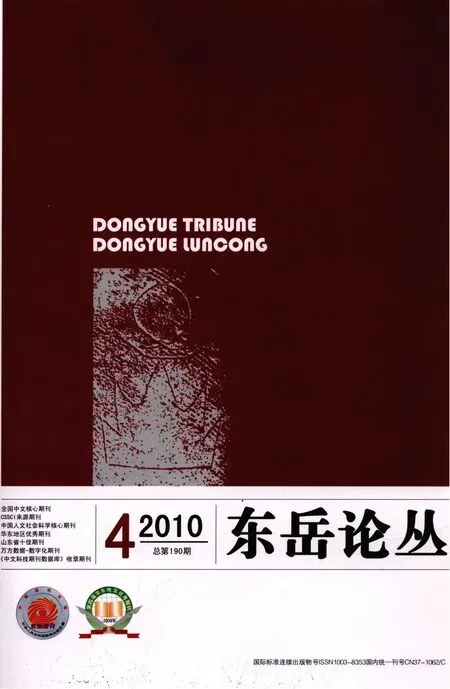论姜贵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坚守
王云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论姜贵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坚守
王云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姜贵的小说并非纯粹的“反共文学”。他的创作,一方面通过古代妇女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旨,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对西方文化潮流秉承了审慎的态度。对传统伦理道德层面的扬弃与坚守,是姜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做出的可贵尝试。
姜贵;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现存文学史中,姜贵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战斗文学”的得力健将,他的长篇小说姐妹篇《旋风》、《重阳》被看作“反共文学”的代表作。由是,以往论者多从反共的政治角度去评判姜贵的文学成就。时移世往,当评论者们意识到政治标杆乃是衡量文学最愚蠢的尺度时,当姜贵笔下的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时,姜贵这个名字是否会随着政治历史的烟尘滚滚而去?海外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对姜贵文学创作的评价甚为贴切:“他正视现实的丑恶面和悲惨面,兼顾‘讽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温情主义’的俗套,可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的集大成者。”①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怪现状,自身亦如浮萍一般四处漂泊,姜贵不能不思索这一切一切的根源。他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流云般飞逝的时代思潮审慎反思,幽默讽刺地激浊扬清,由此显示出他批判的锐利与坚守的执着。
姜贵本名王林渡,一名王意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相州镇。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稍长又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则纷纷从军保家卫国,其所置身之冲突复杂的文化语境、颠沛流离的生活阅历,无不为激发其创作准备了丰沛的源头活水,尽管作者本人也许更希望放弃这种“文章憎命达”式的生命际遇。
姜贵小说的时代背景,绝大部分以其大陆的生活阅历为蓝本,集中于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他曾经说过:“我所谓自己的东西,既不离经,也不叛道,更不违反国策,不过是我所熟悉的,我所能深入体会的,我认为值得写,适合自己写,写着顺手的一些东西而已”②。正是在这些非常熟悉的、融合个体感性体验的过往生活中,姜贵开始经营自己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主题。
姜贵反思的焦点重在传统文化中摧残个体生命的封建礼教,这主要体现在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一为妇女形象。古老的传统中国,受礼教压制最深者莫过于女性,妇女总体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姜贵的故乡相州是山东诸城的一个大镇,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违集》中,姜贵回忆道:
“相州称镇,有个土围子,辛亥时候已经开始倒塌,镇在由北而南去诸城的通衢之上,从北门到南门号称五里,实际不过三里,这条南北大街相当繁荣,虽然一下雨就变成一条泥潭,但‘奉旨’的‘贞节牌坊’却不少,隔不多远就有一座,石料质地细密,规模高大,雕刻精致,初次到相州的乡下人,看牌坊也算一景儿。”③
寡妇用一生的压抑与孤寂换来的贞节牌坊居然沿街林立,甚至成为一大景观,姜贵故乡民风之保守闭塞,礼教观念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之深可见一斑。也许正是为故乡的“名胜”贞节牌坊所震撼,姜贵才对封建礼教“吃人”于无形的本质格外关注。
《曲巷幽幽》中姜贵所描写的小镇,极有可能以其故乡为原型。小镇上“正经人家”的妇女,平日里不能踏出院门半步,不能在陌生男人面前抛头露面,需要买日常用品时则自有专业的卖婆上门。小说中息秀才家的大儿媳妇毓金枝,丈夫早死,她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只是窗子底下巴掌大的一块玻璃。玻璃虽小,却为她提供了全世界。她从小接受传统礼教的熏染,跟自己的小姑说:“做女人省了操心自己的事,不像男人辛苦。出嫁以前,听从父母;出嫁以后,听从丈夫公婆;老了,听从儿子。一辈子都图个现成。这样的福气,男人没有。”④可是她却未有子嗣,她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真熬不过了唯有听从东跨院里那棵大枣树(上吊的意思)。活着没有机会体味生之欢乐,死亡于她反倒是一种解脱,但是她却没有怨尤,槁木死灰般忍受一切,谁让自己命不好呢?《人面·榴花·朝阳》中的媳妇王惜娇命运本来更为悲惨:为冲喜而匆匆忙忙嫁与病危的丈夫,过门当天就从新娘子变为寡妇,成亲几年只出过家门三次,还是为祭奠丈夫。但她也无怨无悔地坚信这是前生的罪孽、今生的宿命。这一类善良懦弱的女性死守着传统社会腐朽的伦理道德,受尽寂寞与凄凉,却还梦想着有一天能“苦尽甘来”,得一块贞节牌坊以“流芳百世”。尽管最后碍于现代读者审美心理的惯性,姜贵为她们安排了命运的转机,但如果不是新思潮影响下社会风气的开放,她们也许只能无可奈何地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了。姜贵以冷峻细致的笔触描摹她们柔弱与屈从的生命轨迹,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封建礼教熏陶下的又一类受害者。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毕其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古代自先秦时期即出现了“士”,其社会功能与西方近现代所界定的知识分子非常接近:“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 (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⑤然而,所谓的士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下,数千年来能真正以身作则或发扬光大者寥寥无几。尤其是明清以来,极权政治几乎完全窒息了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活力,使之成为比普通百姓更服帖的顺民。鲁迅先生曾塑造出迂腐可怜的孔乙己形象,激切悲愤地批判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的摧残。姜贵的笔触却更为含蓄蕴藉,《曲巷幽幽》中他用讽刺手法勾勒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假秀才“息三世”:
“这个秀才,他也不真是秀才,他是秀才的孙子。因为物以稀为贵,在人们的口头上,他世袭了。虽是口头世袭,他本人却弄假成真,仿佛他就是真的。五冬六夏,长袍马褂;走起路来,踱着方步;两撇八字胡,道貌岸然,其实他才四十多岁,字也并不识得多少。”⑥
息秀才非常讲究礼教观念,不让家中女眷出门半步,动辄要“乱棍打死”;每天夜爬大枣树窥探隔壁检家(实为娼妓)的动静,冠冕堂皇曰“鉴察人间罪恶”,其实是为满足自己的淫欲;不事生产却偏要装清高、强撑门面……直至房产被人讹占、女儿被人羞辱仍不知觉醒。虽然主人公并非货真价实的秀才,但由此更能见出封建礼教侵入民众心灵之深。对于旧礼教的荒谬可笑、扭曲人性之处,姜贵没有激切直白、声泪俱下地揭露与批判,而是完全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形象种种心口不一、言行举止的错位来自暴其短,莞尔之余令人深思。《曲巷幽幽》依稀可见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影子,虽然,对于传统文化腐朽陈旧层面的批判乃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但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则明显是承袭了晚清讽刺传统的精髓。
姜贵的创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继承了五四先驱者反封建礼教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对所谓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态度又有所保留。经过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姜贵对于一个典范失序的社会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他以略带夸张的讽刺之笔,细细烘托那一场道德失序的恶的嘉年华场面,为的是达到他“纪恶为戒”的写作主旨。《旋风》描写大家族方家生活腐朽糜烂:方家大少爷浪荡无行,三妻四妾尚不满足,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娶一个品格低劣的妓女;方老太太则是抽鸦片、养小生,更以折磨老姨太太西门氏为生活乐趣,因为她在老爷生前让自己倍受冷落。小说其他的主要角色不是军阀,就是土匪,或者是妓女等等,人性中的色欲、淫欲、贪欲、报复欲……无限膨胀,汇集为一个道德秩序极度混乱的人间地狱。《重阳》更是借柳少樵这个集人性恶之大成的角色,反思种种激进潮流中隐藏的负面作用:柳少樵不喜欢父亲为他挑选的品貌端淑的妻子,却在洞房之夜将其强暴后抛弃,美其名曰反抗包办婚姻;他又打着破除贞操观念的名义奸污了下级洪桐叶的妹妹洪金玲,甚至连洪的妈妈也不放过;对于洪桐叶更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他为种种反伦常、反伦理道德的变态行为加上一顶顶“反叛传统”的冠冕堂皇的帽子,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姜贵用细致的笔触描摹着这个欲望放纵的世界,却没有丝毫个性解放后的欢跃,其冷嘲热讽的行文倒是透露出作者对伦理失范的社会混乱状况的批判与忧思。
由此,对于时人盲目迷信的西方思潮,姜贵亦同样秉持了一种谨慎审视的反思态度。虽然,五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思想潮流早已是尘埃落定,但他坚信这种“后知后觉”文化反思的必要性:
“我的目的只在重现那一时代那一种特异的气氛,给人重新感受,重新体会,用以‘纪恶为戒’而已。或有人以为这个想法有近冬烘,而且为时已晚,我却并不那样悲观。胡适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话。”⑦
长篇小说《旋风》即是出于这种深思远虑而产生的杰作。小说塑造了一个读书人“方祥千”的形象。方祥千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为了改革社会而学习、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支持革命。然而,他所有行为的动力与其说来自于那些还不甚了解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如说根源于他潜意识中儒家文化的乌托邦理想。试看他如何跟自己的侄子解释共产主义社会:
“俄国经过十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种田,大家吃饭,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国家设有育儿院,孩子养下来,往育儿院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点也不牵累你!病了,国家设有医院,免费替你医治。老了,国家有养老院给你养老送终。总之,人家俄国是成功了。”……“这就是孔夫子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⑧
方祥千的革命理想并不是脚踏实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问题,他积极借鉴外来学说却又不求甚解,只管按照自身的文化心理和主观意愿片面地阐释外来文化思潮,用献身理想的激情掩盖严峻的现实问题。虽然,受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姜贵将方祥千革命理想的失败归结为“共产党的兴风作浪”,但是,其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姜贵并未完全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他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意识到:方祥千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境况深恶痛疾,试图完全抛弃传统的一切,移植西方文化来挽救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殊不知,粗暴地拒绝传统、否定传统并不能回避传统的阴影,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主观选择仍然潜在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盲目迷信于外来文化思潮的魔力无济于事,对其吸收借鉴最终仍需建立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根基上,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文化传统的变迁原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狂飙突进式的思潮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摧枯拉朽的目的,但真正将外来的文明吸收化用、以便能有所裨益于本国文化传统的更新则仍需要长期的理性与耐性:理性地认识本土传统文化根源上的利弊,同时系统了解外来文明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耐心地做一番文化嫁接工程。
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姜贵能够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但他又无法完全认同极端激进的社会失范状态。姜贵幼时读的是旧制中小学,每天下午三时放学后,没有功课需要带回家去赶做,善意的老师即给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外之课,选读《昭明文选》、《古文观止》、《论语》、《古诗源》、《全唐诗》等等⑨。山东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再经过着意的培养熏陶,姜贵思想观念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根深蒂固。他一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一面又希冀发掘其有价值的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姜贵发掘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伦理道德层面的操守。
他的小说坚守着传统儒家文化“忠”、“孝”的伦理价值观。儒家文化乃是由宗法—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伦理型文化系统,家族伦理中的“孝”正是其最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下,“忠”其实是“孝”的伦理价值观的外延。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下,传统伦理观念日益僵硬化、教条化,忠只能是愚昧地顺从君主意志,而孝也逐渐演变为窒息个体个性发展的镣铐,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忠孝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但是,姜贵小说中维护的忠孝观念显然有所不同。
首先,姜贵把忠的观念改造成了一种可贵的爱国情感。《旋风》本是人性之恶集中展示的舞台,但作者仍然禁不住塑造了一个方八姑的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她宁死不屈;当周遭的人或为虎作伥、或忍气吞声与日本人打成一片时,她说:“我情愿牺牲我自己,为天地间留一线正气!”[10]“我要叫日本人知道:我们这里不只有土匪、妓女、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也还有百折不挠的硬汉子!”[11]姜贵正是试图以方八姑的形象作为民族正气的化身,虽然她最终被黑暗的恶势力所吞没,但她所代表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则长留天地间激励后来者;《重阳》中的朱广济、钱本四也是这一类坚贞不屈、不向汹涌恶势力低头的民族英雄。总体来看,他们皆能抛弃愚忠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而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出发点,其忠贞不屈已成为一种可贵的爱国情感,这无疑是姜贵为忠的观念注入的新鲜血液,也是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下传统文化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征。
其次,姜贵以一种现代意识改造了传统孝道而又不违背其美德的本质。《曲巷幽幽》中,幽幽曲巷住着两户人家。息家的息秀才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箩筐,却硬要假装斯文、承袭祖父遗风做秀才,结果日子越过越寒酸;非但如此,他居然还死撑面子讲究秀才的礼数,看不起靠劳动吃饭的毓家山的亲家,认为“他这种人家,逼到最后,也只可穷,而万不可贱。一论到买卖,不拘是工是商,都归是贱,那就对不起祖先了[12]。这样的不顾现实环境变化、盲目地遵循祖制,也无怪乎他成为时人眼中穷酸的典型!他的大儿子聪明伶俐,却被父亲用孝道逼着在家做酸腐秀才,结果越来越文弱、竟至丧命;他的二儿子息砚孙在卖婆宋三妹的指点下勇敢地走出家门,到遥远的城市去自己创业,反倒能衣锦荣归,成为父母老来的依靠。何为真正的孝道?姜贵通过息秀才一家祖孙三辈的生活轨迹进行了形象的说明:所谓的孝道仍然应当从内心深处孝敬父母,但绝非因循保守地盲目听从,而是尽量发挥个体才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有立己才能立家进而立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的“检家”。检家实为暗娼窝点,极喜追求时代潮流,他们积极地让自己的孩子走出去闯天下,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女儿做娼妓,最终被人暗杀在火车上;两个儿子则被培养成日本人的走狗。他们拒绝与自己的父母相认,完全为日本人尽忠尽孝去了。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检家家风糜烂、缺乏传统伦理道德的浸润,才使其在动荡社会中迷失了方向。两相对比中,姜贵的创作主旨呼之欲出: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乃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根基所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以适应社会环境变迁固然可以使国家民族摆脱危亡的境地,但如果没有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做根基,所谓的现代化也会因迷失方向而转入另一种歧途。
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文坛上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或被按照政治标准改造,或被作为封建遗毒彻底摒弃。台湾文坛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惨败亦使蒋介石痛定思痛,反省共产党以“笔权”打垮了国民党“军队和政权”的历史教训,于是亦钩织起严密的文学监控网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倡导“反共文艺”、“战斗文学”。无论哪种意识形态之下,中国传统文化都被挤压到了潜隐或边缘状态。此时的姜贵,能够偏离台湾文坛的主流审美倾向,秉承五四文学传统开拓的现代视野、谨慎地回头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以此为本位激浊扬清兼收并蓄地进行文学创作,不仅在边缘地域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从长远来看,更对其现代转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夏志清:《姜贵的 〈重阳 〉代序——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重阳》,台北:皇冠出版社,1973年版。第 9页。
②姜贵:《姜贵自选集·后记》,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 376页。
③姜贵:《相州山海关》,《无违集》,台北:幼狮文艺社,1974年版,第 57页。
④⑥ [12]姜贵:《曲巷幽幽》,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 34页,第 8页,第 19页。
⑤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2页。
⑦姜贵:《重阳·自序》,台北:皇冠出版社,1973年版,第 27页。
⑧ [10] [11]姜贵:《旋风》,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 128—129页,第 319页,第 323页。
⑨柳映隄:《生活在风雨中的人——姜贵先生访问记》,姜贵《无违集》,第 314页。
王云芳,女,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I206.7
A
1003-8353(2010)04-0110-04
[责任编辑:曹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