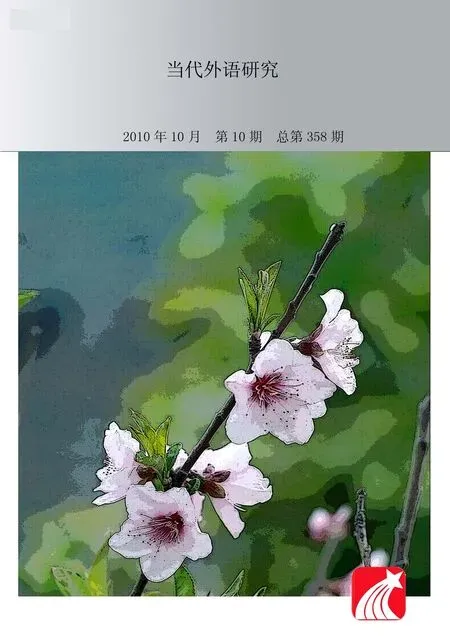马丁的语篇分析观
陈瑜敏 黄国文
(中山大学,广州,520275)
1. “悉尼学派”和语篇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立者M.A.K. Halliday近年来多次强调,他的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的之一是为解决(潜在的)语言消费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理论(Halliday 2006;黄国文等2006)。过去几十年来,该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这是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
自1975年Halliday建立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以来,悉尼及周边地区一直是国际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活跃的地区之一。马丁(James R. Martin)是悉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丁及其同事善于运用语篇分析中总结的语言学规律来指导教学实践,并注重在语篇分析的实践中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提出了基于语篇体裁的读写教学法(genre-based literacy pedagogy),创立了评价分析框架(APPRAISAL analysis framework,也有人称之为“评价理论”),等等。近年来,悉尼学派还与社会学和教育学者密切合作,开展了关于教育语篇特征、知识结构的研究(见Christie & Martin 2007;Freebodyetal. 2008)。以马丁为代表的悉尼学派始终将语篇分析研究与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这与Halliday“适用语言学”的思想一脉相承。本文通过评介马丁近30年来在语篇分析领域的主要论文,对悉尼学派的语篇分析思想作一梳理。这些论文均被收录在近期出版的《马丁文集》(CollectedWorksofJamesR.Martin)之《语篇分析》卷中。
2. 语篇分析的论著
《语篇分析》卷收录了马丁与其同事从1985年到2008年20多年间撰写的关于语篇分析的11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语篇分析中的语篇体裁研究、读写教学法、评价分析框架、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等多个方面。下面的介绍将围绕这几方面展开,同时提供一些延伸阅读,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3. 评介
《语篇分析》卷中的各章节按照文章发表年份排序,但本文的介绍并不完全按照章节的次序,而选择把主题相近的文章放在一起讨论,以便更好地梳理和把握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这些主题涉及语篇体裁研究、人际意义研究、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三部分。
3.1 语篇体裁研究
该卷中的“关于阐释文的分析”和“抽象化之波:阐释文的组篇”两篇文章讨论的主题都是阐释文(exposition)这一语篇体裁,并且都与写作教学密切相关,但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文讨论了阐释文写作与叙述文写作的差别,从词汇语法、语篇、语域和语篇体裁等各个层面考察了阐释文的语言学特征,强调要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和教师的“语篇体裁意识”(genre consciousness)。文章指出,阐释文是从“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来描述事物/事件,而叙述文是记叙特定个体经历的具体事件,与叙述文相比,阐释文较为客观、笼统、抽象,通常阐述的是某一类人或事物不受时空限制的较稳定特征。在语言特征方面,阐释文一般较少运用明确表达作者个人情感态度的词汇(如:The excursion isfun.)或心理过程(如:Ilike...),而采用对情感态度取向进行非个性化的客观处理的做法(如:Itisgoodto have...),并且在表达作者个人态度时,常常伴随着支持这种态度的理由。根据论点性质的不同,阐释文可分为两类:道德阐释(如社论、政治演说和辩论等)和事实阐释(如课堂教学、学术论文和讲座等)。马丁在文章中讨论的主要是事实阐释,他从及物系统、主位、衔接、语域、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考察了事实阐释的语言学特征,初步提出了对阐释文的分类(解释型、解读型、评价型、辩论型),并对比了这几类阐释文在纲要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方面的异同。文章提出,学生的语言学知识水平、教师的态度以及学校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等因素都会对阐释文写作学习产生影响,语言学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向教育工作者提供语法描述和语篇分析,引导教育者更好地了解语言、从事教学。
“抽象化之波:阐释文的组篇”一文的关注点包括阐释文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语法隐喻。通过对一篇学生习作的多个修改版本的分析,作者讨论了主位在组织语篇中的作用,指出名物化等语法隐喻手段在进行小结和充当评价性小句的主位成分、预测语篇发展中的作用,表明不同程度语法隐喻的使用有利于构建语篇中多个层次的抽象化程度。对语法隐喻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Halliday(1985:342-366),Halliday和Martin(1993),Martin(1992),Simon-Vandenbergen等(2003)以及Taverniers(2002)等学者的论著。悉尼学派对语篇体裁的新近研究还表明,阐释文属于历史语篇体裁中辩论型体裁的一种(除了阐释以外,辩论型体裁还包括挑战和讨论),具体可参阅《语篇体裁的关系——文化的映射》一书中的相关论述(Martin & Rose 2008:116-121)。
“疯狂的语言:是方法还是紊乱”从侧面探讨了语篇体裁问题。文章对比了两种“疯狂的语言”的语言学特征:一种是现实生活中脑外伤病人或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说的语言(真正的思维紊乱),另一种是文学作品中作者有目的地使用近似“疯狂”的语言(一种文学手法)。分析表明,从局部的语音和词汇语法的使用来看,精神病患者的语言并不令人觉得异常,但从语篇体裁的角度看,他们产出的整个语篇是破碎的、不连贯的,比如患者在说话时对主位的选择就没有体现语篇体裁的特征。患者的语篇通过词语搭配和语音或语法上的排比来推进,缺乏统领全篇的主题和目的。换言之,现实中癫狂话语的词汇语法不能体现更高一层级的语域、语篇体裁和意识形态,由此导致患者无法跟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往。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疯狂的语言”是不少写作者常用的手法之一,是写作者“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重要手段。马丁进而分析了前景化这一文体学特征,即文学中的某些选择系统地由语域、语篇体裁、意识形态以外的某种因素支配,语境因素并不能穷尽预测语篇的某些特点。文学作品中通过前景化所达到的悬而未决的意味并不会像现实中疯癫的话语那样影响对语篇的整体理解;相反,前景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为写作者的主题服务。Halliday(1982a)从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的分离、“去除自动”(de-automatization)来讨论前景化特征。而马丁则认为,Halliday(1982a)所说的“去除自动”更多的是指语言层面和语境层面的部分分离,虽然文学语言(譬如诗歌)并不完全体现当前的社会语境,但却为特定的文学主题服务。前景化包括相对于语言系统的前景化和相对于特定语篇的前景化,两种前景化都为主题的表达服务。马丁在文章最后指出了构建基于语言学理论、将文学话语和非文学话语区别对待的分析模型的重要性。
“危险,有鲨鱼!——学生写作的评估和评价”一文的主题同样是悉尼学派的语篇体裁理论,这篇文章在首届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The Inaugural Australian Systemic Linguistics Conference,Deakin University,1990)上宣读,反映了马丁、Anne Cranny-Francis、Alison Lee和Robin McCormack等学者关于语篇体裁教学法的学术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20世纪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教育语言学界“语篇体裁与过程”之争(“genre versus process” debate)。过程论者试图将英语中叙述文等写作方式强加于其它学校课程之上,认为阅读和写作是学生发展自我的手段;语篇体裁研究者则认为,叙述型语篇体裁并不能代表学校课程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多种语篇体裁共存的真实情况,他们重视不同社会语境中语言的使用,提出不能低估历史语篇、科学语篇中“事实写作”(factual writing)(Martin 1985/1989)的价值。关于教育语言学界这一激烈争论的介绍可参阅Reid(1987),Threadgold(1988)和Thibault(1989)等。
围绕对语篇体裁教学法的讨论,四位学者对同一篇学生叙述文习作(即“鲨鱼语篇”)分别进行了四种不同角度的解读:(1)机构英语解读,(2)社会符号学解读,(3)语言学解读,和(4)心理分析。各学者对这几种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McCormack的机构英语解读反映了传统读写教学对英语写作的看法,他认为英语写作体现的并不是对概念和程序的掌握,而是道德文化方面的成长,要达到高年级“反思性短文”(reflective essay)的写作要求,学生需要从个体经验中提炼出叙述成分,再将叙述成分转变成写作者的寓意,将情感和理性联系起来。其中“鲨鱼语篇”中的“梦境设计”是儿童文学中常用的写作方法,它将平淡无奇的日常情景与冒险独立等价值观联系起来;同时McCormack也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边缘化社会文化群体的学生处于劣势地位,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与中产阶级儿童一样的社会化过程。Anne Cranny-Francis对“鲨鱼语篇”进行了社会符号学解读,认为该语篇属于常规的“虚构、幻想的语篇体裁”,语篇中一系列的能指(鳍—冲浪板—岩石—鲨鱼—鲨鱼牙齿)推动了叙述的发展,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了一种试图颠覆现有权势关系的破坏性力量;她指出,批判性的教学法有利于学生理解各种语篇体裁的使用和惯例,尤其有利于边缘化的群体掌握话语的权势。马丁运用语言学理论(Halliday 1985;Martin 1992)对“鲨鱼语篇”进行语篇分析,考察的方面包括及物系统、语气、主位结构、评价意义、名物化、指示、词汇衔接、小句复合体和语篇体裁结构等方面,分析揭示了叙事语篇在词汇语法层面和语篇语义层面的语言学特征;他提出,在读写教学中需要一个多角度考察语篇在体裁、语域、词汇语法、音系学等特征的“多模块模型”(a multi-modular model)。最近十几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所涵盖的方面包括语篇体裁分析、语言的技术性与抽象化、评价意义、信息流、多模态话语分析等方面,具体可参阅Freebody等(2008)。Alison Lee对“鲨鱼语篇”作了心理分析,并提出与读写教学相关的三个思考的方面,在此不一一赘述。对悉尼学派语篇体裁教学法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tin(2000/2006,2001)以及Martin和Rose(2007)中的相关介绍。
同样围绕语篇体裁研究的文章还有“对中断的评价:中学叙述文的主题象征”。这篇文章与前面介绍的三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增加了对评价意义的关注,评价分析框架的前期发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阐释。该文在Plum(1988)和Rothery(1990)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人际意义(尤其是情感子系统)在构建叙述文语篇体裁(以轶事为例)中的重要性。文章首先概述了当时对叙述文研究的成果,包括故事语篇体裁(story genres)的系统网络以及复述(recount)、轶事(anecdote)、例证(exemplum)和对个人经历的叙述(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等四类语篇体裁的纲要式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悉尼学派的新近研究表明,故事语篇体裁的系统网络中还包括新闻故事(news story)和观察(observation)两种语篇体裁(Martin & Rose 2008:78)。马丁指出,在理解“语篇体裁”(genre)这一概念时要注意它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符号系统,在分层次的(stratified)语境模型中(Martin 1991,1992,1999),语篇体裁可被视为体现叙述文隐含的价值观等主题意义的表征(token)。文章还考察了语场和语旨等语域要素如何构建语篇体裁、表现主题,同时讨论了叙述的中断(disruption)和对中断的评价(evaluation)这两个参数。文章初步提出了考察情感系统的五个方面(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外在表现还是心理感受、是对特定事物的情绪反应还是笼统持续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强烈程度和情感类型)。马丁此后对情感系统的研究(如《评价的语言——英语中的评价意义》)(Martin & White 2005:46-52)基本遵循了这五个方面,并补充了意图和反应之分等内容。文章指出,情感可被直接嵌入(inscribed)或由概念标记(ideational token)间接激发(evoked,后改为invoked)(Martin & White 2005:67)。语场中断、语旨评价和语篇体裁的阶段性特征三者之间密切相关,语场中断通常伴随着从积极评价到消极评价的转变,这一特征贯穿语篇体裁的各个阶段。其中,“评议”(Evaluation)这一语篇体裁阶段对叙述文的解读十分关键,通常由“指向”(Orientation)和“尾声”(Coda)等部分来加强,在表现故事主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最后提出,需要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研究叙述文语篇,让学生掌握主流的阅读定位,同时了解其它可能的阅读方式,从而获得读写教学的成功。
3.2 人际意义研究
对人际意义的研究是马丁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除“对中断的评价:中学叙述文的主题象征”以外,本书关于人际意义研究的章节还有“宏观提议:意义的程度之分”、“人际意义、劝导和公共语篇:符号的冲击”和“哀悼:联盟的方式”。“宏观提议”一文选自论文集《语篇描述:对筹集资金语篇的多样化分析》,该书汇集了多位语言学家对同一“Zero Population Growth”(ZPG)语篇的语言学分析。“宏观提议”一文在Halliday(1979,1982b)对小句和语篇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语篇在概念意义方面的构成性特征(constituency)和人际意义方面的韵律性特征(prosody)。文章提出,人际意义包括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表达说话者与听话者关系的“行为”(action)和表达说话者个人态度的“反应”(reaction)。从“行为”角度看,语篇可被视为宏观提议,在语篇语义层面由交换结构(exchange structure)来体现,在语法层面则由祈使语气体现;从“反应”角度看,评价意义在语篇中的分布并不是任意的,程度高的评价意义通常与引起注意、提出要求相联系,而程度低的评价意义往往与对服务的阐述相关。人际意义的体现形式具有连续、积累的特点,以韵律的形式贯穿于整个语篇。文章还探讨了体现意义程度之分的语法资源(如amplification的韵律体现)。研究表明,语言内在的多功能性除了与语境层面的语域要素相对应以外,还与语篇体裁的结构相对应;语言的意义和结构密不可分,需要超越形式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探讨语篇语义和小句。
如果说“宏观提议:意义的程度之分”区分了人际意义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对中断的评价:中学叙述文的主题象征”主要关注情感态度、评价意义等主体性特征,“人际意义、劝导和公共语篇:符号的冲击”一文的重点则放在协商等主体间特征。该文考察了澳大利亚主流报纸之一SydneyMorningHerald刊登的一则读者来信中的情态系统,分析指出,人际语法隐喻在语篇中的灵活使用增强了措辞的表现力,情态的语法隐喻包括运用投射(projection)来彰显说话者作为情态评估(modal assessment)的来源(如:I reckon that...),也包括运用名物化(nominalization)将情态评估的主体隐藏为不容挑战的客观事实(如:It is a dead certainty that...)。除导向性(subjectivity ORIENTATION,objectivity ORIENTATION)外,情态系统的其它方面还包括价值(high/median/low VALUE)、表现(implicit/explicit MANIFESTATION)和种类(modalization/modulation)。文章分析表明,情态在对话中是进行协商的重要资源,而在独白中又是进行阅读定位的重要资源。马丁指出,情态系统所能体现的意义潜势并非都能被社会各阶层掌握,这就需要明确的批判性读写教学,培养批判性语言意识(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让学生掌握相应的语法资源及其意义潜势。
“哀悼:联盟的方式”最初发表在学术期刊Discourse&Society的“9·11”事件专号上,分析的语料是HKMagazine杂志在“9·11”事件十天后发表的社论“Mourning”。该文的分析重点也是人际意义中的评价系统,将此文与“对中断的评价:中学叙述文的主题象征”(1996)作比较,可以看出评价分析框架的发展和完善过程。HKMagazine的读者群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多个群体(包括在香港工作的西方人士、海外华人、在西方国家学习和工作的华人等等),文章通过分析“Mourning”一文中态度、分级、介入系统的运用,研究评价性语言资源如何联盟多元化的读者,从而达成阅读取向中情感态度的一致。分析表明,在情感态度的定位上,“Mourning”社论中对“9·11”事件中生命丧失的悲伤情感(affect)逐渐转为对“9·11”之后在亚洲不同地区发生的歧视有色人种个案的评判(judgement),最后的评价取向为对悲剧之后正常秩序被破坏和理性丧失的“哀悼”。具体来说,在态度系统(attitude)方面,情感关注的是情绪,评判关注的是品格和原则,鉴赏关注的是品位和偏好,同情与批评可以并存;就分级系统(graduation)而言,开篇饱和而强烈的情感逐渐转弱,评判和鉴赏被置于超主位和宏观主位,以渲染语篇的态度取向;从介入系统(engagement)看,情态、投射等语言资源的运用协调语篇中多种声音的互动。在理论层面,马丁指出,协商一致(negotiating solidarity)是涉及不同情感种类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复杂过程,随着语篇的展开,评价意义会重新定位读者的阅读取向,语篇中理智(sense)与情感(sensibility)形成动态互动:从意识形态(ideology)看,语篇是围绕理性、事实来展开的;从价值论(axiology)看,语篇的修辞力量有利于联盟读者、在情感态度取向上使之成为一致的团体。
3.3 多模态话语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篇分析开始关注语言以外的意义资源(Iedema 2003:32)。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不断增强,其理论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印刷文本、多媒体视听材料、网页超文本和三维立体实物,研究对象涵盖了交际中常见的多种符号模态(如图像、声音、动作等)。“雅致:‘自由’在单个语篇中的演变”、“中产阶级的想象:生活方式杂志中的再度殖民化语篇特征”和“模态间关系与和解信息:双方的合力”都涉及多模态话语分析。
“雅致:‘自由’在单个语篇中的演变”最初发表于学术期刊DiscourseStudies的创刊号,随后被Teun A. van Dijk(2007)主编的五卷本《话语研究》(DiscourseStudies)的第四卷收录。这篇文章有三个突出的方面:(1)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PDA)的概念;(2)论述了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MDA)在语篇分析中的意义;(3)阐释了对单个语篇的研究在语篇分析中的作用。文章分析的对象是Nelson Mandela的自传LongWalktoFreedom书后的一则自传体复述(autobiographic recount),考察的方面包括及物系统、语气系统、主位、语法隐喻、词汇隐喻、时态、语篇的格律、逻辑语义关系等语言学特征,同时还对该自传相对应的插图本TheIllustratedLongWalktoFreedom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分析表明,语法隐喻的运用使“自由”的表述在语法上更为机动灵活,对Mandela生平的线形描述和他对自由不断加深的理解交织成“螺旋式的”语篇特征。文章还考察了带有照片、批注和文本的多模态语篇,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是Kress和van Leeuwen(1996)的社会符号学分析法,涵盖的内容包括构图意义方面的已知—新信息、理想—真实信息,互动意义中的视觉接触、社会距离以及再现意义中的矢量等方面。
马丁在这篇文章里提倡一种跟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形成互补的“积极话语分析”。虽然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都强调话语理论的社会实践性,但批评话语分析主张批判和解构,而积极话语分析则重视鼓舞和激励。马丁强调,语篇分析不可避免要涉及多模态话语分析。长久以来,语言以外的符号模态(如图像、声音、动作等)被笼统地概括为语境,在语篇分析中也往往没有得到系统的描述。文章提出,语篇分析者需要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解读语境,将语境作为意义系统来考察。对多模态话语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Baldry和Thibault(2006),Bateman(2008),Kress和van Leeuwen(2001,2006),Iedema(2003),Lemke(1998,2002),Martinec(2005),O’Toole(1994),O’Halloran(2008),van Leeuwen(1999,2005),胡壮麟(2007),李战子(2003)和朱永生(2007)等的相关著述。文章最后对比了语篇分析的两种方法:对数量少的语篇进行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和对大量语篇进行分析的语料库方法。马丁指出,两种方法的区分在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考察的参数越多,能顾及的语篇数量自然越小,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语篇,对语篇的考察也不能忽视系统;对具体语篇进行细致的语言学描述,有利于了解语篇的社会影响以及语言变化对语篇体裁的影响。
与上面介绍的“人际意义、劝导和公共语篇:符号的冲击”和“哀悼:联盟的方式”一样,“中产阶级的想象:生活方式杂志中的再度殖民化语篇特征”一文考察的对象也是报纸、杂志等公共语篇。这篇文章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语言学/符号学为进行详尽的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从理论上说,对一个语篇进行穷尽的分析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语篇分析者一般不会这么做,因为穷尽的分析往往不经济,有的甚至是毫无意义或不可能的,分析重点的取舍常常取决于分析者的研究目的、研究兴趣和分析能力(黄国文1988,2001)。在分析具体语篇时,哪些方面是值得分析的?为什么要分析某些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马丁对此的回答是: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马丁首先归纳了系统功能符号学(systemic functional semiotics,SFS)从分层级角度(hierarchy)和从互补角度(complementarity)进行语篇分析的理论方法,并小结了功能语篇分析的功能/层次矩阵。从分层级的角度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精密度(delicacy):分类——从笼统到明确;
■ 级(rank):组成——从整体到部分;
■ 体现(realization):分层次——从抽象到具体;
■ 示例化(instantiation):稳定性——从系统到实例;
■ 个体化(individuation):编码导向——从特定文化中的所有意义潜势到特定个体的语域/语篇体裁集合。
其中的体现、级、精密度等概念较为人们所了解。“体现”用于描述符号系统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以语言为例,包括音系层、词汇语法层、语篇语义层以及语境层中的语域和语篇体裁;“级”描述的是某个层面中的单位或成分的等级关系,以词汇语法层为例,小句由词组(或短语)组成,词组(或短语)由词组成,词由词素组成;“精密度”是指系统网络从左到右不断细分,一个系统的特征可以成为精密程度更高系统的入列条件,例如小句的语气系统包括指示和祈使,其中指示可以进一步分为陈述和疑问。如果分析对象是多个关联的语篇,我们可以从“示例化”的角度来考察该语篇所属的语篇类型、语域和语篇体裁的规律性特征,还可以从“个体化”的角度研究同一作者或同一流派一系列作品的风格。
此外,从互补的角度进行语篇分析,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从发生学(genesis)的角度看,互补的方面有单个语篇发生、个体发生、系统发生;
■ 从模态(modality)看,有语言、图像等;
■ 从元功能(metafunction)看,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组篇功能;
■ 从轴(axis)看,系统和结构是互补的方面。
元功能为功能语篇分析者所熟知。其它互补的方面,就发生学来说,logogenesis(话语发生)指的是单个语篇中语言学特征的变化,ontogenesis(个体发生)考察个体不同阶段在语言学上的发展,phylogenesis(种系发生)研究语言学特征历时的演变。模态指的是交际的渠道,更准确的表述是符号模态(semiotic mode)(Kress & van Leeuwen 2001:20),常见的符号模态包括语言、图像、声音、空间和身体动作等,系统功能符号学主要以话语中涉及的符号系统的数量来界定多模态话语。在研究系统的同时,还可考察意义的粒子型、韵律型、格律型实现方式。
“中产阶级的想象”以一份澳大利亚杂志中包含的文本、人物肖像、风景照片的多模态语篇为语料,分析了该语篇在排版、评价资源、格律、语篇体裁、构图、色彩衔接等语言学和符号学特征。分析表明,该杂志中鼓吹的生活方式仅为少数上层中产阶级所拥有,这实际上是非原著民的中产阶级进行再度殖民化的表现。
“模态间关系与和解信息:双方的合力”是马丁在2006年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多模态语篇与多元读写:符号学理论与教学实践”(Multimodal Texts & Multiliteracies:Semiotic Theory & Practical Pedagogy),主要会议论文被收入由Len Unsworth(2008)主编的论文集《新读写与英语课程:多模态视角》(NewLiteraciesandtheEnglishCurriculum:MultimodalPerspectives)。与“雅致:‘自由’在单个语篇中的演变”(1999)类似,“模态间关系与和解信息”一文的两大关注点同样是多模态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这篇文章的分析对象是一本面向小学高年级读者的儿童图书PhotographsintheMud,主要探讨图书中的语言和图像如何联盟读者、传递“和解”这一主题信息,抚平二战时日澳两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研究指出,语言和图像具有互补的特征,譬如语言中的主位推进等格律特征可以由图像中显著的参与者、框线来互补,语言中的作格(agency)特征可以由图像中的矢量互补,表达态度的语言资源可以由图像中人物情感的体现、色彩渲染(ambience)来互补,投射、介入等语言特征可以由视觉聚焦(focalization)互补。马丁认为,不能把两种模态的互补特征简单地等同起来,模态间关系的解读必须联系语篇体裁。就PhotographsintheMud来说,对图文互补关系的解读必须联系该叙述文关于和解的主题信息(另见“对中断的评价:中学叙述文的主题象征”(1996)对叙述文主题信息的论述)。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图标化(iconization)在联盟社会群体中的作用,正如在概念意义中,下定义等语言技术化过程(technicalization)能将现实加以浓缩提炼,在人际意义方面,图标化能把特定社会团体共享的价值观物化(materialized)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联盟图标(bondicon,如白鸽象征和平),以及其它物化形式如仪式、口号、旗帜、吉祥物等等。PhotographsintheMud中的图标化过程涉及故事中的角色(如士兵和他们的妻子)和象征物(如樱花)。语言和图像的合力表现了“和解”这一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PhotographsintheMud可以被视为一则教育语篇。总结归纳出各种语篇体裁中的模态间互补方式是社会符号学面临的挑战之一。
4. 结语
我们从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悉尼学派的相关研究谈起,以《马丁文集》之《语篇分析》卷为主线,对马丁的语篇分析思想作了评介。最后,我们尝试小结以马丁为代表的悉尼学派在语篇分析研究方面的一些特点:
(1) 对语篇体裁(genre)的关注是贯穿其语篇分析研究的一条主线,以马丁为代表的悉尼学派注重语篇体裁理论在读写教学中的应用,而读写教学中的实践也促进了悉尼学派语篇体裁研究的发展;
(2) 关注语篇语义层面的人际意义研究,在系统地研究赋值语义方面,提出并发展了分析框架;
(3) 重视对语篇进行系统、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强调语篇分析的社会实践性,关心弱势群体,提倡积极话语分析,重视话语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建设性影响,所分析的语料涉及教育领域、社会生活、时政新闻等多个方面;
(4) 重视交际的真实情况,提倡多模态话语分析,从社会符号学出发,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解读语言以外的多种交际模态。
Baldry, A.P. & P.J. Thibault. 2006.MultimodalTranscriptionandTextAnalysis[M]. London: Equinox.
Bateman, J.A. 2008.MultimodalityandGenre:AFoundationfortheSystematicAnalysisofMultimodalDocuments[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Christie, F. & J.R. Martin (eds.). 2007.Language,KnowledgeandPedagogy:FunctionalLinguisticandSociologicalPerspectives[C]. London: Continuum.
Freebody, P., K. Maton & J.R. Martin. 2008. Talk, text, and knowledge in cumulative, integrated learning: A response to “intellectual challenge” [J].AustralianJournalofLanguageandLiteracy31(2): 188-201.
Halliday, M.A.K. 1979. Modes of meaning and modes of expression: Types of grammaticalstructure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by different semantic functions [A]. In D.J. Allerton, E. Carmey, & D. Hodcroft (eds.).FunctionandContextinLinguisticAnalysis:AFestschriftforWilliamHaa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79.
Halliday, M.A.K. 1982a. The de-automatization of grammar: From Priestley’s “An Inspector’s Calls” [A]. In J. Anderson (ed.).LanguageFormandLanguageVariation:PapersDedicatedtoAngusMcIntosh[C]. Amsterdam: Benjamins: 129-159.
Halliday, M.A.K. 1982b. How is a text like a clause? [A] In S. Allen (ed.).TextProcessing:TextAnalysisandGeneration,TextTypologyandAttribution[C]. Stockholm: Almqvist & Wiskell International: 209-247.
Halliday, M.A.K. 2006. Working with Meaning: Toward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R]. (Inaugural lecture to mark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Halliday Center fo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Studies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26 March, 2006).
Halliday, M.A.K. & J.R. Martin. 1993.WritingScience:LiteracyandDiscursivePower[M]. London: Falmer.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1.MultimodalDiscourse:TheModesandMediaof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M]. London: Arnold.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6.ReadingImages:TheGrammarofVisualDesign[M]. (2nd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Iedema, R. 2003.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J].VisualCommunication2(1): 29-57.
Lemke, J.L. 1998. Multiplying meaning: Visual and verbal semiotics in scientific text [A]. In J.R. Martin & R. Veel (eds.).ReadingScience:CriticalandFunctionalPerspectivesonDiscoursesofScience[C]. London: Routledge: 87-113.
Lemke, J.L. 2002. Travels in hypermodality [J].VisualCommunication1(3): 299-325.
Martin, J.R. 1991. Intrinsic functionality: Implications for contextual theory [J].SocialSemiotics1(1): 99-162.
Martin, J.R. 1992.EnglishText:SystemandStructure[M]. Amsterdam: Benjamins.
Martin, J.R. 1999. Modelling context: A crooked path of progress in contextual linguistics [A]. In M. Ghadessy (ed.).TextandContextInFunctionalLinguistics[C]. Amsterdam: Benjamins.
Martin, J.R. 2000/2006. Grammar meets genre: 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 [J].InauguralLecture,SydneyUniversityArtsAssociation(2):28-54.
Martin, J.R. 2001. Giving the game away: Explicitness, diversity and genre-based literacy in Australia [A]. In R. de Cilla, H. Krumm & R. Wodak. (eds.).LossofCommunicationinheInformationAge[C]. Vienna: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amie der Wissenschaften: 155-174.
Martin, J. R. 2002.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Reconciliation and evaluation [A]. In C. Candlin (ed.).ResearchandPracticeinProfessionalDiscourse[C].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87-227.
Martin, J. R. 2003. Voicing the ‘oth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 In G. Weiss & R. Wodak (eds.).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TheoryandInterdisciplinarity[C]. London: Palgrave: 199-219.
Martin, J.R. 2004/2006.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J].RevistaCanariadeEstudiosIngleses(14):21-35.
Martin, J. R. 2007. English for peace: Towards a framework of Peace Sociolinguistics: Response [J].WorldEnglishes26 (1): 83-85.
Martin, J.R. & D. Rose. 2007. Interacting with text: The role of dialogue in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J].ForeignLanguagesinChina4 (5): 66-80.
Martin, J.R. & D. Rose. 2008.GenreRelations:MappingCulture[M]. London: Equinox.
Martin, J.R. & P.R.R. White. 2005.TheLanguageofEvaluation:AppraisalinEnglish[M]. London: Palgrave.
O’Halloran, K.L. 2008. Systemic functional-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F-MDA): Constructing ideational meaning using language and visual imagery [J].VisualCommunication7(4): 443-475.
O’Toole, M. 1994.TheLanguageofDisplayedArt[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Reid, I. (ed.). 1987.ThePlaceofGenreinLearning:CurrentDebates[C]. Geelong, Vic.: Centre for Studies in Literary Education, Deakin University (Typereader Publications 1).
Simon-Vandenbergen, A., M. Taverniers & L. Ravelli (eds.). 2003.GrammaticalMetaphor:Viewsfrom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C]. Amsterdam: Benjamins.
Taverniers, M. 2002.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andtheNotionofGrammaticalMetaphor:ATheoreticalStudyandaProposalforaSemiotic-functionalIntegrativeModel[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hent.
Thibault, P. 1989. Genres, social action and pedagogy: Towards a critical social semiotic account [J].SouthernReview22 (3): 338-362.
Threadgold, T. 1988. The genre debate [J].SouthernReview21 (3): 315-330.
van Dijk, T.A. (ed.). 2007.DiscourseStudies[C]. London: Sage.
van Leeuwen, T. 1999.Speech,Music,Sound[M]. London: Macmillan.
van Leeuwen, T. 2005.IntroducingSocialSemiotics[M]. London: Routledge.
胡壮麟.2007.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1-10.
黄国文.1988.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黄国文.2001.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黄国文、常晨光、戴凡.2006.功能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李战子.2003.多模式语篇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外语研究(5):1-8.
朱永生.2006.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J].英语研究(语篇分析专号,黄国文主编)(4):36-42.
朱永生.2007.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5):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