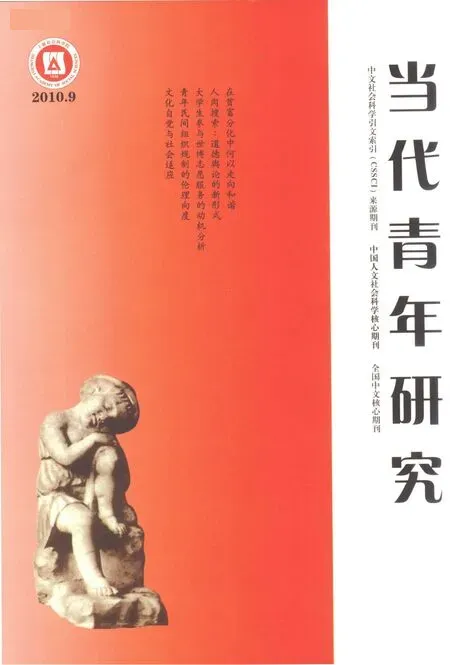都市女性恋爱暴力的质性研究
◎王曦影
恋爱与暴力之甜蜜而疼痛的纠葛在《我的野蛮女友》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也因而在大陆、香港、台湾受到无数年轻人的欢迎,2002年,该片荣登由《新周刊》、新浪网、阳光卫视等40多家亚洲媒体评选的“年度新锐榜”,以标示这一“跨时代”的对恋爱暴力的浪漫想象是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同、青年人的追捧、大众文化的效仿。电影浪漫而且宽容地创造了一个外形美丽且又很有攻击性的女性形象,自此之后,“我的野蛮女友”拥趸无数,这一媒体形象大行其道。这种活跃的大众文化文本刻画了一个现代都市恋爱新模式,即女友任性、野蛮、暴力,男友温柔、体贴、脆弱,也于此彰显了“后野蛮女友时代”的一则隐晦而又含糊的社会文化信息:女性的暴力,尤其在恋爱中的暴力,是 “可以接受的,甚至给她们添加一种魔力”(Worcester,2002,p3192)。
本研究采取深入访谈和焦点小组两种方法,其中笔者于2004年夏共访问了42位年轻人(29名女性,13名男性),2006年春又对其中的15位做了后续访谈。如果说访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关于恋爱暴力的个人经验,那么焦点小组的作用在于:首先给年轻人提供了对恋爱暴力表达态度和观点的空间;其次让研究者可以将访谈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带入小组中进行讨论。从这一角度而言,焦点小组起到帮助研究者分析资料的作用。这一研究一共组织了三次焦点小组,第一组由6名本科女生组成,第二组由5名男研究生组成,第三组由青春热线①20多名志愿者组成。
一、我是野蛮女友吗?
尽管《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在当时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但对如何看待“野蛮女友”这一角色,被访者们意见不一。许多女性被访者说,她们不仅喜欢这部电影,而且觉得自己也有点“野蛮”。
我喜欢那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挺暴力的。我和他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记得有一次,我们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然后,他们就说起来,他以前的女朋友什么什么的,我才知道他以前谈过三次恋爱。其实我不在乎他谈过几次恋爱,在意的是他没有告诉我。我很愤怒,就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踢了他几脚发泄一下。(陈林,女,24岁)
显然,中国年轻女性认同并欣赏电影中的“野蛮女友”,她们希望拥护其攻击性,以及由攻击性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去重新定义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并对在恋爱关系中占有权力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然而,很多男性被访者明确表态,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女友像电影中的女主角那样不分原则地具有攻击性。
女生受这电影影响很大,很多人以为自己就是全智贤。我觉得长得越好看的,越任性,越可怕。 (SEI,男,20 岁)
对他们而言,野蛮女友,只能远看,不能拥有,他们永远是观众,而不是男主角。他们更愿意将大众文化影像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倾向选择一个“传统的”女友。被访者文洁说,她的男友就不喜欢这部电影。
他说他绝不会找那样一个女朋友。简直反了。他一定要找一个性格温柔,能体谅人的。(文洁,女,26 岁)
尽管男女受访者对电影中的“野蛮女友”的态度不一,但是他们的共识是:电影中“野蛮女友”的行为并未构成暴力。在6名大学本科女生焦点小组访谈中,她们这样说:
小王(19岁):那女的不算暴力吧,闹着玩嘛!
小张(20岁):我也觉得不算暴力,关键是打得那个男的开心,就不算暴力。
在由5个男生组成的焦点小组中,说法有所不同。
大虎(24岁):这不算暴力?其实我觉得,在恋爱中男孩子是处处迁就女孩子,但是婚后那就不一样了。的确很多都是这样。如果男孩子那样对女孩子就算暴力。
尽管两个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一致认为“野蛮女友”在电影中的行为不算是暴力,但是他们给出的原因不尽相同。女生小组倾向于认为,“野蛮女友”的行为只不过是闹着玩而已;男生小组的态度则很矛盾,“野蛮女友”的行为,如果换成男生做主角,就是暴力,女生施与男生,就不算什么了。女生小组的声音是:女生只是闹着玩,因为男生不觉得痛,而且男生被女生打,他们一定觉得很幸福;而男生小组的陈述是:女生那点花拳绣腿,伤害不了谁,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一现象及这一现象所延伸出来的叙事都非常有趣,虽然男女双方在认为“野蛮女友并非暴力”这一观点上达成默契和共识,但是他们所用的论证方式和逻辑却完全不同。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中国都市的男性似乎已经树立了很鲜明的立场,他们在坚定斥责男人打女人是不对的同时,面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却摆出一种男性的超然和优越感。
二、任性女孩:中国的野蛮女友?
在本研究中,“任性”这一“描述”个性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被访者的叙事中,被用来解释“为什么都市女性会在恋爱中使用暴力”。本文在此就援引两位女性受访者的原始叙述来定义这一词语:“任性”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让他干什么就必须干,不干就不行”(邓丽,33岁),“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偏不做,他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偏要做”(曾馨,23岁)。两位女性受访者在两句话中分别占据着主动和被动的位置,前者是要求男友的绝对服从,后者则表达了对男友的绝对反抗,而“任性”就成为在绝对服从和绝对反抗之间妥协生存的情绪表达,并在两性关系的青年亚文化解释中,承担了指引恋爱中的种种冲突和暴力行为的责任。
《商务现代中文词典》对“任性”的解释是:听凭自己的心意行事,不加约束。这种“听凭心意、不加约束”的“任性”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往往被用于诟病年轻人很情绪化、按喜好做事、不成熟、小孩子气、被宠坏了、即便做错也不会主动承担责任的情绪和行为。本文中,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受访者都倾向于将有暴力行为的女性定义为“一时任性”,那么女性暴力就被归因为“年轻”、因为“个性和性格”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需要讨论的原则性问题。南悦的叙述非常轻描淡写,也很典型:
如果我看到女孩打男生,我会说那个女生很泼辣,很任性,但不会说她是暴力。(南悦,女,22岁)
一方面,正如Lloyd和 Emery(2000)的研究指出,恋爱可能是女性一生中最灿烂辉煌的时光,也是她们觉得自己最有权力的时候,所以,对于女性来说,既然占据了这么王美这样表述她的理想爱情:
可能是我要求比较高吧,我时时刻刻都要求他把我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还比较任性吧,我就想要一个关心我宠我的人。(王美,女,25岁)
丁林与男友相处的最有力武器是威胁分手。她认为,正是男友的纵容使她变成了一个任性女孩。
他对我就是那种没有原则的好,百依百顺,什么都能容忍,所以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像现在这么任性,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原因造成的。(丁林,女,22岁)
以此逻辑:首先,被男友宠可以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这也成了一条择偶的标准;其次,男友越宠,女性就可能会越任性;最后,既然女性的任性只不过是因为男友太宠,所以男友是自找倒霉。因此,受访双方的共识是,由任性而发展出的“野蛮女友”式的恋爱模式是不能算成暴力的。
研究发现,现代都市女性在恋爱关系中的任性与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有相当的关系。本文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出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诞生的年代,确实,42位被访者中有16位是独生子女。他们大多成长在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家庭环境中,被父母寄予厚望。丁华及其女友都是独生子女。在他的描述中,他与女友之间的相互暴力都用相同一句话来指控对方:“你居然敢打我,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没有碰过我一个手指头。”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任性”是个很有个性的词语。当两个自己定义为“任性”的个体聚到一起的时候,冲突频繁。尤其对于被父母宠爱的年轻女性来说,“碰”都不可以,更不要说“打”了。她们非常明确:要的就是男友的宠爱和对她们任性的宽容。
三、“不是什么暴力,很正常的。”
因为暴力的原因被归于任性,所以男女被访者都认为女性的暴力行为是正常的、无伤大雅的、小孩子气的。前文中焦点小组甚至还“发现”了女性暴力有着增进亲密关系的功能:弹性地进行情感表达、再建沟通模式、丰富情趣甚至感情。邓丽如此描述她与男友的恋爱场景:
吵架之后,我就急着让他向我赔礼道歉。他不赔礼道歉,我就跟他闹。不让他睡觉,把他衣服都泡在水盆里,不让他去上班,把他的鞋扔到楼下去。都是我打他,我也不使劲打他,我就掐他。我让他赔礼道歉,他要不说,我就掐他。有一次掐疼了他,他就撸了我一下,男的怎么也比女的有劲,我那时候,挺瘦的,现在90多斤,原来70多斤,他扒撸了一下,就把我弄一边去了。我就认为他在打我,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拿起来他收藏的鸡血石,很名贵的,什么花边黄、千层洞什么的,我就拿起来一块,我就砸他,他一躲,我就把玻璃砸了一个大窟窿,那是我们打得最凶的一次。然后他也特生气,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让我给弄到楼下去了。(邓丽,女,33 岁)
故事叙述结束后,邓丽用“不是什么暴力,很正常的”来做总结陈辞,她觉得自己的攻击只不过是坚持自己主张、让男友低头认错的一种任性行为而已。而本研究发现,正如邓丽一样,很多年轻女性都期望男友可以宽容她们的“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男友都能心甘情愿,甘之如饴。陈宾正在和一个小他5岁的女孩谈恋爱,面对女友的任性行为,他常常觉得很无助,不知如何是好。
都不知道是谈朋友呢,还是养闺女,这也太累了点吧。(陈宾,男,29岁)
另外一些男性受访者表现出更愿意承受女性的攻击行为,一些人甚至认为女性的暴力可以增强双方的情感。正如萧洪(男,26岁)所说,“我们的爱在吵架、打架中升华”。何荣的女朋友只要是对他不太满意,就扇他耳光。但在何荣的叙述中,他是这样表达的:
我觉得女孩子天生是被男人宠,被男人爱的。我一直觉得不管你对我怎样,我对女孩子比较尊重——习惯了,她被我宠坏了——不过没办法,不管谁的错,她打完以后,不管谁的错,道歉的都是我。(何荣,男,23岁)
O'Keefe(1997)的研究显示,恋爱中的两性都更接纳女性的暴力,这一发现在本研究的诸多个案中也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年轻女性用“正常”来为她们的行为辩护,并拒绝将其定义为暴力,因为传统的中国女性气质(Zhan,1996)概念对她们仍有极深的影响,她们不愿意将自己归类为“暴力”女性。就好像邓丽说的:“我觉得,我从骨子里来说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的,可能自己做起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但我很佩服那些贤慧的、贤淑的女性”。
在邓丽的恋爱故事叙述结束之后,很难想象她会将自己形容为“骨子里”的贤妻良母。而邓丽和其他几位被访者所共同描述的所谓“任性”以及“掐”、“吵架、”“打架”、“扇耳光”等等,是呼应了邓丽所述及的,这些行为只是“贤妻良母”“一时任性”的女性气质的外化表现、只是与传统表现“不太一样”,非常个人(“自己做起来”),受到现代社会文化影响(“对女孩子比较尊重”)。对传统的中国女性气质的自然认同和文化潜意识里的归属也使得很多女性受访者不愿意承认她们的恋爱行为中存有暴力,或被冠以“暴力”之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男性被访者谈论电影中“野蛮女友”的时候,众口一词,这样子的“野蛮女友”不能要,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还是应该传统温婉。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在表明:男性气质在“任性”的“野蛮女友”的影响下,也从民间话语中吸取力量,呈现出令人惊奇的“温柔”张力。正如陈宾(29岁)所说,“好男不跟女斗”,很多男性被访者将这句充满了性别歧视的戏谑俚语转释为现代男性气质征服女性的成功总结。
在男性不将女性恋爱中的攻击行为视为暴力的同时,男性被访者也在恋爱暴力的后叙事中建构起一种心理和身体上的优越感,以及在想象中完成了一个为社会所认可和褒扬的“好男”型塑,以反证这句俚语诞生传播至今男性气质的不可逾越性。身体上,男性具有着自人类出现以来的自然优势,正如岳峰(24岁)所说:“(她们)毕竟是弱势群体,力量还小,打人不是自找苦吃吗。真搞笑”。心理上,“好”男性应是不屑于与女性动武,诸多男性被访者都觉得,女人很难缠,一个“体面的”男人应该避免惹怒她们,更不应该与她们动手。
男性受访者都乐于引用孔子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并在其叙事中,塑造一个自己认同的、宽容大度的、具有现代品质的男人形象。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他们也希望呈现出一个与“有权力的、野蛮的”女性气质并行不悖并和睦相处的男性气质,以寻求恋爱的完满和两性关系的多元表达。事实上,当温和容忍被动的男性气质越来越成为现代中国都市年轻女性选择恋爱对象的标准之时,该标准本身也在中国都市男性的理解中成为一种男性气质的自我塑造成功的证明,所以,男性也不会因为女性的某些“任性及暴力行为”而轻易地放弃与之交往,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女友的暴力行为很“正常”,不会影响两者之间的亲密及恋爱关系。本研究发现,年轻男性之所以要宽容女性的暴力,因为“温柔”已然逐渐成为一种“公认的”现代“男性气质”的准则和要求,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和恋爱市场上的竞争和角逐中。
尽管本研究的发现不能泛泛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本文还是希望借助于这一项男女两性恋爱关系的质性研究,来理解中国现代都市男女两性恋爱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及由此彰显出的两性气质的变迁。首先,这个研究帮助拓宽了暴力的概念,并关注了一直被忽略的女性暴力的问题。在本文中提出的野蛮(任性)女友、温柔男友的形象与以往研究中受害妇女和施虐男性的形象大相径庭。当讨论银幕形象野蛮女友时,女性显示出更多的好感,而男性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排斥感。在日常恋爱关系中,男女两性都拒绝将女性的攻击行为定义为暴力,不仅如此,男女两性还在日常生活中证明这是正常的且具有很多维系并促进两性关系的功能。在男友欺骗的情境下,女性不仅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暴力,且更作为一种正义的行为去惩罚对方。在相互暴力的情境下,女性忽略自己的攻击性行为,扮演成受害者,并将参与的相互暴力定义为家庭暴力。在这一过程中,在野蛮(任性)的女性气质大行其道的同时,温柔宽容的男性气质敷演下的中国都市新男性形象出现了。其次,Gilbert(2002)认为性别角色定型持续渗透社会并创造出暴力女性不是“坏人”就是“疯子”的话语,但是本文却显示了在中国各式各样矛盾而且多层次的性别、爱情、性的话语给年轻人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去论证女性暴力的合理性。恋爱关系中的女性可能很暴力,可是也很有魅力。这一研究中涉及的话语包括:儒家思想要求女性温良恭俭让,要做“贤妻良母”;新社会的口号是“男女平等”,女人是半边天,继而形成“铁娘子”的形象。本文中的被访者更表现了女性是怎么运用恋爱关系中的“诚实与忠诚”这一坐标去证明以暴力惩罚男性的正义性和作为现代都市女性积极去捍卫平等的主动性。总之,本文中的女性被访者大多擅长选择和运用对自身有利的话语去使得女性暴力行为更易被社会接纳。
注:
①青春热线是北京最早的志愿者机构之一,主要服务对象是全中国的青年与青少年。1993年由中国青年报社陆小娅创办,2001年改成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