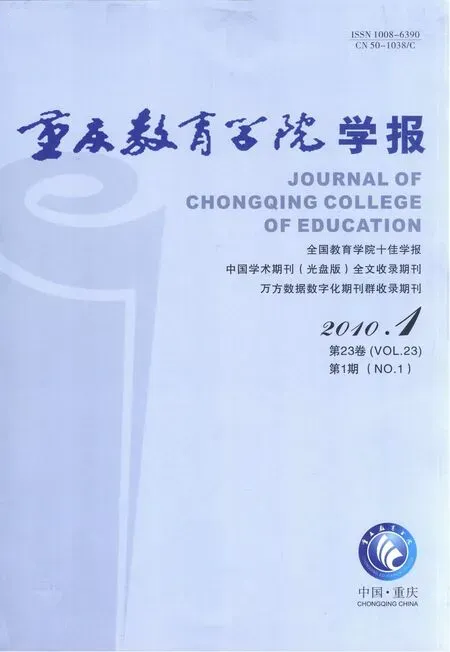迁移者的悲歌——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董书存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主要创作于1964——1971年之间,共收 14篇小说。在这些短篇中,白先勇用其悲天怜人的大椽之笔鲜活地记录下了一个个“台北人”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感同身受地对“台北人”的生存形态和内心精神世界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刻画,深入到“台北人”悲苦的现实命运中,深入到人性的内核里,把“台北人”生存的痛苦、孤独、失望、凄凉的状态,生动细腻地揭示出来。在今昔荣辱,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的变迁中,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感、历史兴亡的伤怀之情,为这些“台北人”唱出了一曲无尽的哀婉的悲歌。为那个逝去的时代唱出了绝望、无奈的挽歌。
这些所谓的“台北人”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随国民党败退而迁移到台湾的,既有贵妇名媛、女仆男佣,又有高官儒将、下层军官;既有大学教授、旧式书生,又有女伶倡优、风尘女子,都是沦落台北的大陆人,身居台北,心在大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人人都在怀旧的心态中步入没落的人生路。这群“台北人”因失去“过去”而怀旧,因失去原“根”而思乡,面对境遇的改变,自我又不能解脱,因而常常陷入苦恼、空虚甚至绝望的境地,结局都十分凄惨。
歌者心声也,悲歌实为白先勇凄楚内心的表白。感同身受的家族经历,使其与其他“台北人”情感上迅速融为一体,面对以商业金钱为主导的严酷社会现实,白先勇用其手中的笔谱出如泪泣血的时代最强音,它哀婉悠长、凄楚沉痛,似在诉说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又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国家兴衰、时代变迁下芸芸众生的浮世图。之所以悲,悲在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命运难以捉摸。这种命运的沉浮、变迁在今非昔比的对比中显现地尤为突出,正如欧阳子女士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萎缩、绝望、丑、现实与死亡。”[1]136在今非昔比的残酷社会现实面前,只能靠驻足于过去,沉湎于过去,汲取精神的食粮,维持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只能在过去、现在、大陆、台湾这四个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徘徊。豪门望族的凄凉晚景与小人物凄惨的命运似乎都在弹奏出阴郁悲凉的韵调,也似乎暗示出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兴衰和人世的虚妄,其情之真切,其情之悲愤,非感同身受者不可为。总的来说,迁移者的悲歌还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台北人”的凄惨人生历程来演绎的,而其人生命运之无常又是在今昔对比中显现出来的。
二
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被冲得人仰马翻,那个曾经给予他们幸福的年代已成昨日黄花,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夕阳西下的凄恻的人生晚景,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悲从心生,歌从悲生。《国葬》中的李浩然将军,堂堂的陆军一级上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建立过不朽的功勋,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其晚年又是怎样的结局呢?从他的挽联——“闻道霸陵夜列何人愿起故将军”中,可以看出作者借用李“故将军”夜猎的典故,来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凉。而《思旧赋》中的李长官一家的变故更是让人唏嘘不已,李长官身体虚弱的“脱了形”,夫人已过世,小姐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了。少爷从国外回来,精神失常,在家族衰亡之际只会“咧开了大嘴”、“嘻嘻地傻笑”。《梁父吟》里的那个“发迹的早,少年得志”的革命元老王孟养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这些国民党的高官将军们,都曾有辉煌的过去,但晚年的孤独寂寞、失势潦倒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此时再读白先勇在《台北人》这部集子的扉页上题写的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时,恐怕对历史变迁沧桑感的体味就会更深了。
作为夫荣妻贵的高官达人们的遗孀及高官达人的依附者,随着高官达人的失势、去世,她们也必然无可挽回地走上没落、衰亡之路,命运之无常,世态之炎凉也使她们尝个遍透。《游园惊梦》、《秋思》就揭示了这一悲苦主题。《游园惊梦》中钱鹏志将军在世时,钱夫人享尽了荣华富贵,不仅有钱有势还有美貌的青春容颜,干什么事都讲究排场,是秦淮河得月台众姐妹中地位最显赫的,出风头最多的,那时的窦夫人 (桂枝香)远不如她风光。而现在呢?一切都翻了个。钱将军早已亡故,参加宴会由专车改坐计程车了,而且穿的布料、款式都已不时兴了,象举办原来如此盛大的宴会恐怕早就不可能了。曾红极一时的钱夫人所拥有的青春、荣誉、地位的失落一览无余,展示出了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悲剧的必然性。骄人的过去、失落的现在,泾渭分明,人世的沧桑巨变恍如隔世。《秋思》中的华夫人在台北遇到了国民党新兴权贵万大使万夫人的挑战,尽管万夫人对她语言很刻薄,而她却不得不委曲求全:“因为万夫人的丈夫还健在于人世,事业飞黄腾达,而一度轰轰烈烈的华将军,却已久离人间,被世人遗忘。”《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似乎是一个永恒“过去”的象征,她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信条也似乎暗示了人生无常,终归于空无、寂寥的悲歌主题。有权有势者在时代风雨飘摇之际尚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处于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呢!《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孤恋花 》、《花桥荣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诸篇什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幅更揪心、更悲惨的人生悲歌画面,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多桀的命运,垂死的挣扎更是作者悲悯情怀的曲折表达。
《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在十五年的期待、十五年的希望被残酷的现实打碎后,变得自暴自弃起来,整天沉溺于性欲的满足之中,最后沉郁自杀。美好的过去,丑陋的现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卢先生的悲剧是理想破灭的悲剧,是人性沉沦的悲剧,是在大的历史变动背景下的人生命运沉浮的悲剧。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男佣王雄对丽儿的“爱情”破灭后,即被“过去”舍弃后,决定以跳海自杀的方式回大陆老家“找亲人”(老家的“小妹仔”)去,然而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漂到大陆,他至死都无法寻到亲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怎样的令人心痛的悲歌啊!
《岁除》中的赖鸣升这位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顶天立地的民国军人,在退役后只能到荣民医院当“伙夫头”,却仍然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且大有虽“死”犹荣的意味,这正是他的悲剧!
《一把青》中的朱青在丈夫死亡的惨痛打击下,前后判若两人,她变得浪荡世俗、麻木不仁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她伤心的了,她对郭轸、小顾二人坠机身亡的不同反应,正是她“哀莫大于心死”的明证,精神已死,空留躯壳!朱青的悲剧命运是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起伏的命运便是时代起落的真实写照。
《孤恋花》中的酒女娟娟的母亲是个疯子,常年被锁在猪圈里。娟娟十五岁被生父强奸,后被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最终娟娟还是用熨斗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柯老雄死了,娟娟也疯掉了。娟娟卑微屈辱的命运浓缩了人生的无奈与悲凉!无论你怎样的挣扎都逃不脱厄运的魔掌,无论你是怎样的无辜!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舞女金兆丽,在拜金的风月场中摸滚打爬了二十多年,如今年老色衰的她却不得不躬行起先前所憎恶的“饿嫁”起来,下嫁给了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真是殊途同归、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不管你怎么跳,早跳、晚跳都跳不出冥冥之中的这个怪圈!作者内心的悲怆溢于言表!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教主”朱焰,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爱情、青春、事业,早已变得白发蓬蓬、背项佝垂,即使被刑警“修理”后,仍然跛着脚到公园寻求肉欲的满足。失去了精神追求的肉体躯壳,何异于行尸走肉!可怜、可悲!
《冬夜》中的两位教授余嵌磊和吴柱国不得不尴尬地面对物欲高蹈的现代商业社会,这时代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冬夜了!他们的心境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通过一幕幕人生悲剧写出了主人公们在历史的激荡沉浮中失掉原有的“优越感”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对那些社会底层沉沦者的哀歌似乎更沉郁、更深沉!世事的巨变,人生的沧桑,命运的乖戾,时代的无情,已经使他们麻木不仁了。不管你是高官达人还是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不管你甘心不甘心,昔日的荣光都早已随时间的推移化作一缕缕青烟,消逝地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可怜可悲的一具具行尸走肉!历史的沧桑感,人生的悲凉感,命运的无常感协奏出一曲曲令人心碎的悲歌!
三
白先勇认为本世纪以来始终处于流离状态的中国人成了精神上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回忆的重担。由此可见探寻“台北人”的精神悲剧,就成了他小说的灵魂。他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余光中语)。生于贵胄之家,衣食无忧的白先勇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是不可能将一个个“台北人”写的如此鲜活,如此的悲凉,如此的如歌似泣!或许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这段话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也认为,作家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思维、创作心态会产生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影响,外界物质形态对主体心理图式的构成可产生特定印迹。白先勇七八岁时染上“童子痨”,“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2]66,“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3]275,或许正是这次灾难的缘故使他变成一个对悲苦特别敏感,并能深深体味的人。随后的那种行踪不定的生活、对陌生环境缺乏安全感的恐惧以及家庭衰败带来的心灵挫伤,使白先勇逐渐在个人不幸体验中加注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使他“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2]176,因此可以说,一个作家看取世界的视角,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于他独特的生活阅历、个性心理和情感特征。
而其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更是其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白先勇曾经说过:“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4]398传统文学中人生苍凉和历史沧桑的悲凉意味自然也就成了他创作小说的一种自觉倾向。白先勇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小说痛苦多、欢乐少”[5],它们是“对过去、对自己最辉煌的时代的一种哀悼”[6]68,它们是写在“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仿徨”、“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2]78之际。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外国作家是福克纳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先勇说:“他们两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基督精神,这是文学情怀的最高境界”[2]89。此在《台北人》的创作中悲悯情怀就成了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
总之,白先勇能从无数从大陆退居迁移台湾的各色人物在历史的风浪中上演着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中发现人生苦难中呈现的美,并诉之笔端,能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并油然而生出忧伤、怆然、悲悯的审美体验,让人感叹命运的残酷莫测、人生的多难和幸福的渺茫以及短暂。以悲情动人的《台北人》无疑是一支意犹未尽迁移者的悲歌!
[1] 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A].白先勇文集 (第二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2] 白先勇.蓦然回首[M].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
[3]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台北: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8.
[4] 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A].白先勇自选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5] 杨锦郁,李瑞腾.把心灵的痛楚变成文字——在洛杉矶和白先勇对话[N].文学报,1987-03-12.
[6] 白先勇.为逝去的美造象卜——谈《游园惊梦》的小说和演出 [A].白先勇.游园惊梦 [M].台北: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