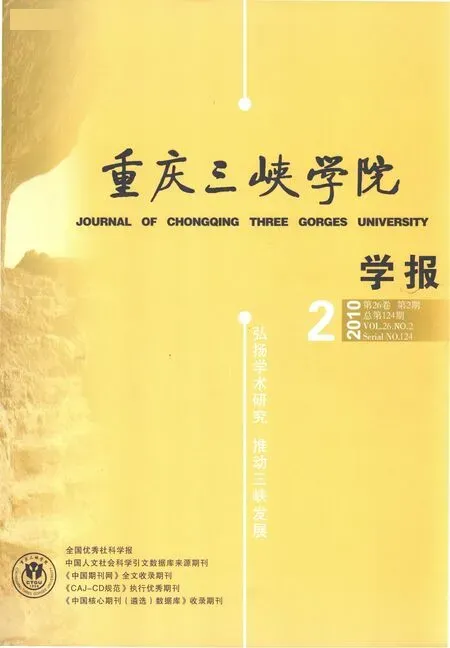论“人面桃花”的文化意蕴
赵长杰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论“人面桃花”的文化意蕴
赵长杰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人面桃花的故事屡见明清小说、戏曲当中,其源出自唐诗《题都城南庄》,作者崔护。这个动人的故事得以长期流传和搬演,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其二,文学形式的演进规律和商贾娱乐文化的推动。
《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文化意蕴
张爱玲散文《爱》因其洗练文笔展示的凄美爱情,感动了时空隧道里无数个你我。痴男怨女的缕缕情思、人世沧桑的戚戚悲剧被其表现得酣畅淋漓。随着阅历的增长,发现感动今人的故事和情思一样感动过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甚至创作出比当代更著名的文学作品。将张爱玲桃树偶遇的故事向上追溯,发现这是一个悠久的文学母题,被神州大地无数文人雅士和民间艺人反复吟咏歌颂,甚至搬演到戏剧舞台,演绎了爱情画廊里又一出诗意的绮丽与哀婉。翻检历代的“人面桃花”故事,发现这一经典文学语境得以延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二,文学形式的演进规律和商贾娱乐文化的推动。
一、“人面桃花”的本事源流
(一)“人面桃花”故事的渊薮
据文献记载,人面桃花的故事初现于中唐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如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1](4148)显然,诗人用一瓣纤巧而敏感的心香吟咏了物是人非的缺失和遗憾。这是继初唐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1](1183)喟叹时空无极生命有限的哲思。刘希夷“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1](885)感慨自然永恒人世代谢的规律之后的又一篇讴歌“恒与变”的诗思旋律。较之前两篇歌行,这首七绝表达的情感更为集中,诗歌背后潜伏的男女主人公也丰盈了这个故事的意蕴和情感。正是如此,中晚唐孟棨的《本事诗》将这个故事大肆渲染了一番,记载如下:大唐中和年间,博陵崔护,姿质甚美,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寂若无人,叩门求饮,一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伫,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卷盼而归,嗣後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题《题都城南庄》诗於左扉,後数日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叩门问之,有老父哭曰:“君杀吾女。”并叙其由来,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以女归之。[2](13)某种程度上,《本事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诗话开山之作,记录了最为后人称道的诗人掌故和奇闻逸事。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经孟棨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但扩充了内容,增加了细节,而且情节曲折,首尾齐全。桃树下春风里一见钟情的故事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
(二)“人面桃花”故事的流变
这样一个流光溢彩的爱情故事,一经形成,遂成为文苑词坛的风流韵事,广泛流播并且历久不衰。宋金元时期,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竞相模写这个故事。宋官本杂剧段数有《崔护六么》、《崔护逍遥乐》(见周密《武林旧事》),戏文有《崔护觅水》(见《宦门子弟错立身》),话本有《崔护觅水》(见罗烨《醉翁谈录》),诸宫调有《崔护谒浆》(见《董解元西厢记》)。元杂剧有白朴和尚仲贤的同名杂剧《崔护谒浆》(见钟嗣成《录鬼簿》),可惜,这些作品都已经散佚。到了明清时期,这种人面桃花的创作又掀起新的高潮,仅传奇就有《题门记》、《登楼记》、金怀玉《桃花记》等几种,杂剧也有凌蒙初《颠倒姻缘》、舒位《人面桃花》等。以上这些剧本均已失传(仅个别剧本存有残曲)。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孟称舜的杂剧《桃花人面》和清代曹锡赫的杂剧《桃花吟》,和无名氏的华剧《金碗钗》。[8]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人面桃花剧本当中,大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类剧本基本恪守孟棨《本事诗》的规模,只写崔护求饮,题诗,女子相思而死,崔护复至,哭祝,女子复生诸情节,而不添枝加叶。今存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即是如此。另一类创作则突破《本事诗》的情节,增添另外的人物与故事,与崔护觅水遇女子之事结合在一起。无名氏的剧本《金碗钗》即是如此。[8]
二、“人面桃花”的文化成因
(一)追溯桃花人面的原型
占尽春光的簇簇桃花第一次被纳入文学殿堂是《诗经·周南·桃夭》,其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歌用妖娆绚烂的朵朵桃花起兴,引出所咏对象——即将出阁的新娘。风光无限的簇簇桃花把打扮漂亮的新娘映衬得万千旖旎。用文学意象的观点来审视这首小诗,无疑,桃花是这首诗的意象。在古典文论的众多范畴里,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周易·系辞》。其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5](249)由此可见,意象的古义是“表意之象”,这个“意”是圣人才能发现的,所以意象的古义是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明确提出了“意象”这一概念和“象征”这一创造“意象”的方法。西方现代派的意象理论也认为审美意象的表现特征是象征性。也许新娘出嫁的时候,桃花并没有怒放,但是通过诗人的虚构和想象,就为读者营造了一种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审美效果。《诗经·周南·桃夭》里的桃花与人面就完全是一种象征与比附,灼灼其华的桃花就是在隐喻年轻女子的美貌与妖娆。换言之,桃花即人面,人面即桃花。
孟称舜的杂剧作品《桃花人面》,女主角芳名叶蓁儿,作者细腻的文笔已经把女主角刻画得非常漂亮,有趣的是,女主角的名字激活了我们对《桃夭》诗的又一次体悟和思索,叶蓁儿就是从“其叶蓁蓁”化用而来,“蓁蓁”意为草木茂盛的样子,叶蓁儿这个名字的选择突出了作者对年轻生命的礼赞和讴歌,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和勃发。尽管女主角有着如花的笑靥似玉的芳名,但是她却难逃命运的罹难,不堪忍受相思的痛苦,泪尽而亡。在这个杂剧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相遇时的一间钟情,离别后的无尽相思,以及见到题诗后的绝望而死,这是一个渐次由乐到悲的情感行进轨迹。此时,再来回味一下崔护的人面桃花诗。次年春天南庄再访,桃花依旧,人面未睹,姑娘也许远嫁他乡,也许生病而亡,无数个也许让他留下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凄凉感慨。当姑娘看到这首诗的时候,热烈的渴望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冻结了她对爱情的希望与执着。无论是崔护还是叶蓁儿,都把对方看作是春天里一株怒放的桃花,没有性别的界限,都是一种律动生命和美好爱情的象征。
(二)“人面桃花”创作热的文化成因
人面桃花的故事经久演绎,以至于成为爱情文学的一个经典母题,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由诗词到小说戏曲的衍变以及商贾娱乐文化的推动。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认为个人无意识还有赖更深一层、由先天遗传的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或称“原始意象”。原型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7](355)当崔护第一次写出人面桃花背后悲喜交加的时候,是一种个体无意识,当这种个体无意识激起古代无数文人的共鸣和同感的时候,他们甚至突破《本事诗》里的故事框架,创作出情节更为复杂,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的小说或者戏曲。这样就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是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沉重的封建伦理枷锁禁锢了古代青年男女在爱情王国里的自由,因此中国古代文苑才出现数量众多的一见钟情的恋情模式。《西厢记》《牡丹亭》都是如此,佛殿前、后院里男女青年不期而遇回眸一笑,顿时让他们如痴如醉难以割舍。在礼教如此森严的古代社会,对于幽闭闺阁的女子,偶遇的男人已经超越实体,变成了神灵,具有高不可攀的地位,因而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产生绝对依附感。孟称舜《人面桃花》就将这种爱情模式最终定型,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学典型。解读戏曲之后,再回眸宋词海洋里的朵朵“桃花”,就不难明白这一古老的桃花语境在不断地生发和延伸出固有的情感意蕴和审美效果。晏殊《清平乐》中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3](92)蔡伸《苏武曼》中的“忆旧游,邃馆朱扉,小园香径,尚想桃花人面。”[3](1006);陆游《钗头凤》中的“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3](1585)可见,“桃花人面”的精神原型早已根植于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每一声关于“桃花人面”的吟唱都触动了中国文人集体无意识的那根心弦,发出对历史积淀和内心体验的回音。
如果说中国文人的“人面桃花”情结是让这个动人故事得以延续的内因,那么文学形式的演进规律和商贾娱乐文化的推动就是让其延续的外因和条件。崔护觅水的故事原本是一个唐诗题材,在盛唐光辉的烛照下,这首诗或者桃花人面的意境就步履蹒跚地跃入了词林、小说、戏曲的天地。较之唐诗,宋词更善于抒情。宋代的话本小说,标志着中国的叙事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加上风云两宋,经济繁荣都市林立,为文人创作话本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人面桃花的故事在宋代就见诸很多话本小说,如《崔护觅水》。对于这个故事,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白朴和尚仲贤都创作过《崔护谒浆》的剧本,但现在已经失传。明末清初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就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杂剧剧本。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和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末清初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文学领域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晚明受到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的影响,“主情”是这个阶段文学创作的主流色调,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个典型,情能够使人死,情亦能使人死而复生,他的这种创作理念很难说与“桃花人面”的情境没有干系。同时,这是一个商业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样就造成了这一题材的广泛传播,读者和观众对这个故事的喜好又促成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同时在商业利润的冲击下,书贾射利,就在崔护觅水的基础上继续添枝加叶,增加复杂的人物和情节,于是这个故事就越来越曲折热闹。历朝历代文人都把“桃花人面”这个原型打扮得精美绝伦,让其芳姿在艺术殿堂里绽放光彩。
综上所述,历代文人对“桃花人面”的歌咏是中国文人渴望美好爱情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在精神上为广大读者和观众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堡垒,在这里可以慰藉受伤的心灵,可以憧憬美好的邂逅。一抹淡淡忧伤笼罩的凄美爱情,几缕绵绵思念氤氲的生命思索,就这样在历史的风烟里不断被重写和刷新。
[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孟 著.李学颖标点.本事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王充.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赵俊.“人面桃花”的衍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89-92.
A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Fair Face and Peach Blossom”
ZHAO Chang-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
The story of “the Fair Face and the Peach Blossom” often found in the fiction and dram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originates from the Tang Dynasty poem “South Side of the Capital City” by Cui Hu. The main reasons of this moving literary story can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adaptions lie in the Chinese literati’s love for the story of “the Fair Face and Peach Blossom”, the law of literary forms evolu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culture.
“South Side of the Capital City”; “the Fair Face and the Peach Blossom”; cultural implication
I207
A
1009-8135(2010)02-0088-03
2009-11-22
赵长杰(1986-),男,陕西汉中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主要研究中国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张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