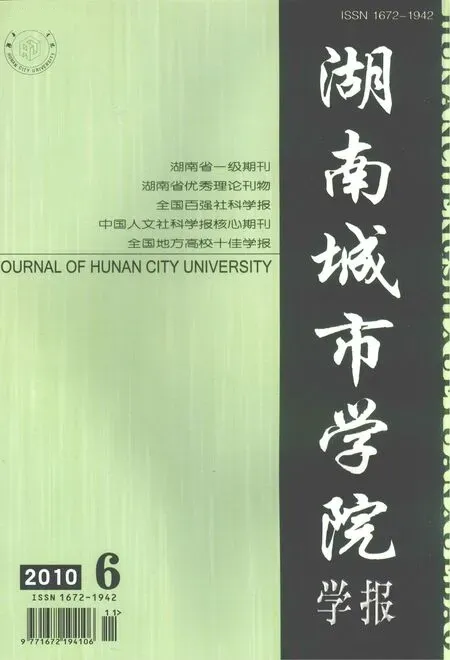梅山双璧—陶澍、魏源经世思想研究
周小喜,肖立生
陶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生于安化县小淹镇,字子霖,号云汀,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魏源小陶澍15岁,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生于隆回县金潭村,原名远达,字默深,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从年龄辈分上论,陶澍是长辈,曾溯资江而上拜访过魏源的祖父魏志顺,向魏家借过进京赶考的盘缠。魏源非常崇敬这位长辈,一生深受其影响,他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1]对于魏源这个小老乡,陶澍亦器重有加,道光五年(1825年),陶澍由安徽调江苏巡抚,他“重魏文章经济之学,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2]延魏源入幕府,这对于科举失利而又满怀经世之志的魏源来说,自然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此后,直到陶澍去世,二人共事十数载,共同成就了震惊朝野的大事业。陶澍和魏源同为古梅山人,一个是封疆大臣,一个是饱读诗书却尚未正式跻身仕途的读书人,他们走到一起并作出超凡事功,有世交的原因,也因了梅山文化古朴的民风带给他们的相似的性格和做派:笃实,勇于任事。他们的思想渊源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一、提倡实学,通经致用
陶魏二人继承清初顾炎武、王夫之实学思想而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陶澍说:“夫学何以实?盖必从‘衣锦尚絅’之始,以驯致于‘不见是而无闷’之域,而后读古圣贤之书,恍若謦暩接而声与通。”[3]陶澍借经学阐述了实学的内在含义,指出实学乃与实际紧密联系之学,不以追求奢华、名利为目的,提倡“以实学为教”。魏源对实学的理解与陶澍不谋而合,他有一联这样写道:“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非常精炼地概括了实学的含义。由此可见,陶魏二人强调的实学都是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即先儒一贯奉行的通经致用。
陶魏秉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研习经学的微言大义。他们对《易经》的一个共同理解就是阴阳互动的变异思想,而这一变易思想恰是他们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石。“易之道,变化之谓也。变化者,刚柔相推之谓也。”[3]“天不能有阳而无阴,世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阴阳齐等,君子小人势均,则将迭为消长。”[3]“一阴一阳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阳以抑阴;一治一乱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拨乱以反正。”[1]他们以经为本,重视通经。魏源认为“万事莫不有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1]陶澍认为经就是本,“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又说:“即末可以知本,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3]从实学思想出发,陶魏二人必然反对空谈,指斥一切不切实际的社会现象。陶澍指出,无实学者,无用于社会。他说:“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以哉!”[3]他批评“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的现象,更痛斥那些“铢心肾、镂肝肺以搜之,穷日夜、限晷刻以迫之,废寝食、忘本业以耽之”之人为“诗役”。[3]魏源则一针见血地批判那些满口王道实却没有实际才能之徒:“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1]
不切实际的空谈无用,不务实的科举制度同样无用。陶魏二人觉察到科举的弊端,从不同角度批判科举制度的腐朽。陶澍指出,自明代八股取士以来,读书人被束缚在八股的形式上,“虽有奇材异能之士,束身八比,童而习之,皓首不能尽”,皓首穷经,无暇顾及其他。然而,国家造就人才,“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之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3]陶澍指出了科举与选才的矛盾,八股取士制度与实际人才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魏源批评八股是“画饼”,是“雕虫”。他说:“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1]指出科举选士是造成国家无可用之才的根本原因。
二、强烈的爱国经世之志
“陶子生长资江之滨,其山……梅山……实宇宙之奥区,冠盖所不至,红尘所不入。陶子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3]“源家资、邵二水之会,是为上游,距安化不百里。方舟朝发,夕宿石门潭,即宫保少时读书之所。”[1]陶魏二人同处资水之滨,陶居资水中游,魏居资水上游,喝资江之水长大,耳濡目染梅山风物民情。他们受的教育是相同的,他们承袭的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是王夫之等人爱国主义思想和济世救民的抱负。陶魏二人在少年时代都曾留下不凡的言辞。十二三岁的陶澍为家乡新建的油榨房拟联为“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4]魏源九岁以“腹内孕乾坤”巧对考官的“杯中含太极”,表现出他们相同的少年壮志。正是因为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爱国情怀,陶魏二人所到之处,都能洞悉社会的种种弊端,探究产生这些弊端的深层原因,并力求有弊即改,有利必兴。关系清廷经济命脉的东南三政,无一不是在陶澍的倡议和主持下得以实行并取得成功的,陶澍因此而成为一代名臣;这些改革魏源都身预其中,并且是得力助手,不可或缺,魏源也因此着称于世,并为以后的更深层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在封建社会,爱国和忠君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这在陶魏二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道光帝临朝,看中陶澍的才干和为人,先于元年擢升陶澍为安徽布政使,再于三年擢升为安徽巡抚,后调任江苏巡抚,委以重任,十年署理两江总督兼江西巡抚,次年并兼理两淮盐政,十五年亲赐御书“印心石屋”匾额。十年间数次擢升,并把江南三大政交给陶澍一人管理,道光皇帝对陶澍的信任与依赖朝野皆知。陶澍则但求能为朝廷为国家贡献毕生精力,“以天心为心,以民事为事”。[5]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一生酬劳,最终逝于任上。爱国忠君,对于仕途不畅的魏源来说也是如此,虽屡经科场失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魏源的经世救民之志。身为僚属,他积极参与陶澍主持的各项改革,为其出谋划策,运笔修文,跑前跑后,鼎力相助。如果说陶澍的爱国忠君主要表现在行动和成果上,那么,对于长期身处幕后的魏源来说,则更多的表现在著书言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无一不打上其爱国强国思想的烙印。
三、深谙民瘼,关心民间疾苦
陶魏二人生于梅山,长于资江之滨,都是成年之后才离家入京,较多接触下层人民,能深入体会民间疾苦,对于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有着最强烈的感触,这种经历也使他们敢于批判现实,揭露黑暗。陶澍从北京经直隶、山东,往来于淮、扬及江、镇、苏、常时,所到之处,观察民风体恤民情,把沿途淳朴的民风和喜人的瑞雪上奏皇上,也把社会弊端、腐败的吏治如实地上达天听。“今之州、县,疲精于奔走、承应之中,救过于纸札、文书之上。十人而聚,无语田桑者也;百人而聚,无语教化者焉。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5]“疲玩因循,遂成累痼。即稍知自爱者,亦无以自拔。吏治之靡,多由于此。”[5]同样,魏源以其特有的敏感来观察世事,站在农民群体的角度来批判现实。魏源第一次北上途经河南,正逢水灾过后。他作诗描写了沿途农民的悲惨景况:“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1]荞麦新种,麦花初放,饥饿的人们饥不择食,明知吃麦花如饮鸩止渴,却还重蹈先人覆辙。诗中表达了魏源对灾后农民苦难生活的深切的同情。
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现实,陶澍和魏源没有退缩,而是实践自己经世致用的一贯主张,兴利除弊,发愤图强。作为封疆大臣,陶澍一方面向道光帝陈述自己改革弊政的决心,一方面积极投身改革浪潮,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四十年如一日;魏源在陶澍的影响和带动下,也得偿夙志:“友天下士,谋救时方”,“功名待寄凌烟阁,忧乐常存报国心”。[1]
四、重践履,事必躬亲
陶澍提倡实学,其目的在于“有实行”“有实用”,要把所学用于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实学,为社会政治服务。这一点,魏源也一样。自入陶澍幕府以后,魏源帮助陶澍除弊兴利,行海运,改票盐,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和检验。
陶澍是实干家,有才有能,他用他的实功向世人证实了他的超凡才能。他任四川兵备道不到一年,就被誉为“四川第一”,得到四川总督蒋攸铦、安徽巡抚孙尔准等朝廷大员的推举,成为道光帝旻宁即位后看中的第一个人才,委之以重任,并自始至终倚重于他。陶澍的成功,来源于他在实学思想指导下的躬行实践。陶澍从政40年,“于海观其一,于湖观其三。于江、汉,于淮,皆穷源而竟其委。于五岳,则登岱望华,遥揖恒、嵩,惟衡在桑梓,犹未一观。而于禹贡之九州岛,则足迹皆已及之,不止于身行万里,半天下矣”。[3]没有对河海的实地考察和海运现场的亲临督导,就没有漕粮海运的划时代成功;没有对淮盐积弊零距离的深切了解,就没有一系列章程的出台,就没有道光时期淮盐裕课的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魏源与陶澍志同道合,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魏源尤其重视实践,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准绳。他有一段著名论断:“‘及之而后艰,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因之,魏源特别重视知识的来源,理论的依据。与陶澍共事的十余年中,他跟随左右勘测实地,考察积弊,并对来自现实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为海运、盐务等拟写出一篇篇理论性的文章,为东南三大政作出理论性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既重践履,魏源一生尤喜游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这一年中,魏源游岭南、澳门、香港,北归途中,又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七省,“往返八千里”,这与陶澍何其相似。
五、重人才,不拘一格
在改革的艰难征途中,陶魏二人都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他们的人才观各有侧重。
书院作为古代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之一。在陶澍的诗文奏折中,与书院、科考有关的文章颇多。他说:“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谓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3]在政务处理中,陶澍强调 “敦行实践,得人共理”,[5]多次提到“以得人为第一要务”之类的话语,“防弊之法,不患立法之不善,而患行法之无人”。[5]在用人方面,陶澍提倡不拘一途,人尽其才,“各适其宜”。他说:“惟是地方情况不一,人材优绌不齐,必须因材任使,方克收治理之效,免致贻误地方。”[5]正因为陶澍注重选拔人培养人,他身边才聚集了那么多的经世之才,同僚中有贺长龄、王鼎、宝兴以及经陶澍亲自上奏得到批准留用的降调道员王凤生等人,幕府中更有如魏源、包世臣这样忠心耿耿而又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身后还聚集了如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一大批湘籍近代优秀人才。
在人才问题上,魏源认为:“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1]因此,他更多的是敦请统治者创设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宽松合理的环境,希望统治者常以“谦卑育物为心”,求贤纳士,广招人才。对沿袭已久的社会弊端,魏源进行了批评:“古之得人家国者,先得其贤才”,[1]而今世则出现“人才如蛰墐户,湫闭槁窳,所至而百物受其怆悢”的怪相,魏源把它列为“六荒”之四,即“人材嵬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贪图享乐,不知居安思危,提醒人们牢记《诗经·蟋蟀》之训导:“无已太康”“好乐无荒”。[1]当然,魏源在实际工作中一样强调得人,他说:“夫集事固在于谋,而成事必在于断,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1]这一点与陶澍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澍的政治生涯中,还有一个人也特别强调得人、用人,这人就是道光皇帝旻宁。道光帝看重陶澍,称赞陶澍“操守好,办事认真”“学问、人品俱好”,对陶澍寄予厚望,在颁给陶澍的谕旨中多次提到“得人”的问题,如在道光十年被擢升为两江总督时,旻宁就告诫陶澍,三省责任重大,非同一般,“当今之要,首在得人”。[5]
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既有其巧合的因素,也有定性。所幸的是,两江总督陶澍之于道光帝,魏源之于陶澍,均可谓实现了他们一致要求的“得人”主张,彼此都遇到了知遇之人。“知遇感殊深,石屋印心,牖北垂询商大计。”[1]这是道光帝和陶澍关系的写照。从选中陶澍作为江南三省的全权长官这一点看,道光帝旻宁着实高明,得到了可信可用之人,不同凡响;陶澍之所以能顺利地实行改革,与道光帝这一强大的后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陶澍器重魏源,凡事与魏源商量,听取魏源的意见,并把身后之事交给魏源,而魏源竭尽全力帮助陶澍,促成清代诸多改革的成功,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
六、超凡的才识和胆识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陶魏二人与其他封建官僚士大夫们的截然不同。
第一,陶魏一生忠君、爱国、恤民。因此,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疾苦,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从这一层面出发,在众人对漕粮海运疑虑重重举步维艰之时,陶澍不计个人得失,力主海运,并毅然决然地挑起重担,与贺长龄等人主持海运。魏源则始终站在陶、贺这边,是他们最得力的帮手和助推器。
第二,他们勇于任事,不惧怕恶势力。陶澍在历史上以清官着称,两袖清风,靠自己的努力博得功名,没有可炫耀的家世,更没有复杂的社会网,这些造就了他一贯的敢做敢当、不瞻前顾后的行事作风,也是他在两江总督任上能和魏源等人取得辉煌的改革成就的前提条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陶魏二人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不拘泥于成法,眼光深邃,能突破时代的局限,在思想上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漕粮海运,这在有清一代是第一次,陶澍主持实行了,并成功了;淮北票盐制,陶澍大量依靠商人的力量,遵循商品规律,并引进竞争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两项的任何一项搁在循规蹈矩的封建官僚手中,都会被视为烫手的山芋,避之唯恐不及。改革成法,依靠商人,把商业资本引入到国家经济活动中来,这在中国亦不多见,它是陶澍的近代意识的大胆萌生。
分析起来,陶澍的经济思想当是清中叶最先进最前卫的思想,而在改革创新路上比他走得更远、把开拓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的恰是他的晚辈或僚属魏源。陶澍去世后的第二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主义的铁蹄残忍地践踏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不再是统一的主权国家。魏源在悲愤中深深地思索这场灾难的原因,在改革成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前不见古人的壮举,是振聋发聩的口号,是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引领中国人做深层次的思考。在开拓创新上,魏源比陶澍胜出一筹,他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开始由传统经世致用向近代社会思潮转型。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陶澍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与前期的改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时代的巨变向魏源提出了新的严峻课题,爱国主义与改革经世思想的日积月累,促成魏源睁眼看世界,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可不谓非陶澍之功。设想,如果假陶澍以天年,谁能否认他不和魏源一道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呢?
七、漕、盐改革崭露近代意识
道光五年的漕粮海运和十一年至十九年的盐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经济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或陶澍决策,魏源运笔,或魏源献策,陶澍采纳,二人密切配合,合力完成,他们思想一致,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容分割。有学者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可以说,道光时期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所有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领导,陶、魏共同设计、执行。没有陶澍,魏源的改革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魏源主要是思想家,则陶澍主要是实干家;魏源是参谋长,陶澍则是司令员。”[4]这是非常中肯的论断。漕粮海运在清代历史上属首次,票盐制的实行也具开拓性,二者中有一个共同的举措就是利用商人力量,把商业资本引进国家经济活动之中,使商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有关陶澍、魏源海运、票盐的其他内容已有很多研究者作过比较全面的阐述,这里只就二人经济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近代意识做一番简单的梳理。
近代意识,在本文的语境中,按笔者的理解,就是在还未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已经具有的一些包含或接近近代社会特征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相对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具有超前性、前瞻性。具体到陶澍、魏源二人身上,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在经济改革中显露的近代商品意识。
(一)正本清源,挖掘漕、盐积弊的根源
清源治源,以端痼弊,这是陶魏二人历来的主张。陶澍说“清治其源,以端吏治事”,[5]魏源说“正其原,顺而循,补其末,逆其棼”,“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裕课必由于轻本,而绌课必由于重赋”。[1]事实上,只有找到引发弊端的根本原因,才能治本,除弊兴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陶魏正本清源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论证漕粮海运和改行票盐的可行性。“渎告灾,非海无由也,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1]“当此河道梗阻,般剥维难。臣等仰体宵旰焦劳,再四图维,舍海运别无良策。”根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提议,陶澍率领一群人等通过查对历史、实地勘察、反复商议论证达成一致意见:海运可以试行。从道光五年海运之事被提上议程到海运告竣,陶澍频繁向道光帝上奏,内容包括筹议海运、沿淮沿河建仓、海运陆续应办事宜、海运图说、收买沙船余米等细节问题,进一步为海运可行提供依据,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海运顺利进行。对改行票盐也是如此,他们深入盐场、了解盐商、分析商情,制定出系列章程。其二,从根本上除弊兴利。以盐务为例。在陶澍的奏折中,有关盐法是最多的。陶澍多年任职苏皖,对淮鹾积弊早有所察,及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更对其了如指掌。陶澍认为成本高、浮费多是引起诸如售价昂、私枭起、盐质差等种种弊端的罪魁,因而提出“弊起于商而利不在商,商既自敝而课因以敝”的观点,提出“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的思路。[1]其次,重商、用商,把商业资本纳入国家经济活动。
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位低下,历来都被视为“四民”之末。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明清,商人力量已经不容忽视,陶魏发现了这股力量,重视商人,并不失时机地借用商人这股力量完成了漕运、盐务、河工三大政。陶魏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他们富有前瞻性,敢于并善于做时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二)陶魏二人的重商思想的主要表现
第一,肯定商人。试行海运前,陶魏充分肯定商人的技术力量,认为他们熟悉海道,技术过硬,能胜任南粮北运;海运进行中,充分肯定商人的爱国热忱,高度评价他们的积极性,夸赞他们“商情感奋”“子来恐后”。
第二,体恤商人。在海运实施过程中,主要措施是:给沙船定额耗米;国库调银20万两,以时价买回沙船余米,使其迅速返回以便二次接运;发给商船运米水脚费、水手水脚余米、纤夫拉挽工价;因事故发生导致漕粮短少、霉变及松舱等,豁免赔补;商船可带一成土宜;船到天津准许北上奉天装豆等。在盐务改革方面,一是裁减浮费以舒商力,减轻商人负担。例如裁减盐政衙门改归总督管理,所省经费岁银16万两有零。二是加斤减价。为了扶植商力,对抗私贩,允许商人每引定额364斤外加盐20斤,并按例给予暑月卤耗16斤,这36斤均免课。三是停止加带积引。积引是指壬辰年未运纲盐。在盐引畅销之前,因“商人止此一副资本,力难课纳两纲”,[5]陶澍为此事三次上奏,要求待盐引畅销后,再议加带。
第三,保护商人利益。为了保护商人利益使不受损,在海运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两项切实可行的措施:配备兵力驻扎畲山,督率防护,协助处理突发事件;在商船所经海面,沿海设立哨所巡防护送,夜间在岛屿处挂号灯,白天竖号旗,使商船不致迷失方向。考虑到票盐“多系民人贩卖,资本无多”的现状,在淮北滞岸票盐试行章程里,特列严禁官吏兵丁索取一条,一经发觉或举报,“严行究办”。[5]
第四,引进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为鼓励商人,海运中实行奖励商船的办法:“运米一万石至五万石以上,均经奏请奖叙;其运米一万石以下者,在外赏给匾额。”[5]在盐务改革中则广泛招商,培植商人势力,规定“凡行销淮盐之处,一体招徕民商”,[5]以此更多地吸收商人参加运转,加大销售力度,提高国课,以改变广大民众“不知盐味”的现状。
魏源在《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中写道:“东南大计,无如漕、盐,二百载来,文法委曲烦重,致利不归下,不归上,而尽归中饱,官民交困。间有讲求刷剔,芟薙更革者,则中饱蠹嗜之人哄起而交持之。”[1]陶澍在当时情况下能力排万难,在海运、淮盐政务上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与魏源等一大批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道光六年海运实施后,次年因运河通畅而停止海运,但在道光八年魏源仍代陶澍作《复蒋中堂论南漕书》,指出海运不由内河,不经层饱,“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为救弊补偏则不足,为一劳永逸则有余”,[1]提出永行海运的主张。陶澍去世后,魏源没有松懈下来,在盐政问题上继续陶澍的未竟事业,进一步深入探讨减价敌私、裁汰浮费之法。魏源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陶澍对魏源深远的影响,共事十余载,这些影响是全面的,包括思想上的、性格上的、行事风格上的、工作方法上的;另一方面,完全可以看出魏源对陶澍的赞同、钦佩之情。二人志同道合,共同为清代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是历史的佳话,也是湖南的佳话,更是梅山的佳话。
陶澍和魏源同为梅山之子,他们身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由于魏源仕途上的坎坷经历和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魏源与陶澍又存在许多差异。陶澍25岁中进士,历任编修、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魏源于 52岁中进士,同年授江苏东台知县,后迁高邮知州,第二年因“迟误驿报”被革职。与陶澍比较,魏源仕途可谓艰难坎坷。陶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建功卓著的封疆大吏,被赞为“一代清官”;魏源恰好跨越了古代和近代的分水岭,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才,在内忧外患交困、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被世人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无论是两江总督还是幕僚,也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知县知州,是“一代清官”还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陶澍和魏源,他们都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他们的急公为国、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勇于变革的思想光照万代。如果说陶澍引领了清中叶中国古代的经世之风,那么,魏源则引领了晚清中国近代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全新风尚。陶澍和魏源,堪称梅山双璧,是梅山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梅山的骄傲。
[1] 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 2004.
[2] 黄丽镛.魏源年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3] 陶澍.陶澍集(下)[M].长沙:岳麓书社, 1998.
[4] 陶用舒.陶澍评传(修订版)[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 陶澍.陶澍集(上)[M].长沙:岳麓书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