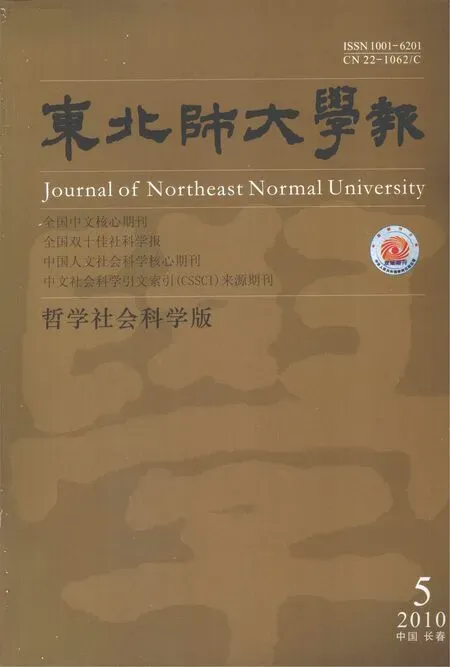“不虔诚的同盟”:16世纪法土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
宋保军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
“不虔诚的同盟”:16世纪法土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改变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劣势,以及获得商业利益,1536年,冠以“笃信王”称谓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结为同盟。法土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维持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及其政治多元化特性,促进了欧洲外交观念的变化和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的崩溃,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新教改革的成功和法国在东地中海经济地位的上升。
“不虔诚的同盟”;法兰西斯一世;法土同盟;均势;国家利益
法土同盟(即法国-土耳其同盟)是16世纪欧洲外交史上的重要同盟。在基督教欧洲遭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情况下[1]210,冠以“笃信王”称谓的法国国王[2]69-70,于1536年同土耳其苏丹签订条约,正式结盟,共同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当时有人指责法土同盟是“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结合”,后来一些学者也称它为“不虔诚的同盟”①参见L.S.Stavrianos,TheBalkanssince1453,NewYork:Rinehart&Company,Inc.1958,p.74.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1543年对法作战的宣言中谴责法土同盟,见HerryVIII,Forasmocheasbycredyblemeanesithathbenedeclaredtothekingsmaiestie……,London,1543,p.1.,但法国却一直坚持这一同盟,并维持法土友好关系长达几百年之久。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斗争与冲突,而对基督教世界面临土耳其严重威胁之时出现的这一“不虔诚的同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少数论及法土同盟的论著,也未能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本文试从国际关系和经济利益等方面分析法土同盟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以及法土同盟对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外交观念、新教改革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一
法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继位时,庄严地宣称要抗击异教的土耳其人。这位“笃信王”在1519年同查理五世竞争神圣罗马帝国帝位时也曾宣称,如果他当选,就决定保护基督教世界不受土耳其人侵犯。然而,后来他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共同对抗查理五世。法兰西斯的言行反差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地缘政治方面,法国试图打破哈布斯堡帝国的三面包围。15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联姻和继承等方式,不断扩大领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通过与西班牙联姻为西班牙、尼德兰、勃艮第和奥地利的联合奠定了基础。到查理五世时,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包括除法国和北欧、东南欧以外的绝大部分欧洲大陆,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法国。“在他们[法国国王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3]31“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4]15。法兰西斯到处寻找盟友,试图突破哈布斯堡帝国包围,至于外交政策在宗教上是否“虔诚”就变得次要了。因此,“法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抵抗哈布斯堡的庞大力量,手段是通过同时利用它的其他敌人——德意志人、土耳其人,并在其最脆弱的时候尽可能强烈地打击它”[5]72。
外交方面,法国在同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对抗中处于劣势。15、16世纪之交,法国没有强大而系统的外交机构,“也没有任何连贯的外交政策”[6]115。到1520年时,法兰西斯也只有在罗马和威尼斯的两个常驻大使为他服务。而且,由于没有处理好同热那亚的关系,本来与法国结盟并可以使其控制西地中海的安德里亚·多里亚和他强大的热那亚舰队投向查理五世。这是法国外交的一大失败。与之相对比,“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之前,斐迪南领导下的西班牙已开始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和培养富有经验的外交官群体”[6]119,并与罗马、威尼斯、奥地利、英格兰等建立了经常性的外交联系。查理当选皇帝后,发展了西班牙的外交优势。他于1521年和教皇利奥十世签订秘密合约;于同年和第二年两次与亨利八世亲自会谈并签订协议,使基督教世界诸如英格兰、教皇国这样的次等强国倒向自己一边。他因此构建了围困法国的外交体系,加强了他本来已经强有力的地位。通过对比,可见法国外交上的明显劣势。为了扭转这种劣势,法国从1525年起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谋求得到域外国家土耳其的援助。
军事方面的劣势也促使法国寻求盟友对抗哈布斯堡帝国。法国不仅在军事技术上无法与西班牙长矛和火绳枪相配合的战术相比[5]77-78,而且在同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作战过程中,接连遭受军事失败。1494年法军首次侵入意大利,但1495年在福尔诺沃同以西班牙为首的神圣同盟军队作战中,遭到失败;1503年法军在加里利亚诺河畔一役中又败于西班牙军队;1522年4月,法军在比科卡战中失利;1525年又在帕维亚惨败;1529年6月在兰德里阿诺战败;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法军在战争对抗上的劣势。为了扭转这种劣势,法国迫切需要找到强大的盟友,而当时欧洲唯一能够与哈布斯堡帝国对抗的就是奥斯曼土耳其。
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法国与土耳其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家财政方面,尽管法王在征税方面比查理五世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后者控制着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尼德兰和意大利,可以从这两个地区和卡斯蒂尔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查理可以从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金融家族——如富格尔家族那里获得巨额借款,并从广阔的殖民地获得金银[7]。在1503-1560年间,西班牙公开从美洲平均年输入贵金属约22万杜卡特[5]55。法国在财政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为了与查理对抗,法国必须寻找更多的财源。而当时威尼斯等国在东地中海地区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促使法国关注东方。法国希望在苏丹那里获得可与威尼斯人相比的贸易特权,为本国的葡萄酒、纺织品和金属器皿开拓市场,分享东地中海贸易的利益。
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法国国王希望同土耳其结盟。而当时的政治现实与外交先例也允许法国这样做。一方面,土耳其同哈布斯堡的冲突为法土结盟提供了现实条件。“土耳其人在1529-1530年以前许久……便进入了这场斗争。甚至在此以前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巴尔干半岛诸国,在中欧,尤其在西方世界的财富仍然依靠于它的地中海——就已经是一个政治现实了。”[8]451土耳其军队在16世纪20年代就控制匈牙利并推进到维也纳城下,在地中海上洗劫西班牙(1529)和意大利(1534)沿海,同哈布斯堡帝国的直接冲突开始了。这个政治现实使法兰西斯看到了战胜哈布斯堡帝国的希望,他因此积极接近苏丹。“这样,法国和土耳其的同盟便必然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产生出来。法国和土耳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室。”[9]325另一方面,先前基督教国家同土耳其苏丹的外交联系也为法国提供了先例。15世纪,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曾同土耳其苏丹进行外交联系,对抗同属基督教世界的商业对手和政治敌人。例如,“米兰、费拉拉、曼图亚和佛罗伦萨曾在1497年联合起来收买土耳其人,帮助它们进攻威尼斯”[10]38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支持这件事。同样,威尼斯和西班牙之间的斗争也争相借用土耳其的力量[11]91-92,甚至教皇为了得到土耳其苏丹的报酬而同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争相囚禁苏丹反叛的弟弟[12]120。因此可以说,法土结盟,也是有先例可循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事”[11]92。
总之,为了能够同哈布斯堡帝国对抗,法国千方百计地扭转自己在地缘政治、外交、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劣势,并在当时文明冲突的政治现实和先前基督教国家外交先例的基础上,积极接近土耳其,试图建立跨文明、跨宗教、跨意识形态的同盟。
二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法国迫切需要寻找盟友来扭转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劣势,这种迫切性在1525年法兰西斯在帕维亚战败被俘时达到了极点。法国认为土耳其人是当时唯一能够抗击哈布斯堡帝国、保护欧洲国家存在的力量。为了拯救自己,尽快同土耳其结盟,法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在法国的第一个特使在波斯尼亚被杀、所有的文件被盗之后,1525年12月又派出了第二个使者——简·富兰志潘尼。他把信件藏于鞋底,顺利到达伊斯坦布尔。他告诉苏丹,如果法王接受查理提出的释放条件,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将变为“世界的统治者”[13]35。对于法国的求助,苏丹决定积极回应,因为“奥斯曼人也认为法国盟友是防止由一个国家支配欧洲的工具”[13]35。苏丹答复到:“帝王战败与被俘丝毫不足为奇。因此要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承诺:“……我不断地征服了诸省和强固难攻的堡垒。我的马昼夜不解鞍,我的刀昼夜挂在身上。……”[14]325,326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就可看做是苏丹在行动上的答复。
国际均势往往是弱国争取生存的理想和期望,并是弱国努力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4]132,法土同盟的形成就是这样。为了尽快恢复均势,法国于1526年再次派富兰志潘尼携带希望建立长期同盟关系的口头和书面指示前往土耳其。此后,法国又于1528或1529年和1532年两次派使者与土耳其谈判。这样,“两个国家,一个基督教的,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它们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打下了,……”[15]453在1535年查理五世忙于进攻突尼斯时,拉·弗赖特被法王派往土耳其提议签订正式的同盟协议。1536年2月,双方达成了正式协定——《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条约内容规定两国人民可以自由贸易与旅行、军事上相互友好、法国人在土耳其境内享有治外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宜[14]326-327[16]2-4。同时,双方还在军事合作和协同作战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这样,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法土同盟正式形成。尽管“这一时间的迟延部分是因为担心动摇基督教世界的道德价值观”[6]154,但“这项协议是使法国国王和苏丹团结起来的日益增进的友谊的明显象征”[8]682,“奠定了此后3个世纪法国-土耳其关系的基础,也奠定了法国在利凡特的商业和文化优势的基础”[6]155。通过与苏丹结盟,法兰西斯成为“放弃基督教世界对土耳其人传统态度的第一人,并使他们成为他对外政策中的一个积极伙伴”[15]451。
条约签订以后,一些虔诚天主教徒谴责法土同盟,尽管如此,“法兰西斯发现,在同奥地利王室斗争中把苏莱曼大帝作为盟友是明智的”[17]452。法兰西斯的继任者不仅重视和坚持该条约,而且还多次修约,促进双方同盟关系的发展。“亨利二世坚持他父亲同奥斯曼友好的政策,并同苏莱曼缔结一个条约,其目标是确保土耳其舰队参与反奥地利王室家族的联合行动。”[17]453苏莱曼于1566年去世,法王于1569年10月派特使克劳德·德·布格前往土耳其,同新苏丹重新签订同盟条约,使法国大使获得高于所有其他基督徒使节的优越地位,并成为在土耳其处理天主教事务的指挥者[18]68,78-80。当法国在利凡特的特权地位于16世纪80年代受到西班牙和英国的威胁时,法国大使雅克·德·热米内于1581年同苏丹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规定除威尼斯人之外的其他西方基督徒只有在法国的旗帜下才能进行贸易,并重申法国大使的优先权。1597年更新条约。1604年再次修约重申法国外交官和商人的优先权;赋予法国商人最完全可能的税收和关税豁免权;赋予法国人以耶路撒冷圣地保护者的权利[15]466-470。
法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土同盟的形成,而条约的改进和修订进一步加强了同盟关系。这一跨文明同盟的形成与巩固势必给欧洲的历史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三
在文明冲突激烈和教派斗争复杂的16世纪,法土结盟打破了宗教阵线和文明阵线的统一性,对16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外交观念、欧洲意识,乃至新教改革的进程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法土同盟维持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及其政治多元化特性。
法土同盟形成前,法国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大国均势的天平明显地倒向西班牙和哈布斯堡一方。同盟形成后,“奥斯曼人……变成欧洲国家体系整体的一部分”[12]119,并与法国配合作战,共同打击哈布斯堡帝国。例如,1536年4月,法国侵入北意大利,苏丹也应约率领大军来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并在意大利靠近奥特朗托的地方登陆;1538年,在一支法国舰队的协助下[13]36,土耳其舰队在普雷维扎海战中战胜查理五世的舰队[19]52;1543年,法国-土耳其联合舰队洗劫了勒佐和尼斯,并攻击了加泰罗尼亚海岸[20]95,土耳其海军还在法国的土伦港过冬;1551年,亨利二世向查理五世宣战,同时一支土耳其军队进攻特兰西法尼亚[21]103。由于法土同盟的联合行动,“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的集体防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22]422,查理五世不得不花费巨资修筑西班牙和意大利沿海的堡垒,并维持一支强大的常规防卫部队。在中欧,“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3]46。土耳其军队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打击和牵制[5]85-86有效地支援了法国在西欧的作战,使法国与西班牙于1559年签订《卡托-康布雷西和约》,确认了法、西之间的相对均势。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和中地中海也同哈布斯堡的军队形成对峙局面。这样,法土两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形成了16世纪前期“法国-哈布斯堡帝国-土耳其帝国(甚至还有波斯萨菲帝国)”[23]350这一大国均势状态。
法土同盟在维持欧洲国际均势的同时,还有利于维持欧洲的政治多元化特性。尽管16世纪初,尤其是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哈布斯堡家族领土的广阔使得欧洲呈现出某种统一的趋势,而“奥斯曼对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打破了哈布斯堡王朝企图重建统一的天主教欧洲的梦想”[24]122,维护了其他弱小国家的独立地位。法土同盟通过在匈牙利、地中海和西欧三条战线上同哈布斯堡家族作战,加剧了后者的内部矛盾,促使查理五世把帝国分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大部分。“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3]35到16世纪中期,欧洲形成了法国、西班牙、帝国-奥地利、土耳其等多强并立的局面,加上次等强国——英格兰、教皇国、威尼斯、丹麦、瑞典等的发展演变,欧洲长期以来的政治多元性得以保持,“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3]35。
其次,法土同盟促进了欧洲外交观念的变化。15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外交活动真正地在国家间问题上使道德分离于政治,开启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近代外交。16世纪的法土结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外交观念从中世纪外交观向近代国家利益观的转变。这个跨文明、跨宗教的联盟,“尽管招致了基督教世界的诽谤,但这仍不可抵挡地诱惑着法国的外交”[5]73。因为“法兰西斯首要关心的是作为一个自由、独立自主的统治者的生存”[25]187,扭转同哈布斯堡帝国斗争的劣势,实现大国均势。“从表面判断,这是对基督教事业的背叛,尽管这是他的行动经常给人们的印象,但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不是简单的一个无原则的冒险者。他也是从事为自由权利的斗争,就他来说,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于遥远的土耳其,而是来自于哈布斯堡皇帝自己。”[25]185-186因而,国王对国家面临的威胁做出反应,国家利益自然是外交的首要动因。从这一点出发,法土同盟尽管在宗教上“不虔诚”,但在外交和政治上还是可以理解的。此后,欧洲各国君主更以个人、家族利益和王朝利益,以及后来的民族利益作为对外关系的重点,近代外交的世俗性和功利性得到充分发展。
再次,法土同盟加速了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的崩溃。中世纪的欧洲是由诸多邦国和城市组成的,但拉丁基督教世界在政治、文化观念等方面具有统一性。“在1400年,西方仍把它自己看作一个社会。基督教世界被最严重的冲突、宗教派别、教条主义的争论和阶级对抗、人民斗争、派系斗争、国王间冲突的地方战争所撕裂。但拉丁基督教世界仍认为它自身是一个整体。”[6]16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不断增强的奥斯曼威胁,他们的宗教身份意识和十字军激情再一次被唤醒。然而,16世纪初,这种整体意识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和法土同盟的建立而彻底崩溃了。1525年法兰西斯向苏丹求助就是“基督教共同体意识的这种渐渐消散的更戏剧化的例证”[26]74。法土同盟是跨文明和跨宗教的结盟,超越了基督教世界内部教派斗争的范围,把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冲突变为文明间与文明内部冲突相结合的复杂性军事斗争。“这就证实了所有关于十字军和基督教世界的言论都是彻头彻后的空谈。……基督教统一体的神话曾起过约束作用,现在却永远消逝了。……中世纪的……骑士准则……在16世纪时对欧洲政治最终失去了约束力。”[8]15-16这样,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彻底崩溃了,代之以王朝的、民族的、国家的意识的崛起。
复次,法土同盟在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新教改革的成功。法土同盟与哈布斯堡帝国的冲突构成德意志新教改革的主要国际背景,在客观上有利于它的成功。一方面,法土同盟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量兵力,使路德教减少了来自帝国、天主教派的威胁和压力,便于其发展。如1552年,土耳其帝国和法国牵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达14多万。正是由于这种牵制,“当他[查理五世]耗费大量的时间、资源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捍卫自己的帝国时,新教势力却在大肆地集聚力量”[24]134。而且,“诸侯们得益于皇帝的世界性义务和费迪南对东方土耳其威胁的专注,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宗教改革问题”[27]230。当查理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德意志宗教问题的时候,新教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另一方面,法土同盟对于查理与路德教徒的任何军事冲突来说,始终是一个威慑因素,这种威慑不仅限制了新教与天主教双方的暴力冲突,促成了德意志内部的和平和新教的持续存在与发展,而且使新教诸侯利用帝国的援助需要同帝国讨价还价,最终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土耳其扩张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资产”[24]138。法土同盟在客观上成为德意志新教改革成功的外部推动力量。
最后,法土同盟有利于法国在东地中海经济地位的上升,促进其工商业的发展和地中海港口的繁荣。16世纪中期,仅马赛港口每年从利凡特进口的货物价值就达850万埃居左右[15]460。意大利战争结束后,法土同盟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法国人陆续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阿尔及尔、突尼斯、摩洛哥等地建立领事馆,保护本国商人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大大促进了法国商业的发展。例如,马赛关税从1570年7 000-8 000里弗(它已保持了此前25年时间)增加到一年后的1.32万里弗,1572年达到1.5万里弗,1573年1.9万里弗。仅东方的香料贸易额就从1560年的2万图尔里弗增长到1571年6.4万里弗[15]464。到1599年的时候,法国商人在利凡特的贸易额达到了50万杜卡特[28]844。法国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商船也不断增加,其中贩运香料的船只从1535年的约20艘到50年后的100至200艘,到路易十三时代,从事利凡特贸易的商船超过1 000艘。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马赛工业的发展。马赛陆续建立了埃卡拉特(l'Ecarlate)制布公司(1570)、精炼糖厂(1574),一个新布厂(1576)和一个肥皂厂(1578)[15]464。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其一,法国国王抛弃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同异教苏丹结盟,是为了扭转本国在地缘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劣势,维护本国利益。从此角度出发,“不虔诚的同盟”的政治合理性就不难被理解。其二,法国经过积极而反复的努力,正式建立法土同盟,并通过修约的形式加强这一同盟,促进本国利益的发展。其三,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法土同盟,对欧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面的、整体性的,涉及国际关系、外交观念、欧洲意识、新教改革和地中海商业等各个方面。因此,法土同盟在16世纪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对其作整体性的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它的重要性。研究该问题也使我们认识到,仅从基督教欧洲内部并不能阐释16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变革的全貌[29]70。
[1]Daniel JVitkus.Early Modern Orientalism:Rep resentationsof Islam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David R Blanks and M ichael Frassetto.Western View s of Islam in M edieval and Early M odern Europe:Percep tion of Other[C].New York:St.Marti's Press,1999.
[2]陈文海.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J].世界历史,2006(4):69-78.
[3][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M].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John 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1:Empire and Absolutism,1516-1598[M].Oxfo rd:Basil Blackw ell,1964.
[6]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 lomacy[M].New Yo rk:Dover Publications,1988.
[7]E.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1501-1650[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8][英]G 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1520-1559)[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苏]波将金,等.外交史(第一卷·上)[M].史源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
[10][英]G R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1493-1520)[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1][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Eugene F Rice,JR.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 odern Europe,1460-1559[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70.
[13]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 pire:The Classical A ge 1300-1600[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
[14]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15]De Lamar Jensen.The Ottoman Turk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Diplomacy[J].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16,No.4.(Winter,1985):451-470.
[16]J C Hurewitz.D ip lomacy in the Near and M id d le East,A Documentary Record:1535-1914[M].Volume I,New York:D.Van Nostrand Company,1956.
[17]W M iller.Europe and the Ottoman Power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J].English H istorical Review,16(1901):452-471.
[18]Charles A Frazee.Catholics and Sultans:the Church and the Ottoman Em pire,1453-1923[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9]Stephen Turnbull.The Ottoman Em pire 1326-1699[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
[20]Paul Coles.The Ottoman Im pact on Europe[M].London:Thomas&Hudson,1968.
[21]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 pire and Early M oder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M].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3][美]斯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M].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4][美]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M].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5]Roger Lockyer.Habsburg&Bourbon Europe,1470-1720[M].Longman Group Limited,England,1974.
[26]L S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M].New York:Rinehart&Company,1958.
[27]Carter Lindberg.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2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9]王晋新.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63-70.
“The Im pious Alliance”:The Establishmen t and Influence of Franco-Turk Alliance in Sixteen th Cen tury
Song Bao-jun
(Center for Histo ry of Wo rld Civilizations,Northeast No 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Charles V,the empero r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to change the geostrategic,dip lomatic and military weaknesses,and to get commercial interests,Francis I,the King of France,w ho has the title of“His Most Christian Majesty”,allied w ith the Sultan of Ottoman Turks in 1536,w ho was the enemy of Christendom.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Franco-Turk A lliance,maintained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multip le politics in Europe,p romoted the transfo rmation of the fo reign concep ts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nity consciousness of Europe,and wasobjectively favorable fo r the successof German Protestant Refo rmation and the rising of French econom ic statu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Impious A lliance”;Francis I;Franco-Turk A lliance;Balance of Power;National Interests
K565.3
A
]1001-6201(2010)05-0056-06
宋保军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
2010-05-11
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重大攻关项目(NENU-SKB2007007)
宋保军(1981-),男,河南南阳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