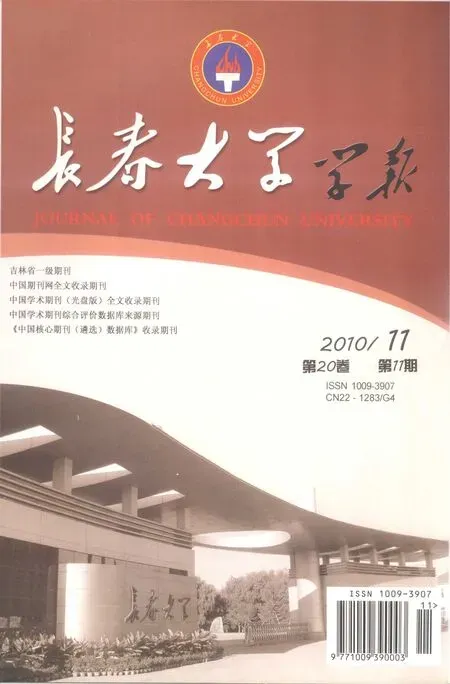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探源
赵玉霞
(延边大学 中文系,吉林 延吉 133002)
嵇康(224-263),字叔夜,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正始士人的精神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是一个较为矛盾的人:一方面,面对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虚伪本质,他愤激而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唱出了这一时代叛逆精神的最强音;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诗歌、辩文和家书中,却又时常表现出对人间世事的关心,对儒家伦理的遵从与捍卫。这种矛盾心理不仅来自他独特的存在体验,更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孟的浸润,老庄的濡染。
我们从嵇康的诗文和言行中,不难发现他内外相悖、极为矛盾的特点。
首先,我们看他脱俗与入俗的矛盾。在很多诗文中嵇康都表达了自己对世俗的鄙弃和对脱俗之美的向往:
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游仙诗》)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五言诗三首》之三)
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五言诗三首答二郭》之二)
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与阮德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答二郭》之三)
但我们在《家诫》中看到的却是他教诲子女如何谨言慎行,如何谙达世故,如何明哲保身,如何远离祸机。正如鲁迅先生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1]515可见,他的脱俗是由现实对他的束缚而造成的反悖,而非纯粹的超凡脱俗。凡此种种,此不赘述。
其次,对于出处问题的矛盾。在嵇康身上纠结的出与处的冲突更为复杂、鲜明。一方面,他对隐逸避世的生活十分向往,而且有过长期的隐居生活;而另一方面,嵇康家世儒学,志向远大,颇有济世之心。在《卜疑集》中他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儒家精神贯穿全篇。在《太师箴》中他又积极谏言为政者,切勿自恃尊贵与威强。在《家诫》中,他进一步强调立志、守志之重要,充满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是出与处的矛盾。
此外,嵇康身上还纠结着悖礼与崇礼的矛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和《释私论》中充溢着对名教礼法之士的辛辣讽刺,对流俗的讥嘲和对仕禄者的鄙视以及对繁文缛节的厌弃,而实际上,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阐释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1]513
在《家诫》中,他要求儿子按照传统礼教的规范做人;他本人在言行上也内省自节,以礼制欲,体现出儒家文化重人际、重内省、重人性完善的特点。而他的社会理想也并未超越名教的藩篱。所谓“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就是在承认等级制度的前提下讲究宽容之道的。《太师箴》则直接美化了他理想中的帝王。
以上种种,我们看到嵇康自身处于矛盾之中,他的内质和外观是不和谐的。在风姿特秀、潇洒飘逸的外表下,隐埋着关注现实、尊崇伦理、笃于友情的真实灵魂。嵇康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正是中国士人在民族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中都要面对的一个精神难题——既要获得精神的自由,又要面对现实。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嵇康为此努力过,抗争过。然而它涉关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并非哪个个人所能为。下面我们从造成中国士人心灵冲突的诸多因素中拈出几端,以此探究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因缘。
1 多重角色
“士”,是中国古代对知识人的称谓。据著名学者余英时的研究,“士”的称谓在孔子之前的商、周文献中是指政府各部门中掌“事”的官员,而且“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士何事》)。但由于他们在政治思想和社会身份方面所受的限定,当时的“士”自然就少了一些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余先生认为春秋以前的“士”还不能算是“知识人”。因为现代观念中的“知识人”,必须发挥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功能。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周代封建秩序的解体,“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始,原在“大夫”之下的“士”逐渐和“庶人”连在一起了。《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论祭祀,便说“士、庶人舍时”、“士、庶人不过其祖”。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社会流动的结果:一方面,“庶人”已有不少机会上升为“士”,另一方面,贵族阶级,尤其是“士”,也大批下降为“庶人”。等到战国时代(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士”不再属于贵族,而成为四民之首①《毂梁传》成公元年条说,上古者有四民,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之后,“士”便从固定的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虽失去了职位的保障,但他们思想不再受“定位”的限制。此时的“士”往往被称为“游士”:一是周游列国,寻求职业;二是从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他们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知识人的原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而且“士”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是“士大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但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相呼应。
有学者认为,“士”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具有动态性、可塑性,二是拥有文化知识。前者指他们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并且“流动”于这两大阶层。退则为民,进则为官。后者是士人阶层的身份标志。文化知识使士人取得官僚后备军的资格从而具有离“民”而为“官”的可能性。
如此,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中,士人阶层实际上是处于中间阶层,受到上下两种力量的牵引。职是之故,无论仕与隐,遇与不遇,其注意力都被引向现实生活,而且其自身也认为自己对整个社会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士人身上还存在着社会管理者与文化承担者的角色冲突。这使他们既具现实精神,又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精神。
由是观之,中国古代士人实际上承担着多重使命,常常处于几种角色的冲突之中,这自然造成了其自身的矛盾,嵇康则是这芸芸士子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一个范例。
2 士志于道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志于道”的观念源于孔子。在孔子之前“道”大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而在原始宗教中,只有少数有特殊能力的人,即卜人、巫、瞽或史可成为天人或神人之间的媒介,但他们只是“士”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士”则和“天道”没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春秋时代,“士”和“道”两个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士”不再受固定身份的束缚,思想获得了解放。这使他们能够对于现实世界进行比较全面的反思和批判,也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探求理想的世界——“道”。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表明,“道”的重心已从“天”转向了“人”。这对后世儒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冯友兰说:“古时所谓道,均谓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上学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②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盛况也彻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框架,“士”作为普通的自由人,承担了以前的王官之学,既然统治阶级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义”的“士”的身上。“士人”以道为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
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论语·宪问》)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荀子《解蔽》)
这样,“士志于道”的精神逐渐传承下来,成为中国士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代代相传。当然,作为正始士人代表的嵇康也不例外。
3 外道内儒
儒家与道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同时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决定因素。儒家讲究入世之道,道家则是飘然脱尘。从表象上看,二者相悖而对立,但实际上却悖反地统一在每一个士人身上。李泽厚先生认为,不仅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包括在人生观和人格观上,儒家和道家也是相互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他认为:“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信念。”[2]在历代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都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套用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事实上,儒道构成了中国士人文化人格的阴阳两面,合起来才是全人,即“自身”。而这恰恰造成了士人心灵的痛苦与矛盾。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不论儒道如何互补,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儒作为封建政体和中国士子的精神支柱,总是行使着它绝对的权利;而道只是作为一种退守的处世策略以弥补儒之不足。所谓儒道互补,纯是以道补儒,而非以儒补道。在陶潜、苏轼这类“超世”诗人身上,儒也无不处在一种“先行”的和主导的地位。实际上儒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权力话语。
可见,儒家的思想观念影响至深。在中国的知识层,只要你是社会之人,无论你自觉不自觉,认同不认同,承认不承认,它已经融入到你的血脉之中,并化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一直起着规范标榜的作用,而且它已由意识进入到无意识,同时又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成为某种思想定势和情感取向、某种特质和性格。进一步讲,它已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尽管也存有道家、法家或佛教的因子,但这些东西已被吸收、包含、融解在儒家中了。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是主流文化,总是以强势文化的状态而出现。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谈道:“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知识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由此他推断,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3]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虽然文化的遵从与背离常常使人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但文化遵从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控制力,任何民族的任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文化遵从的轨道。换言之,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基元已经渗入到中国士人的血脉中。汉魏之际中国社会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儒家的处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士人人生观的基本构架,或出或处,都以之为基本准则。事实上,从建安文人开始,传统价值观就没有退离历史舞台。先看看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儒家文化修养和理想追求便可窥斑知豹了。曹操虽通脱佻伛、重才轻德,但在他评价人的基本价值尺度中,在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中,在自我形象的设计中,儒家价值观仍是基本的尺度。曹丕、曹植等新一辈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缺名《中论序》赞徐斡),更关注与自我实现相关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这实际是以生命融入传统,借传统提升自我的价值,这时的一般文人仍然服膺儒教。有的文人虽崇尚玄学,但因受儒家思想影响深重,如嵇康、阮籍等,故其内在本质仍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
综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铸造了嵇康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总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然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特定的气质、习惯和价值观塑造其社会成员,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强制性的。所以说,文化是一种有形而又无形的力量,不知不觉地沉淀于每个人的血肉中,我们无法抛开先辈创造的精神遗产,而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无意识,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按照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分析,人类的精神是有遗迹的,这就是原型(原始意象):“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它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4]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并非白纸一张,而是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的记忆,人类不仅在血肉之躯上有遗传特征,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有一种承继关系。如若我们抛开其中的先验成分,那么它所蕴涵的文化承传因素则是应该也必须重视的。语言学家帕默尔也认为,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既是在痛苦而缓慢地接受着社会的成规,也是在自然而然地接受并铭记着其祖先数千年来积累而遗留下来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就是说,学习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和一套价值观念。可见,任何民族的任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文化遵从的轨道,文化传统在个人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并“内化”为自我的东西。而且祖先的传统和历史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阻拒的,它以强大的超我确保个人的遵从。如鲁迅先生是反传统的代表,但在文化趣味上、个人生活中却时常遵从、适应传统文化。“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他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由此看来,面对祖先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如同一个有着俄底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舍弃它、背离它常常使人陷入沉重的痛苦、困惑和焦虑中。嵇康的痛苦与矛盾不正是其人格结构中文化遵从和文化背离相互纠结、对峙与矛盾的表现吗?嵇康的“竹林徘徊”,不就是他心灵的徘徊与彷徨吗?嵇康的内外相悖,外道内儒,不正是显示了文化遵从极强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吗?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515.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53.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
[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