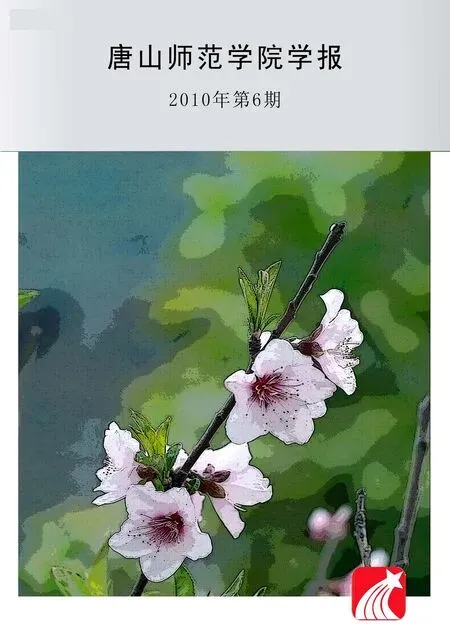西水长流中的融合
—— 近代私塾的改良之路
暴玉谨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私塾这一名称通常认为是从孔子兴办私学开始,一直作为中国社会各阶级最基础的启蒙教育,承担着传播传统礼仪教导、日常杂字、简单的算数记账等基础文化知识和传统思想意识的任务,传统意义上是各朝代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输入的基本保障。但自近代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后,伴随着中国第一部实质性的学制—“壬寅学制”的颁布,私塾的命运也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动。私塾从最初的民间个体设立的教学组织结构,开始成为近代教育及社会落后的代名词,改良的呼声也伴随着社会的改良开始讨论和变革私塾的命运。
一、裂变社会中的私塾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旧因素的变化融合逐渐由政治渗透到教育、社会各领域,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最早由传教士引进。《南京条约》签定后,教会学校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学校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其学制、课程和教科书都移植于西方,代表现代取向。不过由于它与当时中国主流教育方式大相径庭,长期居于边缘而不为人重视。
洋务运动后,兴办洋务的诸多实际需要充分表明,重在人文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需要更张易弦,中国屡次败于外国的命运,使得国人发现只有采取与战胜国一样的教育体制才能挽救危亡,“教育救国”的呼声日高,渐成朝野的共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说批判传统教育制度,呼吁西式教育。郑观应在《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作中抨击科举制度,介绍西方教育,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特设西学科,“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算、地舆、农政、船政、化学、医学之类,及各国语言、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为之”,强调“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建议各省改革传统教育,实行西方教育方式[1]。戊戌维新之时,倡导兴办新式学堂也是维新派的重要举措之一,康有为曾在甲午战后上书光绪帝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盖先未尝教养以作成之,天下岂有石田而能庆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见矣,不可不亟设学以育成之矣。”但是,“顾以中国现时力量及人民程度,而欲大兴教育,广设蒙小学堂,恐无此量数之经费,亦无此数量之教员,则莫如先就旧有之数百万私塾而改良之……变旧习为新法,化私塾为学堂,为今日过渡时代之简易办法”[2,p150]。虽然维新时的举措收效甚微,但却是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布了教育改革政策,其改革的经验教训则对清末“新政”中的教育举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戊戌之后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兴办学校的热潮,改良私塾的倡议也虽之而起。
二、自下而上的萌动
私塾虽然在社会变动中发生阵痛,不得不发生转变力求发展,但这一变动却不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开始的,也未发生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开放城市,而是从民间启动,进而推之全国,形成私塾改良的热潮。
1904年 6月,江苏学务处委员沈戟仪在川沙龚镇首创私塾改良会,拉开了延续半个世纪的私塾改良的序幕。沈戟仪在苏州醋库巷开设私塾改良社,每月招集学生考试,定期举行考核,颇有成效,在沈戟仪的倡导下,六、七月间法华、黄渡、南翔、嘉定、太仓、刘河、常昭、新桥、虹桥等处也设立了私塾改良会。半年后,苏州成立私塾改良总社,至1905年改革私塾教育已蔚成风气,进而得到上海开明绅士的极大关注。1905年6月上海成立私塾改良总会,1906年6月上海私塾改良学会联络各乡各邑官商学界,本着“化新旧于无形,免官私之交哄”的宗旨,争得了“前两江督宪周札饬”、“两江学务处”、“今督宪端札”的支持,正式立案改良私塾,且简定《私塾改良会章程》[2,p103]。既而私塾改良有规可循,使得改良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同期,天津绅士、小学堂教习王新铭(吟笙)发起组织广育学会,为天津私塾改良之发端。1905年北京也设立京师私塾改良会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并催生出主管北京私塾改良的中央教育机关——学部酝酿而生,因此北京地区的私塾改良意义超出了本身的意义,正式拉开了全国性私塾改良运动的序幕。
邻近京师的直隶首先按照学部的指示,着手改良私塾。此时直隶新式教育虽已有所发展,但数量不仅有限,“于私塾比较,尚不敌其十分之一”;而且质量也多不合宜,“教授得法者不过十之一、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塾师之阻力甚大,听之不可,禁之未能”。而此时“私塾改良一法,己为学界所公认”,鉴于兴办新式教育的诸种困难,提学司决定改良私塾,简定改良办法,通饬各属劝学员绅,“一面整顿已设立学堂,一切规模、课程悉臻完善,使之有所观感而起则效之心;一面调查现时所有之私塾,查照以上办法,相与联络实行改良之法,以为教育之补助”[3],自此,直隶一地踏上了兴办学堂与改良私塾并行的道路。
在京师、直隶地区私塾改良运动的影响下,河南、吉林、湖南、湖北、浙江、宁波等地陆续开始了私塾改良运动。各地轰轰烈烈的私塾改良运动使学部逐渐意识到了私塾对于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朝廷振兴学务,实以初等小学为普及教育之基。惟我国地大人众,固贵有完全之小学以养其道德知识之源,而公家之财力有限,自不可无私塾以资辅助”,“私塾所以辅助小学之不及应改良,不应歧视,庶国内多一就学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3,p309]。为使全国的私塾改良更加规范,更深、更广的开展,学部于1910年7月总结各地私塾改良的经验教训,颁布了《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二日(1910年7月28日)学部通行京外学务酌定方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谕令在全国范围内改良私塾[3,p310-322],至此,改良私塾得到官方正式认可。但此时的清政府统治已摇摇欲坠,此章程并未发挥它应有的效用,收效甚微,但至此私塾拉开了持续变动的序幕。
三、清末民初时的二元格局
中华民国建立后,继续清末改良的余热,1912年教育部颁布京师私塾整理办法四条,与清末改良措施相比,此次改良明显侧重于对塾师的甄别改造,并且对不符合标准的塾师采取的措施由原来温和的劝导变成了严厉的干涉解散,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良试验,京师的改良“确收改良之效也”。为使京师成为全国改良的典范,1912年底,教育部再次申明改良京师私塾的政策。至于其他省份,无特别规定,但须以整理为主旨。在其精神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地方性的私塾改良办法,“安徽省订有私塾办法五条”、“湖南订有私塾暂行规程十七条”、“吉林省订有私塾考查规程十三条”、“贵州省订有改良私塾章程十二条”,民国初年的全国性私塾改良运动逐渐铺开[2,p113-115]。
清末民初十几年的私塾改良运动在教育领域影响可谓深远,它揭开了完全意义上的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是这一社会转型期不可或缺的方面。但众所周知,社会转型、传统变迁是一个循环反复、不断推进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较为漫长。私塾改良既而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他的新陈代谢。北京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教育中心,其成效性也极具代表性。据1907年的调查,“下学期查得京内私塾能按照简易小学课程办理者仅有十二处,学生止三百余人,而未经改良者不啻倍蓰,因筹给名誉金以奖励之,颇著奇效。至三十四年上学期查得各处改良私塾共四十二处,学生一千余人,下学期增至八十九处,学生二千二百余人。迨乎宣统元年末,京内私塾之改良者已有一百七十二处,学生达四千三百余人”[4]。故至民初时,北京仍是“私塾无虑数百,旧习未除,教程颇多违谬”。从1912年到1918年,北京地区再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私塾改良运动。但1917年6月,劝学员长祝椿年曾对京师十年的改良状况做过总结:“自京师设区劝学以来,即力筹改良,舌敝唇焦者己十载。于兹惟是义务教育迄未施行,学校扩充限于财力,儿童荒学无校可归者尚不可胜计。则私塾仍未臻淘汰之命运,改良之法仍须依旧进行。况现在私塾之优良者亦正不乏而新发生者亦正未艾”[5]。简短的总结道出了力劝改良者的焦虑与心酸,十年辛苦换来的仍是“儿童荒学无校可归者尚不可胜计”的无奈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私塾改良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同时也表明,在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私塾并没有因新式学堂的兴起与私塾改良运动的开展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学堂一起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共同承担着初等教育的重任,构成了初等教育领域里的二元格局。
四、20世纪30年代私塾的融合
虽然私塾经过十多年的变动和改良,最终却以二元的格局——私塾和学堂的形式构成了近代中国教育主要的方式和组织,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承载着传统的继续,演绎着中国国体的新陈代谢。至20世纪30年代,私塾在现代教育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到1936年,湖南华容县有252所,耒阳县有445所,汉寿县70余所,宜章县78所,长沙县408所,泸溪县81所,祁阳县300余所。
南京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一方面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规,以推动和加快全国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各省严厉取缔私塾,但是由于各地各方面对于改良或取缔私塾不了解,不仅在边远山区,而且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城郊,公然反对“新学”而主张续办私塾的也大有人在,因而推行阻力极大,“除附近学校之私塾加以取缔外,其余分散各处者,鲜加干涉”。初期对私塾的改良成效甚微。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要求各省将原有私塾整理改良,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课程办理,改称改良私塾,对成绩较优者,迳升为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并要求各省市县高级中学或师范学校举办塾师训练班,对各地塾师按照现代教育规范进行培训。在教育部的严令督促下,各省政府和教育厅将改造私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列入各政府施纲要和政府纲要,采取措施,试图尽快促使私塾实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换。
三十年代经过对私塾的改造,成效十分明显,经改造后的私塾具备了现代教育的意识和内容,开始向现代教育发生嬗变。私塾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嬗变首先表现为私塾数量的大为减少,初级小学数量的增加。以湖南省为例,1929年,全省小学17 211,在校学生638 629人,1930年颁布取缔私塾规程后,当年小学校数即增加到23 112所,在校学生达904 490人,以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36年便迅速达到23 779校1 033 407人,1937年更达到28 500校1 194 567人[6]。私塾的减少也可以从学龄儿童入学前曾否就读过私塾的情况看出来。发达地区姑且不论,从教育不发达的湖南湘西沅陵县入学学生群体来看,据1940年的统计,沅陵县新坪乡第四保国民学校,二年一期的16名学生有12人入学前读过私塾,一年二期的15名学生入学前全部读过私塾,但一年一期的16名学生则全部未读过私塾。从而看出即使在边远山区,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开始让位于现代教育形式而逐渐退出教育领域,普通初级小学教育已经取代传统私塾教育而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
私塾在近代的社会中与国家一并经历着其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由起初的固守最终走向由衷的接受,接受外来的变化,接受外来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变化中融合了外来的要素和因子,但都寄托在现实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中,其中传统的文化精神一直保留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以前所谓的士阶层在社会变革中演变成多种阶层承担的责任,同时也主导着现实社会的文化走向。私塾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教育,虽然在变动的社会中承受着无限的压力和责难,但这一基础却在变革之初同样显示了自己独有的力量,与新式教育互补维持着变革社会中培养变革一代的重任,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变动社会中不一样的一代、不一样的社会和民族精神,发扬了不一样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