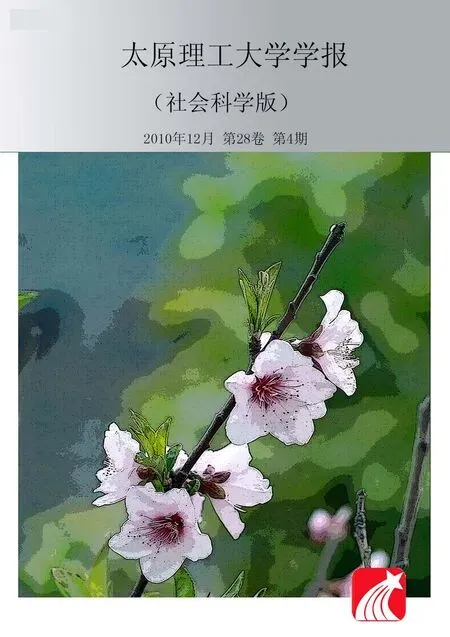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郑建钟,袁 利
(1.重庆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重庆 400054;2.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艰苦传播和发展,成功地移植入中国社会,到隋唐时代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一时期佛教空前繁荣,表现为一流的哲学家大都是佛教徒。然而,佛教的一时繁荣并没有造就唐王朝持续的“盛世”,相反却成了“衰世”之始的“籍口”之一,因而,唐宋之际开始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新儒学运动。而这场运动实际与持续批判、排斥佛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韩愈(公元768-824)的“排佛”论无疑是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标志性事件。关于这个事件,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说:“(韩愈)所持排斥佛教之论点,……,实不足认为退之之创见。”[1](p296)陈认为韩氏排佛并无特别的创见,其之所以影响很大,皆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汤用彤也说:“故韩文公虽代表一时反佛之潮流,而以其纯为文人,率乏理论上之建设,不能推陈出新,取佛教势力而代之也,此则其不逮宋儒远矣”[2](p44)。汤认为韩氏在排佛问题上缺乏理论建设,其思想深度远逊于宋儒。陈、汤二位前贤都认为,韩愈批判佛教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没有系统的理论构建,这一论断既有历史的习见,也对今天的人们认识韩愈批判佛老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以成熟时期的理学体系来反观理学兴起阶段中的思想启蒙而得出的论断,而韩愈正是处在新儒学兴起的发端时期。在文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韩愈的排佛老并非“无特别的创见”,实际上,韩愈排斥佛老不只是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的外缘维度,同时也试探到了佛老的世界观层面,与后世儒家学者深入骨髓的反佛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一、外缘维度:“夷狄之法”论
对于唐之前的排佛言论,许里和在其《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总结出了四种反对僧权的论点:政治及经济、功利主义、文化优越感与道德的论点。[3](p433)这四种论点在韩愈的排佛言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韩愈说他自己“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4](卷十六)此“惑”当然是释老二教的魅力所致,尤其是佛教,形成了当时“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5](卷四十九)的上达天子、中为朝臣士大夫、下致庶民的社会整体倾向性的信仰。然以儒家先行者出场的韩愈,却将“觝排异端,攘斥佛老”[5](卷十二)的活动作为他通往“明先王之道”途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唐宪宗派遣使者去凤翔延请佛骨,京城一时掀起信佛浪潮,当时正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痛斥佛之不可信,主张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听后龙颜震怒,欲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公元765-839),崔群(公元772-832)等人说情,遂将其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所上之表即著名的反佛檄文《论佛骨表》[4](卷十六),此文集中阐发了他“排佛”的理据。其主要论点有以下几个。
首先,他从华夷之辨出发,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与中国先王之法相背离:“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卷十六)其次,他从中国历代帝王治乱兴衰的角度,分析了佛法传入中土之后的社会变化。在佛法传入中土之前:“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自佛法传入以后,社会动荡、国家衰亡前后相继不竭“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4](卷十六)因事佛频繁、用力甚深,都“年代尤促”[4](卷十六);更为严重的是,事佛勤谨的梁武帝,却因溺佛太深,竟最终被逼死台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4](卷十六)所以,韩愈认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4](卷十六)最后,韩愈认为,侍奉佛法既不符合“高祖之志”[4](卷十六),也会造成“伤风败俗,传笑四方”[4](卷十六)的可笑境地,应当立即将迎至宫中的佛骨舍利“付之有司,投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4](卷十六),如此,方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
在这篇裁抑佛教的奏章里,表现出韩愈对待佛教的传统思路:从华夷之辨的华夏族本位出发,将佛教定义为有害治国安邦与引起伤风败俗的夷狄之教。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蕴涵着的“血缘—宗族”观念,运用于裁汰佛教所体现出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此方式非韩愈首创,太祖太宗朝时的傅奕,以及在佛道交涉史中,围绕着“老子化胡”一事的真伪论争此起彼伏,已充分展现了当时三教中人普遍倾向的思维方式。然而韩愈排佛之所以不同于前人,就在于他企图建立一套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的儒家的“道统”。
《原道》[4](卷十一)一文是韩愈最具理论价值的文献,同时也是新儒学运动兴起的宣言书。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韩愈突出阐发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相对的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卷十一)这个“道统论”是后来宋儒最为乐道的命题之一,尤为宋明新儒学中的理心二派论争得激烈。这个“道统论”的提出,必须考虑到韩愈议论所具有的特别时代性,即他所处的时代远则五胡乱华,近则安、史胡种兵祸害国,在社会生活中引起了极大而又长久的影响,这不能不对韩愈有深深的触动。而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佛教此时在思想文化层面形成了巨大的强势地位,一方面是“修身、正心”者都成了释家门徒,另一方面是国家动荡,“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无法实现,在这双重打击之下,韩愈“道统论”的问世,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而且对面临相似的社会问题的宋儒们也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二、哲学维度:“定名与虚位”论
“道统论”是韩愈为排佛而提出的一种抗衡手段,其以儒家的学术渊源来化解佛教对儒家文化的蚕食,对后来宋儒的影响至为巨大。然其对仁义道德“定名与虚位”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也启发了宋儒对佛教“蹈虚”、“一切皆空”的批判,实为韩愈论佛教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首先发现韩愈“定名与虚位”论的价值的当是宋代的张九成(公元1092-1159),其著《横浦心传》中有一对话是如此说的:“或问:‘退之言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处。老子平日谈道德,乃欲扌追提仁义,一味自虚无上去,反以仁义为赘,不知道德自仁义中出,故以定名之实主张仁义,在此二字。’”[6](p1310)张九成肯定韩愈点中了佛、老的要害处,即认为,佛、老的“道”与“德”与儒家之道德以仁义为本是不同的。实际上,若从思维方式上说,这是一种意欲摆脱佛、老在最高哲学范畴中的垄断解释权的初步尝试——佛教有证得涅槃这一最高境界的“道谛”、道家道教有最高的哲学范畴——“道”,那么,儒家的最高的“道”是什么呢?韩愈的回答是:仁义。
我们知道,韩愈所处的时代,儒释道三家都在讲道德,其“不入于老,则入于佛。”[4](卷十一),但是他们每家对道德内容的界定却大为不同。对于儒家的道德,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4](卷十一),而关于仁义与道德的关系,他给出了一个新命题“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6]1310,[7]这个新命题,在朱子看来,与《孟子·离娄上》所引孔子的话:“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和《周易·泰》中所说的:“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意相似。[8](p3271)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新提出的哲学范畴注后世有些儒家学者虽明白韩愈将“道”虚位化的用意,但如二程这样的道学家依然是激烈地反对韩愈的看法,他们以体用一原的关系来说明“道”与“仁义”的关系,认为“道”不是如韩愈所言的一个空洞的容器来盛放“仁义”,而是要求“道”像种子一样自然的生长出“仁义”,参见文献[7]。所以,张九成甚是理解韩愈似的说了折中的话:“既言行仁义之后,必继曰‘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恶佛、老不识仁义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注参考文献[9]中认为韩愈使用的定名、虚位可以相当于今天的“范畴”,定名可以认为是实质的范畴,虚位可以认为是形式的范畴。从笔者接触的材料来看,对韩愈“定名与虚位”范畴最具好感的哲学家当属张岱年,他在文献[9]中就应用了这对范畴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一种独特的标准。,,[9]的“定名、虚位”论,我们认为与先贤的“名实”论有诸多的关联。历史上,孔子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 的“正名”说,墨子则认为需要“以名举实”,才能“察名实之理”。《墨子·经说上》进一步提出普遍性、某一类性与个别性的“达、类、私” 的概念,《荀子·正名》也以“共名”与“别名” 表达了相似的意思。韩愈提出“定名、虚位”的范畴与这些先哲所阐发的哲学概念,有着某种性质上的相似之处。就这两个名词本身来说,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也经常出现,而韩愈却赋予了新的含义。荀子在《正名篇》中说“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这里与韩愈的用法在顺序上是颠倒的。《管子·九守》则与韩愈用法更接近了:“修(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尹文子》里也说:“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定名”之“定”在这里都是以“确定”的动词形式出现,而韩愈却是以形容词“确定的”来使用“定”字。“虚位”二字至迟在《汉书》中就出现了:“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年。”[10](卷十四),这里说的是空缺的帝位。《晋书》也以相同的用法说道:“宣皇未升,太祖虚位。”[11](卷十九)这里的“虚位”若理解为“空缺的帝位名号”与“实际占据此位置的人”的关系,则与韩愈的“虚位”之意也不太远了。韩愈认为,定名是有确定内涵的名称,虚位是空格子,不同学派可以填入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说,道释的道德与儒家的道德在实际内涵上是不同的,儒家主张的道德是“仁义”,这个词有其固定的含义,道释可不同意儒家所说的仁义,但不能借用仁义二字而赋予它以另外的意义,只是对仁义加以批评指责而已。[9](p2-3)从理论构建的基点上说,韩愈并没有如宋儒那般把仁义所代表的儒家“天理”突显与确立起来,但正是因为他区分了“道德”与“仁义”的不同地位,区分了佛道与儒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起点的不同,而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排佛、反对僧权诸如“政治及经济、功利主义、文化优越感与道德”等等论点新趋向,毕竟要确立儒学在社会层面的价值主导地位,首要的就是要从儒学自身构建起足可以支撑其学说的内在理路。以此,宋代崇佛很深的张九成说“此正是退之辟佛、老要害处”。原来,这个“定名、虚位”论,实际上与宋儒从世界观上总体批判佛教,既而构建儒家自身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宋代理学家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儒家思想应对佛教的挑战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在于,在世界观上,他们认为佛教将世间万物视为虚妄与空,即所谓“五蕴皆空”、“诸法空相”,而儒家则认为世界皆有实理,有人伦物理,是真实而非虚幻的。这个批判的视角可以说是远朔先秦的“名实”论,近承韩愈的“定名、虚位”论,既而杂糅成颇具时代特色的“佛虚儒实”论的批判新旗帜。张载认为“知太虚即气”,才能“使儒、释、老、庄混然一涂(途)”[12](p8)。所以“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12](p26),正是佛法本末倒置,以空幻为真,不知虚空实际是实有,“故《正蒙》辟之以天理之大”[12](p4);二程也说:“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13](p4)“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13](p66),事物的生死变化,都是有自己的“实”理;朱熹也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8](p3015)“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13](p380)。在世界观上,宋代儒家学者以这种“佛虚儒实”论来排佛,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也可以说是对韩愈“定名、虚位”论的理论发展,它的深远意义,直到明代,佛门高僧也都不得不承认其批判的力量:“宋儒……,乃曰: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理是实理,他却空了,所以大本不立。彼谓万理俱实者,乃指事物当然之则也,此当然之则,有名可识,有相可指,故曰皆实。”[14](卷七十二)为何儒、佛有“实有”与“虚空”的论辩?从哲学思想上说,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进路来阐发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及其关系而得出的不同结论,这些结论在石峻看来,儒家学者“并未击中佛道的要害”[15](p500),他认为,张载创制“气本论”、程朱提出“天理”论都不过是“用一种本身很难说是正确的观点来反对另一种他(指朱熹——引者注)认为是错误的观点”[15](p148)。本文并不在于讨论以韩愈为开端的,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批判佛教是否从根本上推翻了佛教,而是意在说明,对于批判佛教的视角,其实从韩愈起就开始走向了深度的哲学批判,且有了新的高度。
韩愈当然没有在批判佛教中体贴出二程的“天理”二字,但他在《原道》里也说:“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清净寂灭”即是佛教中“自性”的另一说法,而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万象皆无自性,而是因缘和合而起,缘起缘灭,故“万法皆空”。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韩愈所说的佛法“清净寂灭”的“道”实际就是对应于“虚位”,而与“博爱为仁”(尽管宋儒反对韩愈以博爱解释仁,如二程认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13](p182))的儒家伦理条目相对应的佛教伦理规范就应该是“慈悲”。当然,韩愈本人并没有如此来解说佛教中“定名、虚位”的具体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宋儒张耒批评韩愈“愈者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6](p678)这种“不详”实际为在佛教问题上与韩愈唱反调的柳宗元所点明:“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17](卷七)柳氏将儒家的礼仁义直接对应于佛教的“戒(律)定慧”三学,可谓是说了韩愈所未言尽的话。所以朱熹赞同韩愈的界说,“定名虚位却不妨。”[8](p3271)为什么?“盖仁义礼智是实,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说,却虚。如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此道德只随仁义上说,是虚位。”[8]而且,朱熹在继承二程的思路的基础上,其本身也是在依照佛教所谓“至极”的本体论模式、以儒家本有的哲学范畴来改造佛教已有的概念,进而创制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根据来。[18](p419)这可以说是一种最彻底的吸取佛教的运思方式与命题形式,进而开挖出儒学的本质内涵的融佛又非佛的绝妙境界。而这种境界,在韩愈以“定名与虚位”论来作为批判佛教而非创建新理论体系那里也就出现了端倪。
综上所论,韩愈的排佛思想在传统认知意义上主要体现为外缘维度的“华夷之辨”、“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道德败坏”等,这种批判佛教的视角并没有超越他的前辈学人的普遍看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韩愈为了对抗佛教在思想理论上对儒家思想的笼罩,以“定名与虚位”的哲学范畴来区分和理解儒佛二教理论特征及其界限所在,却是很有先见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对程朱等人对佛教的深入批判与“天理”的体贴有着重要的启示。因而,我们认为,实在不能将韩愈定位为,对于佛教“迹象之粗者转不足责”[19](p1449)的主流评价。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A].汤用彤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 [荷]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M].李四龙,裴 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 (唐)韩 愈.韩昌黎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6]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朱 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57.
[8] (宋)朱 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 (汉)班 固.汉书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唐)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宋)张 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3] (宋)程 颢,程 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 新文丰编审部.卍续藏经[M].台北:新文丰编审部,1983.
[15] 石 峻.石峻文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6] (宋)张 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 (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8] 周继旨.关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论根据上的内在矛盾问题的若干思考[A].国学研究(第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 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