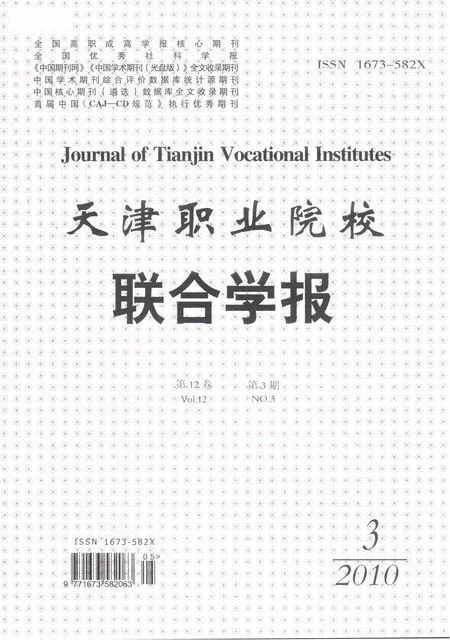美丽总是愁人的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三位少女形象
冯 俏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 300280)
美丽总是愁人的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三位少女形象
冯 俏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 300280)
沈从文在他湘西作品中对少女形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翠翠、萧萧、三三,三位美丽的少女是其中的代表。三位少女懵懂的初恋中的细微感受展示了美好生活,但是结局却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阴差阳错的命运安排。
湘西;少女;初恋;人性;挽歌
一个作家,他的作品逃离不开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他们作品的血脉会牢牢地和一个地方结合起来,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的成了这个地方的象征,如鲁迅之于绍兴,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可无论如何,绍兴、北京、上海它们本身在精神上还是独立的。可有一个作家、一个地方,却是水乳交融的,那就是沈从文之于凤凰,没有凤凰就没有沈从文,可没有沈从文的凤凰,世俗一点说,会这么名声大震,游人如织吗?没有沈从文,它只是中国众多美丽的地方之一,有了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作品,它仿佛有了灵魂。人们去湘西,去凤凰,怀着朝圣的心理,要去看山、看水、看吊脚楼,去亲眼看看是如何神奇的土地养育了翠翠、萧萧、三三、龙朱、傩送和沈从文。
少女形象是一切美好的象征,单纯、善良,不谙实际,充满幻想,少女的初恋青涩而又甜蜜,用尽人间一切美好的辞藻也难以描绘。有很多有少女崇拜情结的男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沈从文作品中的少女便是这样与水密不可分,如水般寻常,却又滋养生命,憾动人心。在这里,我们以其中的三位为例,来看看,倾注了沈从文极大热情的少女形象。她们是《边城》里的翠翠,《三三》里的三三,《萧萧》中的萧萧。三位少女年龄相仿,和湘西的环境融为一体,优美、自然、健康,从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怎样的一些人?滋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一、身世凄凉,生活简单而又辛苦
《边城》中的翠翠,是茶峒白河边摆渡老人的外孙女,两人相依为命,老船夫的女儿,爱上了戍城的士兵,怀了孕,想走又舍不得老父亲,士兵为此自杀,女儿生下翠翠后不久,殉情而死。翠翠成了遗孤。因为住在两山多篁竹的山城边境,篁竹的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便为这可怜的孤雏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翠翠”。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他们日常生活在常人眼里是艰辛的,一老一小,收入微薄,端午节连粽子也包不起。然而,他们十分满足,从未把这些放在心里。他们过着简单又单纯的生活,直到爱情的降临。
萧萧是个孤儿,十二岁就被唢呐吹进了农家,出嫁作了童养媳。小小年纪的她,照顾小丈夫,喝冷水,吃粗砺饭。绩麻、纺车、洗衣、打猪草推磨,浆纱织布,受气,模模糊糊地向往女学生式的自由生活。
三三是堡子里杨家碾房的一个女孩,五岁时,爸爸什么也不说便死去了,于是妈妈作了碾房的主人,三三在米灰里,在碾米声里,也在哭里笑里慢慢长大了。
在优美自然的环境中,她们过着平静平淡的生活。心地单纯善良,率真自然,似乎永远都长不大,有着梦一样的想象空间。
二、对现实有一种朦胧的不满足感和孤独感
翠翠、萧萧、三三都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大自然中,有疼爱着他们的人。她们和自然融为一体,生活简单到有点寂寞,有一点似是而非的不满足感,想要离开现实生活。
翠翠:她爱上了船总顺顺家的二老,一切都不一样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萧萧:乡下人说到女学生,把她们当做奇闻和异类。“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年纪有老到二十四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十居然还好意思嫁人的。”但是,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萧萧被流浪汉花狗引诱怀孕后,想逃走:“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么?”文章最后,萧萧抱着新生的儿子毛毛哄他:“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的逃跑计划如果做周密些,或许已成为女学生了。她似乎始终放不下这自由的女学生的生活。
三三:15岁的三三在一个夏天的黄昏,碰到一个城里来的白脸少爷;而总爷的管事如同说梦话般地对少爷说做媒,少爷可以当磨坊的主人了。三三由此产生了对城里的梦一样的不切实际的向往。“她望着清清的溪水,记起从前有人告诉她的话,说这水流下去,一直从山里流一百里,就流到城里去了。她这时忖想……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去,一进城里就不回来了。“每次到溪边玩,听母亲喊:三三,你回来吧”,三三一面走一面总轻轻地说:“三三不回来了,三三永不回来了。”
翠翠有爷爷疼爱,三三有母亲陪伴和照顾,萧萧身边虽然没有亲人,可身边的人也并没有虐待她。然而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精神的抚慰,有同龄人的陪伴,在这方面三位少女无疑是缺乏的,她们是寂寞的。沈从文把寂寞的,充满幻想又生活封闭,缺少对外界事物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少女心态把握得恰到好处。他对这些少女倾注了无限热情,正像对张兆和的情书中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些正当最好年龄的少女并未从爱情中觅得幸福,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再也回不到从前。
三、初恋懵懂的和细微的感受
他们简单的生活和感受,都发生了变化,这才是重点。恋上一个人,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三位少女的初恋来了,她们生于自然,长于自然,一切都顺其自然,对待感情也是。她们不知什么叫“发乎情,止于礼。”一切出自本心,沈从文先生为我们展现了初恋的不同阶段。
1.翠翠的抉择
慢慢长大后,翠翠的性格有了微妙的变化,多了沉思和羞涩,面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不知是乐是愁。翠翠的初恋是从端午节开始的,她遇到了英俊,勇敢,热情的二老傩送,萌发了朦胧的爱恋。还没等他们开始,二老的哥哥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他更直接,直接提了亲,然而翠翠心已有所属,她不能违背内心,他选择会唱美妙的歌的二老。大老负气出走,死于一场船事故中。这样,翠翠虽然依照自己的内心做出了选择,二老却不能对哥哥的死释怀。他也离开了。翠翠的选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沈从文把初恋的翠翠的内心世界描绘得动人心扉,翠翠常会无缘无故的不高兴。“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度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把烟杆在船边剥薄的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苗族男女是以歌声来传情表意的,而十四岁的翠翠竟在梦中听到了唱给自己听的歌。而当她明白歌里的意思,当她在渡口看到傩送,当她听爷爷讲着一些关于船总顺顺家的事时,她便开始脸红,却又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2.萧萧的受骗
萧萧十二岁作了人家的童养媳,出嫁只是从这一家转到那一家,做媳妇的时候她不仅不哭,而且一个劲儿的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然而当雇工花狗对萧萧生了另外一种心,萧萧有点明白了的时候,她常常觉得惶恐不安。当花狗坐到萧萧身边,要萧萧听他唱那些使人开心红脸的歌,“她有时觉得害怕,不需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于是这个糊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她的怀孕少不了花狗的层层引诱,可这些又是她在听从自然人性的召唤下发生的。她的初恋短暂的,一点儿都不美好的,甚至是算不上“恋爱”的爱恋。
3.三三的暗恋
三三的爱有如一个清凉的梦,这个梦只和她自己有关,是最初的心动。爱与不爱只和她自己有关。城里男人对管事先生说:“女孩子真俏皮。”管事先生笑着说:“少爷喜欢,要总爷做红叶,可以去说说。”又说道:“少爷做了碾坊主人,别的不说,成天可有新鲜鸡蛋吃,也是值得的!”她们这肯定是玩笑话,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可三三没有。她就坐在石头上,脸上发着烧,十分生气。心里想:“你要我嫁你,我偏不嫁你!我家里的鸡纵成天下二十个蛋,我也不会给你一个蛋吃。”她对城里来的那个男人充满了好奇与恐惧,当她听到周围的人逗自己说把三三嫁给城里男人时,当她碰到城里男人同管事先生说着一件关于自己的行为,又不能让人走开,又不能自己走开时,三三就非常着急,觉得自己的脸上像霞一样。三三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城里的男人过多的接触,出于对城市和城里人的一种好奇,她产生过一种朦胧的爱恋。
沈从文把三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在恋爱中的细微感受描写得十分细腻和感性。正如作者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四、善良质朴的人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草一木都美妙无比,至情至善。在《边城》中,人人都善良慷慨,以帮助别人为人生乐事。老船夫,勤劳、朴实、善良,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他觉得“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生活清贫,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作为报答,肉贩们愿意免费送给他肉,水手们愿意送给他一把枣子,都是出自内心的体验。
船总顺顺,“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他的仗义疏财、光明磊落、正道直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信赖。在老船夫死后,他想要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虽然他大儿子大老的死与翠翠的拒绝有关,二儿子又因为不甘心而出走,应该怨恨翠翠才对。
萧萧怀了别人的孩子,面临两种可能,沉谭或发卖。她的结局应该很好地印证“礼教吃人”的社会弊端才对。可是萧萧只有一个伯父,在近处庄子里为人种田。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就决定“发卖”。可远处没有人来买,而后萧萧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萧萧还是做她的小丈夫的大妻子。萧萧的乡间很有情味也很现实。
《三三》中三三母女俩招待城里来的护士小姐和白脸先生,因为护士小姐说南瓜子好吃,又另外取了一口袋的生瓜子。再过几天,那病人却同女人一块儿来了,来时送了一些用瓶子装的糖,还送了些别的东西,使得主人不知措置手脚。因为不敢留这两个人吃饭,所以到临走时,三三母亲还捉了两只活鸡,一定要他们带回去。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不受外界污染的纯朴的乡情。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态度,因为他们封闭在自己的天地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内心生活,她们对外界的认识是混沌和滑稽的。
五、阴差阳错的命运安排
情、景、人都是那么的完美,结局却不那么完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
沈从文说,他将“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在《边城》结尾处,在一个风雨之夜,白塔倒了,心力交瘁又感到无能为力的爷爷死了,带着无限的牵挂。二老走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会来,也许‘明天’回来。”这结局不像是沈从文安排的,是命运安排的。白塔倒了,爷爷死了,傩送走了,一切那么自然而又是命中注定,非人为因素。因为所有人都善良而美好,为别人着想,却阴差阳错。这是翠翠的,也是沈从文的一种痛苦的期待。“明天”是多么近,同时又是多么遥远,它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
萧萧怀了别人的孩子,虽然有幸没有被沉潭,并且多年后同长大了的小丈夫圆了房,生下了她和丈夫的亲生骨肉毛毛,但是这种看似幸福的结局其实是痛苦的,是让人寒心的。十二岁便做了童养媳,十四岁又糊里糊涂的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它是萧萧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同萧萧一样的所有女孩的悲哀。“小说结尾处,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体现了一种轮回,一代又一代继续着她们无奈悲凉的人生。”
三三的母亲一心想把三三嫁到城里,年少的三三也一直对城里充满着好奇。不幸的是城里来的男人最终病死,城市与城里人不再对三三产生吸引力,三三的母亲再也不想把女儿嫁到城里。结尾处:“三三站立溪边,眼望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故事戛然而止,三三和母亲模糊的嫁到城里的愿望犹如美丽的泡沫“啪”地一声碎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为什么写出这么好的人性和人,却赋予她们悲剧。沈从文先生少年时代即步入行伍,成了湘军的一份子,见惯了血腥和杀戮。正因如此,在这些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于人类极为丰富美好的理想。他的湘西作品和同时代的作家比较起来,表面上看起来缺少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作品中的时空好象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有人说他笔下的湘西是“桃花源”、“乌托邦”,作品是田园牧歌式的。沈从文先生自己怎么看:“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毫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与同时代的乡土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写乡土时,对乡村的生活方式很少持批评者的态度,也不会用一个启蒙者的态度高高在上地审视它,他用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展示它、赞美它,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然而毕竟是不同了,谁也阻止不了时代的发展。他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湘西,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来都没有那么完美,如果他没有走出来,他也许还会为它的落后而苦恼。正因为来到了城里,对城市生活的庸俗市侩产生了厌烦和不认同,回忆起湘西,过滤掉了丑陋,只剩下美好,人性的美好。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将近十年后,回忆说:“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苦心经营的湘西世界是作者生命之所系,魂魄之所在。但在现实面前,这个精神家园注定是坚守不住的。现代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都市文明,无论他如何厌倦,对湘西的冲击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事实。现代都市对湘西的步步紧逼,使得湘西世界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沈从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又无力改变什么。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现代化”已经使得“桃花源”式的湘西世界失去了存在的可能,这个世界只能停留在作者心中,成为一个梦。因此在他的美丽作品中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无可明状的、美丽忧伤的意境。他对此的解释是:“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因为你们是城市中人。”这是内心真实的独白,我们据此可以理解他作品中淡淡的,确是最深刻的哀愁。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湘西已经改变了,他的作品成了湘西的一首首挽歌。
沈从文先生在谈到自己作品时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他的小庙就是他的湘西作品,里面供奉的是优美、自然、健康的人性。我们现在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不得不承认文学是真的有所谓永恒主题的,所有人都是阿Q,无论现实如何纷扰,社会如何发展,人人都需要精神家园,我们愿意品读这样给我们带来无穷美感的伟大作品,一代又一代享受这纯美的世界。
[1]沈从文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2]名作欣赏[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9.
Beauty Always Makes the Sad Feeling——Analysis on Three Girl Images Shen Congwen’s Works
FENG Qiao
(Tianji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Tianjin 300280 China)
Shen Congwen devoted great passion to images of young girl in his works of western Hunan,Cui Cui,Xiao Xiao and San San are three beautiful young girls who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images.The fine feelings from three girls’innocent first love show a beautiful life,however,light tragic colors always hang over the endings.These kinds of tragedy are accidental wrong fate arrangements rather than human factors.
western Hunan;young girl;first love;human nature;elegy
I06
A
1673-582X(2010)03-0130-04
2009-11-20
冯俏(1971-),女,河北省广平县人,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文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