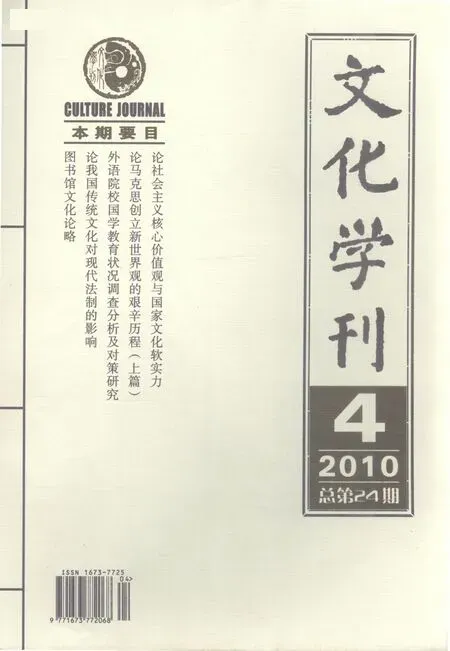论《西游记》的民俗审美与游戏主题
高日晖 李建忠
(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关于民俗的游戏娱乐性质,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写道:“民俗的娱乐功能显而易见”,“人不可能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劳作,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休息体力,调节精神,享受劳动成果,进行求偶、社交等活动。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没有节日、游戏、文艺、体育的民俗,它们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1]也可以说任何民俗都带有游戏的性质,这种民俗的性质可以反映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为人们所容易接受的通俗白话小说中,《西游记》正是这样一部小说。不论是它的形成、创作过程,还是在形成以后对后世的民俗审美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就有意地加入了游戏成分,清人任蛟在《西游记叙言》中曾经提到:“以戏言寓诸幻笔。”[2]鲁迅也曾经说过:“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3]
民间传说、神话和风俗习惯对于《西游记》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该小说大量吸收民间文学进行创作,民间文学中的美和游戏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小说中,这种民间文学中的美和游戏性是不可分割的,下面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仙界描写的非严肃性
《西游记》中有很多关于仙界的描写,但是这种描写并不是写仙界的庄严肃穆,即使是庄严的仙界也是为了衬托猴子的戏谑,可以说游戏性是占首位的,作者从娱乐性的角度来刻画这种环境。这点从《西游记》题材的累积发展中就能体现出来:在《西游记》形成以前的一些作品例如《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以唐朝和尚取经的事情为依据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是摆脱了纪实的桎梏,以取经故事为蓝本融入了一些传说和神话,作者自己创造出了“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孙行者和沙和尚的原型“深沙神”,然而这时候的故事底本还不具备很强的民俗特征,这在对仙界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3回中写道:“行者教令僧行闭目。行者作法。良久之间,才始开眼,僧行七人,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宫了。且见香花千座,斋果万种,鼓乐嘹亮,木鱼高挂;五百罗汉,眉垂口伴,都会宫中诸佛演法。”[4]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描写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而《西游记》中关于严肃的仙界的描写变少了,替代的是非严肃性的带有戏谑意味的仙界,在第5回中,玉皇大帝为了安抚孙悟空将其封作齐天大圣,让他去掌管蟠桃园,猴子的本性就喜吃桃,结果没过多长时间那大圣“脱了冠着服,爬上大树,拣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本来一个为蟠桃盛会提供果品的地方,结果成了他享用美食的圣地。后又因为蟠桃盛会没有邀请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变作赤脚大仙到蟠桃宴上,闻见酒香“口角流涎”,把那些个力士、道人用瞌睡虫弄得睡着了,自己开始吃那些美味佳肴,等到吃喝得差不多了才想起“不好!不好!再过会,请的客来,却不怪我?一时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孙悟空明白自己搅乱了天宫,首先想到的是回府中睡去,既符合猴子的本性,又用这种笔法写出了非严肃性的天宫。在第1回中猴子去西牛贺洲去寻访神仙,遇一樵夫向他指路道:“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灵台”和“方寸”都是指心,而“斜月三星”也是一个心字,唐僧曾说过:“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可见在作者的眼中“心”是最重要的,万事从心生。
二、民俗叙述的趣味性
民俗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趣味性,而小说中的民俗成分更能体现其趣味性,《西游记》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民俗成分,就《西游记》的内容而言,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与游戏性也是非常广泛的。《西游记》所描写的情景不外乎作者的所见所闻和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构思与概括,《西游记》中关于佛教寺院的描写可谓繁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密切联系的,不仅是由于政府对寺院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更是由于在民间人们对于佛教的崇拜和关注。另外是小说中土地、山神和城隍的大量出现,“明代的洪武年间城隍改制,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城隍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使之成为天下通制”。[5]土地庙在各地也风行一时,由于人们对于城隍和土地的信仰,渐渐成为一种习俗、习惯,因而才有《西游记》中孙行者有不解之处先问土地、山神或城隍的描写。例如在第40回,唐僧被红孩儿捉住,孙悟空不明就里找出了山神和土地。神祗是高于妖魔的,可是在这里却反被妖魔控制,还要依靠大圣的力量来打败魔王,趣味性油然而生。明代当时就有这种城隍和土地庙,当时的江南和苏北的一些地区都有这种信仰,而且非常兴盛,加之官方的支持,以至于拜城隍和土地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件大事。猪八戒在取经路上出力也不少,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好帮手有时也有闹笑话的时候。在第32回中因唐僧护短,所以孙悟空只得想法子来让猪八戒去巡山,而悟空就变作小虫跟在他后面,戏耍于他,后见猪八戒“对石头唱个大喏”,“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而且等到快要见到唐僧的时候“又怕忘了那谎,低着头口里温习”。这些让我们更为生动地理解猪八戒的性格特征。猪八戒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所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很多民俗的影子,他老实憨厚,但是却好吃懒做,因为他老实所以唐僧处处维护他。也是由于他的性格,悟空经常捉弄他,他不敢当面冲撞,于是转而向唐僧告黑状,唐僧信以为真就惩戒悟空,悟空当面揭穿八戒的谎言,唐僧并未惩罚。由此观之,在作者眼里甚至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老实本分的人是可以受到褒奖的。
《西游记》中所有角色都充满了人世间的情意,作者使其都具有了人的性格。这样做可以更加体现出作品创作的游戏性。比如在作品第98回中唐僧师徒随阿傩、伽叶去认领经书,二尊者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因索要未成功,竟传他们无字真经,师徒四人到如来处告状,如来竟然如此回答:“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原来“人事”不论到了哪里都是需要的。即使把这种情况放到现在也是适合的,更不用说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了。小说的主人公孙悟空就是一个天生石猴,也具有很强的民俗特性,由于其早年的经历,一直到后来还是保持了一颗童心。比如在第51回孙行者上天查探怪物的来由,见到玉陛“朝上唱个大喏”毕恭毕敬,葛仙翁问其为何前倨后恭,他回答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没有了金箍棒的孙悟空见到玉陛之后也要唱个大喏。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可算是惟妙惟肖。
三、俗语运用的幽默旨趣
《西游记》中有很多民谚俗语,这些俗语运用得非常广泛,大部分都是出自唐僧师徒。俗语内容浅显易懂,有一些是继承前人的,也有的是《西游记》中所独有的,不过,也可能是从民间大众的口中得到的。田同旭提到过《西游记》中的俗语,“无论出自何人之口的俗语、谚言,皆富有哲理,又体现出世俗化倾向,使孙悟空、唐僧以及神佛、妖魔,从神秘的神魔世界进入人类社会,具有明代世俗社会的人情味”,“不仅仅是个小说语言风格的问题,它还给人们认识明代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追求,认识明代社会的时代特点与世俗风气,提供了一部形象生动的教科书。”[6]不论这其中的俗语是来自何地,都深深地打上了民俗的烙印。由于猪八戒在高老庄的生活经历,所以他口中的俗语充满了幽默旨趣。在《西游记》第26回中有关猪八戒和福禄寿三仙的一段描写:那八戒见了寿星,近前扯住,笑道:“你这肉头老儿,许久不见,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来。”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拍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进禄’也!”那寿星将帽子掼了,骂道:“你这个夯货,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个夯货,反敢骂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寿’、‘添福’、‘添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中的“讨彩头”、吉利话在这部著作中的表现,同时猪八戒的行为也能够让人开怀大笑。除此四人之外,也会有其他人说出一些俗语来。比如在第71回中朱紫国娘娘口中就说出:“大王何为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个御虱。”这样带有幽默性质的民间俗语,将孙行者的机灵和妖怪难为情的窘迫的情形展露无遗。在第72回中孙行者说:“我若打他啊,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孙悟空的调皮通过这种浅显易懂的俗语展现出来。第83回托塔天王和哪吒太子去捉妖怪,老怪向太子求情,太子说:“这是玉旨来拿你,不当小可。我父子只为受了一炷香,险些儿和尚拖木头,作出了寺。”第91回中妖怪向悟空喝道:“你是那闹天宫的孙悟空?真个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羞煞天神!你原来是这等个猢狲儿,敢说大话!”这些民间的俗语、歇后语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
正是由于民俗的美和游戏主题的进入,才使得《西游记》充满了历久不衰的魅力,即使在知识和文化如此丰富的今天,《西游记》的影响力也没有丝毫的减退,而且还促进了中国民俗的发展。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1.
[2] [3] 朱一玄,刘梳忱.西游记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360.47.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70.
[5]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3.
[6] 田同旭.〈西游记〉俗语中的人物性格和时代特色[J] .淮海工学院学报,2006,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