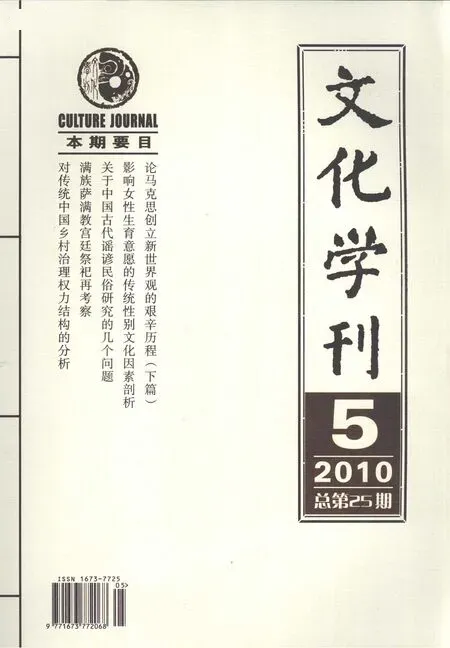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再考察
苑 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7)
一、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典籍与研究概述
关于满族宫廷萨满教的始末,据乌丙安、刘厚生、姜相顺等学者的考察,其始于17世纪初后金和清代的宫廷,终于1924年清王朝末代皇帝移出皇宫。[1]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已经不可能如同对满族民间萨满教进行当代活动的考察那样,对业已消歇了近一个世纪的宫廷萨满教祭祀进行现时性的考察了。然而要对在后金乃至清代宫廷活跃了近三个世纪的满族宫廷萨满教进行考察,我们却并非是无据可依的,目前这方面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关于宫廷萨满教祭祀文献以及往昔宫廷祭祀的场所。基于此,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对满族萨满教的宫廷祭祀进行细节的描述和全景的还原。
“盖自大金天兴、甲午以后,典籍散佚,文献无征,故老流传惟凭口授,历年既远,遂不甚可明考”。①阿桂于敏中:《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跋语。这段写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跋语中的话意在说明清代宫廷萨满教祭祀中神名歧义失解的现象与原因,然而用它来概括清代宫廷萨满教祭祀整体之状况也较为恰切。众所周知,萨满教作为一种原生性宗教,其传承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其领神人——萨满代际之间的口传心授、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比之于其他创生性的宗教,萨满教没有世代流传的教义经典。然而,作为萨满教典型形态的满族萨满教拥有较为完备的历史类型,其中作为国家形态的满族萨满教,唯其受到统治者的规范并颁布了著名的“民族宗教法规”[2]而得以有文本传世,这就是备受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满文本颁布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其汉译本问世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并同时收入《四库全书》,后又有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的《满洲跳神还愿典例》。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上述三个版本中“自然是作为祖本的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洵属可贵,它是研究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主要依据”。[3]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尝试对该法典的重要性作了以下概括:第一,《典礼》正文分为六卷,一至四卷为祭神祭天的神、礼仪、祝辞等内容,五卷为祭神祭天器用数目,六卷为祭神祭天器用图。这些极为详尽的规定是我们了解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各个细节的最佳途径;第二,与《典礼》相关的一系列文献,比如乾隆皇帝为编纂《典礼》而给内阁的《上谕》、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为编纂事宜而呈给皇帝的《奏折》以及附于《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对我们了解《典礼》成书的缘由、具体要求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我们对典籍所记载的满族宫廷萨满教的状况的了解和认知,不仅源自于我们对《典礼》等文献的阅读和总结,还建立在对学术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其中一些是专门以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为对象论著,比如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教祭祀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刘厚生、陈思玲《〈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评析》(《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刘厚生《一部鲜为人知的萨满教典籍》(《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郭淑云《〈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论析》(《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涉及了这方面研究的论著,比如《满族萨满教研究》,上述研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满族宫廷萨满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证,而限于本文的篇幅以及论述重点,我们只对相关的问题加以说明。
二、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分类
学术界素来重视对萨满教神灵以及神灵观念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满族宫廷萨满教神灵体系的研究。学术界向来将对神灵进行分类视为对神灵体系进行认知的重要方式。以往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体系的分类都是以宫廷祭祀的具体情况为依据的。
(一)传统的分类
《典礼》等典籍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记录本身就包含着对其所祭祀神灵的分类。比如,按照祭祀场所分类,分为:堂子亭式殿所祀神灵、堂子尚锡神亭所祀神灵、堂子飨殿所祀神灵、坤宁宫所祀神灵、祭马神室所祀神灵(除翌日祭天,与坤宁宫所祀神灵相同);再如,按照祭祀种类进行分类,分为:堂子圆殿元旦拜天、堂子月祭、堂子立杆大祭、堂子浴佛、堂子尚锡神亭月祭、为马祭神于堂子圆殿、出师祗告及凯旋告成于堂子、坤宁宫元旦行礼、坤宁宫日祭、坤宁宫月祭、坤宁宫报祭、坤宁宫大祭、坤宁宫求福、坤宁宫大祭翌日祭天、坤宁宫四季献神、正日为所乘马于祭马神室、次日为牧群繁息于祭马神室等所祭祀的神灵。[4]
藉此两种分类方法,我们不仅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体系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场所、时间(频率)乃至祭祀种类都有所认识,可见,传统的直观的分类方法是有着基础意义的。
(二)新观点的提出
当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也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对象时,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提出了新的分类尝试,比如姜相顺将其分为天神类、祖先神类、自然神类;郭淑云将其分为自然神、氏族守护神、祖先英雄神。显然,这两位学者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的分类打破了以往按照祭祀场所和种类分类的限制,推动了人们在这方面认识的深化。然而,这种就神灵本身而进行分类的方法没有将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中,因而仍然不足以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乃至整体进行充分的说明。
(三)小结
从上述两方面看来,学术界以往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的认识上存在着为分类而分类的局限,基于对这种局限的认识,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把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与其信仰和实践者联系在一起来说明问题。刘厚生认为,“阿珲年锡(农神)、尚锡之神(农神)、安春阿雅拉(祖先神)、穆哩穆哩哈(马神)、纳丹岱珲(星神)、纳尔珲轩初(星神)、恩都哩僧固(星神)、拜满章京(祖先神)、纽欢台吉(祖先神)、武笃本贝子(祖先神)、喀屯诺延(蒙古神)等等,这一系列神灵充分展示了觉罗氏“万物有灵”多种崇拜的宗教观念。由于历史久远,有的神已不知其源起,如纳丹威瑚里、恩都蒙鄂罗,虽经清乾隆帝亲自主持,“询之故老,访之土人”,也无法说得清楚,这些代表着觉罗氏萨满信仰的古老神,无论在《典礼》颁布以前还是之后,均无法在满族其他姓氏中觅寻得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说明,“满族萨满教始终保持着原始的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民族宗教的特质,传统的势力在这里表现出极大的历史惯性和难以想象的凝聚力,所以才造成每个姓氏在所信奉的神上,以及萨满祭祀里以上的大大小小的差异。”[5]而孟慧英认为“,朝廷颁布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在满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神,如阿浑年锡、安春阿雅拉、穆林穆林哈、纳丹岱浑、纳尔浑轩初、恩都哩僧固、喀屯诺延、佛立佛多鄂莫锡妈妈等,都是相当古老的萨满教神和守护神,再结合皇帝氏族祭祀的神灵,组合成一个新的堂子神群。被保留下来的传统神,对那些被剥夺了萨满和氏族神的部众来说,是个安慰,具有稳定民心的作用。”①孟慧英:《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萨满教特点》,未刊稿。
可见,虽然上述关于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也不乏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在阐释神灵与祭祀主体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对于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进行认知的新视角;其次它们共同承认满族的统治者群体(觉罗氏族或皇帝氏族)所信奉的神灵在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将问题延伸至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性质和功用的探讨,比之于学术界以往依据萨满教信仰的某种神灵类型来规定萨满教性质的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显然融入了宗教社会学视角。就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性质而言,我们有必要对其主体——满族统治者群体身份抑或是其所属于的社会组织类型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主体及其身份界定
(一)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主体
通过对满族萨满教的历时性考察,我们发现,从宏观上讲,满族以及清代统治者群体是推动该民族原生性信仰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而从微观角度看,这个群体也是满族萨满教的宫廷祭祀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这种祭祀活动的实质的认识有赖于对该祭祀的主体,即统治者群体身份的认知。学术界业已开展的对满族以及清代统治家族姓氏和世系源流的考证等工作为这一问题的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大多数从事满族萨满教研究的学者们还没有在宗教和社会相互关联的语境下对这个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主体的性质
我们说满族萨满教研究还没有充分开掘宗教社会学的视角,这种状况也同样存在于学术界以往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研究当中:比如学者们通常比较重视统治者群体对满族萨满教的作用和影响,却常常忽略在满族萨满教发展变化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关于统治者群体性质演变的信息;再如,满族萨满教研究中经常以“皇族”或“爱新觉罗家族”来指代满族宫廷萨满教祭祀之主体,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群体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明确的界定。
众所周知,满族和清代的统治者群体的姓氏是“爱新觉罗”,人们通常称其为“爱新觉罗氏族”或“爱新觉罗家族”。然而“氏族”与“家族”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将“氏族”、“宗族”以及“家族”等还原到满族社会的语境中。研究表明,满语的哈拉(hala)汉译为氏族或姓,满语的穆昆则汉译为宗族或氏,乌克孙(uksun)则是汉语“家族”的意思。作为满族社会血缘组织的三种形态,三者之间是既有重合又有递进的关系,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它们又是内涵各有不同且形式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同时,经由对文献的考证和对满族社会的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穆昆组织不仅是满族社会当中最为典型的血缘组织,还是满族各个血缘群体的最为稳固的自我认同基础,故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满族民间,“穆昆”这个称谓一直以来都被作为“哈拉”、“穆昆”和“乌克孙”三种血缘连续体的统称而使用。
我们在对上述背景知识认同的基础上,已经对满族的统治者群体的性质有了相对稳定的认识:以“爱新觉罗”为徽号的六祖子孙最初作为从觉罗哈拉中析解出来的显贵分支,在日后女真各部统一、满族的形成和崛起乃至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上升为全国的统治者群体;它是一个极大地融合了政治和权力因素但仍以血缘组织形式为外壳的穆昆组织,不仅如此,以其为中心最终形成了清代皇族的宗室、觉罗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经由对满族史材料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那么统治者群体的组织性质在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有关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文本透露了其祭祀主体由觉罗哈拉到爱新觉罗穆昆演变的信息。
颁布于乾隆十二年的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上谕开头为:“meni gioro hala wece(re)ngge oci……”,其汉译应为“若我觉罗姓祭神”;作为《典礼》参照的满文《钦定满洲祭祀条例》中上谕首句也为“meni gioro hala wece(re)ngge……”,汉译为“吾等觉罗哈拉所祭者”。而后来颁布的汉译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的上谕则为“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典礼》的满文参照和满文本与后来的《典礼》的汉译本在上谕首句上的差异说明,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主体最初曾经是作为原初性血缘群体的觉罗哈拉,而不是在满族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才产生的爱新觉罗穆昆;同时,《典礼》在对祭祀仪注作以说明的时候,规定“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洲人等”用统一仪注。结合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这一规定,从事满族史研究的学者指出,“我们知道满族的祭祀跳神仪注,因姓氏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这条规定,将皇宗、宗室、觉罗、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并列,正说明他们原始是一个‘哈苏里哈拉’。”[6]此外,从满族萨满教祭祀的传统来看,主祭人在请神时要先向神灵报告请神的是哪个家族,为何原因等等。而在报家族名号的时候,通常要先报“哈苏里哈拉(hasuri hala)”,其汉译为原始的本姓,然后再报穆昆哈拉(mukun hala),①穆昆哈拉之所以连用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二者作为社会组织的角度讲,历史上满族社会组织曾经历过穆昆宗族从哈拉氏族中析解出来,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独立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被称为哈拉—穆昆,或穆昆哈拉,参见拙文《满族穆昆组织在部落国家时代的演变》,载《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其次,从二者作为组织的名称以及徽号讲,哈拉(姓)是整个氏族时代的氏族的名称,穆昆(氏)是宗族部族时代氏的徽号。然而氏族组织到了宗族部族时代已经没有实质性功能的时候,姓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于是姓氏合而为一,满语称为穆昆哈拉。参见魏业、杨茂盛:《论哈拉、穆昆与姓、氏的联系及义》,载《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即由哈拉析解出来的穆昆的徽号,将这个程序完全按照汉语意思进行,就是先报“姓”,后报“氏”。考察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程序也正是如此,比如其“祭天赞辞”中自报姓名的部分首先就是“安哲上天监临我觉罗某年生小子某”。
上述三个细节性的例证,无论是从对社会群体考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满族史研究的方面入手,抑或是以对满族萨满教的民族学实地考察为证,都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满族及清代统治者所属的爱新觉罗穆昆经历了从觉罗哈拉中析解出来,并逐渐成长为富强的乃至统治穆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个统治为自己“立宗命氏”,定徽号为金,即爱新,这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满族社会对正在形成中的宗族部族权力予以合法化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满族萨满教中某些祭祀权力的垄断来证明本穆昆拥有“天赋”的权力。
其次,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以及围绕这些神灵展开的祭祀活动的性质,反映了其祭祀主体不仅是一个显贵的血缘群体,还是一个以政治和权力因素为核心集结起来的政治和权力组织。
在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神灵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具有非常突出的血缘性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是不能仅仅被视为等同于那些具有严格血缘性质的满族民间萨满教的,它是在血缘基础上大大地融合了地缘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并因此而具有国家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
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国家宗教性质在清宫堂子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皇太极在崇德元年规定堂子圆殿元旦拜天制度,确立堂子祭的国祭地位:“每年元旦,皇帝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堂子首先是皇帝的萨满祭祀场所,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满洲亲贵和来盛京的外族藩王都跟随皇帝上香行礼参加祭祀,从而使堂子祭成了国家的萨满祭祀。亲王多为爱新觉罗氏子弟,随皇帝祭堂子名正言顺。但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官员有不少异姓满洲,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和皇帝统治下,他们已不再有本氏族部落的堂子,礼拜爱新觉罗氏的堂子虽然名不正也只好顺从。外藩诸王(主要是蒙古贵族,多有姻亲关系)参加堂子祭则主要是表示政治上的附属;再如,满族萨满教代宫廷祭祀的这一性质还突出表现在其祭祀者的身份上。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形成以皇帝为首的行祭和参祭组织,在这里,皇帝也就是主祭者不仅是其所属的血缘家族的家族长,还是整个国家的领导者和政治权力的象征。同时,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还专门配备了侍候神灵、进行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也就是宫廷萨满,对于这种角色的性质,已有学者作出明确的说明,指出要成为宫廷萨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必须是爱新觉罗家族氏族的萨满;二、该萨满必须是拥护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特别是在努尔哈赤崛起时原先附从尼堪外兰的堂子中的萨满也必须是转变立场。”并由此得出结论,“清宫萨满同其前产生的萨满不一样,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不仅如此,宫廷萨满在日后还出现了“氏族家族性的松动”。①参见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也就是说,这一角色最初所包含的血缘因素进一步弱化,②这种弱化表现为,《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规定,皇子祭神所使用的萨满既可以在“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之下觉罗”妻室中选用,也可以在“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洲人等妻室”中选用,此外,“如属下并无为司祝之人”,还可以“在各属下包衣佐领管领之下满洲妇人内选择,令其为司祝以祭”,甚至可“另请司祝”。参见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而伴随宫廷萨满血缘性弱化的是“宫廷萨满司祝性的定型”,③这种弱化表现为,《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规定,皇子祭神所使用的萨满既可以在“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之下觉罗”妻室中选用,也可以在“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洲人等妻室”中选用,此外,“如属下并无为司祝之人”,还可以“在各属下包衣佐领管领之下满洲妇人内选择,令其为司祝以祭”,甚至可“另请司祝”。参见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这两个相互伴随的现象或许能说明很多关于宫廷萨满教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满族宫廷萨满教日益冲破其只作为血缘群体局部利益和制度的代言的限制,并最终向着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礼制方向发展。
四、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性质及其对民间萨满教活动的影响
前文在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整体概况进行把握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探讨了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神灵问题和主体问题,并且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都涉及了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性质的考察。学者们以往在这方面虽然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但是结合我们的考察,我们仍可对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性质乃至作用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认识。
首先,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的原型是觉罗氏的萨满教信仰和实践体系。与满族其他姓氏的萨满教体系一样,觉罗哈拉的萨满教体系也具有突出的血缘性质,其具体表现为:它拥有在满族其他姓氏中均无法寻觅得到的个性化的神灵群体;它要求主持祭祀的萨满必须具有爱新觉罗家族血缘的身份。它祭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家族的名誉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仍然保持了以原始的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民族宗教特质。
其次,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是满族萨满教发展到国家宗教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国家宗教形态,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在神灵方面虽然仍以其“哈苏里哈拉”,即觉罗哈拉的神灵体系为主要崇奉的神灵,但同时也融合了满族其他姓氏的神灵,因此是一个经过组合而成的新的神群;在进入稳固的国家宗教阶段之前,爱新觉罗氏的祭祀已经成为以本血缘群体为主,同时允许其他姓氏参与以示臣服的礼制性活动,在其进入宫廷之后,这种礼制性日益强化,同时,其原有的氏族血缘性日益弱化,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最终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礼制。
最后,在这里我们还要列举一些有关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对民间萨满教活动影响的观点。比如一些学者指出,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即以爱新觉罗氏的堂子祭为模本总结而成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是“用爱新觉罗家族的萨满祭祀以法典的形式将满族诸姓世世代代传袭的萨满祭祀加以规范、定型和划一”,“尽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针对的是宫廷祭祀,但对满族诸姓却有着很强的制约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以爱新觉罗本姓的祭祀规法来对民族文化进行规范”;①孟慧英:《通古斯语民族萨满教特点》,未刊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满族萨满教宫廷祭祀是整个觉罗哈拉所共有的祭祀礼仪的总结,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作用和价值“恰恰在于它承认‘姓氏各殊,礼皆随俗’这一萨满教的现实和特性,总结和宣扬了包括爱新觉罗氏在内的整个觉罗氏的萨满信仰习俗,保留了许多觉罗氏原始崇拜意识观念,客观上对民间萨满信仰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又完整地体现了满族统治阶级上层对萨满信仰的理解。《典礼》的颁布,其实际的目的,不在于将整个满族萨满教加以规范和划一,而是将萨满教作为一种满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始终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清朝统治者在民族旗帜的掩盖下便于调和满族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借以稳定清朝封建统治的秩序。清朝统治者始终以‘首崇满洲’的狭隘民族形式,与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效果,这是满族萨满教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重要原因。”[7]我们所列举的上述具有互补性的观点,基本上涵盖了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较为中肯的认识,因此这里不再对其进行再阐释。
[1]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教祭祀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2]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57.
[3][5][7]刘厚生,陈思玲.〈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评析[A].张璇如,富育光.孙运来.萨满文化研究(第一辑)[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58.
[6]薛虹.满族萨满文化史料在满族先史史料学上的价值[A].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C].长春:文史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