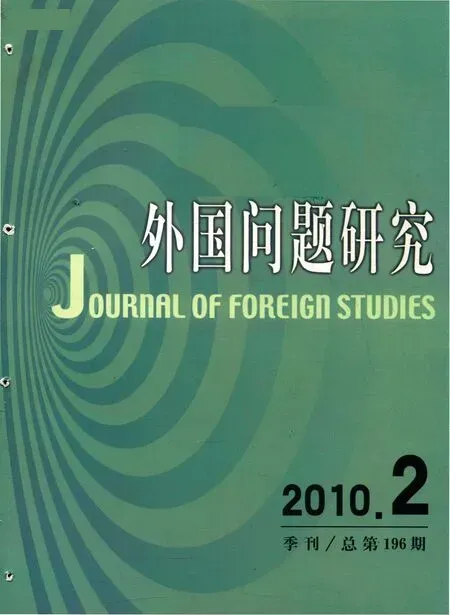《且听风吟》的互文性文本策略
刘研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且听风吟》作为村上的开山之作至今已逾三十年,此间村上文学硕果累累,站在今天的时点,纵观村上的文学世界,我们不得不说:“任何作家的处女作都是极其重要的作品,因为在处女作中作家已经表达了全部,村上春树就是这种情形。”[1]因此有研究者说:“村上春树借助这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俨然一篇文学宣言。”[2]
村上善于在小说中设置充满相互指涉和隐喻的迷宫,制造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这其中互文性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策略。“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3]《且听风吟》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小说文本与历史史实的互文,小说文本与音乐以及广播、电影的互文,文本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内部的自我指涉间的互文。
一、小说文本与历史史实的互文
《且听风吟》由名言警句式的四十个断片构成,叙事时间始于1978年,29岁的“我”决定一吐为快,于是讲述了“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十八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的故事。
1982年,日本著名批评家三浦雅士对《且听风吟》的故事如此重述:“恋人自杀的大学生暑假回到家乡,与一个怀孕的并被与之不相干的男友抛弃的女子相识,这个年轻的女子是唱片店的店员。不经意间二人就相互的忧郁体验有过几次交谈和见面。在女子做完堕胎手术后的夜里两个人什么也没做相互抱在一起睡着了,那是二人的最后一夜。”[4]平野芳信认为三浦雅士的重述完全忽略了小说另一重要人物“鼠”的存在,他细读文本后认为“缺左手小指的女孩”是“鼠”的女朋友,使“鼠”备受困扰的女性就是她,而“我”隐约知道她和“鼠”的关系,也知道她在唱片店工作,他委婉地试图劝说“鼠”,如买唱片送“鼠”的那一细节,然而一切终归一场空。所以他说:“《且听风吟》这部作品,既描写了‘鼠’和‘缺小指女孩’的现在完成型的恋爱,也透雕镂刻了‘我’的过去完成型的恋爱,是明确呈现这一二重构造的作品。”[5]不过,石原千秋却认为平野芳信的观点也只是看到了作品的一部分,他指出,“故事的表层,如三浦雅士所读出来的那样,是‘我’与‘缺小指女孩’那不能称之为‘恋情’的淡淡的关系构成的;故事的内里就如平野芳信所读出来的,是‘鼠’与‘缺小指女孩’的物语。这一故事是‘我’与已经死了的‘和我睡觉的第三个女孩’的故事(这部分被深层隐藏起来)的延续,所以虽说是两组男女的故事,却是‘我’与‘鼠’与‘缺小指女孩’三人关系变换的故事(这是故事表层所潜藏的)。由此而演变成表层故事比深层故事还要复杂的复线结构。”[6]
然而,尽管1970年8月8日开始的故事很热闹、很复杂,但不容置疑的是,作品主人公们的生存状态却与1969年8月15日到1970年的4月4日之间发生的故事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深层故事——“我”和“和我睡觉的第三个女孩”的故事是“我”要一吐为快的直接动力。如果把过去的时间再稍稍向前延伸,可以追溯到“我”和“鼠”初识的1967年,而在小说的第一章就谈到“我”的精神创伤源于十五年前的1963年——“大约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7]3。第6章“鼠”引用了肯尼迪说的话,第9章“缺小指女孩”在梦呓中重复肯尼迪的话,第26章“和我睡觉的第三个女孩”送给他一张她人生中最美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3年8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7]76第31章鼠边摆弄着胸前的肯尼迪铜钱,边闲谈着美军对日本实施的军事占领。“肯尼迪”无疑成为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青年茫然却又十分投入地追随着“民主主义”和个人理想,所谓民主象征的美国及其领袖肯尼迪自然是他们崇拜的偶像。第一章在“大约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这一句之后,沉重地说自己在这十五年中丢弃了很多东西,自然包括孩提时的梦想,热血青春的理想。“鼠”说自己挨了警察的揍,我也对“缺小指女孩说说”自己参加了游行示威,还被机动队员打断了门牙。如果说“肯尼迪”还有些虚幻的象征意味,1968年到1969年席卷日本全国的学生运动却真实无比,小说展现的恰是学生运动走向溃败,年轻人在激情消散后的无所适从。因此村上在谈到写作最初的动机时说:“70年代的十年间是60年代的‘残物整理’。写点这个‘残物整理’比起直接写60年代对我个人来说有更正确的意义。”[8]
于是研究者们把视线集中到《且听风吟》中60年代的这三个时间轴:29岁(回忆的现在),21岁(故事开始的舞台)和过去(1969年8月15日-1970年4月4日;1967年;1963年),其实贯穿这三个时间轴的还有一个更为久远的时间轴,即战争时代。第一章在叙述自己写作的理由时很唐突地插了一句:“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演出。”[7]328章回顾了“鼠”的父亲的血腥发家史,这一发家史正是日本战时和战后发战争财的上流人物的写照。杰氏酒吧的老板杰虽然不是主人公,这部小说关于杰的描写也仅是寥寥数语,我们只知道杰是一个比日本人日语说得还要俏皮的在日中国人,还知道他的酒吧是小说故事得以展开的舞台,更是“我”这群迷茫青年的“乌托邦”和栖息地。在《1973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中我们得知侵华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些发生在东亚的战争与杰的一生紧紧纠缠在一起。《且听风吟》的结尾第38章“我”去酒吧与杰告别,杰说:“不过过几年想回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我都这样想。”[7]117杰从我的口中听到“我”叔父是在中国死的,杰答道:“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①笔者注,林少华译本翻译了前半句,“不过大家都是兄弟”这句话没有翻译。。”[9]饱经风霜的杰传达的是爱与和平,相对于从十七岁到二十岁左右的“我”和“鼠”,他就是“我”和“鼠”的精神父亲。返回东京的汽车上,乘务员对他说:“21号中国。”“中国?”我不解其意,其实以中国(China)作为座位表的C座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为什么我会不知所措,因为我还沉浸在与杰对话的冲击波中。我们在村上日后的创作中看到了他强烈的书写历史的欲望,《且听风吟》中对历史的回顾还是下意识的,更多地表现为他对那场战争的复杂心态:既反讽自己的父辈,又对受害国——中国心怀愧疚和某种恐惧。这种心绪很快在他的第一个短篇《驶向中国的小船》中进一步展开,十几年后他在《奇鸟行状录》中终于将战争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编织进文本。
当我们把小说的四个时间轴并置在一起,小说讲述的就不再是夏日十九日间的浪漫物语了,尽管大家公认村上的转型是在他创作《奇鸟行状录》的1995年,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这一点恐怕作家本人也没有鲜明地意识到,他从创作伊始就从未离开过日本的政治与历史,始终都在关注着当代日本人的精神危机,只不过这里的呈示更为隐蔽和无意识化。小说中的四十个断片在历史事件的ON与OFF之间,不断重复、代替和置换,历史史实和文本虚构融合在一起,打破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赋予了读者无限延展的思考空间。
在这里,村上也初步展现了自己鲜明的历史意识。第21章,小说插入“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女巫》”。儒勒·米什莱是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撰有《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等著作,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死去各代人的已死的声音‘复活’,尤其是过去记叙在‘历史’中未曾记载的声音”[10]。村上的引用正是对一元性的正义的嘲讽与颠覆。第26章我在第三个女友14岁最美的照片中窥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影子,第34章与第三个女友相关的情节中写道:“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我们实际上经常说谎,也常常沉默不语。”[7]101何谓真实,何谓谎言?历史的讲述更是如此,村上通过文学虚构质疑了宏大叙事中的谎言与沉默,复活了在历史洪流中被席卷而去的普通青年人的青春与人生。所以他说,“我这里能够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画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7]5
二、小说文本与音乐以及电影等媒介的互文
美国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以及电影这些亚文化形态构成了村上小说的重要背景。《且听风吟》中此处的文本和彼处的文本在空间上呈共时联系,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呈历时联系,小说文本自由地穿行于文学、哲学、历史、音乐、电影、广播等诸多文本中,任何一个读者阅读小说,也就同时与各类古往今来的文本展开对话。
小说11章、12章和37章分别是电台播音。11章直写了“ON”与“OFF”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存状态:ON,“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神气得不得了……安安静静地听着,实在妙不可言,热浪一扫而光”;OFF,“啊……简直热死了……这里快成地狱了……我都给汗浸透了。”12章中DJ向我阐明“广播”“就是文明孕育的……唔……最好的器械”,“一定要听广播才行!看书只能落得孤独”。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电台的出现与近代文明的产生密切相关,而主持人‘ON’的世界代表了以近代文明伦理性做依据的语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理应传达真实的信息。但对比‘OFF’的世界便会发现,‘ON’的世界里的语言表述与实际相差何其之远。”[11]我们开启(ON)文明的时候,我们必然关闭(OFF)了那些貌似粗俗的人类的自然需求与欲望。不仅如此,DJ的声音、沙滩男孩的《加利福尼亚少女》都是通过电波传到我们耳中的,如果不打开收音机的开关,电波的声音与音乐声就都不能传来;拿起电话,话筒的另一侧传来DJ和“缺小指女孩”的声音。如果不拿起听筒,他们的声音都不能传来。37章是一封听众来信,来自一动不能动地躺在病床上的17岁少女,她的梦想就是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呼吸海水的清香,当然这只是一种奢望,她以这样的方式仍然顽强活着,还点了普莱斯利的《好运在召唤》这首歌。难怪以狗相声演员自居的DJ也热泪盈眶,喊出了“我爱你们”的话语。这一情节处在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它仿佛就是宣言书,就是这样一个难于传达与交流、艰难度日的境遇,我们还要顽强地活下去。29岁的叙述者“我”之所以记录这件事,是因为他从14岁到29岁一路挣扎行来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这个点歌少女的身上已经有了后来卡夫卡少年、笠原may、玛丽、高桥等村上年轻人物的核心精神。
“对于村上而言,音乐是进入深层潜意识——我们精神中那个亘古不变的另一个世界的最佳途径。”[12]《且听风吟》扑面而来的爵士乐主要有布鲁克·韦顿的《雨中佐治亚》、克里登丝·克里维特·里本巴尔的《雷雨初歇》、沙滩男孩的《加利福尼亚少女》、戴维斯·迈尔斯的《白衣少女》、鲍勃·迪伦的《纳什维尔地平线》以及普莱斯利的《好运在召唤》等,这些60年代音乐无疑构成了小说的时代氛围,吹着《米老鼠俱乐部之歌》的口哨,“我”想:“说不定真的算是不错的时代。”在这些背景音乐中,《加利福尼亚少女》尤为令人瞩目,这首歌现身于12、13、17、39章。11章是电台节目,12章中我接到了电台DJ的电话,说高中时代的女同学点歌给“我”,13章是《加利福尼亚少女》歌词,第14章是电台送来的T恤样式图,第15章是“我”穿着崭新的T恤,到港口的一家唱片店买《加利福尼亚少女》,再次邂逅“缺小指的女孩”,16章“我”和“鼠”在杰氏酒吧里碰面,将在唱片店买的生日礼物送给“鼠”,第17章“我”遍寻那位为他点歌的高中女同学,却始终没有影踪,我只好一边喝啤酒,一边听这首歌。这样一来,“我”与DJ、“我”与“缺小指女孩”、“我”与“鼠”乃至“我”的过往都因“加利福尼亚女孩”而联系到了一起。这首歌最后登场是在39章,回到了当下29岁,“每当夏日来临,我都要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7]121因此山根由美惠认为,这种倾听“成为夏日象征,成为回味过去的某种仪式”,“《加利福尼亚少女》是具有将与错综世界相连的‘这一故事’(この話)开启(ON),至8月26日讲述结束‘这一故事’(この話)关闭(OFF)功能的关键性存在。”[13]18这首歌的演唱者沙滩男孩创作了一系列以冲浪为题材的流行歌曲,但实际上他们远非冲浪爱好者,他们在孤独绝望中把音乐作为实现梦想的手段,作为自身的疗愈方式。其中的歌词“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加利福尼亚的……”原文为“I wish they are could be California girl”,“‘wish’意味着那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与沙滩男孩传达的梦已经不在的思绪相似,《且听风吟》的‘这一故事’讲述的也是梦的不在,特别是描写了如同《加利福尼亚少女》歌中吟唱的那样的女孩的不在。”[13]20所以,《加利福尼亚少女》不仅成了“这一故事”ON与OFF的关键,而且也应和了这部小说青春梦想已经不在的主旋律。
“我”送给“鼠”的两张唱片作为生日礼物也令人琢磨。其一是迈尔斯·戴维斯的《白衣少女》,迈尔斯·戴维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爵士乐坛的标志人物,其人其作是浸淫于爵士乐中的“我”和“鼠”所熟知的,陌生的是格伦·古尔德演奏、莱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3号。选择古尔德,而没有选择巴克豪斯的演奏,其实古尔德擅长巴赫,而巴克豪斯擅长贝多芬,但就个性而言,古尔德更显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孤独而异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最善于使用对比与发展的C小调,从此曲开始出现了贝多芬个性追求的那种戏剧性冲突,整部作品洋溢着刚毅、粗犷狂飙的风格,演奏的过程仿佛穿越黑暗,到达光明。虽然在这部小说中“我”送这样的礼物意义不明,但2002年创作的《海边的卡夫卡》中无论是少年卡夫卡,还是青年星野,他们走出人生的阴霾与惶恐与贝多芬等人的古典音乐都有着密切关联。
明里千章在《村上春树的电影记号学》中对村上与电影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序章的题目便是《作为电影的〈且听风吟〉》,他指出村上在小说创作中采用了电影的技法,而且在小说文本中涉及众多电影文本。34章讲述了“我”和第三个女友在去年秋天一起观看《桂河大桥》,电影以1943年日军在泰缅边境修筑铁路桥为背景,在一座日军战俘营,充满绅士尊严和大英帝国自豪感的英军军官、敢于行动的美军军官与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军官形成对比。英军战俘尼科森认为,战争总会结束,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建造这座桥的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批英国军人。逃出的美军战俘希尔兹前来炸桥,尼科森在检查时发现了引爆电线,争斗中被日军乱弹射中的尼科森阴差阳错倒在炸药引爆开关上,几声巨响,桂河大桥被炸毁,飞速驶来的火车也坠入河里,尼科森等人壮烈牺牲。女友问“我”为何死命炸桥,“为了保持自豪。”然而在战争的暴力和荒谬面前,自豪和荣誉到底有多重要?规则和纪律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39章回到29岁“我”的生活,“我”和妻子在看电影方面趣味相近,每当有萨姆·佩金帕的电影上映都去看,“我”中意的是《加尔西亚的脖子》,妻子喜欢《护航队》,之外的影片“我”喜欢《灰与宝石》,她欣赏《修女乔安娜》。萨姆·佩金帕素来以强烈的暴力和慢动作著称,而上述电影无不展现的是在压抑、暴力面前的不屈与反抗,这恐怕是和主人公心意相通的关键。
三、小说文本与经典文学、文本内部自我指涉间的互文
小说第5章写到了“我”正在看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且听风吟》与《情感教育》的人物设置和人生感受极其相似。前者写了两个青年“我”和“鼠”18岁到21岁在社会风暴余烬中的人生历程,后者描写了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和同窗密友戴洛立叶18岁到四十几岁的人生经历,戴洛立叶的内心世界仿佛欲望的海洋,一味沉湎于物质与肉欲的追求中,弗雷德里克鄙视情欲,一心追求精神之爱,然而人的精神之美也无法逃脱肉体的禁锢,最后他们的人生都以失败告终,福楼拜不仅揭示了一代年轻人悲剧的社会动因,还隐喻了人类在自我抉择中的茫然和无奈。所以《且听风吟》在开篇提到了这部小说,起到了提纲挈领式的作用,也暗示了《且听风吟》同样是部青年成长小说,同样在生命中体验着彻骨的徒劳感。
第9章“我”照顾醉酒的“缺小指女孩”,面对女孩质问“你是谁”,我在辩白中提到了《热铁皮房顶上的猫》,并说“每当我一个人喝酒,就想起那段故事,满以为脑袋里马上会咔嚓一声变得豁然开朗。”《热铁皮房顶上的猫》是美国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白手起家的富豪老爸身患重病不久于世,他的两个性格相反的儿子古柏、布雷克带着妻子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从白天到入夜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在贪婪、情欲、自我欺骗、自我麻醉等种种欲望炙烤中诸多人等都仿佛成了热铁屋顶上的猫。布雷克因自己误会挚友(即他的同性恋人)致使他自杀身亡,同时他认定妻子与挚友有染,更痛恨的是自己的两个挚爱对自己的背叛。“热铁皮房顶上的猫”显然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写照,但这里因为是“我”对“缺小指女孩”的解释,在小说文本的蛛丝马迹中,很多日本研究者认为这个女孩是鼠的恋人,尤其是“我”在对她讲到“鼠”时一直极其熟络地说“那小子”怎样怎样,言谈中有委婉劝说女子的味道,而到了35章、36章中,“我”和“缺小指女孩”的情感发生了微妙变化。如此一来,《且听风吟》就有了对《热铁皮房顶上的猫》中布雷克的故事戏仿的意味。
小说中说“鼠”惊人地不看书。可是从16章开始“鼠”开始苦着脸看书(其实“鼠”的名字本身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地洞》中的那个穴居小动物),先是看亨利·詹姆斯那本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笔者推测可能是《一位女士的画像》,詹姆斯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一位青年女性的自我评价和对世界的思索。之后18章“缺小指女孩”说“鼠”在读莫里哀,27章“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赞扎基思的《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鼠”在小说文本中读的最后一本书。《基督最后的诱惑》是走下十字架做一介布衣,享受肉体之爱、夫妻之爱、子孙之爱。然而,成为圣者必然要抛弃这一切,必然要直面世人不解的孤独,最终耶稣在弥留之际得知真相和自己的责任后,重返十字架牺牲自我拯救人类。卡赞扎基思如此阐述基督的本质——如人一般渴念,却又超凡地要从人身升华为神体,其内心所有的痛苦,喜乐和悲伤,都源自这灵与肉之间永不停歇的惨烈斗争。也就是在这一刻,“鼠”告诉“我”:“算了。”31章中“鼠”引用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话说:“汝等乃地中之盐。”接着又说:“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放弃了与女孩的瓜葛,放弃了尘世,由此开始自己的圣者之旅,这一点我们在后续作品《寻羊冒险记》中可知“鼠”为了消灭绝对恶的化身——羊终于献祭了自己。“鼠”与“我”的一体二元是极其明显的,“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既暗示其与基督有某种关联,同时又以相差一天来表明他绝非基督,日本有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上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到作家及他笔下的人物既为基督所深深吸引,但另一方面又对与自身语境不同的那个基督有所避让,他们无法从基督那里获得心灵的安慰。
《且听风吟》颇具元小说特征,不仅直接指涉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反映了作家在创作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且揭示了小说的编织技巧。“我”苦闷了八年之久决定一吐为快,29岁的“我”开始创作小说而“我”的文章写法大多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哈特费尔德是作家虚构的作家,虽然并不实际存在,但村上指出他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是同时代人,在小说文本中不仅引用了他的作品,虚构了他的传记,在40章还煞有介事地描写了“我”去拜谒哈特费尔德墓地,墓碑上还引用了尼采的“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哈特费尔德21岁开始创作,锲而不舍地战斗了8年零两个月,然后在1938年6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与之相应的是,21岁的“我”苦恼不已,倾听不已,终于在29岁时开始写作,尽管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尽管“我”对语言表达充满质疑,尽管我对“文明”多少有些不屑,但只有“传达”才能确认自我的存在,所以我必须写下去。
“鼠”很早就想写小说,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死亡与性爱是文学的两大主题。而“鼠”说:“或是为自己本身写……或是为蝉写。”“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每次写东西,我都要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7]90-91
哈特费尔德和“鼠”的文学追求极其相似,他也极少直接涉及人生、抱负和爱情,尾声中说“鼠”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由此,“我”、“鼠”、哈特费尔德的小说创作互相指涉,共同呈现了作家本人对写作的思索,而这种片段式沉思型写作形式又多少有些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子。
总之,在村上小说文本话语的背后,潜藏着很多欲言又止的片断。“开关……关。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声音的传送。开关……开,也不意味着仅有这些声音的传送。”[14]ON与OFF之间,我们再次品味到村上谜一般文学世界的魅力。
[1][日]清水良典.村上春樹はくせになる[M].朝日新聞社,2006:90.
[2]董群智.村上春树的文学宣言——《且听风吟》的一种解读[J].河南大学学报,2008(7):121.
[3]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75.
[4]转引自石原千秋.謎とき村上春樹[M].光文社,2007:23.
[5][日]平野芳信.村上春樹と「最初の夫の死ぬ物語」[M].翰林書房,2001:64-65.
[6][日]石原千秋.謎とき村上春樹[M].光文社,2007:96.
[7][日]村上春树.且听风吟[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8][日]村上春樹.インタビュー物語のための冒険[J].文学界,1985(8):36.
[9][日]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M].講談社,1982:146.
[10][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8.
[11]杨炳菁.试析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1):96.
[12][美]杰·鲁宾著.冯涛译.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
[13][日]山根由美恵.村上春樹「物語」の認識システム[M].若草書房,2007.
[14][日]小森陽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A].栗坪良樹,柘植光彦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01)[M].若草書房,199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