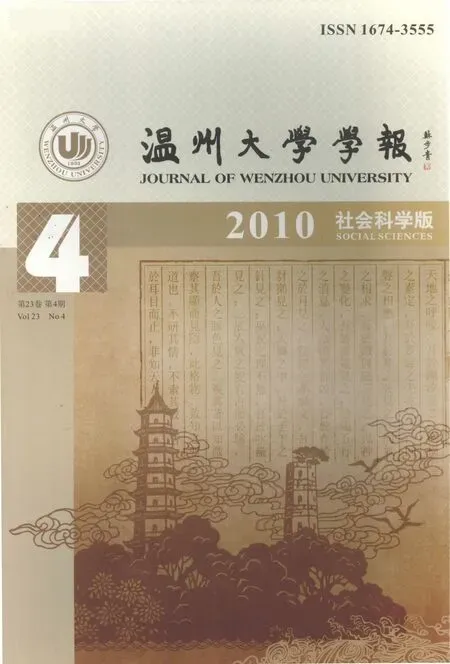精魂拘闭,谁之过乎?①
—— 道教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建构初探
康 豹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台北 11529)
精魂拘闭,谁之过乎?①
—— 道教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建构初探
康 豹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台北 11529)
1987年余英时先生发表了一篇有关招魂仪式的短文,其中对于地狱司法体系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促使研究者认真思考中国文化中宗教与司法的关系。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地狱信仰的历史与演变,尤其是Stephen Teiser(史太文)的两本专著分别探讨了佛教中元普渡与十王信仰的发展,对于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或许是因为上述研究把重点摆在中国佛教史这个领域,因而低估了中国本土宗教传统(特别是道教)在地狱信仰发展史中也曾扮演的关键角色。以余先生引述《太平经》地狱司法体系作为基础,可以说明道教对于中国法律文化之建构所发挥的影响。
宗教,司法,道教,佛教,地狱司法体系
1987年余英时先生发表了一篇有关招魂仪式的短文[1],其中引用古代道教经书《太平经》的文字以说明亡魂面对地狱司法体系的情形[2]615:
为恶不止,与死籍相连,传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时复出乎?精魂拘闭,问生时所为,辞语不同,复见掠治,魂神苦极,是谁之过乎?
余先生对于地狱司法体系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文化中宗教与司法的关系,笔者遂对此一题目产生很大的兴趣。实则从 198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地狱信仰的历史与演变②参见: Teiser S F.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Teiser S 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M].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泽田瑞穗. 修订地狱变: 中国の冥界说[M]. 东京: 平河出版社, 1991, 以及: 文献[21]; 文献[48]: 115-145.,尤其是Stephen Teiser(史太文)的两本专著分别探讨了中元普渡与十王信仰的发展,对于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或许是因为上述研究把重点摆在中国佛教史这个领域,因而低估了中国本土宗教传统(特別是道教)在地狱信仰发展史中也曾扮演的关键角色。本文以余先生引述《太平经》地狱司法体系作为基础,试图说明道教对于中国法律文化之建构所发挥的影响。
本文提出下列假设:1)在佛教信仰尚未传进来之前,中国本土宗教传统(包括道教)认为地狱是一种类似人间法院(衙门)或监狱的场所;2)除了地狱司法体系的信仰之外,道教仪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道教驱邪仪式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类仪式往往把驱逐妖魔鬼怪的过程当做神判仪式来进行,跟阳间真正司法审判有重叠之处;3)道教驱邪仪式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可以显示出其司法面向,它们特别强调所有鬼怪必须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方能受到惩处;其司法体系甚至也包含对道教的神明与神职人员的约束,构成了“司法性的驱邪典范(judicial exorcistic paradigm)”[3]38-39,[4]。
一、古代中国的地狱信仰
中国地狱信仰最早记载出现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当时已经把地狱想象成一种行政体系,里面的官僚是王室的成员,其工作范围包括了相关官方文书的编纂与处理[5]。此外,也有不少资料把地狱形容为一种又暗又湿的地下恐怖空间,并且用“黄泉”、“九泉”、“幽都”来称呼它[6]。关于地下世界这种可怕的形象,在《楚辞·招魂》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7]:
值得注意的是,幽都中的土伯有官员的特征,具有治理阴间的权利。据东汉文学家王逸的注解:“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除了《楚辞》之外,《庄子》也提到阴间的官员,就是负责计算活人阳寿的司命神。根据Donald Harper等人的研究[8-10],司命神具有明显的官僚特征,而他所统治的地狱行政体系已经出现了司法式的行为,因为活人可以透过此体系为刚往生不久的亲人申诉,请求司命神为死者延寿。
关于地狱司法体系的源流与演变,最关键的史料应该是秦汉时代的镇墓文。这类史料是由古代的神职人员所撰写的(可能还包括早期的道士),用以跟死者一起埋葬,目的在于帮助亡魂能够顺利通过地狱司法体系的各种关卡和考验。其后镇墓文所描写的司法体系也越来越复杂,官员包括土主、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等。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阴间与阳间的官僚体系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重叠之处,如镇墓文的一种“遣册”,在汉代官方文书中也相当常见。
镇墓文的另外一种重要的特色在于它们清楚地指出:阴间的官僚具有判决死者过错的权力,也可以对有罪的亡魂执行各式各样的刑法,所以镇墓文中经常出现一种法律用语“解谪”,希望死者能够被判无罪。又,在镇墓文里面,地狱的概念越来越具体,因为这些史料中常常用“狱”来形容阴间,里面的官僚包括“狱使”和“主墓狱史”,其所处理的事务以“狱事”为主。在镇墓文中一再提及中国地狱信仰重要圣地之一——泰山,它的主管神明“泰山府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东岳大帝)也被当作司法神来看待,泰山神不但负责监督阳间人民的行为,同时也掌管死者在地狱的判决与惩罚[11-13]。
这种地狱形象的出现大致上跟秦汉时期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法家思想的出现,各国也纷纷撰写“刑书”[14],国家运用合法性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越来越明显,到了秦始皇时代达到高峰[15-16]。当时国家法律权力的高涨,对中国古代宗教传统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所以Donald Harper曾经指出,早在纪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地狱司法体系就与战国时期的法律系统有许多类同之处[8]。
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代一直到今日,中国本土的地狱司法神(尤其是东岳大帝和城隍神)也是各种“神判仪式”的主角。所谓的神判仪式,是指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并且无法确定某一方有理或无理,乃至于有罪或无罪时,祈请神明裁决的仪式。这种神判的过程与人间的审判过程不同,因为一般人相信神明不必像法官一样,立即作出判决,而是在事后处罚有罪者。因此常以当事人是否在仪式举行之后遭到天灾人祸的报应,来判断其人是否有罪。中国汉人和非汉人的社会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神判仪式,最主要的是“立誓”(包括“斩鸡头”)、“放告”(又叫做“告阴状”)和“审疯子”。这些神判仪式清楚地反映汉人社会的正义观念,强调正义(或者说是“报应”)的普遍性和现世性——也就是所谓的“现世报”[3]47-104,142-178,[17]。
到了东汉时代,上述地狱司法体系的信仰与仪式被吸收到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同时,其刑法的特征和道德观念的联系也变得更加明显。如在著名的道教经书《太平经》①有关此经书的历史与意义, 请见: Kaltenmark M.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Ching [C] // Welch H, Seidel A. Facets of Taoism.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45; Hendrischke B. The Scripture on Great Peace: The Taiping Jing and the Beginnings of Daoism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中,清楚地强调阴间的官僚除了审理死者之外,也可以对于有罪的亡魂执行各种严厉的拷问与刑罚[18]。除了前述的内容之外,下列两段文字对于地狱的司法体系也有详细的描述:
(俗人)自以当可竟年,不知天谴神往记之,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地神召问,其所为辞语同不同,复苦思治之,治后乃服。[2]526
大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年。算尽之后,召地阴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2]579
第二段引文提到必须先把死者召唤(“召”)到地府(“土府”),并且对它进行考问(“考”,也就是拷问);这或许跟下一节所讨论的考召仪式由关联。
除了《太平经》之外,第五世纪道教经书《女青鬼律》也对于地狱司法体系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尤其是相关司法神的职责②见《女青鬼律》卷一. 另外参考: 黎志添. 《女青鬼律》与早期天师道地下世界的官僚化问题[C] // 黎志添. 道教研究与中国宗教文化. 香港: 中华书局, 2003: 2-36.:
高天万丈鬼,百鬼,中皇姓,系天六方鬼之主,住在太山东南角道水中,诸死人所归。鬼亦上天,对问考罚,月一上。上古以来,已三万六千余年,如有三万六千神与鬼等数。南乡三老鬼,俗五道鬼,姓车名匿,主诸死人录籍,考计生人罪,皆向之。此鬼在太山西北角,亦有官属。
不过,有另外一种道经的司法倾向比起《女青鬼律》更加明确,就是《女青诏书律令》。虽然前者比较有名,但是它主要的内容在于给神职人员提供各种鬼神的名单,使他能够在混乱时期保护自己。至于《女青诏书律令》则是属于一套用来治理并规范阴间鬼神的法令,因而常常用到“依玄都鬼律治罪”等字眼②。此外,根据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的研究,也有部分道经如《赤松子章历》和《女青玄都鬼律令》,不但拟妥了对于鬼神的法规,而且透过其它律令来规范道教神职人员,乃至一般信徒的行为[19]。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宋代的道经中也非常明显(见下面讨论)。
早期道教经书除了一再提及泰山(《女青鬼律》中的“太山”)之外,也经常形容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地下监狱“酆都”。从第四世纪以来,有许多道经深刻描述了酆都的庞杂司法体系,包括各式各样的衙门、官吏、监狱等等,几乎比阳间的司法体系更加完善。陶弘景(456 – 536)的《真诰》卷十五中“阐幽微第一”载:“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回三万里……山上有六宫……第一宫名为纣绝阴天宫,以次东行,第二宫名为泰煞谅事宗天宫,第三宫名为明晨耐犯武城天宫,第四宫名为恬昭罪气天宫,第五宫名为宗灵七非天宫,第六宫名为敢司连宛屡天宫。凡六天宫是为鬼神六天之治也。”
上述概念对于佛教在中国所推动的地狱信仰也有所影响。首先,早期把佛经译成中文的高僧常常用“泰山地狱”来代表梵文“niraya(地狱)”字眼,如四世纪(姚秦)竺佛念翻译的《出曜经》卷十“诽谤品第九”提到:“或因博戏致恚,罪心已固不虑后缘,出言招祸以灭身本,渐当入泰山地狱饿鬼畜生。涉诸苦难无有穷已。”此外,部分佛教的经书也会形容泰山(太山)的苦刑①参见: Gjertson D E. Miraculous Retribution: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ang Lin’s Ming-pao Chi [R]. Berkeley, CA: Centers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9.,如后汉安息国三藏安世高所翻译的《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中有如此描绘:
佛言听说,作恶得恶,诸弟子皆叉手言诺受佛教。佛言:人于世间喜杀生,无慈之心,从是得五恶,何第五?一者寿命短,二者多惊怖,三者多仇怨,四者万分已后,魄入太山地狱中。太山地狱中,毒痛考治,烧炙煮,斫刺屠剥,押肠破骨,欲生不得。犯杀罪大,久久乃出。
又,五世纪在江南地区非常流行的中国撰述的佛经《佛说灌顶经》②有关这部经书, 请见: Strickmann M. The Consecration Sūtra: A Chinese Book of Spells [C] // Buswell R E.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75-118, 以及文献[45]: 118-119.(《疑经》)也把阎罗王当作司法神来看待,其所治理的地府跟道教地狱司法体系非常相似:
阎罗王者,主领世间名籍之记。若人为恶,作诸非法,无孝顺心,造作五逆,破灭三宝,无君臣法;又有众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设有受者,多所毁犯,于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简,除死定生,或注录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阎罗。阎罗监察,随罪轻重,考而治之。
当时的志怪,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也有类似描述[20]:“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所提到的“考治”也是跟阳间司法实践有关,如《新唐书》中的“杨慎矜列传”所述:“帝方在华清宫,闻之震怒,收慎矜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卢铉、杨国忠杂讯。驰遣京兆士曹参军吉温系慎余、慎名于洛阳狱考治。”陈登武的研究也很清楚地说明[21]:中古时期佛教的地狱观跟早期道教的一样,受到国家司法体系的影响。因此,相关佛经与艺术品也经常形容判官、胥吏以及他们所负责的各种酷刑,甚至于当时的佛教以其教义能够说服一般人勿为非作歹为由,试图取得国家的信赖和支持。
除了地狱司法体系的信仰之外,早期道教也发明了不少相关的宗教仪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古时期的“冢讼”。所谓的“冢讼”,是指死人在阴间透过地狱的司法体系对活人所做的诉讼,古人相信在这种“死人告活人”的情形下会导致活人生病或死亡。根据Peter Nickerson的研究[22-23]:最晚从秦汉以来,担心自己会被死者告状的人,往往会请道士、巫等神职人员做一些阻止冢讼的仪式。约在六世纪成书的《赤松子章历》卷五中有“大冢讼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仪式先由道士叙述“患者”(被死人告的活人)所遭遇到的灾祸,和引起此灾祸的各种冢讼。“患者”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超荐其祖先,或因先人的冢墓侵犯到神灵、或其他亡者的冢地纠纷,或先人横死未安,也有被其亡故的亲属所告的。因此,道士在作法时,可能有收治其祖先的必要:
上言:今有某州县乡里某甲,投辞列款,称门祚灾衰,家累疾病,所作不利,所居不安,求乞章奏,解除冢讼。今据其事状,粗可根寻,必恐其七祖九玄、周亲近属,生存之日,过犯既多,亡殁已来,被诸考谪,子孙未与拔赎,冥漠得以怨嗟,或葬在水源之讼,或殡当神庙之讼,或坟茔穿穴之讼,或棺椁损伤之讼,或旧冢相重之讼,或新冢相犯之讼,年月浸远,胤嗣不知,或水溺火烧之讼,或虫伤药毒之讼,或刀兵牢狱之讼,或瘟疫瘫疽之讼,或伯叔兄弟,或姑侄姊妹,递相连染,以作祸殃。
臣辄依千二百官仪,并正一真人三天法师所授南岳紫虚元君治病灭恶之法,谨上请天昌君,黄衣兵十万人,收某家中百二十殃怪……十二刑杀之鬼,皆令消灭。又请无上高仓君,兵一万人,为某家收治五墓之鬼,伤亡往来,住着子孙,作殃怪祸害疾病某身,致令死伤不绝者,皆令消灭……又请四相君五人,官将百二十人,为某销散家中有考讼鬼祟诸不正之气,侵扰宅舍,致不安稳者,皆即收剪,解释讼考,分别清浊。又请赤天食气君,官将百二十人,为某驰斥亲属远近,及有异姓之讼,逮诸凶恶怨诉,共相侵扰,不肯散退,所为祟害者,悉皆制绝销灭。又请收神上明君,官将百二十人,为某身解除恶梦错乱,魂魄不守,精神离越者,令得安善,使夙注销歇……又请无上天生君,兵士一万人,无上方相君,兵士一万人,并为某收家门先后死亡,有相注逮者,令消灭之。
这段资料一方面谈到自古以来活人对于死者的恐惧以及家庭里的矛盾,另一方面则试图透过法律途径来处理这些问题。“大冢讼章”虽然也提到了死者的道德缺失,但是同时利用法律概念来形容他的过错与死后的处置。此外,因为在地狱负责进行判决的官僚就是司法官,所以无论是死者也好、活人也好,如要想胜诉就务必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武力的重要性。只要相关司法程序完备,有正当性,就允许动用道教里的天兵天将来消灭恶鬼,这些现象可见于下面探讨的考召等道教驱邪仪式。
二、当司法遇上驱邪——道教的考召仪式
由上述的“大冢讼章”可以看出,道教在面对各种鬼神对于人类的威胁时,不排除利用法律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等于是把司法程序融合到了驱邪仪式里面,这种情形在道教的考召仪式中特别显著。考召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仪式,根据林富士的研究,早在汉朝时期,古代的道士就会透过“召劾”仪式(也可称为“符劾”)来治疗恶鬼附身所造成的精神疾病(即所谓“邪魅病”)[24]。此外,著名道教人物葛洪(283 – 343)所撰写的《肘后备急方·治卒魇寐不寤方第五》也生动地描写了古代的神职人员如何综合司法与武力来治疗类似疯癫的病症,并且把重点摆在诘问经过:
又方:以其人置地,利刀画地,从肩起,男左女右,令周面以刀锋刻病患鼻,令入一分,急持勿动,其人当鬼神语求哀,乃问,阿谁,何故来,当自乞去,乃以指灭向所画地,当肩头数寸,令得去,不可不具诘问之也。
《太平广记》①有关《太平广记》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 请见: Dudbridge Glen.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道教司法性驱邪仪式的故事,包括以下讨论的“考召”,这类仪式甚至也可以用来对付狐狸精: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明,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值得注意的是,考召跟下面即将形容的雷法似乎也有关联,如《太平广记》另一故事所谈到:
到了宋代,考召仪式更加盛行。根据刘仲宇的研究,当时考召仪式的驱邪与司法面向都非常明显,其目的在于“拘捕为害鬼神精邪,并加刑询拷问,逼其招供”①因此, 或许“考召”也可以理解为“考招”或“拷招”.,并且在考召过程完成之后,更“依鬼律行法,对鬼魅处置或押赴地狱”[25]378-381,389-390。Edward Davis的研究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考召仪式的结构与宋代的司法程序有不少类同乃至重叠之处,包括起诉(劾)、考问、苦刑、带枷子、关监狱等②参见: Davis E L.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M].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另外请见: Hymes R.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根据Poul Andersen(安保罗)的研究,考召仪式是宋代著名道派天心正法科仪传统核心的一部分[26-27],从该道派最重要的经书之一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一对考召的叙述,可知它是用来对付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的驱邪与司法仪式:
或新屋内鬼神聚集,旋风入宅,狐狸乱鸣,大木无风倒折,釜鸣并溢,家事器物,辄自行动。小儿夜啼,不宜男女。奴婢多走,牛马瘟疫死伤。白日鬼物见形,怪声光影千幻。万妖侵生,蠹物之事,卒述难穷。今略举此数例,庶知法中有律制伏,事无巨细,皆有法度。
又,本书卷七、卷八的内容几乎全与考召仪式有关,包括相关存神、步罡(如禹步)、符咒、手诀等等,其中部分内容也有明确的司法特质,如卷七“辅正除邪考召法”提到:“应治疾患,令患家周细具状,陈得病缘由,为祟之因,至于年甲,逐一诉说。然后依法行持,考治救疗。”另外,这两卷中也生动地描写了许多司法和刑法的措施,包括制劾邪魔、立狱召鬼等。有一部分的苦刑跟人间的司法体制比较接近,如杖子拷法、缚鬼法、枷鬼法;但也有一部分比较像阴间的折磨,包括立火牢咒、烧鬼法、四渎冰祟法等等。这点多少也表现出中国宗教文化中阳间与阴间刑罚形象的互动与互补情形[28]。
至于考召仪式的实际举行情况,则可以在宋代笔记中找到一些线索。其中,洪迈(1123 – 1201)的《夷坚志》中有不少相关的故事,也强调考召仪式的司法特质。如《夷坚志·丙》之卷一所形容的温州地区一个大家族在被山魈困扰的情况之下,分别请当地巫师与天心正法的法师利用考召仪式来解除,其中包括不少调动神兵及使用雷法的情形[29]: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兴二年(1164)秋,比邻沈氏母病,宣谴子、与何氏二甥问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贵……召会城隍五岳兵……烧符追玉笥三雷院兵为援……命置狱考竟。地狱百毒,汤镬锉碓,随索随见,鬼形糜碎,死而复苏屡矣。讫不承,安之呼别将蓝面跨马者讯治,叱左右考鞫,亲折鬼四支,投于空而承以槊,大抵不能过前酷,而鬼屈服受辞,具言乃宅旁树,刳其腹得一卷书。曰:“此女魂也。”投之于口,亦入其顶中,是夕小愈……薛氏议呼道士行正法……张彦华偶随请而至……华归焚章上奏,扫室为狱……五雷判官者进,曰:“元恶毙以阴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余阴雷击之。”
另外,宋代的考召仪式与古代一样,也可以用来治疗今日医学所认定的癫痫疾病[30]。如《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有部分內容谈到这种情形,而且跟前述资料一般,强调这类仪式跟司法和武力有密切关联:
一治癫邪鬼祟:先取本人诣实文状,据其事理,合用申行去处。先扎付本家司命五道土地,次牒所属州县城隍,或奏本部兵将收捉,或用奏上天,建立天狱,收捉鬼祟。凡申发文字及差兵将,先用赏设讫,方给帖牒关引等付之案,令奉行,次给符水与病人吞佩。蒙恩之後,再用赏兵。
宋元时期的道教科仪类书《道法会元》卷55“清微治颠邪文检品”描述了治疗癫痫的考召仪式;不过这个科仪本同时也提出:病人必须忏悔其过去所造成的罪过。这点与明清至近代时期浙江地区的“审疯子”仪式比较接近[3]105-107。
除了天心正法以外,其他的宋代道派也大量地运用考召仪式,其中的一个例子为神霄派的《太上玉司左院秘要上法》。此外,净明忠孝道的《灵宝净明院行遣式》也强调神职人员应该透过东岳大帝、城隍神及其下属的“法院神将吏兵”来捉拿并判决祸害信徒的鬼怪,并且“依天律施行”。《灵宝净明院行遣式》里有三份“判状差神将式”特别重视这点,如第一判状差神将式所说的:“搜捉再身为祸作病邪神鬼祟,男伤女亡,土木山精,倚草附木等神鬼。牢固擒缚,送东岳,依天条施行。”
甚至连道教著名的雷法仪式中也包含了许多司法面向,如《灵宝净明天枢院都司法院须知法文》中的天枢都司录纠察法所提出:“如遇人物、妖鬼,有为十善民之害者,驱雷火以击之。”此外,根据《道法会元》卷262 – 263的“酆都考召大法”,雷法的目的在于:“速捉速缚,重枷重刑。轰雷挚电,报应分明。”这些科仪本背后有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雷法等于是一种天愆。这点可以在《太上说朝天谢雷真经》里看得很清楚[31]:
天雷十二条者,不忠君主,不孝父母,不敬三宝,抛掷五谷,诃风骂雨,裸露三光,扬恶掩善,不遵正道,心昧天地,信巫厌祝,灭人福果,毁坏经教,犯此天条,则天雷检察……遇雷击之後,北酆为鬼,难求出离苦楚,岂不痛哉。
上述各式各样驱邪仪式的司法面向,也可以显示它们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意即被捉到的鬼怪必须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之后,才能被惩处。根据《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必须先向天枢院告状,才能够抓鬼(“治人间精邪为害……即令具状,经本院投押”)。又,《道法会元》里面的最后一部科仪本《太玄酆都黑律仪格》也强调,所有的案子务必按照书名中的“黑律”来审判:“当院今为某人投词,有某见被邪鬼侵害,丐求驱治施行……如有下界通灵魔鬼,敢当符截奏者,仰唯九泉号令,速送西台御史,依黑律治罪。”
即使亡魂有冤屈,想要控告阳间的人,也必须遵守相关规范,假如违反这些规定,其在地狱的刑责就要加重。关于这一点,《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写得非常清楚:“诸亡者有怨于生人,曾经地府陈理,未结绝而擅于人家,作祆异尅害他人,侥求功果为报,虽非损人命,而动烦立狱仇对平人者,关地府灭形。”《道法会元》中一部篇幅很长的经书——《太上混洞赤文女青召书天律》卷251 – 252也谈到这点:“诸人死鬼生前有冤枉于生人,已经阴司决断,而再投行司申论者,不得受理。”换句话说,亡魂有提出告诉的权益,但务必要遵守既定的程序正义。因此,没有经过地狱司法体系而回到阳间闹鬼的亡魂,就要被驱逐。反过来说,假如在阴间胜诉的鬼魂至阳间要对于加害者索命,即使请到法力高强的道士或法师也没有用[3]103-104。
此处必须强调的是:不只是鬼魂要收到道教司法体系的约束,连道教的神明与神职人员也一样。因此,像《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太上混洞赤文女青召书天律》等道教的经书,都提出了许多具体、严格的规范。《上清骨髓灵文鬼律》提及:凡是玩弄是非,或押人取财的地狱司法神(“地司官”),就要遭受最严厉的处置:“诸地司官妄以亡人无罪为有罪……无冤枉为有冤枉……如此之类者,并各分形。故意拘留希求财利,加一等。”又,《太上混洞赤文女青召书天律》也规定:除非民众向神职人员提出的状纸的格式有错误,否则一定要受理,违者要受罚:“诸行法官受民间词状而不即时行遣者,徒一年。如状不合格式者非。”这些规定多少反映了人民对于司法的理想以及期待正义的渴求,甚至于希望阳间的司法体系能够如阴间般的公正[3]38-39,[32]。
因为道教对于司法特别看重,所以其神职人员经常被当做司法专家来看待,如《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强调:信徒可以委托道教神职人员替他们向司法神申诉冤屈(“诸民人有事告诉行法官”)。道教神职人员的这种能力对于他们社会地位的确立应有所助益,甚至于可能影响到官方司法体系的发展,因为今日司法人员的职称之一“法官”,也是对传统道教神职人员的尊称。
三、道教驱邪仪式中司法与武力的结合
道教驱邪仪式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特色是在面对各种鬼神对于人类的威胁时,除了依靠司法以外,也不排除动用武力。根据刘仲宇的观察,“捉妖法术的模拟对象是军事上围歼敌寇和狩猎中围捕禽兽的场面”[25]404。此外,Judith Boltz(鲍菊隐)也强调道教的驱邪仪式有明显的暴力倾向,甚至于在相关科仪本中经常出现“杀”等字眼,也提到古代军队所用过的可怕武器,包括火鸟、火兽、炸药等[33]。因此,除了司法神之外,武神在道教驱邪仪式中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开始做法之前就要请神,仪式进行中也要做适当的调度。不过,其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仍然要放在法律脉络来理解,也必须充分配合驱邪仪式中的相关司法程序,如《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七“辅正除邪考召法”所描述:
思存行考召诀:凡考召,思师出兵,一一如法。即存二十八宿罗列于身上。次三将军吏兵……毕,即向案边坐,依仪读文,即召鬼神,考问作祟者名字,判付收禁。如是顽恶,后上赤章,请天兵诛斩鬼神①这种情形在《金锁流珠引》卷四也有类似记载: “考问作祟之者名字, 判付狱收禁. 后上赤章, 请天兵诛斩鬼祟.”。
十二神将捉鬼枷缚考责法:召神将称:“急速为吾追捉病人某身中祟病鬼神,不以庙社灶君宅神,凶死恶亡精灵,妖怪之鬼,应曾作害病人者,一一追收,立附患人身体,受吾正法,考问通说因依姓名。
武神的司法面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就是神职人员跟这些神明的关系必须透过立誓、斩鸡头等司法仪式来建立并确认。如《道法会元》卷123“邵阳火车五雷大法”中叙述道士如何以斩鸡头的方法来请武神,包括温元帅(温琼)、关元帅(关羽)、赵元帅(赵公明)、朱将军等。首先,要存想雷电风雨的官将兵吏,跨步罡,奠酒祭神,念咒焚符等:
次左手执生叫鸡,令侍者捉鸡足及翅,师执鸡头,右手仗剑斩鸡,沥血於空盏内,以酒浸入,用剑搅匀,将血与酒与将吏誓曰:“仗剑在手,吾以斩鸡,沥血为誓。誓愿代天行化,助国救民,役召风雷,驱别人鬼,汝等吏兵,兵随印转,将逐令行,闻吾符召,疾速降临,兴云致雨,驱风起霆,有命即行,毋违吾令,显扬道法,救疗群生,彼此有违,并依天律。”
道士立誓之后,还得喝一口血酒。由此可见,这种斩鸡头仪式具有向天立誓,以及与武神建立联盟关系的意涵。同时,由于需要喝血,表明违反联盟者会招致天谴,所以和古代的血盟相当类似。道士作法时,不一定要喝鸡的血;又,除了鸡之外,还可以用鹅、羊、鳝鱼,甚至于自己手指头的血[34]。
关于神职人员跟武神所建立的联盟,究竟是属于甚么性质?《上清骨髓灵文鬼律》中的“誓神将文”有相当详细的描述。这些武神被视为东岳大帝的部属,因此还是属于地狱司法体系的一部分:
因为这些武神本身非常血腥、凶悍,所以道教的神职人员对于它们有许多顾忌,甚至于会感到害怕。根据 Mark Meulenbeld(梅林宝)的研究,道士往往会用“败军死将”、“乱军死兵”来形容这些鬼神。同时,武神不像其他道教的神明吃素(“猛烈,须用血食祭之”),因为道士所要支配的武神是很凶猛的,所以祭拜它们的时候得用荤食[35]。这是因为武神是他们科仪传统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一般新徒弟的第一份符箓中也以各种神兵为主。这些武神不只具有协助道士进行驱邪仪式的责任,同时也有监督其行为的权限,万一有道士违背道教的相关规定,这些神兵有义务向道教的司法神检举,其中包括考召四君,可见武神与司法神仍然是分不开的。等道士往生之后,他的同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神兵收留下来,相关丧葬仪式才可以起动。古代道教就如此,现代道教也如此①参阅: Kleeman T (祁泰履). Who or What are the Clerks and Soldiers? [C]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cripture and Ritual.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8; 叶明生. 屏南县龙潭潭村宗族道坛与宗族社会活动关系述考[C]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议程.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8; 刘劲峰. 传统视野中的身份认同: 以一位职业道士的丧葬仪式为例[C]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议程.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8.。
道教驱邪仪式中司法与武力的结合一直维持到近现代,《藏外道书》中的许多清代道教科仪本,如《朱将军大法》以及《温帅血脉家传》②《温帅血脉家传》的全名为《地祗铁甲飞雄上将冀灵昭武使都巡太保温元帅血脉家传》.,保存了与《道法会元》非常类似的法事,如考召、雷法等,并且经常运用天兵天将来捉拿恶鬼[36]。此外,也有不少明清的笔记描写了这类仪式,如《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下列故事[37]:
槐亭又言:有学茅山法者,劾治鬼魅……遂考召四境之狐。胁以雷斧火狱,俾纳贿焉,征索既频,狐不堪扰。乃共计盗其符印,遂为狐所凭附……役使鬼神,以驱除妖厉,此其权与官吏侔矣。受赂纵奸,已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溪壑,天道神明,岂逃鉴察,微群狐杀之。雷霆之诛,当亦终不免也。
此外,徐宏图在浙江省南部平阳县的研究也显示,当地的道士也会利用司法神与武神进行驱邪仪式,所请的神明包括各种元帅、将军与判官,所画的符也跟《道法会元》有许多相似之处[38]。笔者在浙南泰顺县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也有同样的发现。2008年9月间,我跟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祁刚到泰顺的筱村乡访问一位姓雷的畲族闾山法师,并且记录其部分科仪本的内容。根据雷法师的口述,假如当地有人发生精神异常,就要在病人家里进行“治癫金科”仪式,其内容如下:首先,法师要存身、请闾山派的祖师,次则必须在病人家中的大厅生火,举行“暗火科”,包括发军令跟点兵将。等到所有兵力召集时,就得三次进入病人的房间,第一次用草席、第二次点燃圣火(哪吒火)、第三次请闾山派法力最高强的守护神陈靖姑(临水夫人)。第三次进房时,法师手拿着鞭、剑,将病人拉到祖师坛前(通常会叫病人咬住鞭的柄),然后进行考召仪式,以判定造成病患的灵魂是哪一类。考召结束之后,把病人拉回房间,整个“治癫金科”仪式就告一段落。一年之中,上述仪式至少会进行10次以上。
1949年以前,“治癫金科”更加普遍,偶尔规模也更大,持续3天之久。第三天中午还要举行“包公断案”的仪式剧场(ritual drama),由法师高台端坐饰包公,左右八人分别饰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还得请村民打扮成仪式中的士兵。仪式一开始,就要依序请府城隍、县城隍、当境地主、各村土地、门神、灶神等神明,讯问他们为何信徒家中有人发生精神异常,最后由灶神供认有恶鬼藏在病患床下(通常会事先把象征恶鬼的替身“稻草人偶”放好)。此时,法师会派遣士兵(村民)去捉拿恶鬼“稻草人偶”,然后举行考召、打稻草人偶36大板、收回患者的三魂七魄,最后把稻草人偶烧掉。由此看来,虽然天心正法这个道派已经消失了,但其发展出来的考召仪式以及融合司法神与武神的传统仍然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过去的研究比较重视台湾[39-40]与西南瑶族[41],但是浙江地区的仪式似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 语
由上述内容可知,道教在中国法律文化建构过程的角色可以从3个方面来思考:首先,道教非常强调地狱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地狱的司法神一方面掌管亡魂的处置(即死亡后的报应),另一方面也能够替信徒伸冤、判定是非、主持公道。第二,这些地狱司法神的属下包括许多武神,这些武神最主要的角色是率领他们的兵马去执行勤务,特别是捉拿跟拷问各种妖魔鬼怪。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阳间的司法体系基本上不会动用武力:虽然国家可以用军队来镇压土匪或叛乱,但是文官要执法时通常是会动用衙役(或警察),不会利用士兵①有关这个现象, 请见: Allee M A.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odde D, Morris C.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Translated from the Hsing-an Hui-la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ü T T (瞿同祖).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M]. Paris, France: Moulon, 1961; Hegel R E, Carlitz K. 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rime, Conflict, and Judgment [M].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Huang P C C (黃宗智). 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Republic Compared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三是合法性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包括亡魂在地狱所遭受的苦刑,以及恶鬼在驱邪过程中所受到的折磨与消灭。这点牵涉到暴力在中国文化的定位问题。虽然William Rowe(罗威廉)[42]等学者一再强调儒家思想消除暴力倾向的作用①参见: Aijmer G, Abbink J. Meanings of Violence: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M]. Oxford, UK: Berg, 2000; Haar B T. 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M]. Leiden, the Netherland: E J Brill, 2006.,但是道教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道教的驱邪仪式(如考召)将武力强制地放在司法脉络中发挥作用,明确地表现出暴力只能够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后运用的想法,也成为“司法性驱邪典范(judicial exorcistic paradigm)”的主要成分。这点或许也跟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所提出的中国宗教两种核心面向有关[43]:一种是天神所掌管的和谐与正义,另一种是驱逐鬼祟的祈禳仪式。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由中国地狱信仰的发展以检视道教与佛教的不同。首先,在武神方面,在密宗的驱邪仪式中佛教的元帅神阿托婆拘(Aţavaka)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没有甚么明显的司法特征[44-45]。此外,Meir Shahar(夏维明)关于少林寺的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佛教的著名武神金刚(Vajrapāņi)跟紧那罗(Kimnara)同时具备武力和驱邪的功能,但是跟阿托婆拘一样,不采取或配合任何司法行动[46]。由此可以显示:道教与佛教对于驱邪仪式的武力面向的差别态度,正代表着这两个宗教对于宗教与司法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这个问题也是笔者未来想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更有趣的是,虽然早在汉代佛教已经传进来了,但是要到隋唐时期佛教才真正深入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②参见: Zürcher E.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M]. Leiden, the Netherland: E J Brill, 1959.。这点也影响到道教与佛教地狱信仰的互动,乃至整个中国地狱信仰的发展。关于此问题,可以用荷兰汉学家Erik Zürcher(许理和)关于“hard(硬)”跟“soft(软)”的观念,来解释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现象[47]。许理和原来是用此一观念研究中古时期佛教对道教不同程度的影响,他发现:在佛教还没有传入之前,道教所没有的观念——如因果、轮回、普度众生等,那么道教在这方面就比较“软”,受到佛教的影响就比较大。相反地,在佛教还没传来之前,道教就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观念——如地狱司法体系,那么道教在这方面算是比较“硬”,受到佛教的影响则较小。正因如此,所以佛教多采多姿的地狱观(如十八层地狱等)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其它狱神(如阎罗王)并未取代道教的地狱司法神,特别是东岳大帝和城隍神。此外,在处理闹鬼问题方面,因为道教的地狱司法体系与驱邪仪式已经相当定型,所以也没有被佛教仪式取代。佛教所用来处理鬼魂的方式主要为念经、超度亡魂,避开了道教所假想的地狱司法体系、救援困在地狱的囚犯,如《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所描述:“亡人百日更恓惶,身遭枷械被鞭伤,男女努力造功德,从兹妙善见天堂。”[48]这点与道教地狱司法体系的性质与内涵完全不同③这些假设在文献[3]: 24-26也有讨论. 另见: Teiser S 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M].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Wang-Toutain F. Le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en Chine du Ve au XIIIe Siècle [M]. Paris, France: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98; Zhiru N. The Making of a Savior Bodhisattva: Dizang in Medieval China [M].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就中国法律文化建构的过程来说,除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之外,道教的信仰与仪式也不容忽视。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我们需要包含弹性和广阔的视野,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官法”与“冥法”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反而是一体的两面,其背后也包含法律概念。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信仰与仪式带动了中国法律意识(legal consciousness)[49]的发展,一方面构成司法体系的主观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法律生活的实质内容有所影响。也因此,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所谓的正义不限于官方的判决,同时也包括地狱司法神的神判。假如我们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界定以前者为重,忽略后者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理解不仅是片面的,也与现实生活有深入落差。余英时先生长期所进行的汉学研究——包括关于招魂仪式的短文,也提醒我们:只有透过更完整的分析角度,我们才能够对于中国文化史达成全面性的掌握。
[1] Yü Y S.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7, 47(2): 363-395.
[2] 王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 Katz P R. Divine Justice: 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M].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9.
[4] Katz P R. Trial by Power: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Judicial Roles of Taoist Martial Deities [J].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008, 36: 54-83
[5] Keightley D N. The Religious Commitment: 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J]. History of Religions, 1978, 17: 211-225.
[6] Poo M C (蒲慕州).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M].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8: 65-67.
[7] [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01-202.
[8] Harper D. Resurrection in Warring States Popular Religion [J]. Taoist Resources, 1994, 5(2): 13-28.
[9] Harper D. Contracts with the Spirit World in Han Common Religion: The Xuning Prayer and Sacrifice Documents of A.D. 79 [J].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04, 14: 227-267.
[10] Kohn L. Counting Good Deed and Days of Life: The Quantification of Fate in Medieval China [J]. Asiatische Studieren, 1998, 52: 833-870.
[11] Seidel A. 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ry Texts Found in Tombs [C] // 秋月观映. 道教と宗教文化. 东京: 平河出版社, 1987: 21-57.
[12] 刘增贵. 天堂与地狱: 汉代的泰山信仰[J]. 大陆杂志, 1997, 94(5): 1-13.
[13] 乐保群. “泰山治鬼”说的起源与中国冥府的形成[J]. 河北学刊, 2003, 25(3): 27-33.
[14] Bodde D. Basic Concepts of Chinese Law: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Legal Thought in Traditional China [C] // Le Blanc C, Borei D. 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1-194.
[15] Lewis M E.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M].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0.
[16] Haar B J T. Rethinking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C] // Aijmer G, Abbink J. Meanings of Violence: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Oxford, UK: Berg, 2000: 123-140.
[17] 康豹. 汉人社会的神判仪式初探: 从斩鸡头说起[J].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2000, (88): 173-202.
[18] Espesset G. Criminalized Abnormality, Moral Etiology, and Redemptive Suffering in the Secondary Strata of the Taiping Jing [J]. Asia Major: Series 3, 2003, 15(2): 1-50.
[19] Verellen F. The Heavenly Master Liturgical Agenda According to Chisong Zi’s Petition Almanac [J].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04, 14: 291-343.
[20] 刘义庆. 幽明录[M]. 台北: 新兴书局, 1980: 306.
[21] 陈登武. 从人间世到幽冥界: 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M]. 台北: 五南图书公司, 2006: 285-286, 296-306,320-324.
[22] Nickerson P. The Great Petition for Sepulchral Plaints [C] // Bokenkamp S R.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30-274.
[23] Bokenkamp S R. 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6-58, 111-118, 130-138.
[24] 林富士. 中国早期道士的医者形象: 以《神仙传》为主的初步考察[J]. 世界宗教学刊, 2003, (2): 1-32.
[25] 刘仲宇. 道教法术[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
[26] Andersen P. Tianxin Zhengfa and Related Rites [C] // Schipper K, Verellen F.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1056-1080.
[27] Andersen P. Tianxin Zhengfa: Taishang Zhuguo Jiumin Zongjiao Biyao [C] // Pregadio F.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8: 951-952, 989-993.
[28] Brook T, Bourgon J, Blue G.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2-151.
[29] 洪迈, 夷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64-369.
[30] 松本浩一. 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M]. 东京: 汲古书院, 2006: 371, 380-385, 395, 400-402.
[31] Skar L. Ritual Movements,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 in Song and Yuan Times [C] // Kohn L. Daoism Handbook. Leiden, the Netherland: E J Brill, 2000: 413-463.
[32] Hansen V.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 – 1400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9-221.
[33] Boltz J M.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the Battle with the Supernatural [C] // Gregory P N, Ebrey P B.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241-305.
[34] Haar B J T.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M]. Leiden, the Netherland: E J Brill, 1998: 15-17, 154-157, 167-170, 187-189.
[35] Meulenbeld M. Civilized Demons: Ming Thunder Gods from Ritual to Literature [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32, 107, 111.
[36] 胡道静. 藏外道书; 第29册[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63-70, 98-110.
[37]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715-3716.
[38] 徐宏图. 平阳县的温琼信仰及其相关仪式[C] // 康豹, 徐宏图. 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370-401.
[39] 刘枝万. 台湾的道教[C] // 福井康顺. 道教: 第1册. 朱越利,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16-154.
[40] 许丽玲. 疾病与厄运的转移: 台湾北部红头法师大补运仪式分析[C] // 林美容. 信仰、仪式与社会: 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2003: 339-365.
[41] Strickmann M. The Tao among the Yao: Taoism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South China [C] //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の会. 历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 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 东京: 国书刊行会, 1982: 23-30.
[42] Rowe W T.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43] Von Glahn R.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M].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3-17, 263.
[44] Katz P R.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M].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79-80.
[45] Strickmann M. Chinese Magical Medicine: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3-151.
[46] Shahar M.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M].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35-37, 83-89.
[47] Zürcher E.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J]. T’oung Pao, 1980, 66: 84-147.
[48] Teiser S F. The Growth of Purgatory [C] // Ebrey P B, Gregory P 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122.
[49] Silbey S. After Legal Consciousness [J].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05, 1: 323-368.
“His Soul Will Be Imprisoned and His Doings in Life Questioned”—— Taois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nitive Underworld
KATZ Paul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bei, China 11529)
This paper draws on Professor Yü Ying-shih’s observations about the Chinese underworld as portrayed in “Summoning the Soul” ritual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law in Chinese cul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Stephen Teiser and other scholars have produced an impressive body of research describing Buddhism’s impact on the ethical and judicia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underworld, few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ways in which China’s indigenous religious traditions (especially Taoism) have helped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world legal system and Chinese legal culture.
Religion; Law; Taoism; Buddhism; Underworld Legal System
B958
A
1674-3555(2010)04-0003-14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赵肖为)
2010-03-13
康豹(1961- ),男,美国洛杉矶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近代中国宗教社会史
① 本文的繁体版原刊于: 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