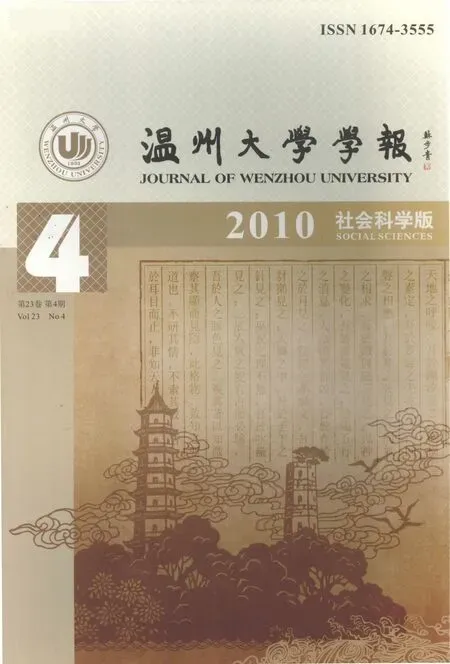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电影情结
李金凤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电影情结
李金凤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文化中心,看电影成为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上海租界的特殊文化语境孕育和催生了张爱玲的电影情结并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的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创作及其小说创作。
租界文化;上海;张爱玲;电影情结;文学创作
关于张爱玲与电影的研究,目前见有李欧梵、朱水涌、宋向红、陈雪岭等学者的文章①参见: 李欧梵. 不了情: 张爱玲和电影[C] // 子通, 亦清. 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356-366. 李欧梵. 张爱玲与好莱坞电影[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 48-51. 朱水涌, 宋向红.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5): 86-90. 陈雪岭. 张爱玲与电影的不解之缘[J]. 民国春秋, 1999, (3): 44-47. 高扬.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特征[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 (2): 69-72. 吴晓,封玉屏. 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 (1): 204-208.。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未有学者专门从租界文化语境探讨张爱玲与电影的复杂因缘。本文力图从租界文化视角研究张爱玲的电影情结以及电影对她的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租界文化语境下的电影迷
租界辟设后,一批批英、法、美等外国人来到上海租界安家落户,上海摇身一变成为洋人的殖民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跃居世界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上海租界在外国势力催生下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外国人把西方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制度和思想带到了上海。西方文化逐渐被理解、接受、模仿和采用,最后形成一种时尚渗透到上海市民社会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租界文化逐渐形成。
作为地道的上海市民,张爱玲就是浸润在租界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她于 1920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少女时光和青春岁月是在上海度过的。前半生,除了在天津住过几年,在香港住了三年,就没有离开过繁华摩登的上海。贵族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使她更容易接受租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纵观张爱玲的衣食住行和娱乐方式,或多或少沾染了租界的文化色彩。张爱玲与上海租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生命体验与租界城市和谐地融为一体——“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1]。租界这个借来的时空给予张爱玲充分享受生活的机会,也左右了张爱玲的娱乐选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在租界化的上海,张爱玲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看电影是她选择的主要娱乐方式。
在租界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上海成了一个新兴的消费城市。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听媒介,与报刊、书籍、图书出版一起构成了上海特殊的文化标志。影戏院成为上海滩一道最抢眼的现代风景线,电影的时尚风潮也由租界区域席卷到整个上海。电影中传达的西方文明时尚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时髦男女们学习模仿着好莱坞影片中的洋镜头和洋风尚,一时间,“看电影对上海的男男女女来说,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去电影院。”[2]127当时有名的大光明戏院、国泰大戏院、大上海戏院、南京戏院等一流大戏院都在英、美、法、日租界内,而且多放映外国片。“看电影的习惯对新文学的很多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来说,都是重要消遣”[2]103,茅盾、夏衍、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都是电影爱好者,更不用说贵族出生的张爱玲了。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最大的爱好也是看电影,她喜欢电影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和电影同步风行的还有电影杂志以及流行期刊上的电影专栏和文章。据张子静回忆,在中学时代,张爱玲就订了一系列的英文影迷杂志,和小说杂志一起摆放在床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和当时中国的明星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外国的葛丽泰·嘉宝、贝蒂·戴维斯、加利·库伯、克拉克·盖伯、秀兰·邓波儿和费雯·丽,中国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赵丹、胡蝶等,都是她喜欢的影星,他们出演的电影,她几乎每部必看[3]。张爱玲如此喜欢看电影,明显受到了租界文化语境的影响。十里洋场的好莱坞影片和当时辉煌一时的华语影片,给张爱玲的电影情结就提供了现实语境和文化空间。
二、上海租界时期的电影
上海是中国最早的电影之都,从1896年徐园公园放映“西洋影戏”,上海就开始了电影的新纪元。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的电影中心,放映的影片特别多。尤其是30年代,好莱坞影片盛行一时。除上海之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也输入中国各大城市,租界城市如天津、武汉、广州等,非租界城市如北京、南京、重庆等。但租界城市与非租界城市,所播放的电影迥然不同,即使是租界城市之间,上海与其它租界城市还是有所区别。上海作为一座租界面积最大、租界时间最长的殖民化城市,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它失去了管辖权和自治权。它成为“国中之国”,洋人借助租界这个便利的时空向中国人传输西方文明与生产方式,并着重在意识形态方面加以渗透,达到殖民的目的。外国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输入电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文化传播方式来说,电影是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外国文化正是以电影为媒介源源不断地传入上海的。
租界时期的上海是一个缺乏文化根基的城市。受到殖民文化影响,上海人都带有点崇洋心理。租界影院有着大理石铺筑的大堂、艺术化的装饰风格、舒适无比的座位、新奇斑斓的世界,氛围是十分洋气的,与欧美电影有一定的文化呼应。相对而言,非租界城市就没有这样的特点,好莱坞电影在其他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并不盛行。在那里,观看电影的只是上层社会少数有钱人,并未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时尚消费方式,电影的影响也没渗透到一般的市民生活中,所以也没有像上海人那样几代人都有好莱坞情结。
最重要的是,在上海租界这个特殊的环境,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带来的浓厚的趣味主义倾向、消闲色彩,轻松、新鲜与刺激,迎合了紧张、快速、逼仄的都市生活环境中广大市民的需求。况且,好莱坞电影以一种文化策略侵占了国产片的市场,国产片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影响较小,上海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形成了一整套西方人的价值理念。电影被投机商人所掌握,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市场需要什么电影商人们就投机什么电影。如“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就醉心于“欧化”电影风格,制作了渲染半殖民地生活方式的影片。政治局势的动荡、战争的破坏,尤其是 1941年上海成为孤岛之后,租界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迫不及待地追求刺激、冒险、疯狂,急切地渴求发财、成名。众多影片公司畸形繁荣,为谋取暴利、吸引观众,制作了一系列粗制滥造、迎合低级趣味的电影。同时,由于租界当局对日本侵华战争保持中立立场,使得表现正面抗战的影片遭到禁映与修剪。这也迫使各电影公司改拍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娱乐片,制作了一系列古装片、时装片、喜剧片、侦探片、鬼怪片和恐怖片等,这是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造成的。相对而言,非租界城市制作的影片带有较多的进步内容,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教育作用。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在国统区,电影的宣传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重庆为例,“战时国统区电影出品具有两大动向:一是新闻记录影片的繁荣;二是故事影片中纪实性美学趋向的出现和‘农村电影’的提倡。”[4]
由此可见,上海租界城市的特殊环境有利于影迷的形成与培养。“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即是上海电影史”[5],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即是租界上海的电影史。优越条件下滋生的电影迷与租界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张爱玲作为一个在上海租界城市中成长的影迷,无论是西方影片还是国产片都耳熟能详。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得“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像张爱玲这样从小到大一直为电影着迷的,恐怕不作第二人想。”[6]
三、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创作与电影
(一)张爱玲的有关影评及其电影剧本创作
1942年,张爱玲辍学从香港回到上海,谋划着如何在繁华摩登的城市成就一番事业。上海租界为她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空间,租界制度也有利于躲避战乱,提供一个现世安稳的创作环境,更重要的是上海租界众多的杂志报刊依然在战乱中出版发行,这样就给她提供了卖洋文的机遇和市场。我们看到,张爱玲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标志就是为英文《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不久,又开始为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文章,写得最多的还是影评。《二十世纪》的主编是克劳斯·梅奈特,这份报纸的主要对象是羁留亚洲的西方人,尤其以生活在上海租界外国人为重点。报刊杂志的性质决定了张爱玲在开始卖洋文为生的创作中要以西方人的兴趣爱好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带有殖民地文化色彩。这种殖民文化在租界文化里常常以复杂和隐蔽的方式存在,甚至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租界文化积淀”。张爱玲从发表《Wife, Vamp, Child》(评《梅娘曲》和《桃李争春》)开始,到1943年底,几乎每一期的《二十世纪》都刊有张爱玲的影评文章。如《The Opium War》(评《万世流芳》),《China Education in the Family》(评《新生》和《渔家女》),《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评《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①参见: 余彬. 张爱玲传[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78.,《谈跳舞》[7](评《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若不是张爱玲的影评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与理念,这些报刊杂志也不会发表她的影评。从另一方面而言,大量的观影经验和张爱玲对电影的迷恋,也催生了这些影评。
在上海租界,铺天盖地的电影广告刊登在《申报》、《良友画报》、《电影艺术》、《影戏杂志》等报刊杂志上,每一部新影片都会登广告、开展宣传、进行包装。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租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地商业文化味很浓厚的电影是要迎合大众流行口味的。读者意识很强的张爱玲势必思考如何使作品拥有更多的观众。张爱玲于 18岁逃离父亲的家,必须靠写作自力更生,此时的上海租界动荡不安、前途惨淡,世纪末的恐惧笼罩在租界人的内心深处,身处其中张爱玲更是感觉“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8],害怕失去上海租界的环境而追求“出名要趁早!”[8]。如何在日渐式微的租界文化语境下一鸣惊人,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这是张爱玲当时考虑的问题。恰好 40年代初好莱坞电影在上海文化市场上随战争进行而逐步缺席,上海市民却对好莱坞电影情有独钟,从而为张爱玲的剧本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空间和市场,于是张爱玲不再满足于影片的评论,开始创作类似好莱坞电影风格的剧本。
张爱玲曾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改写成舞台剧本。不久,又创作了第一部电影剧本《不了情》,讲述了一个婚姻不幸的忧郁男主人公夏宗豫和贫寒善良的家庭女教师虞家茵相爱了,流言蜚语不断,家茵最后不得不离开,类似电影《简爱》。代表张爱玲最佳编剧水平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1947年),是一出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轻喜剧,剧本讲述了聪明能干的年轻太太陈思珍,为家庭的和谐不断说谎、费尽心思、八面玲珑,甚至委曲求全、克己牺牲,仍不讨好的故事。丈夫在外面找了女人,思珍不堪忍受,想与丈夫离婚,最后却不得不妥协,破镜重圆。《太太万岁》上演时影院内笑声不断,风头盖过当年引入国内的美国好莱坞喜剧大片《出水芙蓉》,荣登1947年上海票房第一。这部电影的成功关键在剧本。《太太万岁》吸取了众多好莱坞影片的元素。张爱玲十分熟悉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爱情“谐闹喜剧”,这种喜剧的特色,“就是对中产(或大富)人家的家庭或感情轇轕,不加粉饰,以略微超脱的态度,嘲弄剖析,情节的偶然巧合与对话的诙谐机智,在这类作品里,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9]显然,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就借鉴于此。细节是喜剧的灵魂,《太太万岁》喜剧性细节的运用不仅精彩而且颇具象征意味。多次出现的扇子、别针正如“谐闹喜剧”的经典影片《一夜风流》中那条挂在百万富翁女儿爱莉和新闻记者比德之间的毛毯一样超越了普通的道具意义而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尤其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张爱玲对20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生活的准确体验和深刻表达,使得她创造的女主角成为这一阶层的代表。剧中的主人公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这些游离于社会政治环境之外的女性是当时“浮华遍地、十里洋场”的租界上海的代表性人物。以陈思珍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太太”在忠孝守节、相夫教子的传统文化和纸醉金迷、十里洋场的租界文化的夹缝中生存。被无线电、电影、洋行、离婚等新名词包围的“太太”们既无法恪守传统妻子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也无法如新一代革命女性那样和传统决裂,因此陷入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双重焦虑中。这也是张爱玲通过剧本所要表达的有关租界文化影响之下女性何去何从的问题。
上海于 1945年收回租界,并不意味着租界文化即刻消失,这是一个日渐式微的过程,它以一种潜在文化方式渗透到市民中,但上海租界的收回最终将导致租界文化语境的消失。缺失了这一语境,张爱玲就难以在上海再谋发展。作为一个与租界文化融为一体的人,她一直在追寻一个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租界上海有着相似文化氛围和品质的繁华城市,然而,租界上海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张爱玲的创作最终因失去了最熟悉、最亲切的租界上海而走向了下坡路。唯有香港还保留了一些租界上海的城市记忆,令其怀有希望。1958年,张爱玲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南北一家亲》、《小儿女》、《六月新娘》、《人财两得》、《一曲难忘》、《南北喜相逢》和《魂归离恨天》等。这些影片都具有类型化的、“电懋”特有的喜剧模式。
(二)电影元素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呈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电影中心。租界的文化语境孕育了张爱玲对电影的特殊爱好,这必然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在影评中我们能感受到租界的文化的影响和她对电影艺术的鉴赏力。在电影剧本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她杰出的编剧才华,那么,在小说创作中电影对她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她是个镜头感很强、很熟悉电影技巧的作家。她的小说,在场景、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融入了电影的诸多元素,可称为“纸上电影”。
小说《多少恨》是根据 1947年编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改编的,浸透着租界文化语境下引进的好莱坞电影的众多元素,从文字中可以幻象出一幅幅声、光、色、影的画面,给人以特殊的影视美感。
当虞家因的父亲向夏宗豫开口借钱,镜头开始转换,张爱玲把笔触聚焦在虞家茵的脸上,用相当于电影特写的方式,来探索家茵内心深处的隐秘瞬间。“家茵听到这里,(镜头移动)突然掉转身来望着她父亲,(上移)她头上那盏灯拉得很低,那荷叶边的白磁灯罩如同一朵淡黄色的大花,簪在她头发上,(特写)阴影深得在她脸上无情地刻划着,她像一个早衰的热带女人一般,显得异常憔悴。”[10]在灯光下,家茵内心深处的恐慌毫无遗漏地写在她憔悴的脸上。时光易逝、青春不再,灯光照出了一个女人的衰老和迟暮,时间带走了家茵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她的幸福最终将在父亲这一群人的手中葬送。她和夏宗豫之间夹杂着友谊的爱情以及淡淡的婚姻期待也变得渺茫了。这个特写为家茵的空欢喜、为她的黯然离开埋下了伏笔,悲剧的命运在此定格。光、影、色彩的巧妙融合,构成了一幅充满视觉影像的悲情画面。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喜欢用镜子,镜子成为她小说中一个明显的意象,而镜子也是好莱坞电影中惯用的道具。女主角在镜前搔首弄姿,摄影机跟随其后,镜头对着镜子而不露痕迹,原是好莱坞电影的技巧。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多次运用了镜子这个道具,例如:“长安在穿衣镜里端详自己,忍不住将两臂虚虚的一伸,裙子一踢,摆了个葡萄仙子的姿势,一扭头笑了起来道:‘把我打扮得天女散花似的!’长馨在镜子里向那小大姐做了个眉眼,两人不约而同也都笑了起来。”[11]163长安的审美情趣与自恋跃然纸上,镜子呈现了她的美,也传达了她的期待与喜悦,一场烟花般的爱恋即将上演。
在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小说中处处可见电影语言的运用不足为奇。电影语言使得画面具有视觉冲击力,同时又能传达言外之意,让我们领悟到人物的心境,达到“传神写照”的境界。如《金锁记》中就有很多精彩的画面。“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11]166这是一幅相当美好的画面,带有梦幻般的色彩,只有在电影中才能逼真地呈现,透过这些语言,我们能感受到长安内心深处的心境:快乐、浪漫、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幸福的难以置信的感觉。
张氏小说曾五度搬上大银幕,《倾城之恋》(许鞍华导演,1984年)、《怨女》(但汉章导演,1988年)、《红玫瑰与白玫瑰》(关锦鹏导演,1994年)、《半生缘》(许鞍华导演,1997年)、《色戒》(李安导演,2007年)等都是。显然,若不是张爱玲的小说极具电影风格,导演也不会瞄准它们。租界的文化语境是她小说创作的背景。张爱玲与电影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这情结的渊源是租界文化的特殊语境。
四、结 语
张爱玲,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叙述者,尽心地抒写着市民的都市趣味和小资情调,她“笔下的凡俗人生是租界生活的底子”[12],她心中的电影情结可以说是租界文化生活的投影,打下了租界文化的色彩。倘若没有租界这个“借来的时空”造就的电影事业的繁荣和电影娱乐方式的流行,张爱玲的电影情结也就失去了依存的现实语境和文化空间。正是租界文化语境成就了张爱玲一生的电影情结。
[1]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C] // 张爱玲. 流言.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1.
[2]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 [M]. 毛尖,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3] 张子静, 季季. 我的姊姊张爱玲[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96.
[4] 周晓明.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 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25.
[5] 陈文平, 蔡继福. 上海电影100年[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458.
[6] 陈子善. 编后记[C] // 张爱玲. 沉香.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281.
[7] 张爱玲. 谈跳舞[C] // 张爱玲. 流言.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164-165.
[8]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C] // 张爱玲. 倾城之恋.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456.
[9] 李欧梵. 不了情: 张爱玲和电影[C] // 子通, 亦清. 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360.
[10] 张爱玲. 多少恨[C] // 张爱玲. 郁金香.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195.
[11] 张爱玲. 金锁记[C] // 张爱玲. 倾城之恋.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12] 李永东. 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53.
Zhang Ailing’s Film Complex on Contexts of Concession Civilization
LI Jin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Shanghai had become the Chinese center of film culture in 1930s and 1940s. Going to the movies had become a major entertainment style of Shanghai’s citizens. Zhang Ailing’s film complex, which was represented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s, was in ges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ose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of Shanghai concessi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oncession civi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Zhang Ailing’s film reviews, scenario creations and novel creations.
Concession Civilization; Shanghai; Zhang Ailing; Film Complex; Literary Creation
I206
A
1674-3555(2010)04-008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09-12-06
李金凤(1986- ),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