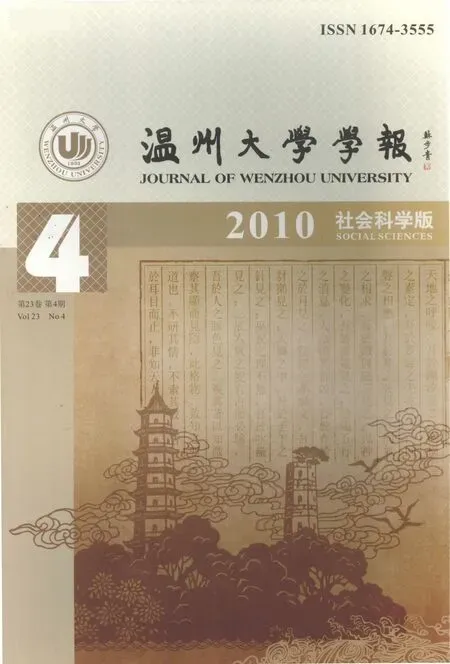作为“作家细读”的传记
王 永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作为“作家细读”的传记
王 永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作家细读”是作家传记的着力点,甚至是其目的。传记作者通过“作家细读”,对作家生平中有意义的但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遮蔽、擦除的“琐事”、“心事”的深度解读,从而揭示作家隐秘的心灵纹理以及情感脉络。注重作家细读的作家传记无疑构成了对文学史的补充。
细读;作家传记;文学史
作家传记的写作已经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卓有成绩的作家大多都有人为其立传,甚至不乏一人多传。近年来,作家传记的探讨、研究成为学术的热门论域。董炳月、晓华、王政、贺仲明、邹溱等研究者的论文都是对作家传记探讨、研究的重要文本①参见: 董炳月. 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J]. 文学评论, 1992, (1): 133-142. 晓华, 王政. 作家传记与文学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 (2): 124-126. 贺仲明. 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原则与方法[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 (2): 121-123. 邹溱.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J]. 北京大学学报, 1999, (3): 117-123.② 参见: 王永. 还原·想象·阐释: 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8: 1-163.。笔者的博士论文最早集中对诗人传记进行了研究②。本文着眼于作家传记对文学家隐秘的心灵纹理及情感脉络的“细读”,旨在揭示其对于传统文学史的补充作用。
一、文学史的限制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就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不断总结的过程。它让我们见证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里的文学实绩,同时也暴露出文学史写作的固有局限,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旗帜下,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反思和审视,学界对此展开了争鸣与讨论,这种学术讨论一直延续到新世纪。
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一方面,它会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作一个史学框架的描述,选择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来进行叙述,从而理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案例。但各类判断往往受一定时期的文学史观和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左右,如某些作家的文学史排位、某个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前途,常在文学史权力框架中被预先设定;另一方面,作为逻辑化的必然后果,文学发展史上的大量经验时有偏废、忽略,从而造成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游离、显露和隐秘等不同等量的文学史事实。”[1]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所说:“每一部写成文学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2]现代文学史对于胡风的评判可以显示出文学史的这种“筛选”、“塑造”功能。在胡风被彻底平反之后,主流文学史就将胡风塑造为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严酷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他因为坚持启蒙主义的理想而遭到了左翼文学的围剿。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胡风就被定位为“‘五四’新文学传统最热烈最自觉的捍卫者”[3]。其“三十万言书”更成为了争取作家创造自由、坚持“五四”文学理想的标志性文献。然而,胡风在 1954年的《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的发言》却被文学史家“无意”忽略了。在发言中,他竭力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对朱光潜、俞平伯等“胡适派”的批判,认为“朱光潜是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单纯地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都是掩盖了问题的”,并认为《文艺报》对待朱光潜的态度,是“把思想战线上的敌我关系当作进步阵容里面的意见不同”,是在向朱光潜求和,“实际上等于求饶”①参见: 胡风. 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的发言[C] //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上.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242-243.。这一文学史“忽略”的材料,引起了敏锐的学者“有点刻薄”的设想:“联系到胡风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许多作家,如沙汀、曹禺,特别是对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采取的猛烈抨击的态度,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假如胡风他们掌握了文艺界的权力,那又会怎么样?”[4]
新时期初期及以前的文学史往往把文学的历史理解为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目的论或者进化论的过程,这是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留给我们的理性迷梦之一。这种理解必然要以抽干历史的具体性、偶然性作为代价,历史的真实性在其中难免要打上折扣。而作为大型个案研究的作家传记相对于要容纳众多作家的文学史自然更多了些文学史料和作家的过从、行藏的记录,或者说,不符合文学史的叙述逻辑而被文学史家所剪裁掉的史料有可能会在作家传记中浮现。这些内容丰富了文学史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学史有补充(甚至有时是修正)作用。有学者就指出,历史生命的力度和广度以及我们反思理解和解释它们的能力,构成文学史理解的基础。而能实现这一理解与解释的最佳的文学史研究方式是作家论或传记形式,“在文学史研究中传记的形式或作家论的形式将越来越重要,在传记中,生命从生到死的所有外部事件都可以成为理解的材料,文学史思维就大大扩展了其理解活动的范围,这一点也是符合我们当代的文学史治史实践的。就现代文学史而言,当代最卓越的现代文学史家都有注重传记研究的倾向”[5]。甚至有的修史者着力于带有传记研究方式的“诗人/作家细读”,以个人来呈现主流,而非以主流来附带个人,认为“唯有这样方能回到诗的历史现场及其主体,重现诗歌发展历史的原貌和脉络,揭示其真相。”[6]
二、传记对于作家心理的探求
在笔者看来,“作家细读”正是作家传记的着力点,甚至是其目的。“细读”(close reading),原是英美新批评所提出的理论术语,意在通过对文本进行细心的阅读,从中发现文本中的意象、象征的内涵,甚至文本结构本身的意味。在本文中,“作家细读”是指对作家生平中的有意义的但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擦除的“琐事”、“心事”的深度解读,从而揭示作家隐秘的心灵纹理以及情感脉络。
作家传记是一门“严肃地写琐事”的艺术,其“故事化”的叙述风格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而文学史则从大处落笔,专注于思想、艺术的“潮流”。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个人的内心选择、私人的情感交往都被文学史过滤掉了,比如,周氏兄弟的失和、沈从文在建国后的惶恐与转向、王辛笛为何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突然放弃诗歌重入商界、郭小川在写“检讨书”时的真实心态,艾青与何其芳之间的论争是否出于“文人相轻”的意气之争,等等。这自然就妨碍了我们对现代作家的主体精神、情感状态和生存遭遇进行深入的探问,我们也就无法突破文学史的屏障,看清一个世纪的中国作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心路历程。郭沫若在 1922年写下引人深思的一段话:“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武器,下之划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言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种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我从前也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之中借披着件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不然,只抱个死板的概念去创作,这好像打破鼓,只能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和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于强烈的作品很容易使人麻痹,颠转不发生感受作用。”[7]由郭沫若的“忏悔”,可以看出其真实的、不同于文学史叙述的写作动机和心态。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文学史中所叙述的郭沫若的创作观:“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但郭沫若自己则披露,有时为生活计,也“专门做些稿子”。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年曾与郭沫若论战的茅盾仍然认为这段话表明郭沫若自己否定了《女神》,“真正出人意外”[8]。据此,我们似乎可以从这“出人意外”中悟得一些郭沫若当年激昂诗风形成的缘由。——而这些都是被文学史所过滤的。而对于诗人传记来说,就是一种“诗人细读”的方式,诗人个人的内心选择及私人的情感交往正是其所要关注的对象。程光炜的《艾青传》意在写一部知识分子奋争与思索的心灵史,这部传记就着意关注了文学史所不能包括的这些内容,比如艾青身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艾青在 1938年春在西安城郊犹疑徘徊,他对于命运的选择令传记作者程光炜深为不解,艾青当时为什么没有随民族革命大学的人马越过黄河,也没有跟好友田间、李又然去延安,而是留在四处不靠的西安附近呢?本来,他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可他偏偏选择了犹疑,最后,又向武汉退去。“个中原因,很难猜测,也不便猜测的。也许,这就是艾青?”[9]而1941年,身在重庆的艾青对于延安去还是不去的惶惑同样引起了传记作者的关注。
三、作家传记的独特资源
作家细读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日记、书信等带有私密性质的文献。文学史往往不采用这种文献,而在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历史语境之间进行合乎“逻辑”的建构。而这些文献资料则是诗人传记作者极其重视的资源,而且也理应受到传记作者的重视。因为,这些文献里面可能藏着更为具体的真实,一种逸出“逻辑”之外的真实。在刘志权所著《闻一多传》中,在叙述闻一多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历程和心理时,就引用了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给挚友饶孟侃写的一封书信。信中说:“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①参见: 刘志权. 闻一多传[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9: 154.书信的引用,真实地呈现了传主的内在心理状况,展现了传主自我解剖的痛苦,同时也为闻一多在学术上“向内转”提供了内在动因。在1925年3月,闻一多还给梁实秋写过一封信,信中有云:“我们若有创办杂志的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哄动一时。”[10]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闻一多正准备与友人一起步创造社的后尘,结社、办刊,他其实已经明白了创造社“打架”的奥妙。在这封信中他就规划了又一群无名青年闯入文坛的策略。尽管闻一多希望“与《创造》并峙称雄”的刊物未能如愿出版,但在刘纳看来,“这些半个多世纪后披露的私人信件中有关办刊物策略的设想却能为我们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切入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史、文学思潮史提供真实可信的材料。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形成文学社团、文学派别的较为冠冕的原因之外,往往还隐藏着另外一些带有明显功利性的理由。”[11]
这里还要提到在新世纪之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郭小川全集》②参见: 郭小川全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这部全集采取“给一个典型的历史个案以一个全真的文本”[12]的编辑方案,其中作品只占了一半篇幅;而另外的一半六卷是日记、书信、笔记、检查、检讨书等文字。这样“别开生面”的编辑方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郭小川不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担任过其他社会联系面很广的职务。他是政治和文化风云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这些文字具有“档案性”,在当代中国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郭小川的这些文字的发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见证。(与之形成有趣味的对照的是,有的所谓“全集”对传主的此类文字讳莫如深。)洪子诚认为,这部全集所收入的日记、书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笔记、思想鉴定、会议记录、检查交代,应该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和文学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全集》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当代’文学评价机制的性质和实施状况。从《全集》载录的思想检查交代和批判会的记录等材料中,也多少能窥见到环绕作家的社会压力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这种压力又怎样转化为驱动人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内部压力——这一点,即压抑的机制和自我压抑的主体的形成,是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研究的关键。”[12]这些于“知人论世”极具价值的材料对于传记写作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杨匡汉、杨匡满所著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③参见: 杨匡汉, 杨匡满. 战士与诗人郭小川[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这部传记,由于当时缺乏这些对“知人论世”极具价值的材料(当然也有时代语境的局囿),难免对传主做出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评价。张恩和在写作《郭小川评传》④参见: 张恩和. 郭小川评传[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时,虽然也无法看到如此丰富的资料,然则参考引用了1988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郭小川家书集》⑤参见: 郭小川. 郭小川家书集[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8.,较之十多年前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更深入地进入了郭小川真实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之前少有人触及的郭小川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对于郭小川研究也有所拓展。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作家传记作为一种“作家细读”,有利于对作家作心态研究、精神分析,揭示作家隐秘的情感纹理,从而进一步照亮文学史的阴影,构成对文学史的有益有力的补充。
[1] 吴德利. 经验史研究对文学史的意义: 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J]. 中国图书评论, 2006, (12): 56-58.
[2] 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邱仁宗,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64.
[3]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
[4] 洪子诚. 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46-147.
[5] 葛红兵. 正午的诗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61.
[6] 杨四平. 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2.
[7] 郭沫若.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N]. 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 1922-08-04(2).
[8] 茅盾. 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J]. 新文学史料, 1979, (4): 1-15.
[9] 程光炜. 艾青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165.
[10] 闻一多. 闻一多书信选辑: 四[J]. 新文学史料, 1984, (2): 169-186.
[11] 刘纳. 创造社与泰东书局[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163-164.
[12] 邵燕祥, 钱理群, 洪子诚, 等. 走近真实的郭小川: 郭小川全集出版座谈会纪实[J]. 社会科学论坛, 2000, (3): 30-35.
Study on Biographies as Close Readings of Writers
WANG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China 066004)
Close reading of writers is a focus point of writer’s biographies and even its purpose. Through close readings of writers and profound explanations of writers’ anecdotes and thoughts, which were meaningful but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hidden and eliminated from historical narration, biographers have revealed writers’ hidden spirit and emotion contexts. Writers’ biographies, which focused on close readings of writers, doubtless constitute a useful complement to literary history.
Close Reading; Writer’s Biography; Literary History
I052
A
1674-3555(2010)04-0078-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09-12-28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HB2009G15)
王永(1976- ),男,河北河间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新诗理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