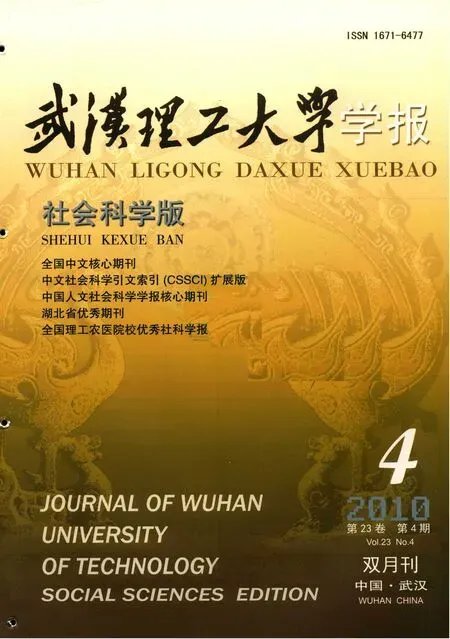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分析
李 明
(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构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分析
李 明
(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指出了生态危机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动因,稳态经济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目标,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建思想有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它在其理论分析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值得深入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稳态经济;民粹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5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北美出现的,而后成为整个欧美地区的一个重要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加拿大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美国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以及法国高兹的《生态学与政治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等。此外,阿什顿、博克金、哈维、拉比卡、佩珀等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该学派之所以能够在70年代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社会从6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生态运动越来越引起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其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危机理论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内部存在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奥康纳的财政危机理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上两种危机理论都没有超越传统经济危机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到了生态危机。
其实,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在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已见端倪,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例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曾深入探讨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并不断地加以深化,同时结合冷战结束、东欧剧变的国际局势的演变,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的现状,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动态,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方面的探讨,在理论上显示批判性与构建性的统一,其中构建性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重要特征。这种构建性主要体现为对未来社会的构建动因、构建目标、构建途径等提出了一套见解,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构建理论。
一、生态危机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动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内含着需求理论的一本巨著,在该著作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理路: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工人阶级由于失业或一贫如洗就会起来造反,采取革命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具体地说,就是资本家通过操纵消费,使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产生一种被强加的“虚假要求”,即“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2]。目的在于“把个人转变成完全被动的消费者”[3],从而盲目地购买商品、消费商品。这种盲目购买与消费行为一方面刺激异化劳动,因为,只有劳动即不断地出卖劳动力才能有工资支付消费,这在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继承扩张下去,另一方面让人们在消费中消除掉对异化劳动的不满,因为,人们在生产领域中无法实现自由,便渴望在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里得到自由的“补偿”。消费领域恰好有这样的特性:只要“占有金钱,我就有权利得到并支配我所喜欢的一切”[4]。也就是说,只要有钱,“我”就可以进行“自由”地购买,也就从劳动中的被动主体转化为消费中的积极主体。于是,“我”自由了。这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5]495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往往并不思考这种消费是否是自我真实的需求,导致消费走上异化之路,异化消费又进一步麻痹人们的革命斗志,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因为在异化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至于是在何种制度下得到满足的,人们却并不关心。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日益增加的对需要之满足是否由专制或非专制制度来实现,似乎无关紧要。”[6]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社会性质如何,只要能满足“我”消费欲望的就是好社会、好制度。这种社会心理的蔓延极易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转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注意力和其缺陷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公共合法性,其办法就是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5]494。
为此,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生产,消耗大量资源,从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生产无限扩大与生态系统有限所造成的,其实,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7]168。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在当前已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最根本的不合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从而导致“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7]8。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借助控制自然的观念实现对人的控制,破坏人的自由,否定人的解放。因而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才能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而解脱人对人的控制。这一切都需要进行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来完成,而这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根植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过程是由有限生态系统确定的”[5]486。
那么如何进行这场变革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往往只局限于生产领域,不注重消费领域,只看到“异化劳动”,没有看到“异化消费”,即没有看到“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地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494。异化消费观诱惑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人幸福程度高低的标准。于是,消费由原本只是满足人需求的手段,幻化成人生存的目的,这便进一步刺激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造成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劳动的恶性循环。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进行社会变革,只有打破上述的恶性循环引导人们同违背自然倾向的资本主义作斗争,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让人们充分注意到“生态命令”,即让人们认识到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的工业增长,从而改变原先的需求方式,放弃幸福等同消费的观念。需求方式、消费观念的改变将促进异化消费向“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转变,如此,恶性循环也就不攻自破。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劳动行为、日常行为,并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社会变革……由人们征服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5]498。所以,生态危机成为未来社会的构建动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建动因之源。
二、稳态经济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目标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将稳态经济视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它认为“稳态经济”这个概念远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态化的思想里就已经凸现了。只是这个思想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人们盲目追求生产,消耗资源、破坏自然,以致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为此,人类必须在生产上由原来追求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自动放慢工业增长步伐,“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能促进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确定”[5]493。此种合理确定的生产和消费也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稳态经济,若要实现稳态经济又必须要以特定的“组织形式”来保证。资本主义由于追求“过度生产”、“过度消费”显然不可能成为这种理想的“组织形式”的承担者,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的严重的生态危机总有一天势必会使人们对改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思考。
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韦伯式的官僚制度,即科层制、等级制,在生产上实施的是高度破碎化的分工作业制度。上述制度都是以效率作为组建政治与生产模式的依据,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全社会运作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二者又都是以破坏人自身价值完整性为代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看到了官僚制度与破碎化分工制度只注重人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人的“价值理性”的缺陷,对二者持强烈批判态度。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等级制的合法性是以人的精明与愚笨的区分为基础的,但工业生产在本质上并不取决于精明的人告诉愚笨的人应该做什么,那种从上到下进行支配而为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等级制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劳动高度破碎化,即在大规模技术生产上把劳动分解为无数独立工序的高度分工,只能使工人在组织这种分工管理的专门知识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使工人劳动丧失创造性。
基于上述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生产管理中应该废除等级制,实施民主化管理,在生产技术上采用小规模技术,以便使工人能够参与到每一道工序中,从而消除劳动高度破碎化现象。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界定的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具有人性的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是借用了舒马赫小规模技术的见解,其目的却在于将此见解运用于他们所主张的技术和生态的激进理论中去,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5]501。也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同时还要将其“马克思主义化”,以彻底改变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主义构建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就是指在放慢工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表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最新设想,即“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8]。
三、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途径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葛兰西主张文化领导权斗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马尔库塞提倡“大拒绝”和美学救世,弗洛姆希望通过心理革命达致健全社会,等等,不一而论。但这些理论普遍倾向于非暴力革命,淡化阶级斗争,乃至取消阶级斗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信奉甘地主义,把甘地的格言“无所谓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就是路”以及马丁·路德·金的话“我们不能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是或则非暴力或则灭亡”当作座右铭。因此,非暴力路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构建论的重要成分。
倡导非暴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如何来设计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呢?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并不有助于人们来思考使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模糊的,且带有威胁性的前途,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大多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只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极权主义而已;与此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与资本主义劳工组织和工会失去了联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力量必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传统政治力量之外寻找新的基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新兴基础就是民粹主义,而且本·阿格尔更加具体的认为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即美国人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要求,其主要表现为对集中化的官僚组织的不信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选中美国民粹主义,原因在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国民粹主义中内隐着主张社会正义、渴望基层民主,强调废除家长制,尊重妇女权利和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有助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例如,社会正义就包含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交往模式,强调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三层意义;基层民主包括直接民主,权力交于基层,权力分散三个方面的意思。
不过美国民粹主义毕竟缺少社会主义成分,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民粹主义中去,“把人们对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庞大企业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引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去”[5]510。这就需要对工人和广大消费者进行必要的“精神扶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探索“生态学、政治学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以便将民粹主义激进化。在“精神扶贫”的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体制上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解放不是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是从调整分工”[5]512。而开始的,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的过程中还要讲求一定的策略。首先把高度破碎化的分工作为批判对象,然后再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总体性、彻底性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生态危机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解放因素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开辟社会主义的前景中结合起来。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建论的意义
以上论述,我们大体上勾勒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建论的图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当前一支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该派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深切思考,并提出了一套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构建论,无疑是众多原因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笔者认为意大利的葛兰西在20世纪的前期用“文化领导权”理论向我们论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20世纪后期用“生态危机”理论向我们阐释了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总之,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固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关注点,因此,有学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回到马克思”[9]。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构建是在不恰当地夸大生态问题基础上,推导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已从经济危机转到生态危机,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的错误结论,根本没有认识到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而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其实,正如福斯特所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问题早在马克思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就已经涉及到了[10]。无论是其所分析的未来社会的构建动因,设定的构建目标,还是指明的构建途径都并不切合实际,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倾向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不管是建立或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都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做保障。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是有政治理想的,当然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就是另一回事情了。对于我们而言,要想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就显地格外重要了。另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未来社会构建的理论分析过程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却非常值得人们认真探讨。例如,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要避免异化消费的产生,帮助人们树立和谐的消费观;生态技术的必要性、可行性问题;如何树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科学技术观问题;切实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问题;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 米洛斯 尼可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8.
[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 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6.
[3] 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M].黄颂杰,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79.
[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32.
[5]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 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 马尔库塞.单面人[M].左晓斯,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
[7]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9-440.
[9] 王凤才.追寻马克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281.
[10] Foster:Marx‘s Ecology[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66-88.
Ecology Crisis and Socialism Construction——An Analysis on Visual Field in Ecology Marxism
LIM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Anhui,China)
Ecology Marxism inspects relations of ecology crisis and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cology crisis will be the futur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gent,the stable economy is the futur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goal,and the union of the Marxism and American Populism is the futur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way.Socialism construction through Eco logy Marxism disobeys the basic Marxist principles,but some concrete questions involving in its theoretical analysis process are worthwhile actually.
Ecology Marxism;ecology crisis;socialism;stable economy;populism
D0-0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4.004
2010-02-15
李 明(1978—),男,安徽省巢湖市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8SK046);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01)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