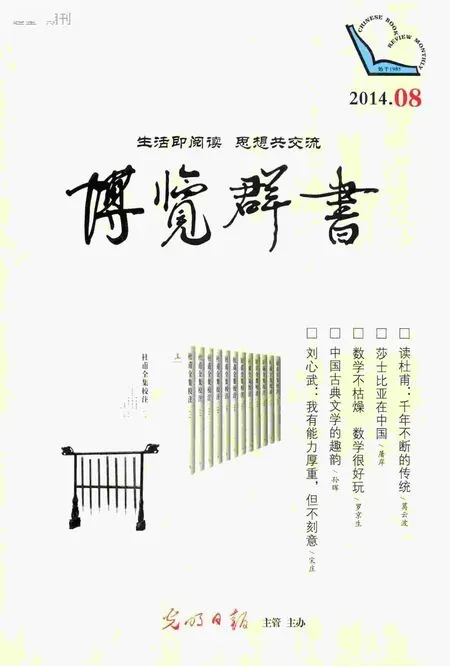台湾书商盗版大陆书的各种奇招
○古远清
台湾于1949年开始“戒严”,并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严禁大陆作家、学者的书在台湾出版和流通。可是,有不少大陆学术著作,对于台湾地区的学者、研究人员、学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都想看。慑于台湾当局的压力,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读。出版商为了适应读者这一需求,只好采取盗版的方式。盗版可免付作者稿费,对讲究经济效益的书商来说,是一本万利的事。为避免查禁,台湾书商只能将大陆学者的著作加以“整容”。有时“整容”得越离谱,检查时反而越容易蒙混过关,从而导致某些大陆书被盗版后面目全非。
1976年,台湾出版界出现了一桩怪事:已于1948年8月12日去世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在1976年10月竟出版了由台北华联出版社印行的《语文通论》新著。此书共收论文11篇。台湾古典文学专家黄永武和现代文学专家周锦均认为它是伪书,应为当时还健在的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所著,但来不及考证明白。另一古典文学专家林庆彰在1978年超越许多障碍,终于读到了郭绍虞的《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考证出华联出版社取郭氏《语文通论》的前三篇和《语文通论续编》的前八篇拼凑而成,并将郭绍虞的名字改为朱自清。所谓朱自清著《语文通论》的真相,《书评书目》1980年4月号曾加以详细披露。
林庆彰通过对近千种盗版书的研究,归纳出台湾书商盗版大陆书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一、删改书名和作者
鲁迅等合著的《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被台湾书商改为“鲁迅著”,书名亦被改为《〈阿Q正传〉的成因》。
台湾开明书店翻印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时,版权页上的作者变为“台湾开明书店”。
台湾商务印书馆翻印贺昌群的《元曲概论》时,作者被改为“贺应群”。
中华书局在翻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时,将著者的名字改为“本局编辑部”。这种改法,显然是出于无奈,刘大杰是留在大陆的学者,按规定其名字不能出现;但这样改毕竟有剽窃他人成果之嫌,1957年6月第二版问世后,被人检举;后来几经交涉,才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学发达史》。



五洲出版社在1967年11月翻印茅盾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时,将作者改为“曹开元”,书名易作《世界文学名著评话》。华贸出版社于1976年翻印时,则将作者茅盾改为林语堂,书名改为《世界文学名著史话》。
大汉出版社于1977年2月翻印朱光潜的《我与文学》,将书前的序言由叶绍钧所作改为朱自清。
元山书店翻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时,故意漏掉作者的“泽”字,成了“李厚著”。
华联出版社翻印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时,作者被改为“张世禄”。
长歌出版社翻印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时,书名改为《古小说搜残》,作者用杜撰的假名“孟之微”。
台湾商务印书馆翻印叶绍钧(叶圣陶)点校的《传习录》时,将作者改为“叶钧”。
宏业书局翻印胡云翼的《唐诗研究》时,将作者改为“胡云”。
牧童出版社翻印北京大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时,书名改为《中国思想史资料导引》,作者用假名“马冈”。
某出版社翻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用“换头术”的办法,改为另一历史学者杨宽所著。这也是为了逃避检查。
二、删除序跋
删除序跋,使伪书难于考证,有利于盗版的顺利进行。
例如,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艺文印书影印时,删去前面的《序言》等18页。
河洛图书出版社翻印周氏注释的另一本《汉学师承记》时,删去周氏的《序言》54页。仁爱书局在翻印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时,删去周祖谟的“前言”4页。
三、删去部分篇章
本铎出版社在翻印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时,删去第十二编第三章《我们今天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必要与可能》部分。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翻印朱自清与叶绍钧合著的《精读指导》、《略读指导》时,将叶氏所作的部分删去。
四、合数书为一书
如郭绍虞的《语文通论》的例子。
五、什么都不改,照原稿用,可在扉页上无大陆作者授权的签字或说明,版权页倒印上“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在以上几种手段中,最常见的是删改作者的名字。因这些作者大都列入国民党警方编印的禁书名单,尤其是像鲁迅、郭沫若这样敏感的人物,更不能亮相。这就难怪李何林所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不但书名篡改为《中国新文学研究参考资料》,而且书中凡提及鲁迅、茅盾、瞿秋白、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的名字,均被简化为鲁、茅、瞿白、周、郑、郭。对此内行人自然猜得出来,但对青年学生,无疑要误人子弟。
至于其他篡改方法,如前所说,有的是为了瞒天过海,掩人耳目,更多的是出于营利目的。因当时两岸未沟通,大陆作者均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著作被盗版。现在两岸实行民间文化交流,盗版的事再也掩盖不住了,有不少大陆作者通过亲友去讨版税乃至上法院控告。也有一些出版商一旦查到被盗版者的地址,登门道歉,补送样书和稿费。可见,“海盗”不是没有,但毕竟不能代表台湾出版界的主流。
令人钦佩的是台湾有林庆彰这样的专家审理戒严时出现的伪书。为彻底了解大陆近四十年出版传统文史哲图书的总数,他曾邀请数位老师、研究生一起编辑《大陆出版文史哲图书总目(1949—1989)》。这本书的完成,除可供台湾学术界翻检大陆图书之用外,也是考辨这些伪书不可缺的工具。(林庆彰:《如何整理戒严时期出版的伪书?》,台北,《文讯》,1989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