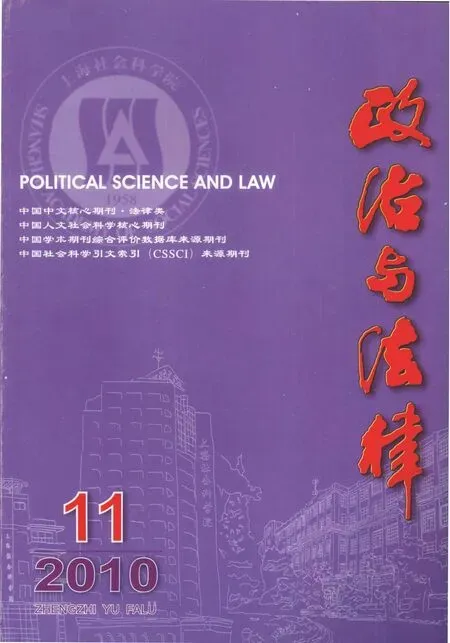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
——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
梁云宝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
——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
梁云宝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中内含了消极侧面和积极侧面。这使“罪刑法定”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依附于社会保护机能。罪行说、折衷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其人权保障机能得到还正,必然延伸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罪行说;罪名说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所规定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不尽一致。由此展开的刑法理论上的争辩颇为激烈。概括起来,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结合我国刑法第3条关于“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规定来看,随着罪刑法定原则根基的确立和深入,对该条款的法律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的转换,恰恰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深入理解和纵深贯彻的表现。
一、罪行说:罪刑法定原则的虚化
(一)罪刑法定原则之社会保护机能
我国1979年《刑法》未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其中,前半段被称为罪刑法定原则规定的积极侧面,后半段被称为消极侧面。较之西方罪刑法定原则传统的格言表述,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Nul lum crimen,nul la poena sine lege.)”1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到确立的同时,刑法对其规定带上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即附加了积极侧面,而该侧面毁誉参半。
罪刑法定原则应否包含社会保护机能,理论上存在激烈的争辩,但彻底否定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社会保障机能是不现实的。肯定说通常肯定罪刑法定原则对一般预防的作用,如“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对社会防卫,还是对个人自由,均是不可或缺的”,2并赞成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保护机能。如“社会保护机能是通过对犯罪的惩治来实现的,因而属于罪刑法定的积极机能或曰扩张机能……罪刑法定的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协调发展”。3否定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无论是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其精神实质都在于保障人权,社会保护机能是刑法的机能而非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4笔者认为,现代刑法基于“个人·社会”本位确实承担了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等机能,但不宜由此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下仅具有人权保障机能,这在规定了包含积极侧面的罪刑法定原则之我国,尤其如此。否定说在逻辑上无法周延。其认为刑罚、刑法规范、罪刑法定原则都是刑法的构成要素,社会保护机能主要通过刑罚及包含刑罚的刑法规范产生,人权保障机能则主要通过罪刑法定原则产生,这混淆了概念、要素间的关系。尽管从一项准则的形式上看,它是一条规则还是一项原则,常常不是很清楚,但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深度——份量和重要性的深度,且二者的区别是在逻辑上。5刑法法条固然由刑罚、刑法规范、罪刑法定原则等组成,但刑罚在位阶上低于刑法规范、罪刑法定原则,刑罚在现代各国刑法中都是刑法规范与罪刑法定原则的选择性要素,而刑罚集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于一身的双重目的,使通过刑罚及包含刑罚的刑法规范来主要承担社会保护机能的观点之合理性,值得商榷。即便否定一般预防是罪刑法定原则理论基础的Schünemann和罗克辛等人,也不反对刑罚及罪刑法定原则能产生一般预防的效果。6笔者以为,刑罚、包含刑罚的刑法规范、罪刑法定原则之社会保护机能是一种交叉关系,但承担人权保障机能兼顾社会保护机能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侧重点更应倾向于人权保障机能。
为摆脱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突出的社会保护机能所受的诟病,“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之积极侧面的立法宗旨被阐释为:“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7即其突出的是“依法”,是对司法机关的限制。部分学者也将其解读为:不宜将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必须定罪处刑理解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8张明楷先生更是主张,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9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在现行刑法中的确立过程上看,其不无疑问;10若将视域扩大至同时代的宪法规定,则上述阐释愈加缺乏说服力。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非我国的优良传统,法律在现实“挑战——应对”模式下带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文革”结束后刑法的价值得到了凸显,“那个时候亟须制定一部刑法,结束无法无天的日子”,“我们刚刚进行刑事立法的时候,更强调的是社会的保障……怕就怕遗漏犯罪”。11对秩序价值极度渴求下颁行的1979年刑法,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其实,罪刑法定原则缺位的同时类推制度法典化,与其说是苏联刑法模式影响与意识形态因素使然,毋宁说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与社会保护机能在秩序价值上合一的表现。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后,其积极侧面使得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成为首要价值取向,而罪刑法定原则所独有的人权保障机能退居其后,仅为社会保护功能之附随。12即使1997年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只采取了消极侧面的表述,其人权保障机能在秩序价值下也难免受到某种程度的弱化,甚至虚化。作为法治国精华浓缩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带上了“中国特色”之后,其社会保护机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取得了超越人权保障机能的地位,故罪刑法定原则之积极侧面即使是出于“限制司法机关”的本意,秩序价值也会迫使其额外地承担起社会保护机能。
(二)罪行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
包含积极侧面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第17条第2款的法律解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才负刑事责任,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虽然该答复明确了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以下简称八种罪行)8种行为的,须承担刑事责任。这是罪行说的立场。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究竟如何确定罪名,仍不明确。
因此,作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进一步明晰,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在罪行说的立场上,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依据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规定来定罪。
罪行说受到了诸多诟病,其中有力的批判是认为该说使得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相当宽泛,因为“这实际上是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能够以故意杀人、放火、爆炸等8种犯罪行为触犯的罪名”。13且采取罪行说立场的解释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为这导致定罪时评价了刑法不允许评价的部分行为。14由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观之,该原则要求犯罪构成的明确化,而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犯罪构成是确定这种根据的判断标准。据此,基于罪行说的立场,大前提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小前提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具体行为,结论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成立其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犯罪。问题是,行为人的部分行为本因主体的不适格而被刑法排除在评价的对象之外,但罪行说的“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会不当地导致年龄对犯罪性质限制作用的丧失,从而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如刑法不允许评价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绑架行为,故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最多只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罪行说主张的“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这既评价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杀人行为,又不当地评价了其为刑法所不允许评价的绑架行为。
无论是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解释为八种犯罪行为,还是解释为八种罪名,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是一致的,并且应当以八种罪名承担刑事责任,都是对罪行说“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之内容的误读,不当地舍弃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对犯罪性质的限制作用,评价了刑法不允许评价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部分行为,从而混淆了罪行说与罪名说的界限,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是不科学的。
如前所述,罪刑法定原则之积极侧面弱化了人权保障机能,突出了社会保护机能,这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根基尚浅的情况下,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采取罪行说的立场,成为可能。因为“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隐含的内容突出了社会保护机能的弊害,强调有罪必罚和出罪从严,以确保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受到刑事追究。这导致了在趋向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保护机能下,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不当入罪,并不存在太多的困难,而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误区,也会消减对人权保障机能意义上罪刑法定原则背离的质疑。因此,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该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纵深贯彻,《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的转换,是还正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决定作用上必然的逻辑延伸。
二、罪名说:罪刑法定原则的还正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还正
解决问题,扬汤止沸只是权宜之计,釜底抽薪才是根本之道。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要采取正确的立场,必须还正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虚化《刑法》罪刑法定原则规定的积极侧面,使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摆脱对社会保护机能的依赖。
包含积极侧面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突出的是出罪禁止的社会保护机能,甚至可以认为积极侧面无异于入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必然压缩了其本身所兼具的人权保障机能,亦远离了以天赋人权为逻辑起点、以限制国家刑罚权为内容、以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为首要或主要目标的原初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实,社会保护机能在西方法治国家并非完全或主要由罪刑法定原则承担,“罪刑法定主义在防杜罪刑擅断主义之流弊,肇始于十八世纪,至今尚为刑法之基本原则,惟近世文明日进,社会利益占重要地位,法律为保障共同利益,有时不得不限制个人利益,以资调和。”15带有鲜明苏联刑法痕迹的1979年刑法,在未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保护机能更多地由刑法的任务、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等来承担。修订后的刑法叙明了包含积极侧面的罪刑法定原则,使兼具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大机能的罪刑法定原则之社会保护机能得到了凸显。
如前所述,对积极侧面所作的限制司法机关之阐释,难以让人释疑。毕竟,限制司法机关,是否有必要通过这样的积极侧面为之,值得省思。因为,追溯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其原本即被赋予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本旨,再通过积极侧面强调“依法”,以明示对司法机关的限制及禁止法外制裁。这与消极侧面在立法技术上是实质性的重复,而积极侧面的内容与宪法的相关规定、现行刑法的目的、任务,在立法技术上是形式上的重复。现行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目的和任务下,不容置疑,附加积极侧面的重复式表述实无必要。即使实务中出现了司法权的恣意或法外制裁,也不应简单归责于单纯消极侧面的罪刑法定原则隐含的弊害,域外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仅采取了消极侧面而已,故所谓的司法权的恣意或法外制裁,大抵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得到切实的落实,出现了偏差或异化。但与作出限制司法机关之解释的立场相适应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正逐步受到关注,并向还正该机能的方向推进,这应当给予肯定。
由立法技术视角观之,较之1979年刑法第1条,修订后的刑法省却了“刑法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而是由于这在现行宪法的序言中有明文规定,同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之宪法具有至上的权威,故“根据宪法”的刑法出于立法技术考虑,省却了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必要的重复式表述。据此,立足于摆脱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对社会保护机能的依赖,笔者主张,对罪刑法定原则之积极侧面作省却处理,社会保护机能更多地交由刑法的目的、任务等承载,还正罪刑法定原则原初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机能;在此之前,权宜之计是采取“补正解释”的立场,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即积极侧面的意旨为严禁司法权的恣意行使,防止不当入罪,以最大化地消解其负面影响。
(二)罪名说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穿
较之1979年《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修订后的刑法叙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其第17条第2款删除了“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内容,以列举的方式使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犯罪范围具有了相当的明确性,这无疑是“在犯罪主体方面进一步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16立法者的努力值得称道。因为,以列举方式规定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5种具体犯罪的同时,以概括的方式,即带有兜底性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犯罪范围,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1979年《刑法》施行后,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不断地将一些犯罪纳入“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中,这实现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但也致使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附加了积极侧面,其突出的社会保护机能使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的限缩大打折扣,而采取罪行说立场的解释,前已述及,“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会不当地导致年龄对犯罪性质限制作用的丧失,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使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上几乎被虚置。因此,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上转向了罪名说的立场,这既是对原先罪行说立场的纠偏,又是进一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还正其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的体现。
罪名说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8种具体罪名,而非8种具体犯罪行为。罪名说内部又存在狭义说与广义说的分歧,其中,狭义说主张《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8种具体罪名,仅限于单纯一罪,不包括实质一罪和裁判上一罪。如有论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既不能定绑架罪,也不能定故意杀人罪,而应当不负刑事责任。17这种观点坚持了刑事责任年龄对犯罪性质所起的限制作用,即不得评价刑法所不允许评价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部分行为(绑架行为),但该观点不当地否定了刑法允许评价的部分行为具有独立性,曲解了罪刑法定原则,亦即使刑法允许评价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行为部分,对刑法不允许评价的行为部分具有了从属性。其逻辑为:绑架过程中杀害行为从属于绑架行为,由于刑法不允许评价绑架行为,因而不能评价杀害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杀害被绑架人”作为绑架罪的量刑情节,是以绑架罪的成立为前提,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绑架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考虑量刑情节的杀害行为,便成为无稽之谈,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对犯罪性质的限制,使得绑架过程中的杀害行为在性质上不是作为量刑情节,而是作为具体行为存在的。“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18与之类似的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因年龄对犯罪性质的限制,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不成立,丧失了向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基础。因此,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行为,只能依据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和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分别以绑架罪、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而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5条、第10条对相关内容做了重大修正,进一步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广义说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8种具体罪名,不限于单纯一罪,还包括实质一罪和裁判上一罪,但应当依照本条款的规定确定罪名。这为多数学者所支持。广义的罪名说的逻辑推理为——大前提: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小前提: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具体行为;结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成立其所触犯的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确定的罪名。此时,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以外的行为,如故意决水造成他人死亡的,故意决水行为因主体不适格而被排除在刑法评价的对象之外,若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则依照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其实,罪行说与罪名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在“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确定罪名上迥然有别。罪行说主张根据刑法分则具体条文对犯罪的规定来确定罪名;罪名说主张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本身对犯罪的规定来确定罪名。这种分歧恰恰是虚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强化、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之所在,是突出社会保护机能还是还正人权保障机能之所在。因此,广义的罪名说既坚持了年龄对犯罪性质的限制作用,又恪守了不得评价刑法所不允许评价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部分行为;既使得《刑法》第17条第2款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犯罪范围上较为明确,进一步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又还正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防止了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不当入罪。
折衷说认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不是一个智识性问题,而是一个政策性问题,并立足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一体化,进而主张该条款中的“罪”并不意味着要么是“罪名”,要么是“罪行”,而意味着有时候是“罪名”,有时候是“罪行”。19诚然,罪刑法定原则始终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李斯特语)。预防犯罪是刑法的重要内容,预防犯罪与刑事政策联系紧密,但刑事政策绝不能成为对刑法解释恣意的借口,相反,刑法解释时对刑事政策的考虑不应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且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根基尚浅,其积极侧面突出的社会保护机能,在强调有罪必罚和出罪从严以确保国家刑罚权的有效行使时,有不当入罪的隐患。因此,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还正该原则所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是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最高人民检察院采取“罪行说”的立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故以解释是一个政策性问题为由,得出《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罪”往返在“罪名”与“罪行”之间的结论,同样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是不妥当的。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责任范围上由“列举+概括”式向列举式演进、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彰显的都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功效。所以,任何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和纵深贯彻,还正的人权保障机能难免使其成为历史的遗迹。
三、结 语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到确立的同时,附加了积极侧面,这使其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依附于社会保护机能。对罪刑法定原则积极侧面作出限制司法机关之解释的立场,彰显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正逐步受到关注,并向还正该机能的方向推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该解释仍难令人释疑,故有必要省却罪刑法定原则之积极侧面,还正罪刑法定原则原初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机能。在此之前,应采取“补正解释”的立场,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即积极侧面的意旨为严禁司法权的恣意行使,防止不当入罪,以最大化地消解其负面影响。与之相适应,刑法解释不应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然而罪行说、折衷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其人权保障机能得到还正,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是罪刑法定原则进一步得到贯彻的征表。
注:
1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5页。
2[法]卡斯特·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3陈兴良主编:《刑事法总论》,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4参见周少华:《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5[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8页。
6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 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7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8参见陈兴良:《入罪与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法学》2002年第12期。
9参见张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法学家》2008年第4期。
10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提出及表述的出台,可参见张军、姜伟、郎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11张军、姜伟、郎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第7页。
12参见刘艳红:《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13陈志军:《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之检讨》,《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
1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15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6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7参见孟庆华:《关于绑架罪的几个问题》,《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
18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19参见欧阳本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另一种解释》,《法学》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文 武)
DF61
A
1005-9512(2010)11-0121-07
梁云宝,东南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